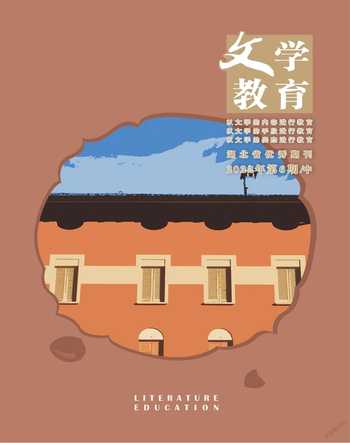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叙事性解读
郭立南
内容摘要:《桃花源记》作为陶渊明的代表作,学界对其进行深入探究的兴趣经久不衰,成果亦是层出不穷。学界已有不少学者从叙事学角度对《桃花源记》进行作品的解读,体现了研究的新意。通过综述发现,学界以叙事学为方法论解读《桃花源记》尚有掘进空间,尤其是文体、文本和语式方面鲜明的叙事性的探讨尚需要进一步深究。
关键词:《桃花源记》 陶渊明 叙事性
《桃花源记》作为陶渊明的代表性作品,寄托了他的社会理想和个人志趣。从作品本身而言,其不光是诗,更是叙事性文本。“叙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基本的人性冲动,它的历史几乎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1]“自人类社会始有生灵,叙事就已经存在。”[2]“‘叙事’的概念从广义上理解,即一切‘有秩序的记述’行为均可视作‘叙事’。”[3]目前学界已经关注到《桃花源记》的叙述性特征:高鑫从时间叙事的角度进行解读:“在《桃花源记》中实际上存在三种叙事时间,分别对应过去、现在与未来。这种时间的异质性被赋予两重空间:一是桃源之内,二是桃源之外。”[4]侯向军认为在文体上,《桃花源记》“好像是小说,又好像是散文;好像是游记,又好像是寓言故事;好像是单独成篇的歌赋,又好像是序跋类文体中的诗序”[5]。张静从叙事性文本的解读内容、解读立场及解读策略等方面对《桃花源记》进行了剖析。陈梦盈在《〈桃花源记〉与〈桃花源诗〉之时空叙事意识管窥》中认为“《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叙事类作品,但两篇作品中都贯穿着十分明晰的空间叙事意识及时间叙事意识”,“构建了一个互通有无的时空体系”[6],从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角度对《桃花源记》进行了叙事性解读……
笔者通过综述发现,学界以叙事学为方法论解读《桃花源记》尚有掘进空间,尤其是文体、文本和语式方面鲜明的叙事性的探讨尚需要进一步深究。
一.《桃花源记》文体的叙事性
陶渊明写桃花源,用了“记”与“诗”两种文体,这里主要谈“记”。
《说文》上说:“记,疏也。”《廣雅》记载:“记,识也。”不难看出,记即为识记。“为了识记,就要运用语言文字书写于一定的材料上。”[7]所以“记”最初是为了记录,如《学记》就是古代中国典章制度专著《礼记》中的一篇专门论述教育和教学制度、原则以及方法的文章。“《尚书》中的《禹贡》和《顾命》被视为记最早的源头”[8],而后“记渐渐由经学向史家倾斜,成为官方记录帝王言行或国家大事的专用文体”[9],记的内涵也由“以往的侧重记言转向了侧重记事”[10],并“在六朝时期获得了它的文体生命”[11]。因此,“记”是一种带有强烈叙事性的文体。
就“记”来说,部编版初高中语文教材中所选取的如《岳阳楼记》《游褒禅山记》《黄州快哉亭记》《黄冈竹楼记》等几篇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都属于“有秩序的记述”,具有极强的叙事性因素。《岳阳楼记》揭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仁人之心,表达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情怀,是通过写岳阳楼的景色以及阴雨和晴朗时带给人的不同感受来进行叙述的;《游褒禅山记》以游山为喻,叙议结合,兼具记游与议论,记游只是引子,说理才是全文的中心,因事见理,通过“未能极尽游洞的乐趣”告诉我们要成功,“志、力、物”缺一不可,要想实现远大理想,在研究上必然要“深思而慎取”;《黄州快哉亭记》,紧密围绕“快哉”二字,用所见之景与及其生发的感想道明“快哉”之意,寓情于景,夹叙夹议,因事说理,借劝慰谪居生活的好友和兄长不要以谪居为患之机,表达自己希望那些人生不得意之士能胸中坦然的乐观倔强之情怀,揭示出失意之人应“不以物伤性”,“心中坦荡则无望而不快”。《黄冈竹楼记》王禹偁以楼明志,用托物言志的手法,先叙后议,按照建竹楼→享竹楼→议竹楼的顺序,抒发自己的闲居之乐,从而生发自己身处逆境而豁达自适的乐观情怀,表明自己向往不朽人生的崇高心志。
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是《桃花源诗》的序言,与《桃花源诗》构成一个互通的世界,通过虚构的写法以及悬念的设置等,以饱蘸现实色彩的笔墨沿着行进之路线叙述了桃林的神秘、景色的奇异、环境的特别、民风的淳朴、离去不可再觅的神奇,将桃花源令人向往的世外之境展现在世人和读者面前。诗人在时空变换中沿着行进路线“有秩序”地记述,景随人转,画随人换,境随心生,开头便勾起了读者的好奇心,中间别开生面的人物、空间以及所发生之事的记叙,结尾一波三折的富有张力的冲突性,使得文章呈现出鲜明的叙事性。
二.《桃花源记》文本的叙事性
“所谓叙事性文本,顾名思义,就是一种以叙事功能为主的文学作品。”[12]《桃花源记》的文本就带有浓厚的故事性。文章开端,陶渊明借渔人的视角向我们描绘了一片美好闲静的桃花林,以此作为铺垫引出一个淳朴而自然化的美好世界。桃源人为什么要避世于此,其原因作者没有明说,但从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洞见一二,“避秦世乱”“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简短的十余个字,隐隐约约让读者和世人可以猜测出一点儿原因。这个令人神往、透着神秘的桃花源,对生活在倾轧黑暗、动荡不安、天灾不断、战乱频繁、没有人权、朝不保夕的俗世中人来说,是一种近乎于信仰般的存在,作者所表现出桃花源的自然祥和的安居气氛,使桃花源更富有传奇性的同时,让魏晋时期生活在底层的穷苦大众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
文本的叙事性首先体现在故事有起伏、有层次。《桃花源记》所叙述的故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从捕鱼为业的武陵人“忘路之远近”开始到“忽逢桃花林”,再到“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始终给读者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使得故事颇具有传奇色彩,给人以无尽的遐想和无穷的回味;同时,《桃花源记》在故事的叙述上脉络十分分明,由发现与众不同的桃花林开始起笔,继而写进入桃花源、离开桃花源,最后到再觅桃花源,层层推进,向世人展现了这个与桃花源外完全不同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世界,对于魏晋时期那些饱受战乱与压迫、无家可归的穷苦百姓来说,这里无疑成为了他们想要追寻的精神乐土,是令人心驰神往之境。
文本的叙事性还表现在故事有详略、有虚实。《桃花源记》着重描写了进入桃花源后“武陵人”的所见所闻,通过“武陵人”的视角,给我们展现了桃花源的自然环境和民风的淳朴,在做客桃花源的过程中故事发展至高潮,展现出一个与当时黑暗的现实世界完全对立的美好蓝图。作者虚虚实实,文章一开始交代渔人生活的年代以及籍贯,写得煞有其事,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把读者带入到了如梦似幻、美好娴静的桃源仙境之中。渔人误入桃林生动而真实,而桃花源的一切又美好得如此不真切,虚实结合,给故事蒙上了一层如梦似幻的面纱,更符合读者的猎奇心理。渔人“处处志之”。返寻所志,“不复得路”;乃至“南阳刘子骥”“欣然规往”,依旧不可得,则更是神来之笔,使桃花源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将读者从这理想化的化外之地拉扯回现实之中,心中充满了对桃花源的留恋和向往,艺术地展现了作者对当时黑暗的现实社会的愤懑与不满,以及对乌托邦式大同社会的美好憧憬和理想寄托。
文本的叙事性最重要的表现则是故事中有人物。作者借“武陵人”之眼之口,以及所生发的所想所思,让我们看到了桃花源这块世外净土。一入桃花林,这里就展现出了不同寻常之处,所到之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正可謂是个家室皆宜的地方;桃花源中多是四世同堂、三代同宿,民风淳朴,热情好客,“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桃源人的安居乐业,让我们从字里行间不由得露出艳羡之色;另外,桃花源人与世无争,从对渔人“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叮嘱可见一斑。
《桃花源记》有故事,有人物,有情节,语言如诗,文本具有强烈的叙事性。
三.《桃花源记》语式的叙事性
《桃花源记》故事分为三个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衔接自然顺畅,作者在遣词造句、布局谋篇方面造诣精深。兹维坦·托多罗夫在《叙事作为话语》中认为:“叙事性存在着两种主要语式——描写和叙述”。从“描写和叙述”两个方面,我们依然可以对《桃花源记》进行解读。
在描写上,《桃花源记》通过词汇进行衔接,从而“增强文章各部分在意义上的连续性”[13]。文章一开始从渔人“忽逢桃花林”处写起,奇异之景引发了渔人的好奇之心,不禁“甚异之”,产生“欲穷其林”的想法,“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等词汇道出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引出桃花源中淳朴质真的民风民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孔”这段描写中,顶针的衔接方式将段落与句子连接起来,通过词汇衔接的方式,为文章增添了寓言式的神秘色彩,带着读者打开了一个别有洞天的世界。
除了词汇运用外,作者还用了浓重的对比色彩。如:从“初极狭,才通人”到“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桃花源入口两侧的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给人以豁然开朗、柳暗花明之感;再如“处处志之”,到“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寻向所志”和“寻志未果”,事情发展的前后形成了一定的反差,形成强烈的对比,加重了桃花源的神秘色彩;而“不复得路”“规往未果”“不足以外人道也”等情节,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暗示世人这个社会不复存在,给人以无限的遐想空间。
在叙述上,《桃花源记》“几乎没有用到人称指称”[14]。行文过程中省略的处理很有规律。像“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应为“(村民)见渔人,(村民)乃大惊,(村民)问所从来。(渔人)具答之。(村民)便要还家,(村民)设酒杀鸡作食。”这一连串主语相同的句子中,只有一个主语与其他句子不同,省略主语将文章变得干脆利落,既不影响句子的衔接又避免重复。另外在文中多次出现“此”,然而意义皆不相同。如:“此中人语云”的“此”与“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的“此”所指并不相同,前者指生活在世外桃源的人,后者则是指桃花源,这也体现了作者驾驭语言的高深技法。
罗钢在《叙事文本分析的语言学模式》中指出:“过去,人们在分析叙事作品时,注重的是小说的情节、人物、主题等等,而叙事学的文本分析,是从文本语言的有机构成开始的。”[15]《桃花源记》在行文过程中特别注意语言的内部构成。“缘溪行,忘路之远近。”一个“忘”字即写出了渔人专心捕鱼,没有关注路程的远近,又暗示其在不知不觉中已所行深远,说明了桃花源是偶然所遇,不可“规往”。“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即道尽桃林之美,又与后文写桃花源的自然景色相呼应,不寻常的渔人偶遇不寻常之处,故事的开篇便带有虚幻的色彩。而“初极狭”待到“豁然开朗”,深有柳暗花明的韵味。“问所从来。具答之。”只一“具”字,就将“渔人”所要询问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解答,简约至极。随后几语向我们展现了桃源人的热情好客。“自云先世避秦时乱。”“乃不知汉,无论魏晋。”避世原因及时间之久。临别嘱咐“不足为外人道也”,婉转表达了桃源人不想被外界所扰的愿望。渔人返回途中“处处志之”,违背了桃源人的叮嘱,想要重来,结果自然是“不复得路”。待到刘子骥的“寻未果”,既写出了仙境难觅,又表达出了桃源人不愿被“外人”所扰之意,与临别前桃源人“不足与外人道也”的嘱托相呼应。
“桃花源”是一场幻境,是乌托邦式的空想。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穷苦大众生活在道不尽的剥削压迫与水深火热之中,使得这个凌驾于现实之上的对理想生活的憧憬与幻想富有了现实意义。《桃花源记》可谓寓言,记述的是陶渊明心中的理想社会,但作者却给我们奉献了一篇经典性文学作品,虚构与真实混融,抒情与叙事交织,是诗,更是小说和散文。
注 释
[1]田园.青春镜像中被规训的唯美叙事——台湾偶像剧叙事研究[D].四川大学,2011.
[2]张松.陶渊明诗文叙事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11:1.
[3]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M].东方出版社,1999:10.
[4]高鑫.精妙的叙事层叠的境界—《桃花源记》小说性评析[J].七彩语文·中学语文论坛,2019,(5).
[5]侯向军.谈《桃花源记》的构思与叙述技巧[J].文理导航,2019,(8).
[6]陈梦盈.《桃花源记》与《桃花源诗》之时空叙事意识管窥[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5(9).
[7][8][9][10][11]曾军.从经史到文苑——“记”之文体内涵的源流及变迁[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2).
[12]张静.叙事性文本的解读内容、解读立场及解读策略[J].小学语文教学·园地,2019(11).
[13]陈光辉.《桃花源记》的文本解读新视角[J].语文天地,2019,(6).
[14]张琪.解读陶渊明《桃花源记》的衔接与连贯[J].汉字文化,2018,(8).
[15]罗钢.叙事文本分析的语言学模式[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