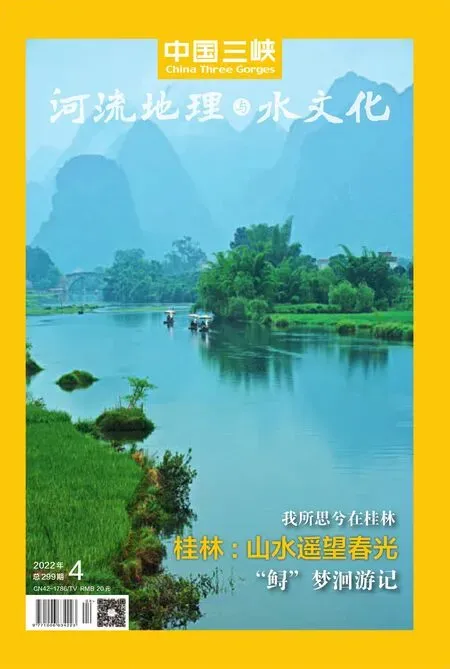生态之美
栏目主持/任红 编辑/王旭辉
作为“手刹”的陶渊明
文 | 杜鹏
《陶渊明的幽灵:悠悠柴桑云》
(全新修订版)2021
鲁枢元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鲁枢元先生的《陶渊明的幽灵:悠悠柴桑云》是近些年来颇受关注的一本生态文艺著作。这本书不仅收获了像鲁迅文学奖这样的重要奖项,还是国内不多的被译介到国外的理论著作,并引发了海内外一系列的关注。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近三十年的学界,“生态批评”以及“生态研究”一直是个热门课题,然而,在这样一个热门的课题下面,海内外的学者所面对的却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和困境,其核心在于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处。正如鲁枢元先生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说,“从当代生态学的角度看,陶渊明的意义就在于他为走入迷途的当代人提供了一个人生典范:物质的消费极低,达成的生活品位极高”。而这本书则通过对陶渊明这样一位东方先哲的当下解读,在全球面临着生态危机的时候,贡献一份来自古老东方文明的精神礼物。
严格来讲,在我们当下,无论我们有多么热爱陶渊明的精神及其作品,我们都很难做到完全像当时陶渊明那样,“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因为作为生活在现代社会的现代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妥协。但是,我们妥协的目的又是为什么呢?我想妥协的真正价值并不完全在于那些因妥协而换来的世俗上的成就,而是那些用妥协的方式来保护我们的本真的一面。
陶渊明作为一名“杰出的例外”,他的人生因生活上的“退步”而得到精神上的“进步”,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范围内,都是极为罕见的。而这种罕见既来自于自身的修为,也同样来自于他的时运。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陶渊明的存在和历史上很多先哲一样,都具有不可复制性。即便如此,在一个“日日新”的社会里,陶渊明的幽灵依然为我们当代人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可能,而这种可能在我看来更多的来自陶渊明身上的那种伟大的共情能力。就像鲁枢元先生在书中所说,陶渊明遵循着“水利万物”的轨迹“往低处走”,即出于生存的大智慧,也是天性上对于自然的认同。而这种对“自然的认同”和“往低处走”的实践与行动,其实就来源于陶渊明在内心深处,将自己认为是自然的一部分,故而才有这种堪称是伟大的共情能力。而在一个“拉黑”和“点赞”的“无共情时代”,这种“共情能力”尤其值得我们当代人去反思。
如果把现在社会比做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那么陶渊明式的共情在我看来更像是这辆汽车的“手刹”。首先,陶渊明作为一名继承了老庄哲学的思想家式诗人,他的人生哲学更多是一种“退步哲学”。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而言,这种“退步哲学”所提倡的是向自然法则的妥协,以及用“守拙”的方式保护我们的“本真”。而在现代社会之中,科技进步的必然性是向前发展,这是历史发展到今天的客观规律。作为“退步哲学”的重要代表——陶渊明,他的人生哲学显然是很难像培根、笛卡尔、牛顿等人那样,为现代社会这辆高速行驶的汽车提供动力的。但是同时,我们知道,一辆汽车是由很多个部件组成的,每个部件都有自己独特的用处,只有发动机的汽车也不能被称为是汽车。任何一辆汽车都有它的“手刹”,尽管它和汽车的其他零件相比,它的使用频率并不算高。“手刹”最大的功能就在于停车的时候不“溜车”,使得汽车减少不必要的向后滑行。我想,陶渊明的当代价值或许就在于,他的精神以及他所提倡的生活方式,能为主流文明社会这辆高速行驶的汽车提供一份来自“手刹”的保护。如果更多的人能够意识到陶渊明的幽灵可以作为“手刹”一样的存在,那么或许当他们在追求“理性”以及因“理性”而带来的“进步”的同时,还能有所迟疑,并在这迟疑之中,对自然保有一份来自于人的共情。
而只有这种共情的存在,陶渊明的幽灵不至于成为时代的亡魂,才能继续“诗意的栖居”在我们中间。

《树的秘密生命》2018
[德]彼得·渥雷本 著
⑨Raimo Tuomela,A Theory of Social Action,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4,p.1.
钟宝珍 译
译林出版社
彼得·渥雷本是林业工作者,有着数十年的护林经验。在这本书中,作者用散文诗一样的语言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森林里我们看不到的秘密世界。在彼得的笔下,树木不仅是有“声音”的,同时还是有“个性”和“情感”的,而它们所营造出来的“自适应系统”还有待我们人类进一步去认知和学习。
与自然争鸣
文 | 杜鹏

《争鸣》沼泽乐队
声锐文化
2018
沼泽乐队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艺术摇滚乐队之一,成立于九十年代的后期。沼泽乐队从2006年开始探索将电声古琴融入到现代音乐之中,并在2010年的首张古琴器乐专辑《沧浪星》中让这种融合趋于成熟。虽然沼泽乐队通常被归为后摇乐队,但是因为他们探索的音乐方向实在太广,从电子乐试验,到古乐再到交响乐,所以我将其归为艺术摇滚。
《争鸣》是沼泽乐队在2018年11月发行的专辑。从这张专辑的题目上看,有“群鸟争鸣”之意,乐队或许也想通过这样一种“争鸣”的方式来表现音乐与自然之间的“争鸣”状态。值得一提的是,这张专辑的录制大部分是在比利时的一处小森林中完成的,如果听众足够敏锐的话,会听到这张专辑中传来的鸟鸣声。故此,乐队将这张专辑命名为“争鸣”,并非完全出于一种概念上的考虑,更多的是源于一种切实的经验的流露。
我关注沼泽乐队已经有十多年了,曾经看过两次他们的现场演出,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非常遗憾的是,《争鸣》这张专辑我并没有听他们现场演绎过。在我的印象里,沼泽乐队虽然是一支多以器乐演奏为主的乐队,他们的绝大部分作品是没有人声的,但是乐队的核心海亮却是一个颇为健谈的人。他总是在演奏的间歇和观众进行交流和引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通常情况下,后摇乐队的现场是很少和观众互动和交流的,他们更多的作为一个整体呈现,而不是某几个人。而海亮的这种“话痨”式的现场,其实本来就很有些“争鸣”的味道,因此他们后来做出一张名为《争鸣》的专辑,在我看来也是情理之中。
《争鸣》只有一曲,却长达四十多分钟,但整张专辑听完,却让人没有丝毫的审美疲劳。沼泽的这张专辑很像是一首长诗,而长诗最讲究的就是结构。音乐也同理,对于流行歌曲来讲,不存在氛围的切换问题,只需要将想表达的某个情绪表达清楚就可以了;艺术摇滚则不然,大部分艺术摇滚乐队都有一种宏大的叙事倾向,而这种宏大叙事的前提是因为某个特别重要的艺术问题才引起的。我想他们或许想通过这样一种“争鸣”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一种生态观,一种人与自然之间共声、共振的关系,故此他们选择了比利时的一座小森林来完成这张专辑的录制。从音乐上来看,这首曲子是非常典型的“沼泽”式乐曲,用现代的方式来诠释中国山水画式的古典意境。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摇滚乐(或现代音乐)就已经有这种东西方乐器相融合的范例,并产生了像崔健的《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这样的金曲,而沼泽的贡献与这些前辈所不同的是,古琴在他们的音乐中占据了核心,而不是点缀。如果说沼泽的每一首曲子都是一片水面上的波纹,那么古琴的作用就像是投入水面的那颗石子。在《争鸣》中,这颗投入水面的石子则不是直上直下的,而是像一种近似于打水漂的形式在音乐中呈现。因为古琴演奏在乐章之中的跳跃式运动,使得这首曲子自带一种叙述效果。但是如果仅有这种单一的叙述效果,可能会容易让听众产生疲劳,于是在此同时,在乐章之中,暴风骤雨式的演奏也扮演了很重要的一部分。在这里,海亮创造性地用琴弓拉古琴,以此营造出一种森林中似有千军万马奔腾的效果和氛围,配合着箫声恰如其分的加入,使得这首曲子在情节上有着一种动静分明的张力。
作为一张在自然的环境下录制的专辑,《争鸣》的存在本身就是一次向自然的致敬。《争鸣》中的自然和生态环境中的自然是有着内核的相近之处的。自然之所以伟大,在于其包容,音乐也一样。《争鸣》也同样具有这种和自然相似的包容性,我们可以从乐器的争鸣声中听到自然界的争鸣声,丝毫没有任何违和之感,仿佛它们天生就属于彼此。

《此时此刻》许巍
金牌大风
2012
这张专辑是许巍及其团队在云南西双版纳制作的一张同期录音专辑。在这张专辑里,没有MV,也没有打榜金曲,只有开阔的境界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共鸣。
鳐鱼要走的路鳐鱼知道
文 | 王年军
《兹山鱼谱》是一部去年上映的韩国电影,导演李濬益携知名演员薛景求,联手打造了一部艺术性与商业性兼备、完成度极高、且极具阐释空间的作品,它的最为特殊之处,是以黑白影像复现了韩国社会从古代到近代转折时期的文人心态和世俗生活。主角丁若铨从一个刚刚开始读书的贱民昌大那里,学到了关于各种各样古书所不曾记载的鱼类的详实确凿的知识,这对他这个刚刚从庙堂来到乡野的文人构成了重大的冲击,促使他写下《兹山鱼谱》这部也许是韩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鱼类百科全书。影片的故事发生在一个遥远的、文化尚未完全普及的海岛上,丁若铨通过跟岛民的互动,向当地人热切地学习着如何有效地获取鱼类资源,也了解了他们对官方的松树保护政策的消极应对方式。这呈现出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也即韩国进入近代前夜时期,人们跟自然、海洋的多维互动。因为它涉及大量关于人和鱼类、人和自然如何相处的故事,涉及人对生物的命名,它具有一种初步的生态主义色彩,然而它关于分类和生物形态学的兴趣,又受到儒家“格物致知”学说和西方的博物学、地理学、生物学的影响而产生,这使这部电影成为了解近代前夜东亚文人、民间与自然关系和在自然面前心理状态的重要参考资料。
“真实”的历史是不在场的,它的组织和叙述要依靠档案、文献材料,以及绘画、小说等艺术作品,而这些从来不是中立的再现中介。在《兹山鱼谱》中,故事发生的年代同样有一种主导性的媒介,那就是受到中国国画影响的山水画和肖像画。它所呈现的文人意境、文人趣味,使得作为历史片的故事背景变得可信。

《兹山鱼谱》 2021
导演:李濬益
编剧:金世谦/金郑勋
主演:薛景求/卞约汉 等
在这个故事中,至少有三重之“黑”:首先是影片的黑白色调,它与主人公丁若铨被贬谪兹山、抑郁凄凉的心境有一种直接的映照。其次是“黑山”,因为觉得不吉利,后被改名兹山,它在影片中呈现为大海上的茫茫黑色异物。第三,尽管影片很少直接以山水画的构图来描写环境,但这些人物的造型、服饰,在黑白影像之中恰切地还原了韩国古代肖像画中的人物风貌。影片中有一种非常均匀的光色设计,我们几乎不会见到晃眼的阳光,也无法识别出天气、温度的状况,因为是按照东亚传统绘画的光学设计的,它大体上遵从了散点透视的原则,人物在稳定的构图中移动就像置身于画,对弈、对诗、农妇家庭生活、稚子求学、渔夫捕鱼、书生读书写字的场景,都以古典绘画、诗文的意境作为原型,因此在表象上就容易使观众沉浸于18至19世纪之交的前现代环境。
这部从昌大的角度看具有教育小说或成长小说样貌的电影,把故事的聚焦点放在中央与地方、庙堂与江湖、士大夫(两班)与贱民、性理学与西学、入世与出世之间,在师徒二人、丁若镛/丁若铨兄弟二人的不同选择之间,制造了复杂的张力。从老夫子丁若铨到年轻的学生昌大,这种“教育”随着丁若铨对地方知识的了解而变成双向的互动。丁若铨最初想教昌大读四书五经的正确方法,但紧接着被对方丰富而准确的鱼类知识所吸引,开始写一本叫作《兹山鱼谱》的书。“鳐鱼要走的路鳐鱼知道,鲭鱼要走的路鲭鱼知道”,这类新鲜的表述从未被记录在典籍之中,普通人也从未觉得它们有什么了不起,这让丁若铨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他欣喜于自己是第一个给这些海生动物“发明”可被书籍记载的名字的人。从昌大通俗准确、看似直白的描述中,他知道每一种鱼都有自己行走和捕食的方式,而且用一种综合了民间的俚俗感和知分子审美趣味的命名,给那些从来没有被记载的事物发明一个在文献中的位置,这让他感到生活有了新的寄托。其实丁若铨对鱼类的命名和编谱方式,不是一种类似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这样的汇编和总结。尽管它也是百科全书式的,但是丁若铨本身对于来自边缘岛屿的生物,尤其是鱼类,对那些从来没有被文人所记载的鱼类的关注,尽管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学动力,但已经超出了实用价值,而成为对生命状态的研习,意味着他是朝鲜历史上最早对于海洋文明、对于西方文明产生兴趣的人,并且由此影响到自己观念的觉醒,他成为一个捍卫“个体”多样价值的现代人。他的处境也典型地体现在中国的郑观应、冯桂芬、张之洞、洪仁玕等一批爱国救亡的知识分子身上,他被发配到边疆,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在宗教上受到的牵连,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确实是从性理学、西学、民间学问的相对性之中,意识到了人类并无贵贱之别。他期待着没有两班和贱民之分,没有嫡子和庶子之分,没有主人和奴隶之分,也没有君王的那种世道,但这无疑是一个遥远到看不见阶梯的乌托邦。他知道若写下这种惊世骇俗之论,自己的家眷也会受到牵连,这使他无法像他的弟弟那样发表众多著作,看起来是在名山宿儒所不齿的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窄。实际上,他回避了圣王之学,回避了经学考据,只是因为他已经超越了那个阶段,开始重视个体的价值,这些个体包括贱民、村妇和生生不息的鱼类,他意识到自己的所想已经无法见容于当时的社会。
因此,这部电影从丁若铨何以如此关注在文人雅士那里看来毫无意义的关于鱼类的知识这个疑惑中,解开了被历史淹没者的内心图景,他的觉醒着的痛苦。黑山最终成为囚禁他的铁屋子,而“鳐鱼要走的路鳐鱼知道,鲭鱼要走的路鲭鱼知道”作为隐喻,也成为影片中所有人物的寓言。昌大一心想超出自己的贱民身份,但是即使中了进士之后也仍然被嘲笑,“这两班啊,走路姿势和普通贱民就不一样,要慢慢学习,知道吗?”当看到往稻米里面掺石头、给婴孩征税等酷吏暴行之后,他难以容忍地决裂了,他知道对老师的背叛和“弑父”以失败告终,绝望地回到家乡,却发现自己的老师已经死去。
每个人最终走的只能是自己的路,就像每条鱼都有自己的路一样。从昌大的悔悟和老师在《兹山鱼谱》序言中对他的感激而言,这种彼此的成长教育倒似乎是接近完成的。
影片也用了很多提喻的手法,以小见大地呈现出当时人们在中西、新旧、文野之间知识的“错位”,比如从海上捡来的地球仪,象征性地提示了大航海以来地理学对韩国的影响,但在普通人这里,直到19世纪,“地球是圆的”这件重大发现仍然是不被有效感知的。而陪伴丁若铨的那位村妇,也被丁若铨视为有过人的见识,像一个才女:“好种子才重要吗?播种的父亲,怀胎的母亲,缺一不可。如果地不好,种子就不会发芽。”她戏谑地说,本以为读书人的想法会更高明,会懂得这个道理……没想到这又是一次鲜活的反向教学——经常是“无知者”的道理,启发了那些饱读诗书的人。这次流放,因此使丁若铨受到人生的第二次文化冲击,第一次是他通过性理学接触到西学,包括西方历法、地理学和几何学,让他对欧洲科学技术的先进程度感到震撼,并皈依了基督教;第二次则是他意识到在贱民、村妇那里也有文人那里最缺少的诗性和知识,开始打破不同学问的差别,在不同视域的交点上展开自己的工作。因此,他的三本书《兹山鱼谱》《松政社议》《漂海始末》,都是从民间听来的故事受到启发,而用文人化的语言进行了记载,这种记载又是受到西学强大在场的影响。
总体上看,丁若铨打算放弃那些抽象的道理,研究具体直观的东西。这是朝韩历史上的“实学”传统在一个流放者身上不期然开出的花朵,也是西学第一次来到朝鲜之后对文人生活影响的一个缩影。也许,生态思想只是这部电影的一个侧面,丁若铨思想的最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是在东方与西方、古代与近代的“接触地带”形成的,这是一种关于坐落在不同视差之间的知识的命运的电影。在这个问题上,马丁·斯科塞斯的《沉默》也是一部值得提及的电影,背景是16-17世纪的日本,涉及最初的几代天主教徒在一个仍然奉行本土信仰的国家的命运。斯科塞斯的影片是史诗的,而李濬益的《兹山鱼谱》则是抒情的和艺术性的。后者对于士大夫趣味、民间文化以及二者之间错位方式的理解,是相当现代的,这部电影展现了文人传统中最好的方面。丁若铨娶了一位当地的、几乎是文盲的妻子,这是一个在今天才变得“可见”的选择。这意味着他被黑山的文化所同化了,成为一个“当地人”,最终不是他留给典籍的那些生僻鱼类的汉文名字被记住,而是他作为一个被遗忘的人被记住,就像那些生生不息的鱼类,不需要官方的、中央的知识来给它们命名,它们就生活在水中,有自己的生活、习性和自由,一代代繁衍不息。就此而言,丁若铨也确实通过在著述中死亡,从昌大这位“老师”那里学到了宝贵的知识。在中国历史上,在屈原、苏轼、柳宗元等流放者身上,我们理应也会发现这种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