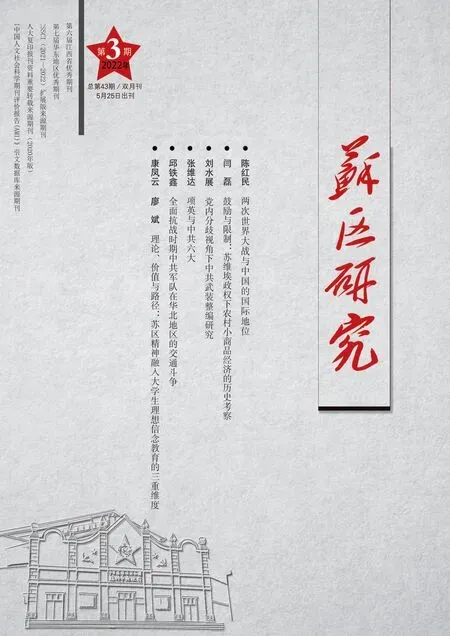党内分歧视角下中共武装整编研究
——以1929年红四军第四纵队整编为中心
刘水展
提要:革命进程中武装整编引发的党内分歧颇为普遍。1929年6月,毛泽东、朱德在闽西推行的红四纵队整编引发了闽西地方精英傅柏翠与红四军及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等人的争论,双方在红四纵队建制统属、教导连保留还是混编以及肉刑制度的去留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傅柏翠所坚持的红四纵队编入红四军系统以及保留教导连的主张均被否定,其所主张的废止肉刑虽被认可,但亦未能得到妥善的解决,三者的叠加最终导致傅柏翠的辞职。武装整编过程中的各类关系对此次党内分歧的产生、演进与结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发展需要武装的支持和保障。中共的革命武装具有不同的军事层级,作为最高层级的主力红军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是中共领导的一支主力红军。从1927年10月毛泽东初上井冈山到1929年5月红四军第二次进入闽西后,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武装升级的理念,该理念的核心在于将地方赤卫队整编为地方红军进而升编为主力红军。武装升级理念实现了农民运动与军事运动的结合,完成了从吸收、训练农民到将农民转化升级为主力红军的过程。武装升级的核心在于地方红军的打造,它既可以实现与主力红军的并轨,亦能实现对赤卫队等更低层级武装的辐射与提升。红四军第四纵队的整编即是毛泽东运用武装升级理念升编地方武装、打造地方红军的首次实践。
整编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也是一个容易引发分歧和冲突的过程。这主要体现在人事职权的安排、建制统属以及不同武装之间的融合等方面。武装整编过程中引发的分歧非常普遍,红四军第四纵队的整编就曾引发闽西党员傅柏翠与朱毛红军及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等的分歧。目前学界对红四纵队整编引发的分歧还未有过细致的讨论。故此,本文以1929年5月朱毛红军进入闽西后的红四纵队整编事件为中心,探讨傅柏翠与朱毛红军、邓子恢等人产生分歧的缘由。
一、红四军第四纵队整编分歧概况
1929年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次进入闽西,开始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从1929年5月至1930年1月,红四军在闽西长达半年多的游击与割据推动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最终形成。作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武装升级”政策也得以不断完善和发展。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指出,武装升级是指“扩大武装组织从乡暴动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以至于超地方红军”的过程。这一过程成为克服中共农民武装思想落后、临时性大、易聚易散、战斗力弱的有效方式,同时也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地方革命运动中军事建设的基本政策。
“武装升级”的关键在于“升级”。作为“升级”的一环,地方红军是连通赤卫队和超地方红军(或称主力红军)的重要桥梁,也是毛泽东自井冈山以来一直尝试构建完整军事层级的关键环节。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后,毛泽东开始在闽西尝试升级整编地方武装力量,红四纵队的整编即是毛泽东通过武装升级方式打造地方红军的最初实践。
1929年5月初,蒋桂战争基本结束,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以3个旅的兵力向赣南推进,企图围歼朱毛红军。5月13日,广东军阀陈济棠发布讨桂宣言,粤桂战火燃起,毗邻粤东地区的闽西大小军阀先后投入战斗。中旬,闽西龙岩县地方军阀陈国辉追随国民党新编第一师张贞部出兵潮汕,闽西腹地空虚。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致信红四军,建议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再入闽西。鉴于赣南敌军集中、闽西敌军空虚的情况,毛泽东、朱德等决定避开赣敌进攻锋芒,再度入闽,开辟闽西割据区域。
5月下旬,红四军由赣南进入闽西。5、6月间,经过对上杭、龙岩、永定等县敌对势力的打击,6月9日红四军前委在上杭旧县召开会议,决定将长汀、永定、龙岩、上杭四县地方武装升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中旬,朱德在连城县新泉宣布前委决定,正式成立红四纵队,以傅柏翠为纵队长。傅柏翠对此欣然接受。19日,红四军第三次攻打龙岩城,傅柏翠领导红四纵队七支队参加战斗。6月下旬,红四纵队进驻龙岩城,于翁家花园整编。此次整编,傅柏翠提出辞职。此次整编距离红四纵队成立仅十余天,傅柏翠的态度却发生极大的转变。这与此前傅柏翠的积极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5月21日,红四军抵达连城县庙前。当晚,毛泽东、朱德接见上杭地方武装负责人傅柏翠等人,听取闽西革命形势与敌我力量情况,指示傅柏翠完成四项任务:阻击敌人四小时;侦察后方敌情,了解行动,将情况送交龙岩县委转红四军前委;尽快地集中地方武装组编59团,随红四军行动;后天到龙岩见面,有事交待。傅柏翠积极完成上述各项任务,尤其是组编59团。22日,傅柏翠交待北四区区委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准备成立59团。26日,北四区各村武装于蛟洋编立59团,傅柏翠任团长。两三天后,傅柏翠接龙岩县委通知,率59团到小池铜钵帮助农民组织暴动,后转到蒋武协助发动暴动、成立苏维埃政权、组织赤卫队。6月3日,傅柏翠率59团与红四军第三纵队二克龙岩城。7日,59团攻克上杭县北三区丘坊村,取得胜利。8日,傅柏翠率队至上杭县白砂镇,协同红四军政治部开展俘虏宣传工作。可以看出,红四军入闽的最初阶段,傅柏翠的表现非常积极。
傅柏翠的表现获得了毛泽东与朱德的认可,其所运用的游击战术亦得到毛泽东的赞赏与肯定:“游击和战术进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在敌军四周出没无常,以此与敌军持久斗争)。”出于对傅柏翠的信任,朱德将缴来的部分枪支交予傅柏翠,由其转交地方,武装赤卫队;同时指示傅柏翠在蛟洋设立红军医院,安置治疗红四军伤病员。
傅柏翠对红四军的到来抱有较高的期望,亦积极配合红四军打击敌人。那么,从红四纵队成立到整编这短短十几天的时间里,为何傅柏翠的态度会从积极配合转变为抵制进而提出辞职?
对于6月下旬龙岩翁家花园整编一事,傅柏翠在后来的回忆中谈道:“在整编中有人主张划归地方建制,我曾坚持要编入红四军系统,并固执地要保留一个过得硬的连队,反对强弱混合编制,此外,我对调来四纵队任职的一些军阀作风较严重的干部有意见,提出了辞职要求。”这份回忆大体表明了傅柏翠不满整编、提出辞职的三个原因。那么,为什么傅柏翠要反对红四纵队划归地方建制,坚持将其编入红四军系统?为何他要保留一支过硬的连队,反对强弱混合编制?“军阀作风严重”意味着什么,傅柏翠为何有意见?
二、红四纵队建制统属问题的分歧
关于红四纵队整编情况,邓子恢在文件中写道:“长汀赤卫队,永定湖雷、溪南游击队,及一部分土匪及北四区五九团三部分合编成四纵队,成立七支队。另令:永定、龙岩、上杭东五区武装编为八支队。”可知,红四纵队来源于闽西早期革命暴动的队伍,即傅柏翠领导的北四区(大体等同于蛟洋乡)武装、张鼎丞等人领导的永定溪南金丰武装、杭永岩等地武装以及红四军1929年3月第一次进入闽西组建的长汀赤卫队。这些武装大都经过长达一年的武装斗争,游击经验丰富,是具备相当战斗力的游击队伍,同时也是中共在闽西的主要地方武装力量。
闽西地方武装力量升编为红四纵队,对红四军和闽西而言意义重大。这不仅是毛泽东以武装升级的方式实现红四军规模扩大的首次实践,也有助于提升闽西地方红军的战斗力,推动闽西革命的发展。因此,红四纵队的建制统属问题需要反复斟酌。事实上,整编过程中就出现了建制划归地方还是红四军的争论。傅柏翠的回忆隐含了闽西地方领导人内部关于红四纵队建制统属问题的分歧。
闽西地方武装升编是闽西革命的要事。作为闽西中共的最高领导人,特委书记邓子恢参与了讨论。邓子恢是“主张划归地方建制”的代表人物,与傅柏翠看法相左。邓子恢的这一主张,一方面是建立在对此前闽西革命斗争情况判断的基础上,一方面是遵照中共福建省委指示作出的决定。
邓子恢曾在龙岩、上杭、永定三县领导革命斗争,对各地的情况颇为熟悉。对于此前闽西革命斗争失败的原因尤其是武装力量不够、战斗力不强等因素,邓子恢明确写道:“闽西二百余军及数千赤卫队,均因为子弹缺乏,不能与敌人抵抗,割据区域有逐渐被反动派镇压下去的趋势。……在武装斗争中,武装自然是重要的条件之一,假如我们单有广大的群众而没有充分的武装,也很难得到胜利的。”邓子恢后来的回忆亦指出:“过去两年闽西群众斗争之所以时胜时败,此起彼伏,主要原因就是缺乏战斗力坚强的红色武装。”
对闽西革命成败的认识,使得邓子恢非常重视战斗力较强的地方红军的构建。1929年3月,闽西特委再次成立,邓子恢担任书记。特委复立初始,邓子恢便开始谋划地方红军的成立事宜。“三月间特委成立时便计划成立二个教导队,由各县派忠实勇敢同志分别到蛟洋、溪南里训练,准备组织闽西红军。”5月前后,“特委计划在永定编红军二百人,上杭一百五十人,龙、武、汀各五十人,合计五百人,编做一营”。虽然成立红军背后有福建省委的指示,但亦可见邓子恢的急切之心。红四军二入闽西后,邓子恢建立地方红军的态度更加急切。5月23日,红四军攻占龙岩城,毛泽东指示邓子恢重视武装建设,建立政治上坚定、组织上巩固、军事上具有坚强战斗力的红军。邓子恢非常认同,请求毛泽东调派军事、政治干部加强闽西红军的建设工作。红四军进入闽西后连续作战,邓子恢随军行动。当6月6日于永定县坎市镇稍有闲隙时,邓子恢便召集特委扩大会议,讨论建立闽西红军的问题。半年后,红四军决定带红四纵队离开闽西,邓子恢致信毛泽东,要求留下红四纵队在闽西游击,帮助消灭敌人,巩固红色政权。可见,邓子恢非常希望闽西拥有自己的红军。在闽西还未成熟地通过武装升级将赤卫队升编为地方红军时,只有红四纵队“划归地方建制”隶属特委,闽西才算真正意义上拥有地方红军。因此,邓子恢主张红四纵队“划归地方建制”。
邓子恢秉持这一主张,另一方面是迫于福建省委的压力。红四军是一支机动性很强的超地方红军,受战争形势影响在各省间游击转移。为避免受地方主义的累害,经过毛泽东的努力和争取,红四军前委机关实现了对特委的领导,同时弱化了省委对红四军的指挥权,尽管此时中央还未在制度层面肯定前委领导特委和省委的权力。这意味着,当红四军进入闽西后,前委可以领导闽西特委,闽西特委受福建省委和红四军前委的双重领导。1929年5月,红四军二进闽西,先后攻占龙岩、永定、上杭等县。邓子恢等人随军行动,受前委指挥。虽然名义上特委受前委和省委指挥,但省委机关远在闽南厦门,而红四军就在闽西,地理上的远近决定了特委更多听命于前委,特委由此忽视了与省委的联系。此种情况引发了省委的不满,省委屡次去信指责特委只顾随军跑,忽视对地方工作的指导,不知及时向省委汇报情况。
事实上,1929年3月红四军一进闽西时,闽西党组织对红四军的期望便十分高涨,并将希望寄托于红四军身上。对此,福建省委曾提出批评:“(党内)对于朱毛存过大的幻想,以为朱毛来闽……,什么都有办法了;这种观念在闽西一带最容易发生”;“朱毛到闽西,闽西工作为目前中心工作之一,这是对的。但不能成为唯一的中心工作。……闽西农民起来暴动,在策略上我们应积极的去领导,使农民暴动有最高的组织性。闽西党部应计划到如何建立苏维埃区域并扩大之,如何扩大武装,如何延长苏维埃区域的存在时间,使政治影响扩大并延长起来。但这一计划应以群众为中心,而不是计划朱毛今天打这个地方,明天打那个地方,变为单纯的军事行动。这一计划应该以群众为主体,朱毛军队为补助力量。依赖朱毛力量去发展群众工作的‘偷便宜’思想,要严格的防止”。5月,红四军再次入闽,特委依附红四军的情况更加严重,这使得福建省委更加不满。省委多次指责特委:忽视群众斗争,过分依赖红四军;交通往来不频繁,情况汇报不及时;“党随军走”现象严重。为加强对闽西特委的领导,省委屡屡派出巡视员前往闽西巡视。
省委不仅担心闽西“党随军走”,也担心闽西武装力量跟着主力红军跑。因此,在批评特委的同时,省委不断强调闽西地方红军作为独立武装力量的重要性。1929年5月12日,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前,省委就已明确指示:“闽西工作勿与朱毛军队相混合,为组织红军不可与朱毛混合起来。”26日,省委再次去信特委,要求“在苏维埃区域必须极力扩大红军和赤卫队的组织,极力扩充武装,使朱毛红军去后,仍能相当保存这些苏维埃的政权”,“特委要很注意这一工作”。后来红四纵队成立,省委的态度更为坚决:“四军未离开闽之前,第四纵队当然要实地跟着四军去工作,去学习。他同四军要离闽时,犹要设法保留一部分在闽西帮助群众去斗争。因为闽西地势不同,交通困难,我们如有一部分的武装仍然可以维持相当的政权,可以帮助群众应付反动派。”
面对省委对特委的指责与批评,加上省委对闽西地方红军独立性的强调,1929年6月下旬红四纵队整编讨论建制问题时,邓子恢不得不重视和考虑省委的意见,主张红四纵队“划归地方建制”。以上即是邓子恢主张红四纵队划归地方建制的大体情况。
与邓子恢不同,傅柏翠坚持红四纵队划归红四军系统。对于傅柏翠的这一主张,蒋伯英指出:“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正是反映了傅柏翠在人民军队建设上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就是后来毛泽东在古田会议所批评的试图脱离无产阶级领导的‘单纯军事观点’和‘军阀主义的道路’。”这一判断抓住了红四纵队建制统属分歧的关键,即党军关系问题。傅柏翠虽为中共党员,但组织纪律观念非常淡薄,不重视且不认同作为领导核心的“党”。比如,1928年初,中共北四区区委成立,傅柏翠担任书记。不过,傅柏翠并不看重书记一职,为腾出时间从事军事斗争,将书记一职转予副手傅希孟。5、6月间,邓子恢、郭柏屏等人以上级党组织的身份到北四区推行中央和省委指示,傅柏翠极力抵制。8月,傅柏翠不顾省委常委王海萍和闽西特委的反对,强烈要求分兵回乡,甚至在上级表示反对的情况下以举枪自杀相威胁。12月,邓子恢以特委宣传部长和特派员身份致信傅柏翠,要求傅柏翠取消北四区武装斗争,遭到傅柏翠的反对与指责。傅柏翠淡薄的组织观念,使得他时常无视上级指示,屡屡拒绝上级党组织的领导。相较于党的建设而言,傅柏翠更加重视武装建设和武装斗争,而且屡次拒绝上级党组织对其武装的领导。红四纵队整编时,傅柏翠反对将其划归地方建制,实际上正是傅柏翠反对闽西特委对红四纵队的领导和控制,亦即反对党对军队的领导。
红四纵队整编对于红四军而言非常关键。这不仅是毛泽东“武装升级”政策的首次尝试,也是实现扩大红军、支持革命斗争的重要保障。因此,作为红四军领导人,毛泽东参与了整编的讨论。对于红四纵队建制统属问题,从当时红四军内部的争论来看,傅柏翠的主张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可。1929年,红四军内部发生“朱毛之争”,双方争论的焦点颇多,核心为党军关系,即军队到底遵从“个人领导”还是“党的领导”,亦即两个思想系统的争论。毛泽东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也是后来古田会议所确立的建军原则。从1929年5月底的湖雷会议到6月8日的白砂会议,再到6月14日的新泉会议,最后到6月22日的红四军党的“七大”,红四军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争论以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结束,毛泽东等人被调离前委,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红四纵队整编一事即发生在红四军“七大”会议后的几天。经过此前的激烈争论,毛泽东没有赞同傅柏翠反对党领导军队、反对红四纵队“划归地方建制”的主张。
傅柏翠仅仅是上杭地方武装的领导人,在党内无任何职务。而邓子恢是特委书记,是中共在闽西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倾向于党的领导,认同邓子恢的主张。另外,必须明确的是,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虽然弱化了省委对红四军的指挥权,但还未在制度层面获得超越和领导省委的权力,前委事实上仍然受省委领导。因此,前委必须考虑省委屡次强调的闽西地方红军保持独立性的问题。最终,傅柏翠的主张被否定,红四纵队划归地方建制,隶属闽西特委,即党的领导归闽西特委,军事行动由红四军指挥。
三、关于教导连保留还是混编的分歧
红四纵队整编过程中,傅柏翠提出的另一主张是“保留一个过得硬的连队,反对强弱混合编制”。傅柏翠所言“过得硬的连队”,是指由其一手带起来的教导连。这支武装主要由傅柏翠的家乡民众组成,是傅柏翠自1928年6月蛟洋暴动以来开展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1928年6月,蛟洋暴动爆发;7、8月间,傅柏翠奉省委命令率暴动队伍前往龙岩、永定、上杭等县游击;9月重返北四区,在古田、蛟洋一带坚持游击,击溃郭凤鸣驻军。正是凭借这支武装,傅柏翠重掌北四区,并取得多次战斗的胜利。1929年初,罗明到蛟洋传达中共六大会议精神,指示傅柏翠将40人左右的游击队改为教导队,培养下级干部人才。3月,省委介绍中央派去指导红四军工作的罗瑞卿、曾省吾到蛟洋担任军事教官,对教导队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傅柏翠颇为重视此事,率队活跃于北四区一带。5月,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傅柏翠遵照福建省委和红四军前委指示,以教导队为基础,集合北四区各村武装成立59团,协助发动地方暴动,参与红四军二打龙岩城及攻打上杭北三区丘坊村的战斗。
由上可知,红59团主要是经蛟洋武装改组为教导队,并以教导队为基础整编而成的。59团基本上由北四区武装构成,不过构成59团的队伍对于傅柏翠而言意义并不相同。傅柏翠更偏爱教导队。这支武装主要由蛟洋民众组成,与傅柏翠有血缘与地缘关系,曾跟随傅柏翠出生入死。而且,教导连游击能力强,经过罗瑞卿、曾省吾二人的训练和指导,不仅具备较强的战斗力,而且拥有较高的政治和军事素养。红四纵队整编时,傅柏翠就曾表示出对这支队伍的喜爱:“在整编中,有争论,我是主张要保留选编一个精干的连队,在打仗的关键时刻才有保证,不然我们指挥官的头很容易被敌人割去。我们思想就是还要保留原来59团的那个教导连,不能拆散。我是很喜欢这个连,精干又会打仗,都是一些骨干。”傅柏翠的意思非常明确。但是,“保留选编一个精干的连队,在打仗的关键时刻才有保证,不然我们指挥官的头很容易被敌人割去”的说法则有夸张之嫌。傅柏翠此言意在阻止教导连混编。保留教导连说明傅柏翠重视武装,但也凸显了傅柏翠浓厚的地方观念和强烈的地方主义倾向。如果用红四军内部争论的话语来看,傅柏翠的“小团体主义”特征明显。
傅柏翠关于保留教导连的主张和理由没有获得毛泽东等人的认可。傅柏翠在回忆中写道:“他们主张要拆散混编,把原来的教导连的人分到各个连队去,我思想不通,如果要这样编,那就全军混编。”为保留教导连,傅柏翠提出“全军混编”的办法。
傅柏翠之所以提出这一办法,与他所知悉的红四军的情况密切相关。红四军由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余部合编而成。自成立伊始,两部就存在明显的“分团主义”。从1928年到1930年,杨开明、陈毅、熊寿祺等人曾就红四军内部的“小团体主义”有过详细的描述。在井冈山时期,中共湘赣边特委书记杨开明指出:“红军第四军中有一最不好的现象,就是分团主义……二十八团原是朱德带领的,三十一团原是毛泽东带领的,两团之间,似乎有二十八团与三十一团之分别,团与团之间似有点历史上的界限。”在闽西时期,代理红四军前委书记的陈毅就朱毛之争的情况向中央汇报,其在关于红四军党务概况的报告中写到:“因四军是由各种自有其本身奋斗的历史部队而组成,混编的办法始终未执行,因此历史的残余尚保留在一般同志的脑中,武昌出发(毛部)南昌出发(朱部)的资格在军队中是有相当的尊重的,尤其军队的习惯,一班,一排,一连,一营,一团,生活各为一集团,农民的自私关系,自然要划分界而且非常清楚,因此小团体主义的色彩就很浓重,各团为各团争利益,如〔各〕营为各营争利益,各连为各连争利益,如枪弹人员之类则主张自己要多,如担任勤务则主张自己要少一点。”1930年5月,时任红四军代理书记的熊寿祺在《红军第四军状况》的报告中指出:“小团体主义倾向,这种表现是各纵队、各支队〈部〉、各大队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只晓得自己这一个小团体,没有看见整个的革命集团。如像一个纵队内,要往各支队去拨人拨枪,各支队就不大愿意拨,拨些有病的人和损坏了的枪支出来给别人,自己把好枪留下。甚至有些部队把人、枪藏起来,使你考查不到。……像这种小团体主义的倾向,不是普遍的是如此,同时也不是纵队这一级是如此,因为纵队这一级,政治水平比较高一点(不过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小团体主义倾向最〈利益〉厉害的是支队〈部〉以下有一些部队如此的。”
从上述三人的描述来看,红四军内部的“小团体主义”现象较为严重。1929年5月,红四军入闽后爆发的朱毛之争,部分原因就是“分团主义”导致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与以朱德为军长的司令部之争。在随后的湖雷会议(5月底)、白砂会议(6月8日)、新泉会议(6月14日)和红四军党的“七大”(6月22日)上,傅柏翠参与了后面的三次会议;在此期间,红四军还召开过诸多小会讨论朱毛之争问题。双方的争论较为激烈,争论的焦点也比较集中和突出,因此傅柏翠较为清楚红四军内部的分歧所在。傅柏翠后来回忆道:“红四军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六)宗派主义:因为红四军官兵有来自武汉警卫团和叶挺、贺龙部队的;有来自湘、赣、闽的农民;有来自被俘人员;有来自水口山工人。各方面人员组合在一起,又不是混编,各纵队之间无形中产生本位主义和宗派主义。”正因如此,傅柏翠利用朱毛之争之机与红四军“分团主义”的现象,于整编时提出“全军混编”。在傅柏翠看来,“全军混编”不可能实现,提出此议是为了迫使红四军作出让步,从而达到保留教导连的目的。
虽然红四军内部存在“分团主义”现象,但毛泽东一直试图打破朱毛两部界限。1929年6月,在给林彪的信中,毛泽东对红四军的发展历程进行阶段划分时,其中一个标准便是“小团体主义”在四军的变化情况。“从四军成立(1928年4月,笔者注)到去年(1928年,笔者注)九月重回边界的第一个时期”,“小团体主义充分存在而发展”;“从去年九月重回边界到三月十四日(1929年,笔者注)占领汀州是第二时期。这时期内,党能开始在理论上建设(“建设”二字,从上下文分析,疑为“批评“二字之误)小团体主义了(虽然在实际上还不能)”;“从汀州到现在是第三时期”,“因一、二、三纵队的编制,小团体主义从事实上开始减弱”。毛泽东不仅强调了彭德怀部队对红四军“小团体主义”的冲击,同时还指出了“小团体主义”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五军不能给四军以多大的影响,但在打破小团体主义一点上确还给予四军相当的刺激,特别是柏路会议讨论四、五军合编问题时,彭德怀同志的愤激的表示,给了少数同志以颇大的打击。”“军阀军队残余的小团体主义是造害红军的最大问题之一。少数同志们不但不肯努力去消灭小团体主义,反而有助于小团体主义的倾向。小团体主义不消灭,不能如二、四团一样的完全由集体的党领导,则红军只是一个好听的名称罢了!”1929年1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古田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再次对“小团体主义”进行严厉的批评:“(2)小团体主义。表面上是个人主义的放大,骨子里仍然是极狭隘的个人主义,他同样的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红军中历来小团体的风气很盛,奋斗的结果消灭了许多,但残余是依然存在的,还须加上奋斗的努力。”
毛泽东力图破除红四军内部“小团体主义”、改善各团关系的行动表明,傅柏翠在整编时坚持保留教导连的主张没能获得毛泽东的认可。最终,教导连混编,融入红四纵队,傅柏翠也被冠以“农民意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称号。教导连保留与混编的分歧以傅柏翠的“落败”告终。
四、肉刑制度废与留的分歧
傅柏翠提出辞职的第三个原因是:“我对调来四纵队任职的一些军阀作风较严重的干部有意见,提出了辞职要求。”在另一份回忆中,傅柏翠有着同样的表述:“我因对整编就有思想问题,再加上这些事(指军阀作风问题,笔者注),我思想不通,就提出不干了。”傅柏翠所谓的“思想问题”即上文所述的建制与教导连论争问题。不过,红四纵队干部的“军阀作风”问题更像催化剂,强化了傅柏翠的不满情绪,导致傅柏翠萌生了退意。
1929年6月10日,红四军于新泉休整,前委决定从红四军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纵队抽调部分干部到第四纵队。傅柏翠非常重视武装建设,对于前委的这一决定尤为赞同。然而,只过了十余天,红四纵队于翁家花园整编时,傅柏翠就对调到红四纵队的军事干部颇为不满,严厉指责军事干部“军阀作风”严重。当时红四军内部有着“军阀作风”“军阀习气”和“军阀主义残余”等各类说法,这些说法的内涵都较为宽泛,一般都包含有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小团体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将政治与军事对立、肉刑等内容。不过,傅柏翠这里所说的“军阀作风”则特指肉刑,即官长对士兵的体罚。
毛泽东曾指出:“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红军既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旧式军队的肉刑制度在红四军也留存了下来。朱毛两部会师井冈山后,肃清旧军队习气的改造全面开始,肉刑虽被明令废止,但一直没能真正停止。粟裕回忆:“那时部队打人风气比较严重,虽然已经有明令废止肉刑,但还未被一些人所接受。第二十八团有一个干部,因好打人而得名‘铁匠’,意思是他打人象铁匠打铁一样狠。有个旧军官出身的人,打人成瘾,打得军需、上士、传令兵、伙夫差不多都跑光了。还有老兵打新兵的。事实上越是打人,纪律越涣散松垮。如果哪个单位战士逃跑多,几乎不用调查,就可以断言那个单位打人成风。”古田会议决议案也有详细记载:
各部队中凡打人最利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显著的例子,如第三纵队第八支队部某官长爱打人,结果不仅传令兵伙夫差不多跑完了,军需上士及副官都跑完了。九支队第廿五大队曾经有一时期来了一个最喜打人的大队长,群众送给他的名字,叫做铁匠,结果士兵感觉没有出路,充满了怨恨空气。这个大队长调走了,士兵才得到解放。特务支队第三大队打人的结果,跑了四个伙夫,一个特务长,两个斗争的好久的班长。其中一个名肖文成,临走留下一封信,声明他不是反革命,因受不起压迫,才逃跑。四纵队初成立时,一二三纵队调去的官长一味的蛮打士兵,结果士兵纷纷逃跑,最后这班官长自己也立不住脚,都不得不离开四纵队。
正如粟裕和古田会议决议案所言,打人越多,部队纪律就越涣散松垮。但是,即便打人官长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官长打人的现象依然存在。这是因为旧式军队留存下来的肉刑做法对于官长强化军事纪律、领导队伍行军作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主要在于通过吸收农民组建起来的红军往往容易出现开小差、逃跑、害怕战争、不听从指挥等一系列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案关于废止肉刑提出的纠正方法就从侧面反映了一些问题:“(2)举行废止肉刑运动。……这样才能使官长方面不但不至废止肉刑觉得兵带不住,而且了解废止肉刑之后将要更利于管理教育。士兵方面不但不至因废止肉刑更顽皮了,而且因废止肉刑,增加了斗争的情绪,撤去了官兵的隔阂,将要自觉的接受管理训练和一般的纪律。”这段材料表明,废止肉刑可能导致“兵带不住”、不利于“管理与教育”、士兵“更顽皮”、士兵不“自觉地接受管理训练和一般的纪律”等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处于战争形势下的中共和红军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可以说,适当的肉刑与体罚对于提升军队的军事纪律是有一定作用的。萧克曾回忆:“至于犯其它错误的,就罚立正或打几下手板。这样做的结果,队伍就比较整齐了。打屁股,打手板,现在看来是笑话,那是旧军队的恶习,1929年12月红四军九次代表大会批评为军阀残余,是完全对的。但当时我们管理水平低,只知道这种办法,并且初见成效。”
也正是如此,在红四军内部的部分官长眼中,不采取体罚和肉刑的做法便无从管理队伍。红四军内部因此流传着这样一些说法,即“不打人看怎样能够管理?不枪毙逃兵看有〈怎〉什么办法止得住逃兵”“不打不骂带不好队伍”“战士是城隍庙里的鼓,三天不打就上灰”“不打不成兵”。即便古田会议上毛泽东、陈毅决心废止肉刑,一纵队司令林彪竟还当场表示反对。可见,在红四军内部,以林彪为代表的官长对肉刑尤为推崇。这种管理士兵的治军理念与提升军事纪律的方式方法根深蒂固地嵌入旧式军队出身的官长思想中。
关于红四军内部存在的肉刑制度,身为红四纵队司令的傅柏翠感受颇深。“当时打骂士兵,枪毙逃兵现象很普遍。特别是一纵队,因为纵队司令员林彪本人,动不动打骂下级,主张兵不打不听令。我在新泉整训中,我亲眼看到把逃兵毙死在路旁。”如果说这种感受还属旁观者之感的话,那么,当自己所领导的红四纵队士兵遭遇肉刑时,傅柏翠已然不会再有置身事外的感觉了。
红四纵队由七支队和八支队组成。不过,八支队远在永定,直到1929年10月红四军攻打上杭城时,两个支队才集中起来。换言之,傅柏翠虽为红四纵队司令,但一直只领导七支队和纵队司令部。1929年6月10日红四军于新泉编训时,前委决定从第一、第二、第三纵队抽调部分干部到红四纵队,实际上正是抽调到七支队。因此,七支队的官长成分有两种,大部分是红四军派来的军事干部,少部分是地方成长起来的地方干部。另外,七支队士兵的成分也有所不同,一部分习惯军队生活与训练,一部分则过惯农村生活。官长与士兵成分的不同,最终导致七支队内部矛盾的爆发。
关于这次冲突,特委书记邓子恢曾有报告:“七支队士兵成分,部分是由前委提过来的,于长汀赤卫队,平常已受过军队生活,军事训练已成为习惯。另一部则地方赤卫队改编为五九团湖雷游击队等,平素过的农村生活,当然受不惯严厉的军事训练。同时官长中也有二种成分,大部分是四军派来的,对士兵训练取严重主义,官长阶级极严。另一部分是当地农民领袖(傅柏翠,笔者注),反对那种计□式的训练。这两个极端主张日益冲突。同时一般农民士兵受不惯这种,加以混编,结果士兵反觉不惯,因而匪兵日多,更增官长间冲突,致有同志与一般官长消极辞职之事,这种事情双方都有不是,□□□(李任予,笔者注)同志过于姑息,□□□(傅柏翠,笔者注)同志则过于燥,其四军派来官长也有很多坏分子,因此形成四军内部纠纷。”这里所谓的“对士兵训练取严重主义,官长阶级极严”,实际上就是指肉刑。换言之,傅柏翠所领导的地方武装59团士兵遭遇了红四军派来的下级官长的体罚。傅柏翠曾言:“我们这个部队,都是刚从农村来的,没有通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什么立正、稍息、左右转、齐步走等都不懂,当然更不懂得什么敬礼,生活较散漫,纪律性差,也不严肃。可是从红军派来的军事教官,因还存在着军阀的打骂作风,在上军事课时,往往动作不对就骂,甚至打。如有一个士兵在出操时笑了一声,就被教官用藤条抽打。有一个士兵吐了一口痰,教官就罚他要从地下吸起来。”下级官长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傅柏翠的治军理念。傅柏翠所领导的59团多由其家乡农民组成,其治军理念和提升军队纪律的做法更多依靠传统社会关系的联结以及士兵对他的信仰和敬重。这也意味着下级官长和傅柏翠之间的治军理念存在严重的分歧。从地方武装升编起来的士兵对肉刑制度意见纷纷,跑去向傅柏翠诉苦,要求回家。面对这些由其从家乡带出来的农民,傅柏翠深感愧疚和不满,要求红四军派来的下级官长停止肉刑。然而,因红四纵队党代表李任予“过于姑息”,傅柏翠的要求没有得到重视,他反而被下级官长污蔑为“造谣”。其实,傅柏翠所言属实,古田会议决议就明确记载:“四纵队初成立时,一二三纵队调去的官长一味的蛮打士兵,结果士兵纷纷逃跑,最后这班官长自己也立不住脚,都不得不离开四纵队。”为缓和士兵与官长之间的矛盾,傅柏翠还曾向一纵队司令林彪反映此事,希望林彪出面调解。然而,林彪并不赞成傅柏翠的意见,坚持“军队不对士兵严格要求是不行的,棍棒底下才能出将军”。结果是作为当地农民领袖,傅柏翠不能有效安抚农民士兵的情绪;作为红四纵队司令,傅柏翠不能有效阻止下级官长的肉刑做法。加上红四纵队党代表李任予“过于姑息”、林彪拒绝出面调解,傅柏翠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双方都不讨好。红四纵队内部士兵与官长间的冲突最终不仅演变成傅柏翠与官长们的冲突,也使得傅柏翠对自身所带出来的农民武装深有愧疚。两者的叠加导致了傅柏翠的“消极辞职”。
此后红四纵队内部召开党员生活会,傅柏翠被批为“农民意识”。朱德参加此次会议,一方面替傅柏翠解围,一方面做傅柏翠和其他官长的思想工作。会后,朱德、毛泽东再次对傅柏翠进行开导和安慰,并经前委决定,进行人事调整,李任予调任二纵队,二纵队党代表谭震林调任红四纵队党委书记,张鼎丞升任红四纵队党代表。“经前委特纵,为四纵队全体党员大会批评的”,“纠纷始告结束”,整编继续进行。
虽然红四纵队内部纠纷得以解决,“但官兵官长间尚留有不少裂痕”。红四纵队下级官长仍旧是原班人马,尽管朱德做过思想工作,毛泽东亦极力反对肉刑,但官长的体罚作风依旧存在,士兵与官长的冲突仍然存在,作为红四纵队司令的傅柏翠仍继续面临双方的压力。
总而言之,由于整编过程中主张屡屡被否,加上作为纵队司令无法自在地领导军队,傅柏翠最终在整编时提出辞职。
结语
革命进程中的党内分歧在所难免,武装整编更是一项容易引发分歧的艰难工程。毛泽东、朱德在闽西实施的红四纵队整编就曾引发傅柏翠与红四军、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等人的分歧。这些分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的争论也揭示了各类关系对党内分歧的形成、演进与结果的影响。
首先是红四纵队建制统属问题的分歧。基于对闽西革命成败的认识,以及福建省委对闽西特委只知听从红四军前委而不顾省委指示的指责与批评,加上省委对闽西地方红军独立性的强调,特委书记邓子恢主张红四纵队划归地方建制。傅柏翠组织观念淡薄,反对党对其武装的控制和领导,坚持将红四纵队编入红四军系统。经历红四军内部权力之争与党军关系的激烈争论,强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毛泽东没有支持傅柏翠,红四纵队最终划归地方建制,建制统属争论以傅柏翠的“落败”告终。在这个过程中,红四军内部的党军关系,红四军、地方党组织与地方红军之间的军地关系最终影响了红四军的地方建制划归问题。
其次是教导连保留还是混编的分歧。教导连主要由蛟洋民众组成,与傅柏翠存在血缘和地缘关系,且与傅柏翠出身入死,战斗力强,政治、军事素养高,深受傅柏翠喜爱。故此,傅柏翠主张教导连作为独立连队不参与混编。在此主张被反对的情况下,傅柏翠提出全军混编,试图迫使毛泽东、朱德作出让步。然而,反对“小团体主义”、力图破除红四军内部分团现象的毛泽东未同意傅柏翠的主张。最终,教导连混编,融入红四纵队,教导连问题再次以傅柏翠的“落败”告终。
最后是肉刑制度去留的分歧。红四纵队七支队官长主要由红四军派来的军事干部构成,这些旧式军队出身的官长实施肉刑制度,使得农民士兵抱怨连连。傅柏翠深感愧疚和不满,要求下级官长停止肉刑,但遭到下级官长的反对。虽然后来朱德、毛泽东出面调解,毛泽东亦极力反对肉刑,但官长的体罚作风依旧未能改善,士兵与官长的冲突仍然存在,傅柏翠不得不继续面临双方的压力。红四军内部的肉刑惯习所引发的红四纵队官兵关系的不洽,最终导致傅柏翠与下级官长及其农民士兵关系的恶化。
可以看出,红四纵队整编过程中,傅柏翠所提的三大主张,两条被否决,一条虽获认可,但亦没能得到较好的解决。三者的叠加最终导致傅柏翠的辞职。
这一武装整编引发的分歧在中共革命历史上是一种普遍且普通的情况。然而,这次整编对于傅柏翠个人生命史及闽西土地革命战争史而言,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此次武装整编后,傅柏翠领导红四纵队的态度日渐消极,与红四军及邓子恢等人的矛盾愈发严重,傅柏翠最终放弃红四纵队弃职回乡,单方面与中国共产党脱离关系。这一事件同此前傅柏翠与闽西、福建党内人士的冲突事件构成一组连续体,导致日后傅柏翠与闽西党内人士更加严重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事件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