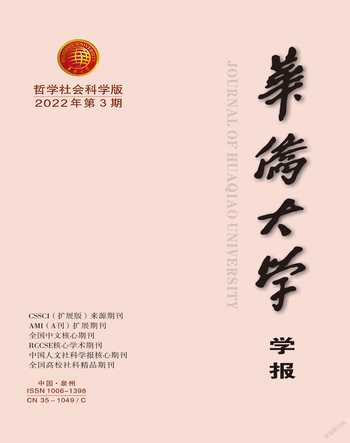刑法立法公众参与如何发生
摘 要:中国刑法立法公众参与如何发生须区分非建制化和建制化阶段进行类型化讨论。社会热点事件驱动、立法机关的会期、互联网主阵地、道德判断策应和媒体推波助澜素描非建制阶段刑法立法公众参与的总体面貌,而建制化阶段刑法立法公众参与讨论则需要区分刑法立法草案提出、刑法立法草案审议和刑法立法草案表决公布等不同阶段进行细致性探究。刑法立法草案提出阶段,相关部门通过立法座谈会、听证会、咨询会、调查问卷和实地调研等方式听取公众意见,公众也可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就刑法草案提出意见和建议。刑法立法草案审议阶段,最高立法机关及时公布刑法审议进程信息,向社会公众公布刑法草案及草案说明并听取公众意见。刑法立法草案表决公布阶段,公众可列席和旁听刑法草案的表决会议,参加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方式表达其对刑法公布及其实施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刑法立法;公众参与;非建制化阶段;建制化阶段
作者简介:王群,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学(E-mail:wangqun19882@163.com;重庆 400041)。
基金项目: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重点调研课题“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刑法边界研究”(2021DXXTZDDYKT073)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2)03-0111-10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光明日报》,2021年11月12日,第1版。)。推动刑法立法公众有序有效参与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内容,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方式。长期以来,学界高度重视刑法立法公众参与问题研究,有从人民主权、社会资本、耗散结构和多中心治理理论等角度阐释刑法立法公众参与的内在逻辑;(王志祥、戚进松:《从危险驾驶入刑看立法的民主性与科学性》,《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45—50页;王群:《再论把公众参与带回刑法立法——从社科话谈到耗散结构的价值再发现》,《理论月刊》2021年第7期,第126—133页。)从刑事立法发展历程与实践中肯定刑法立法公众参与的经验做法;(赵秉志:《中国刑法立法晚近20年之回眸与前瞻》,《中国法学》2017年第5期,第47—68页;赵秉志、赵远:《修法特点与缺憾——<刑法修正案(九)>简评》,《求索》2016年第1期,第4—10页。)但也有学者从社会公众非理性、社会公众难以被代表提出刑法立法公众参与的隐忧。(李翔:《论刑事立法公众参与的限度》,《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62—67页。)甚至认为可能会带来情绪立法的问题,(刘艳红:《象征性立法对刑法功能的损害——二十年来中国刑事立法总评》,《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3期,第35—49页;郭玮:《象征性刑法概念辨析》,《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0期,第91—108页。)还[KG(3x]有学者从刑法立法信息公开、公众意见反馈和立法程序优化等方面提出了刑法立法公众参与的完善路径,(熊永明:《论我国刑法立法民主性的贯彻与提升》,《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80—85页;李怀胜:《刑事立法的共识观及其双重面向》,《中国刑事法杂志》2015年第3期,第36—47页。)等等,相关论述要言不烦,极富启发意义。然而,对刑法立法公众参与问题研究的原点,无疑还是刑法立法公众参与如何发生,只有理解并深谙刑法立法公众参与如何发生,才能更好地理解刑法立法公众参与为什么要发生、如何更好地发生。遗憾的是,存量理论研究对此阐释仍显不足,以致于我们经常谈论刑法立法公众参与,但当我们进一步追问刑法立法公众参与真正是什么的时候却时常深感迷惘。鉴于此,代之以刑法立法公众参与价值、问题和路径等传统研究进路,以我国刑法立法公众参与广泛而生动的社会實践为素材,探讨作为本体意义上的刑法立法公众如何参与的基础面相就有其显著研究意义,进而为刑法立法公众参与为什么要发生、如何更好地发生提供有力支撑。
一 非建制化与建制化阶段:一个分析框架提出
长期以来,人们对刑法立法公众参与存在一些认识论上的误区。例如,将刑法立法公众参与仅仅看作是立法审议阶段的公众参与,辟如公众参与立法座谈会、听证会或咨询会并提出意见建议;或者偏执地将刑法立法公众参与看成是公众借助社交媒体进行立法意见表达的方式,甚至不加区分地认为刑法立法公众参与就是作为整体性民主立法的制度载体和实现过程,不可避免呈现“社会公众参与的非理性”“社会公众难以被代表”等特征,(李翔:《论刑事立法公众参与的限度》,《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62—67页。)从根本上忽略了刑法立法公众参与本身的复杂性、广泛性和层次性。如前所述,存量研究又习惯将刑法立法公众参与作为现象研究的起点论述其背后价值、困境和路径等问题,而很少将其作为现象研究的对象给予应有的理论关注,更遑论围绕刑法立法公众参与过程进行细致化展开,以致于刑法立法公众参与如何发生的原点问题长期被忽视,或者被当作是已知问题而认知。事实上,刑法立法公众参与不是整体性概念认知,而是呈现阶段性和层次性交织,如果不对这种阶段性和层次性进行精准把握,不但无法理解刑法立法公众参与如何发生的真实逻辑,甚至还会因为这种主观认知上的谬误而带偏刑法立法实践,进而背离现代刑法立法之民主真谛。
众所周知,哈贝马斯亦曾将立法中的商谈清晰地分为两个阶段:非建制化阶段公共领域中的商谈和建制化阶段立法机构中的商谈。其中,前者以“日常语言”为交往手段,以“相互理解和允诺”为交往目的,以“开放、互动”为交往品格,商谈主体间不仅地位平等,而且整个立法过程的讨论呈现非建制性特征,立法商谈结果也不是决策意义上的定论,正所谓:“对于议题或提议的同意,只能作为或多或少穷尽争论——在这种争论中,建议、信息和理论或多或少被处理的”([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6页。)。后者则发生在正式立法程序中,往往有严格的商谈程序与规则,立法商谈的时间和空间被提前确定好,商谈主体拥有明显的专业化和精英化倾向,一般经过严格的选举和任命程序,例如,作为立法商谈主体的全国人大代表或者常委会委员。代之以笼统的立法公众参与讨论,非建制化和建制化阶段的类型化划分更便于我们细致观察并理解立法公众参与何以发生的问题。受此启发,本文拟将我国刑法立法公众参与的讨论也技术性地划分为非建制化和建制化阶段,具体以刑法草案进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程序为界分点,在刑法立法草案进入最高立法机关立法程序之前的公众参与为非建制化阶段的刑法立法公众参与;在刑法立法草案进入最高立法机关立法程序之后的公众参与为建制化阶段的刑法立法公众参与,只有对不同阶段刑法立法公众参与呈现的特征、规律、问题进行细致性的讨论,围绕刑法立法公众参与的路径完善建议才会更有针对性和建设性。E0AE9804-87AA-435E-9602-66FD7DB6AD1B
二 非建制化阶段的刑法立法公众参与
公共领域是非建制化阶段刑法立法公众参与的重要场域,我们考察非建制化阶段刑法立法公众参与的实践样态,关键就是要探讨置于公共领域中的公众是怎样参与刑法立法,特别是通过什么方式影响最高立法机关的刑法立法?
(一)典型原因:社会热点事件驱动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越来越多公众不再像古希腊城邦公民那样痴迷于轰轰烈烈的“广场政治”,也不再执拗于宏大又抽象的启蒙政治话语的想象与建构,相反,他们更关注发生在身边的社会热点事件,这越来越成为当代公众参与国家立法治理的一种“实惠”而又简便的方式。无论是影响性社会事件还是恶劣的刑事案件,正日益成为推动公众参与刑法立法最直接动因。社会热点事件给生活在其中的公众以道德感官上最直接的触动,以朴素情感上最强烈的共振,公众基于朴素的正义感和道德观念激发他们更深层次了解事件是非曲直的欲望,如果发现事件同刑法立法密切相关,特别是相关社会热点事件是由刑法立法的缺陷引起的,人们逐渐就会由对事件本身的关注转为对刑法立法的积极讨论,所有关于刑法立法利弊得失情况都将被再次审视甚至被放大,围绕刑法修法的民意就会甚嚣尘上,而立法机关不得不回应这些民意,有评论将此称为“被民意裹挟的立法”,个案披露舆论哗然震动高层立法动议立法通过日益成为非建制化阶段公众参与刑法立法的典型特征。联系近年来的刑法立法,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引发公众关于是否提高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罪刑罚之争;山东辱母案推动人们对刑法立法中正当防卫规定的反思;幼儿园虐童事件引发人们关于虐童刑法规定的反思;(例如,我国有学者曾就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件提出如下刑法立法的修正建议:1.在刑法第236条强奸罪的第三款增加一项作为第六项: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六)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奸淫被监护、看护的幼女的。2.修改第237条第三款“猥亵儿童罪”为:猥亵儿童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猥亵儿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一)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二)猥亵儿童多人的;(三)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的;(四)附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猥亵被监护、看护的儿童的;(五)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校车安全事故的接二连三发生,使人们关注甚至放大校车超载、超速行为危害,由此推动特定运输车辆超载超速行为入刑;养老院护工虐待老人事件频发推动刑法修改关于虐待被看护人员的规定;针对因医患纠纷引发“医闹”“伤医”等热点事件,《刑法修正案(九)》将破坏医疗秩序行为纳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规制范围,正式在立法中明确了“医闹入刑”;针对“打虎灭蝇”的反贪腐社会热点问题,不仅增加了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剑指那些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迂回包抄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其他有特定关系的人,或向已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或其他有特定关系的人行贿,同时,还增设了专门针对贪贿犯罪的终身监禁刑;针对轰动一时的成都“孙伟铭案”“杭州飙车案”等事件,公众更是积极发声推动刑法对危险驾驶罪的修改,“醉驾”和“飙车竞逐行为”相继入刑;针对三鹿奶粉、地沟油等一系列触目惊心食品安全事件,公众强烈呼吁并要求在刑法中增设单独的食品监管渎职罪,以发挥刑法对负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威慑;针对山西黑煤窑强迫农民工从事危重劳动事件,公众对强迫劳动罪的刑法流弊猛烈开火,之后最高立法机关修改“强迫劳动罪”,将“用人单位”修订为“一般主体”,从而将个体老板等也纳入刑法规制范围。(我国有学者专门统计了引致立法议程改变的公共事件、相关法律制度规范及其立法议程改变距离媒体曝光时间的关系的案例数据,其中在刑法领域,由公共事件引发的立法需求通常与公众对一些社会现象体现出的价值冲突密切相连。张欣:《大众媒体、公共事件和立法供给研究——以2003—2013年公共事件为例》,《法学评论》2016年第5期,第128—132页。)社会热点事件使公众快速意识到危险就在自己身边,借助刑法预防、控制甚至消灭危险成为公众面对危险的应激式反应。事实上,社会热点事件一出现,公众在公共领域围绕刑法立法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讨论就会随即展开,社会热点事件是非建制化阶段刑法立法公众参与的典型原因。
(二)时间节点:立法机关的会期
立法机关会期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刑法立法的时间,在此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或常委会委员要结合刑法立法草案进行集中或者是分组审议,以决定刑法立法是否通过或者需要进一步修改。立法机关会期是刑法立法草案能否去“草案”之名称而成为正式法律的关键时间节点,社会公众普遍关注,日益成为刑法立法公众参与的重要时间节点。必须承认,在民主立法备受瞩目的当代中国,立法机关倾听公众对刑法立法的意见建议尤为重要,我们说立法机关不必服从公众舆论,但绝不是说立法可以回避民意,否则,刑法立法就会丧失正当性,甚至引发刑法公众认同危机。置身于公共领域的公众深知自身难以直接进入立法机关进行直接立法,立法机关会期成为他们影响刑法立法的最佳时间窗口,事实上,他们也非常愿意并实际利用这一重要时间窗口,如前所述,经过社会热点事件催化而来的公众意见固然能引起立法者的注意,但这种发声如果不恰好发生在立法机关会期,久而久之就会被新的热点事件冲淡,相反公众在立法机关会期围绕社会热点事件广泛讨论并积极立法建言,实际上是试图以“人民”主权者身份对国家立法事务再嵌入,势必会引发立法机关的重视,极大提升相关意见建议被采纳的概率。正因为如此,在立法机关会期,非建制化阶段的刑法立法公众参与往往会迎来高潮,广泛而热烈的民意从仅是公共领域自由意见表达向政治领域立法商谈演进甚至被立法机关接受。笔者注意到,每当立法机关会期,针对新近出现或影响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的刑法立法讨论总会“如期”而至,例如,2015年6月,一则《人贩子一律处死》的朋友圈刷屏就恰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刑法修正案(九)》的前夕和期间,企图影响最高立法机关对拐卖儿童罪的决策,(同样是在立法机关会期,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针对近年来“精日”分子频频做出诸如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拍摄有侮辱性语言和低俗语句视频并上传网络这类亵渎民族情感的行为,有政协委员就提案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刑法修正案》,将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格、侵犯中华民族尊严等行为纳入刑法的范畴。参见贺云翱:《开玩笑和侮辱行为有本质区别》,《北京青年報》2018年3月10日,第A08版。再如,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公众围绕“醉驾造成每年30万人入刑”话题讨论是否需要修改或废止醉驾入刑条款。潘高峰:《“醉驾入刑”该取消吗?》,《新民晚报》2021年3月11日,第09版。)而一旦立法机关对公众提出刑法立法的建议采纳的话,媒体就通常冠以立法博弈中“平民的胜利”为题广泛报道,从而营造公众参与对刑法立法的巨大影响力,事实上,这反过来也会激发公众投身刑法立法的积极性,进而提升非建制化阶段刑法立法公众参与的效果。E0AE9804-87AA-435E-9602-66FD7DB6AD1B
(三)参与场域:互联网渐成主阵地
虽然非建制化阶段公众参与刑法立法的方式多种多样,它可以表现为公众参加由最高立法机关组织的刑法立法座谈会、专家咨询论证会、内部征求意见等,但更多时候公众还是通过互联网参与到对刑法立法问题的讨论中,例如,公众通过互联网了解刑法修正背后的背景、动议、争议、进程和知识等海量信息;通过互联网传播并讨论现有刑法立法缺陷;公开提出对拟立刑法条文的意见建议;回应他人所提出来的对刑法立法赞同或批评意见,等等。此外,互联网还助益刑法立法公众参与呈现更多“场景”,赋能更高“效率”,例如,公众借助网络对他人所提刑法立法意见口诛笔伐或心悦诚服;发布并传播关于某类法益侵害行为域外刑法规定及其借鉴可能性;就刑法立法程序优化提出意见;监督最高立法机关更好地回应公众的刑法立法关切;最高立法机关亦可通过互联网集中或者针对性地回应公众所提刑法立法的意见,等等。互联网日益成为非建制化阶段刑法立法公众参与的主阵地,同互联网在信息聚合和传播上得天独厚的优势密切相关,无论是谁提出来的刑法立法意见和建议,只要是上网传播的,公众就能以最快的速度获取相关情况;不仅如此,互联网还能将与议题相关的全部类似和背景信息进行系统集成并帮助普通公众更好的智能识别搜索,使不同信息之间相互印证,不断提升公众获取信息的质量,在此基础上公众通过网络就刑法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深入互动,了解他人为什么要刑法立法,相关刑法立法建议又重点关注了哪些方面?能够解决什么样社会问题?自己又是如何看待他人的刑法立法建议?互联网帮助这些意见实现即时呈现和互动,降低信息成本,提升沟通效率,促进主体间“重叠共识”最大限度达成。与此同时,最高立法机关也能在互联网上第一时间了解公众围绕刑法立法议题的相关讨论,从中发现并识别最具稳定性和代表性的社情民意,待条件成熟的时候,将其吸收并反映在刑法立法文本中。如果最高立法机关不关注互联网上公众的声音而主观想象式的任性立法,显然,人们就应该责备最高立法机关这种极端的任性。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年来,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坚持在各项立法活动中全面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将线下和线上民主有机统一起来,积极关注并听取互联网上的社情民意,切实走好新时代网络群众路线,在刑法立法公众参与中,努力做到过程民主和成果相统一,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
(四)持续动力:道德判断的策应
非建制化阶段刑法立法公众参与是公共领域的非正式性立法商谈,最高立法机关没有必须听取公众围绕刑法立法建议的强制性义务,公众也没有正式的程序抑或法定制度来保障这种参与行为的持续性,特别是当最高立法机关实际上对公众参与持消极无所谓态度,甚至对公众所提的刑法立法建议动辄反对的时候,非建制化阶段立法公众参与就不可避免出现集体“沉默”,造成立法的噤蝉效应。这个时候,来自道德判断的策应就变得异常重要,它成为支撑非建制化阶段刑法立法公众参与的持续性动力。所谓道德判断的策应,是指当公众对刑法立法所提意见建议面临来自最高立法机关和公众内部多重质疑情况下,围绕刑法立法是否正当的道德判断就成为支撑公众捍卫自身意见的强大精神动力。在刑事立法语境中,每当新的社会失范现象出现,出于朴素的正义观和所处风险社会的焦虑感,公众为了避免这种失范风险降临在自己身上转而对风险予以煽动式的集体讨伐,而讨伐的方式之一就是寄希望于通过刑法对这类风险予以严厉规制,只是,一旦这种通过刑法控制风险的讨伐型参与被最高立法机关“告知”背离了刑法谦抑性或者其他理由而不被采纳或者接受时,即便最高立法机关告知的违反理由实际上并不存在,公众也容易对自己的主张产生怀疑甚至是出现自我否定的情绪,进而在刑法立法公众参与上“偃旗息鼓”,除非公众充分认识并坚信自己围绕某一社会现象进行刑法立法背后道德命题的正当性和必然性,一旦公众获得了这种暗示,即刑法立法正当,即便面临最高立法机关或其他方面的阻力,也会重新燃起他们推动刑法立法的热情和信心,成为推动非建制化阶段刑法立法公众参与持续繁荣的不竭动力,更是非建制化阶段刑法立法公众参与的重要规律。当然,笔者也注意到,道德判断策应成为推动刑法立法公众参与持续动力的背后还在于法律和道德的相融性,正如习近平强调:“要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中,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靠制度支撑。法律法规要树立鲜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立法、执法、司法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习近平:《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1日,第01版。)。
(五)关键角色:媒体的推波助澜
媒体被誉为现代民主政治国家中的第四权力,深度参与包括国家立法在内的各项治理事务,尤其是在非建制化阶段的刑法立法公众参与中,媒体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正如前文所述,非建制化阶段刑法立法公众参与勃兴于公共协商领域,是一种缺乏正式权力资源支撑的公众参与形式,虽有利于公众自主地表达对刑法立法的各种意见和建议,但也极易因公众自身力量不足而导致参与不连续、不有效,例如作为个体的公众力量弱小,围绕刑法的发声最高立法机关可能“听不见”,又如公众意见不统一,无序化的嘈杂发声最高立法机关可能“听不准”。不过媒体的出现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充当公众和最高立法机关围绕刑法立法的“传话筒”增强公众表意能力,帮助立法机关更好地识别民意。一方面,为公众发出刑法立法意见和建议提供渠道。代议制危机使人们认识到仅依赖公众代表代替自己围绕刑法发表意见和建议的局限,无法保证公众代表准确了解了公众的意见,更无法保证了解了公众意见的代表们能将公众意见写进法律。于是,通过媒体传递自己的刑法立法意见就成为可能的策略,而媒体为获取公众支持也愿意倾听并传播这些声音,例如,它经常有策略地用夸张方式将行为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对立情绪传播出去,让公众同情被害人,舆论氛围的整体性力量就会给最高立法机关带来压力,使他们不得不认真倾听公众提出来的刑法立法建议,否则就可能被扣上立法不民主的帽子,而这是最高立法机关无论如何也不愿承担的政治责任;另一方面,最高立法机关借助媒体及时地将最新刑法立法信息公布出来,或者通过传媒将公众对刑法立法的意见进行集中反馈,从而为掀起新一轮刑法立法公众商谈创造条件,此外,一系列由媒体曝光的公共事件客观上对刑法立法变迁也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毋庸讳言,传媒的推波助澜有力地推动了非建制化阶段刑法立法公众的可持续性参与,包括刑事被害人在内公众立法声音被及时反映到最高立法机关面前,正因为如此,卡拉布雷西曾将媒体角色视为推动立法的四个条件之一,提出媒體不仅主动设置议题建构公众的认知,而且还能充当商谈渠道和公共平台,从而聚合公众认知,促成“一致行动”,影响对立法资源的分配和部署。(卡拉步雷西认为公共事件成为立法推动力的四个条件:(1)使立法迟钝性的成本骤然过高从而克服了政府的迟钝性和含糊;(2)激发了公民的立法要求;(3)媒体强调危机,加强了前两个作用;(4)一系列长期现身于此的改革者能够利用这些危机。[美]盖多·卡拉布雷西:《制定法时代的普通法》,周林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0页。)E0AE9804-87AA-435E-9602-66FD7DB6AD1B
例如,《南方周末》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问题报道—立法反思—学者观点”的媒体议程设置模式,不仅关注社会突发事件的追踪报道,还注重对社会突发事件背后规律性问题的主动挖掘,对其中可能存在的刑法立法问题进行理性反思,吸引了包括公众、知识分子和最高立法机关在内各方面主体的积极参与,提升非建制化阶段刑法立法公众参与的效能。公共政策学家托马斯·R·戴伊曾指出:“决定哪些问题将成为政策问题甚至比决定哪些将成为解决方案还要重要”([美]托马斯·R·戴伊:《理解公共政策》,彭勃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32页。)。而充当现代社会舆论聚合器的媒体恰好能胜任这一角色,许多现象、问题和声音都在媒体上汇聚、表达、传播和交锋,它事实上能够决定哪些问题成为政策问题,公众借助媒体发表对刑法立法的意见和建议,成为刑法立法民主化的积极促因,再加上媒体、公众和最高立法机关的良性互动很容易产生“政策之窗”的效应。
三 建制化阶段的刑法立法公众参与
建制化阶段的刑法立法公众参与是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正式立法程序下的公众参与。一般而言,刑法立法首先是由最高立法机关根据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组织或者委托相关方面起草刑法立法(修正)草案,也可以由全国人大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直接组织起草,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召开由有关部门、团体、专家学者、全国人大代表以及社会有关方面等参加的座谈会并进行刑法立法讨论和论证,广泛听取各有关方面对刑法草案的意见建议。在完成上述刑法立法起草前期准备工作后,经全国人大主席团或者常委会决定公布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个月,公众将对刑法草案的意见建议反映给有关部门,然后最高立法机关再根据这些意见建议对刑法草案进一步完善, 反复讨论,形成刑法草案表决稿并提交给最高立法机关审议通过。为了更好地理解建制化阶段的刑法立法公众参与如何发生,结合我国刑法立法的实际情况,笔者拟将建制化阶段的刑法立法公众参与区分为刑法立法草案提出阶段的公众参与、刑法立法草案审议阶段的公众参与和刑法立法草案表决通过阶段的公众参与。
(一)刑法立法草案提出阶段
所谓刑法立法草案提出阶段是最高立法机关围绕刑法文本内容如何起草,以及起草什么的正式立法程序,它直接影响之后进入立法审议程序的刑法的基本样貌,因此,它属于建制化阶段的刑法立法。刑法立法草案提出阶段的公众参与是非建制化阶段公众刑法立法商谈的继续,公共领域商談结果开启了政治领域立法商谈的阀门,使得正式的刑法立法议题最终确定下来,随后,最高立法机关就会自行或委托相应机构就刑法草案内容展开起草工作。一般而言,刑法立法草案提出阶段的公众参与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相关部门会就刑法立法草案的起草召开立法座谈会、听证会、咨询会、发放调查问卷、开通热线电话和实地调研等方式听取公众意见以及书面或网上征求公众意见等方式来了解公众对刑法立法的意见和建议。例如,我国《刑法修正案(九)》起草过程中就通过各种座谈会、专家论证会听取相关单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普通公众的立法意见和建议,而且还史无前例地组织召开刑法立法草案的立法评估会,2015年8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邀请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专家学者、律师和公检法部门基层执法人员,对《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主要制度规范的可行性、修正案出台时机、实施的社会效果和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立法评估。(赵秉志、袁彬:《中国刑法立法改革的新思维 以〈刑法修正案(九)〉为中心》,《法学》2015年第10期,第18页。)在刑法立法草案起草阶段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已成为我国刑法立法起草过程中的一种常规性做法,它最大程度地在立法前端口保障了刑法立法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使得相关争议问题在刑法立法起草阶段就能充分呈现并得到国家立法机关重视,以及时修改完善刑法草案的相关内容。其次,公众主动通过各种途径向有关部门呈送围绕刑法草案起草的意见和建议,尤其是在刑法草案起草工作组深入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单位进行专门刑法草案起草内容的调研活动时,公众积极向工作组围绕刑法立法相关内容建言献策,例如,在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起草过程中,公众围绕刑法草案修正中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非公有制经济平等保护,修改证券犯罪、洗钱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等具体罪名内容规定,增设袭警罪等方面广泛讨论并提出了意见建议。实践中公众不仅“被动”地响应最高立法机关就刑法草案起草的意见和建议征集,还主动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方式就刑法草案内容提出相应完善意见和建议,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刑法立法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国在刑法立法起草阶段注重刑法草案起草工作的公众参与,但这种公众参与仍然存在不均衡的情况,例如,在废除、修改或者解释刑法立法的时候,公众对相关刑法废改释文本内容和过程的参与还明显不够,特别是在最高立法机关进行刑法解释和立法评估的时候,公众部分参与、配合参与和形式参与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王群:《论司法解释制定中的公众参与》,《江淮论坛》2018年第5期,第112页。)未来,我国在刑法立法草案提出阶段的公众参与场域还需拓展、参与形式还需丰富,参与内容还需完善,以不断提升刑法立法“前端口”的公众参与质效。
(二)刑法立法草案审议阶段
所谓刑法立法草案审议阶段是指刑法立法草案进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审议程序的期间。根据《立法法》相关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草案的审议一般要历经三审程序才交付表决,当然,对于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或调整事项较为单一的部分修改的刑法草案也可以经两次甚至一次审议就可以交付表决。目前,刑法立法草案审议阶段的公众参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人大网站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个人信息的依法有效披露。众所周知,在对刑法立法草案审议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们的意见、态度和认知对刑法立法有重要影响,而对委员们个人信息的依法披露能够帮助公众了解委员们相关情况。目前,中国人大网站上对委员们信息公开的情况主要包括姓名、民族、党派、学历、职务和专业等基本信息,鉴于他们的民意代表身份,未来可否探索公开更多诸如工作邮箱等联系信息值得期待。其次,中国人大网站专门开辟人大常委会栏目对历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进行专题报道,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刑法立法草案过程中委员们的发言意见也部分地公之于众,甚至还有对委员们的部分访谈节目的公开,这种关于刑法立法审议过程的信息公开值得肯定,它有助于公众及时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其委员们对刑法立法审议的进度情况,掌握相关信息,在此基础上推动公众更加有序有效地参与到刑法立法中。再次,全国人大在对刑法草案第一次审议后,会在中国人大网站或者其他主流媒体渠道向社会公众公布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公开接收意见的电话号码、电子信箱和来信地址,中国人大官方网站还在“立法工作”栏设立专门的“法律草案征求意见”板块,公众只要填写自己所在省份、职业、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在线对正在征求公众意见的法律草案征求意见稿留言,发表自己对法案的看法和建议。例如,最高立法机关就《刑法修正案(九)》曾两次向社会公开刑法立法草案的审议情况并征求公众意见,第一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共有社会公众15 096人提出了51 362条意见;(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参阅资料(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次审议稿)参阅资料》。)第二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共有76 239位网民通过网络提出了110 737条意见,参与人数和所提意见数量都是创历次刑法修正之最高,(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参阅资料(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三次审议稿)参阅资料》。 )基本上做到了最大限度的立法民主,集中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最后,刑法立法审议阶段公众参与形式也非常广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仅设立了供全国人大代表和普通公众参加刑法立法审议的旁听席位,还通过现有全国人大常委会22个基层立法联系点直线联通社情民意,听取公众对刑法立法的意见建议,同时还视情况举办各种规格的刑法立法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以及通过网络、报纸等方式面向公众广泛征求刑法立法意见,其中,刑法立法座谈会是针对刑法立法的有关内容,尤其是刑法立法中的重点、焦点、难点和争议问题邀请各方面公众代表进行座谈交流,采取最直接方式现场了解刑法审议过程中公众立法心声;刑法立法听证会是针对刑法立法中的关键性内容,在相关部门的主持下,由代表不同立法主张的双方或多方参加,对刑法立法草案关键性内容设置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可行性等进行辩论,使得刑法立法中的相关争议点再次被聚焦并逐个澄清,主持听证会的有权部门根据辩论情况和结果,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在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或者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这既增加了刑法立法的透明度,来自不同利益相关方对刑法草案的意见全方位地呈现在立法机关面前,也使立法机关有一个正式场合了解公众对拟刑法立法条文支持或者反对的态度及其理由,促进刑法立法中公众意见的表达、博弈、竞争和承认,助益刑法立法在公众意见“视域融合”中建构“重叠共识”。E0AE9804-87AA-435E-9602-66FD7DB6AD1B
(三)刑法立法草案表决、公布阶段
所谓刑法立法草案表决、公布阶段是指刑法立法草案审议完成以后,草案即将交付或交付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表决通过的立法程序,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刑法草案经国家主席签字正式公布实施,这一阶段也被认为是刑法立法的最后完成阶段。由于刑法立法草案表决是全国人大代表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特定时空内依法履行立法职能的职权行为,普通公众很难深入参与刑法草案表决的全部过程和全部环节,实践中主要还是最高立法机关邀请包括专家学者在内的普通公众列席旁听刑法草案的表决会议,以起到对刑法立法草案表决程序的公众监督之效用。当然,根据《立法法》规定,对拟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的法律案进行立法评估时,公众还可围绕主要制度规范的可行性、法律出台时机、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和可能出现的问题等发表意见。在刑法公布阶段,公众可通过参加最高立法机关举办的公众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方式,发表自己对已公布并生效实施刑法的意见和建议,例如,公众对刑法立法生效实施时间提出意见建议;公众对刑法公布如何同接下来刑法普法宣讲和研究衔接贯通提出意见建议,尽量减少刑法公布和刑法普法和研究的“空窗期”,促进两者的无缝有机深度衔接;再如,对已公布刑法规定中的罪名如何表述和称谓提出意见建议,等等。实践中,不论人们是否承认,刑法立法草案表决、公布阶段,目前无论是在公众参与的数量还是质量上仍显不够,这值得我们认真反思。某种意义上,刑法立法草案表决、公布阶段的公众参与是刑法生效实施前的最后阶段,公众参与过程本身也是对新生效实施或修正刑法的熟悉和普法的过程,它有利于刑法立法和公众民意全方位的互动和熟悉,推动刑法在法律实施阶段更好地获得公众普遍拥护和真诚认同。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包括刑法在内国家立法的公众参与,在理念上提出“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施政方略;在实践中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立法公众参与动员和实践,从建國伊始“五四宪法”制定过程的人民动员再到历次刑法修正中的公众参与,公众参与始终是我国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依法立法的鲜明标识。理解刑法立法公众参与,首先要理解刑法立法公众参与如何发生,准确把握刑法立法公众参与在建制化和非建制化不同阶段呈现的特点、规律及其问题,才能为公众更加有序、有效地参与刑法立法提供针对性的理论支持,进而提高我国刑法立法质量和水平。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Legislation of Criminal Law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ized and Non-institutionalized Stages
WANG Qun
Abstract: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legislation of Chinas criminal law should be classified into institutionalized stage and non-institutionalized stage.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legislation of non-institutionalized stage refers to the overall appearanc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such as social hot events, the meeting period of the legislature, the Internet, moral judgment and media support, while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legisla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ized stage means the careful discussion in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proposal of criminal law legislation draft, the deliberation of criminal law legislation draft and the voting and publication of criminal law legislation draft. At the stage of proposing the legislation draft of criminal law, relevant departments listen to the publics opinions through legislative symposiums, hearings, consultation meetings, questionnaire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the public can also put forward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draft of criminal law through grass-roots legislative contact points. At the stage of deliberation on the legislation draft of criminal law, the supreme legislature promptly releases information on the deliberation process of the criminal law, makes public the draft of criminal law and its explanation to the public, and listens to the publics opinions. An the stage of voting and promulgation of the legislation draft of criminal law, the public can attend and sit in on the voting meeting of the draft of criminal law, participate in the symposium, demonstration meeting, hearing, or express their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promulg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riminal law through grass-roots legislative contact points.
Keywords: legislation of criminal law; public participation; institutionalized stage; non-institutionalized stage
【责任编辑:龚桂明 陈西玲】
收稿日期:2021-12-30E0AE9804-87AA-435E-9602-66FD7DB6AD1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