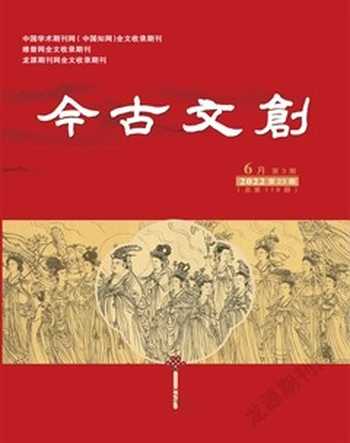景观叙事:重构《红字》中的“荒野”形象
【摘要】 纳撒尼尔·霍桑的作品《红字》中所描绘的“森林荒野”往往被解读为故事的背景或道德真空的象征。然而,本文借助文学地理学的批评方法,从景观叙事的角度探讨荒野被创造的现实基础及其在作品中的呈现,得出霍桑笔下的荒野是一种由社会建构的景观。荒野同清教思想和超验主义自然观影响下的环境伦理相交织,并与“如画”的审美意趣和民族性构建相关联。如画的荒野不仅挑战了清教徒对荒野的偏见,更将荒野审美上升到道德层面,这一观念的更迭也反映了19世纪美国社会的变革。
【关键词】 景观;荒野;如画;文学地理学;纳撒尼尔·霍桑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23-0019-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3.006
《红字》(The Scarlet Letter)是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一部杰出作品,在1850年出版后便受到广泛关注。《红字》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7世纪新英格兰马萨诸塞州,主要讲述了主人公海丝特·白兰(Hester Prynne)和丁梅斯代尔(Dimmesdale)产生私情后受到清教社会处罚的故事。海斯特佩戴代表通奸罪的红字“A”于胸前,用善行进行赎罪,而丁梅斯代尔多年隐藏罪行而内心受到摧残,在奄奄一息之时才将真相大白于世。
学界对《红字》的研究蔚为大观,多围绕自然、道德和人性善恶的主题,从原型批评、象征主义、女性主义等视角进行分析。近年来,有学者从空间叙事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霍桑使用隐喻和象征等手段,“以空间场景为结构,以空间场景的转换为时间的表征”[1]46,由此空间被赋予了并置时空的能力。然而,少有学者对《红字》的空间叙事内容进行深入探究,尤其是“森林荒野”的形象。诸多研究只考虑到它作为故事背景或象征的作用,却没有在更为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探讨。而近年来兴起的文学地理学,源自空间批评并吸收文化地理学等理论成果,关注文学想象建构得更加典型化的空间关系,认为文学中的景观和地域是折射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的象征系统[2]114。颜红菲指出,地理景观本身就存在于一个与文化活动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因此能够“成为折射、成为隐喻、成为蕴涵人类情感与价值观念的象征体”[2]114。以景观为考察对象,关注景观作为价值和意义的象征载体所传达的意义,本文称之为景观叙事,并以此作为研究《红字》的切入点。作为一个重要的跨学科的构建,景观“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实体,而是一块画布,文化在其上描绘他们的世界,他们的欲望,他们的文化和政治信仰”[3]5。在对景观的绘画般创作过程中,审美活动的构建不可忽视。
有学者认为,《红字》使霍桑对荒野主题的探索达到了高潮[4]40。“荒野”是美国环境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地理存在,也是精神领域。环境历史学家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Roderick Frazier Nash)通過追踪“荒野”一词的词源,提出该概念既可以是“不存在人类的、野兽的栖息地”,也可以解读为 “一个人很可能进入的混乱或‘荒野状态的区域。”[5]2《红字》中,霍桑对波士顿海边的原始森林进行了清晰地描绘,该景观位于“小镇的郊区、半岛的边缘,远离其他居住所” [6]143,脱离了社会活动的范围,是一片远离文明的荒野。而建构在荒野之上的社会意识,是霍桑将17世纪清教徒的波士顿和18、19世纪的美国转型社会进行空间并置的结果。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来看,荒野不仅是景观存在的场所,还涉及了审美活动和环境意识的构建。《红字》中的荒野形象体现出清教主义、“如画”理念和超验主义思想的碰撞交融,同时也表达出霍桑对当代美国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的审视。
一、集体记忆中的荒野
霍桑作为马萨诸塞湾殖民者的直系后裔,从17世纪和18世纪清教统治下的新英格兰中汲取创作灵感。尽管霍桑是一个忠实的基督徒,但他并没有完全认同祖先的加尔文主义信仰[7]38。他谈及清教徒时写道,“ [ 他 ] 具有所有清教徒的特征,包括善与恶”[6]9,可见霍桑对清教的态度是较为矛盾的。
记忆是一个文本交织的互文领域,它为个体所共享,以创造集体特性。因其常依附于场所中,所以整个景观能融入记忆的肌理之中[8]62。在清教徒的视角中,荒野是一个充满邪恶、未被文明开化的场所,会引诱人远离宗教信仰的纯洁性。这一印象可追溯至犹太-基督教传统对荒野的排斥,它使得17世纪第一批新英格兰定居者对荒野就存在先入之见,加之他们面临着自然环境的威胁,“每一个不受人类控制的生物都被宣布为野性的,带着猖獗、野蛮和危险的负面含义”[5]。《红字》中的波士顿清教徒认为宗教纯洁与不可恕的罪恶、清教社会与未开化的森林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当海丝特被判通奸罪时,镇上的人认为她和黑暗森林里的“黑男人”(the Black Man)有往来,是受到了黑男人的诱惑才犯了罪,而“黑男人”是在17世纪中流传的“魔鬼”的一个常见称呼。海丝特自己也相信黑暗、神秘的森林符合她天性中的狂野,而她的罪和耻辱是深深扎进土壤里的“根”。在对罗格·齐灵渥斯(Roger Chillingworth)的人物塑造中,霍桑常将其心灵的丑恶同森林意象相结合。除此之外,神秘幽微的森林也是隐藏秘密的场所,如当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的秘密谈话结束时,霍桑写道,“山谷独自留在黑暗的老树中,它们用无数个舌头低声谈论那里发生过的事情”[6]166。尽管霍桑在《红字》的前半部分对森林荒野的直接描写微乎其微,通过清教徒对荒野的集体记忆的抽取,依旧渲染出了邪恶和恐怖的气氛。
与清教徒对荒野的带有强烈偏见的想象不同,19世纪美国人对自然的态度处于一种“过渡状态”[5]66。随着城市的发展,严格的清教规范与人们对自我解放的追求并不一致。正如森林让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远离清教迫害,自然也成为人们摆脱现代社会的喧嚣和约束的临时庇护所,人们对荒野的刻板印象也逐渐动摇。《红字》中,海丝特在林中摘下压抑她天性的帽子时,她露出了久违的“灿烂而温柔的微笑”,自身的女性特质和青春气息全都从清教主义的监禁中恢复过来,这正是霍桑借荒野传达出的19世纪美国社会对自由的诉求。4560DEE8-F4B7-4D23-9B63-350281FD8FA0
二、如画的荒野
霍桑是大自然的爱好者,他喜爱在生活中亲近自然并从中获得独处的快乐和创作的灵感,加之受到如画美学理论和超验主义思想的影响,霍桑眼中的荒野具有更积极和神圣的形象。“如画”审美起源于17世纪的意大利和荷兰风景画创作,在18世纪的英国社会中迅速发展后于该世纪末期传入美国[9]142。作为一种审美标准的流行,其应用领域颇广,而其概念在各家争鸣中也并无定论,但从本质上看,“如画”是一种构建国人对本土风景的欣赏和审美自信的方式[10]73。“如画”审美在美国经历了本土化的吸收和改造后被赋予了道德维度,服务于国民品味的塑造和民族性的建设。罗斯金(John Ruskin)从道德和社会责任的角度解释“如画”概念,认为根据形式特征的正确与否可以将其分为“高贵的如画”(the noble picturesque)和为“低等的如画”(the lower picturesque)。高贵的如画审美是能够观察到景观所反映的人世苦难并进行共情,由此能够触碰到上帝赋予人类的最高贵的精神,即“质朴谦虚、不屈不挠的心灵对苦难、贫穷或衰败的高贵的忍耐。”[10]83 如画的美学理念表明,只有摒弃偏见和刻板印象才能欣赏到真实的风景。
作为一种观看和描绘自然风景的方式,如画美学对霍桑的创作风格有显著影响,他曾说“自己的创作必须完成得像荷兰画一样细密”,在作品中注重描写能够增添如画效果的元素,强调光线与色彩的运用,突出明与暗的对比[11]130。同时作为一种审美理想,如画的应用能够增加叙事的张力和景观诠释的复杂性。在《森林谈话》一章中,霍桑笔下的森林荒野是如画审美的完美载体:
“他们坐在一堆繁茂的苔藓上;在20世纪的某个时代,它曾是一棵巨大的松树,它的根和树干深入树荫深处,树冠高耸入云。他们坐在一个小山谷中,两边是铺满落叶的河岸,小溪从中间流过,越过一片倒下的、被淹没的树叶的河床。悬在上面的树木,不时地投下大树枝,阻住了水流,在一些地方形成了漩涡和深渊;而在水流湍急而又活泼的河道里,则出现了鹅卵石和闪闪发光的棕色沙子。 顺着溪流往前看,在林中不远的地方就能看到水面反射的光線,但不久就在盘根错底的树干和灌木丛中失去了踪迹,而且还有一块长满灰色地衣的巨石。”[6]146
这段描写的叙述视角在森林之中,视野虽有局限,却刻画的具体细致,给人以真实感。“盘根错底的树干”和“淹没成床的树叶”等意象突出其远离文明的特点,这片原始森林散发着不被文明控制的力量,激起人类的敬畏和恐惧。另一方面,河道里显现出“闪闪发光的棕色沙子”和曲折的光线,明暗的对照与丰富的层次感展现出森林灵动的一面。置身于山水之中,森林里黑暗与光明、粗糙与平滑的特质形成一种动态平衡感,而较小的空间距离似乎也拉近了心理距离,这些特质介乎“优美”(beautiful)和“崇高”(sublime)之间,初步给人以“如画”的审美体验。除了对森林的描绘,霍桑的“如画”审美也投射在海丝特身上,多次以“如画”来描述她的形象。例如,他称海斯特的服装“工艺繁杂(picturesque)”、她的性格“狂野而独特(wild and picturesque)”[6]44-46。当然,在这表面的、充满想象力的、低等的如画审美之上,霍桑也有对荒野存在本质的体悟,以此实现感官和心灵的共振。高贵的如画美蕴涵于霍桑关于自由和道德完善的哲学理想中,主要通过对海斯特道德生活的审视来体现。
三、道德完善的荒野
霍桑与超验主义的渊源颇深。面对不断工业化的社会和彻底变革的自然环境,19世纪上半叶出现的超验主义思想主张改革加尔文教,建立一个真正道德完善、民主自由的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超验主义者充分肯定人的作用和价值,提倡回归自然、净化心灵才能接近上帝[12]122。这些思想引起了霍桑的注意,他曾加入在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这个乌托邦式的小型社区,并结识了爱默生、钱宁、梭罗等先验主义者[13]。修立梅提到,爱默生、梭罗“赋予‘如画以道德、想象和心灵内涵,将其演变成一种形而上的如画(metaphysical picturesque)”[9]142,可见如画审美在美国社会的盛行和文人对艺术与道德结合的诉求。
深受加尔文主义教义影响的霍桑对超验主义的思想持批判态度。与坚持人性本善的先验主义者不同,霍桑认为每个人的灵魂中都有罪,但是罪恶并非如清教徒所说的不可拯救。他吸取了超验主义思想中的补偿论的观点,认为罪恶可以转化为善,使人走向成熟、获得教育[14]26。海丝特在接受清教法庭的判决后受到了社会的排斥,“牧师在街上停下来规劝她,引来一群人围在这个可怜的有罪的女人周围,他们时而露齿而笑,时而皱着眉头……如果她走进教堂……却常常不幸地发现自己成了布道的文本”[6]61。 而丁梅斯代尔在隐藏罪恶的道路上也饱受痛苦,憔悴不堪。在森林里呼吸着未被基督教化的、无法的荒野中的自由气息时,海斯特的天性得到了包容,丁梅斯代尔也如重生一般,似乎与上帝有了更紧密的联系。正如霍桑唱赞大自然的同情心——“森林里狂野的、异教徒的自然,从未被人类的法律所征服,也没有被更真的真理所照亮”[6]159。森林荒野并非是“道德的荒野”,而是存在不同于清教主义的道德观念,是精神真理最不被钝化的环境[5]66。
霍桑克服了传统的荒野道德真空假设,提倡人通过内省来发现自身的“超灵”神性,并用以来发现人与自然的真善美[12]123,而这一理想道路与如画审美提升道德的潜能无不相关。当海丝特的监禁期结束时,她选择住在半岛边缘的荒野作为惩罚,耻辱的折磨将“最终净化她的灵魂,恢复她失去的纯洁”。海丝特以慈善表示忏悔,牺牲自己的享受去为穷人做衣服,最终成功地改变了人们对她的态度,把猩红的红字由“Adultery”(通奸)变为“Angel”(天使)。不仅弥补了她的错误,海丝特还获得了独立思考的自由,荒野把她的“激情和感觉”变成了“思想”。在海丝特住在海边茅屋七年后,她的智慧和心灵仿佛在荒野中安了家,而她能够在那里自由地漫游。独处的机会让她能以旁观者的视角审视清教社会建立的一切制度,深入思考女性和种族问题,“她几乎不比印第安人更尊敬地批评牧师的丝带、法官的黑袍、颈手枷、绞刑架、家庭或教会。”[6]156尽管这一行为在清教徒眼中是一种“比红字所代表的更致命的罪行”,但她在荒野中汲取了足够的勇气,透过表面看到人类社会中的不幸与苦难,由此获得了个人的成长。4560DEE8-F4B7-4D23-9B63-350281FD8FA0
然而,霍桑指出,羞耻、绝望和孤独都是她的老师,教会了她坚强,但也让她有所曲解。当海丝特试图摆脱罪责的枷锁同丁梅斯代尔逃离新英格兰、把胸前象征着“罪恶的幻影、心灵的沉沦”的红字扔掉时,她受到了阻挠。珠儿拒绝同二人相认,不愿穿过林中小溪加入他们,并强迫她母亲重新佩戴红字。潺潺小溪代表了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界限,摘掉红字的行为犹如忘记过去,而这是不被认可的,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也无法走向美好未来。霍桑有意强调海斯特必须在认识自身之恶的基础上进行内省,才能更新自我,开启新的生活,并由此凸显在真实生活中审视自我、他人乃至社会的如画体验。总之,《红字》中的荒野是宽容的、如画的。在荒野中,苦难的洗礼能够让海斯特进行心灵的升华,霍桑借此挑战了虔诚但有偏见的清教社会,有力地表达了自然界的神性及其在道德与精神生活中的意义。
四、 总结
荒野的概念极具可塑性。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霍桑,将清教徒对荒野的集体记忆同先验主义的自然观融合在一起,发展了道德与荒野共存的信念,把荒野塑造成一个自由、如画和神圣的领域。通过将《红字》中的荒野进行前景化处理,本文得出荒野具有如画美学的审美价值,荒野的幽静、野性呼应人性对宁静、自由的渴望,由自然之美上升到道德精神层面,为道德完善的哲学理想提供有力的支持。此外,霍桑塑造的荒野叙事,与美国的民主、独立和审美的理想建立了联系,是一次构建独特民族身份的有益尝试。霍桑在研究新英格兰历史的基础上,结合对自然的深刻认识,创造出一片属于美利坚民族的荒野,为美国文学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毛凌滢.多重空间的构建——論《红字》的空间叙事艺术[J].江西社会科学,2009,(05).
[2]颜红菲.开辟文学理论研究的新空间——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述评[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67(06).
[3]Yang, S. R., and K. Healey. Gothic Landscapes[M].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6.
[4]Matthew, and Guzman. Writing the Environment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Ecological Awareness of Early Scribes of Nature[M].Ed.Steven Petersheim and Madison Jones. Lanham: Lexington,2015.
[5]Nash, R. F., and F. Miller. 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M].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
[6]Nathanial Hawthorne. The Scarlet Letter (Oxford World's Classics)[M].Edited by Brian Hard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7]Boonyaprasop, Marina. Hawthorne's Wilderness: Nature and Puritanism in Hawthorne's “The Scarlet Letter” and “Young Goodman Brown”[M].Diplomica Verlag,2013.
[8]马修·波泰格,杰米·普灵顿.景观叙事:讲故事的设计实践[M].张楠,许悦萌,汤丽,李铌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9]修立梅.艺术与道德——《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如画”审美[J].外国文学研究,2021,43(02).
[10]萧莎.西方文论关键词 如画[J].外国文学,2019,(05).
[11]毛凌滢.多样的缪斯——摄影、如画美学与霍桑《七个尖角顶的宅第》的审美追求[J].国外文学,2021,(01).
[12]任宁.善恶并存 道德救赎——霍桑对爱默生超验主义的认同与反叛[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3(03).
[13]Corey, S. H..Eden on the Charles: The Making of Boston.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2011.37(3).
[14]廖杨洁.霍桑对超验主义的吸收,怀疑与超越[D].湘潭大学,2006.
作者简介:
何念念,女,汉族,安徽阜阳人,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英语专业本科在读。4560DEE8-F4B7-4D23-9B63-350281FD8F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