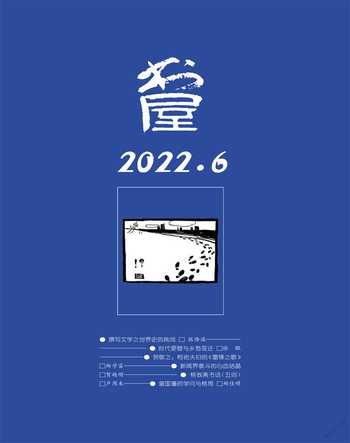“准贩东西洋”:晚明的海外贸易
齐悦
中华文明兼容并包,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唐、宋时期,我国对外高度开放,陆上交通、海上丝绸之路,使得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对外交流都十分频繁。元朝时期依旧遵循前朝旧制,对外政策一直较为宽松。
明朝开国伊始,沿袭宋、元方针,对外交流频繁,载满生丝、茶叶、香料、象牙、瓷器的中外商船穿梭于海洋之上,促进中外文化和物资交流,后因沿海倭寇泛滥、海面不靖等政治军事因素,开始实施“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封锁对外往来。永乐年间,朝廷将民间海船“悉改为平头船”,使其无法远航;禁止近海人民建造三桅以上大船下海与外国贸易,违者照谋逆罪处斩。海禁政策作为祖训载入《大明律》,被后世子孙长期遵循,也为近代中国的自闭与落后埋下伏笔。
明朝在实行海禁的同时建立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朝贡制度是在民间海外贸易往来受阻的情况下,由中央制定的官方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它满足了明朝对海外物品的需求,也便于受理海外藩国的贡赋缴纳之事。因此,明前期海洋管理政策是在政府强制实行的海禁之下,由官方主导开展实施朝贡制度,进行中外贸易往来。
1370年,明廷在广东广州、福建泉州、浙江宁波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诸国朝贡和贸易事务。1374年,由于倭寇问题严重,明朝停摆这三处市舶司。明成祖即位后,一改朱元璋保守的对外政策,1403年下令恢复了三市舶司。1408年,三市舶司分别建怀远驿、来远驿和安远驿,以更好地接待贡使,彰显大明朝国威。1408年,朝廷设交趾云屯市舶司。市舶司主管朝贡贸易,负责查验贡使身份、安排食宿及抽分征税等。与此同时,明成祖组织了大规模的遣使海外外交活動,特别是郑和七下西洋,开辟了经印度洋到达西亚和非洲东海岸的远航航线,广泛进行友好交往,朝贡贸易盛极一时。
明朝初年,朝贡制度和海禁相辅相成,成为明朝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政策。朝贡贸易成本极高且不合经济规律,明中期以后,朝贡制度逐渐衰落,而后继统治者仍严厉践行着海禁政策。嘉靖年间,英国的都铎王朝正极力推行拓海政策,中国的海禁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嘉靖皇帝曾下令“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
“海禁愈严,贼伙愈盛”,沿海奸商滑民因商道不通,无以为生,在严苛法律与巨大利益的共同刺激下,私人海外贸易被迫畸形发展,从过去的合法商业活动转向走私乃至武装走私,并出现了一些大的海上武装走私集团。沿海的农民、渔民“资衣食于海”,也因“海禁太严,渔樵不通”而生活艰难,迫于生计而投入倭寇的怀抱,形成了三分真倭,七分假倭的罕见历史景象,且假倭的骚扰规模和次数,远高于真倭。
嘉靖年间,最大的海贼头目王直、徐海,都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徽州商人。王直拥众数十万,先称“靖海王”,后称“徽王”,“南面称孤”,与大明王朝分庭抗礼。倭寇之乱,屡打不绝,王直之后,吴平继之,吴平死后,曾一本兴起,造成旷日持久的“倭寇之乱”。
世界的另一边正在发生着惊天动地的社会变革,新航路的开辟,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西方殖民者的东进,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对海防及海禁政策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倭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商业问题,连年倭患皆因私通贸易而起,“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血的教训表明,如果不想逼良为盗,只能调整海禁政策。他们认为开海不仅可以消弭倭患,稳定沿海社会,也可富国裕民,充裕国库和民众收入。此外,开海贸易与海外各国交流往来,洞悉海外习闻动静,知己知彼,有备无患。
嘉靖年间,福建巡抚谭纶就在闽地放宽海禁,允许百姓近海捕鱼、经商,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沿海人民私通倭寇。继任的巡抚涂泽民继承谭纶的海防思想,隆庆初年,他毅然上疏请求开放海禁,允许沿海商民与外国商人开展贸易。
隆庆皇帝登基之初,锐意改革,内阁辅臣高拱、赵贞吉、张居正皆治世之能臣,在内政外交上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而困扰明帝国数十年之久的“南倭北虏”问题必然成为政治改革的重点。高拱、张居正等内阁辅臣也意识到,沿海平倭战争源于贸易限制,无论是嘉靖年间的王直、徐海,还是曾一本、林凤,旷日持久的“倭寇之乱”令政府消耗了大量财力物力,四处围剿终究是治标不治本的应急之策,必须转变思想,调整对外政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维护地区和平。
隆庆皇帝听从高拱、张居正之建议,起草诏书宣布“除贩夷之律”,选择东南隅的福建月港作为中外贸易的窗口,厉行二百年之久的海禁政策终于被打破,为海上贸易活动开启绿灯。这次开海无论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还是对外贸易史上都极为重要,史称“隆庆开关”。
海澄月港位于漳州府城东南,地处沿海,“外通海潮,内接山涧”,“其地之形水萦之如月然”,故而得名月港,唐、宋以降即称“海滨一大聚落”。成、弘之际,月港已成为走私贸易的基地,“趁舶风转,宝货塞途,家家歌舞赛神,钟鼓管弦,连飚响答。十方巨贾,竞鹜争驰”,已有“小苏杭”之称。嘉靖年间葡萄牙人在福建海商的诱导下转移到月港,夏来冬去,往来贩易,月港成为福建走私贸易的重要据点。
明政府在月港开禁,准许私人出海贸易。福建政府以月港为治所设立海澄县,设立专门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的督饷馆,并对其征收关税。考虑到日本经常侵犯沿海,对日贸易仍在禁止之列,所有出海船只均不得前往日本。若私自前往,则处以“通倭”之罪。
开海政策虽仍有诸多限制,开放的月港也只是一处小港口,但民间私人海外贸易毕竟已获得朝廷的认可,只要遵守政府的管制,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就被视为合法经营。海外贸易政策的调整,突破了朝贡贸易的局限,带动了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从月港进出口的商品种类丰富,月港陆饷收税商品就多达上百种,有龟筒、西洋布、玻璃瓶等工艺品;胡椒、木香、丁香、苏木、檀香、奇楠香、象牙等奢侈品;也有冰片、阿魏、没药等药材;还有虎豹皮、獐皮、孔雀尾、红铜等原料。
每年春夏之季,十余万中国海商从月港扬帆起航,盛况空前,出洋商船“大者,广可三丈五六尺,长十余丈;小者,广二丈,长约七八丈”,“澄商引船百余只,货物亿万计”。当时主要的海外贸易基地是菲律宾,菲律宾首府马尼拉与月港的距离较近,更主要的是西班牙殖民者开辟了从马尼拉至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航线,把墨西哥银元载运至马尼拉,换取中国的手工业品。大量的福建商船载着中国商品从月港载运至马尼拉,然后由西班牙大帆船转运到拉美和欧洲各地,中国产品已成为拉美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时,月港贸易也促进了拉美地区的经济繁荣,作为大帆船贸易终点的阿卡普尔科随着大帆船的到来而逐渐繁荣。荷兰东印度公司将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从月港转贩到日本及东南亚各地。
明朝的丝织品、瓷器、茶叶、铁器等远销海外,广受世界各国欢迎,白银大量流入明朝。据估计,在此后的七十余年间,自葡萄牙、西班牙、日本等国输入明朝的银元,至少在一亿元以上,有力地促进了明朝国内商品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生改善和社会进步。在世界形成一个整体的历史进程中,月港使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接起来。
西方学者丹尼斯·弗莱恩和阿拉图罗·热拉尔德兹提出,世界贸易在1571年即明隆庆五年诞生。当世界逐渐形成一个整体之时,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也随之产生了。这个体系不是西方创造的,明代中国曾积极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为整体世界的出现作出了重要贡献。
诚然,从隆庆元年“准贩东西二洋”,到万历年间月港对外贸易长达半个世纪,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的月港体制。福建商民利用这个通道,大规模出海经商贸易,进而移居南洋、日本,不仅在华商中一枝独秀,而且成为南海贸易中强劲的海上势力。海禁的解除,海外贸易的开展,增加了明朝廷的收入,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然而,月港体制也有相当的局限,它只准福建商人出海贸易,不许外国商人入境通商,可见月港模式并不是完全彻底的开放,而只是一种局部开放,这无疑限制了外贸的受惠面,影响着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廣东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港口众多,素有对外贸易传统。与月港体制不同的是,广东不准私人出海贸易,只允许外商前来贸易。嘉靖年间,广州每年定期举办贸易会,允许葡萄牙人到广州城买卖物品。“隆庆开关”鼓舞了广东商人,地方政府虽明面禁止私人出海,可广东出海人数也逐年增加。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革,广东当局也逐渐调整对外贸易政策。万历六年,两广总督凌云翼提请在妥善处置海禁情况下,准许商人出海贸易。
这时的明王朝正值“江陵柄政”时期,内阁首辅张居正励精图治,攘内安外,基本平定了山贼海寇。张居正认为广东亦可仿效福建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国库收入,中央政府遂放宽对中国商人出洋贸易的限制。广东继福建之后,成为对外交流的又一个窗口,相对福建“有往无来”的单向开放,广东则采取“互通有无”的全面开放模式,不仅允许外商前来经商,而且也允许广东商人出境贸易。广东商人只要领取海道发放的证照,不夹带违禁货物,就能置货出洋做生意。
自此,从广东出海的中国商船络绎于东西二洋,甚至远去月港模式所禁止前往的日本,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东南沿海地区的私人海外贸易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
万历时人郭棐的《岭海名胜记》附有一张广州城与省河形势图:广阔的江面上船只争流,白鹅潭江面停泊着一艘五根桅杆的大船,海珠石江面停泊着一艘两根桅杆的大船,旁边标有“乌艚”字样,显然属于远洋海船。反映出晚明广州商舶贸易的繁荣景象。
万历八年,朝廷选择在省城广州举办春夏两季“交易会”,展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广州交易会规模空前,周期较长,进出口商品结构较为复杂。每次交易会展期长达二至四个月,春季在一月举办,主要展销销往马尼拉、印度和欧洲等地的商品,夏季在六月份举办,主要销售运往日本的商品。各国商人怀着对东方大国的心驰神往,趁着东南季风或东北季风起航来到中国,云集在广州这个华南重镇,在广交会上不仅可以买到高质量的好货,而且可以根据海外市场需求订制适销商货。
珠江三角洲西岸的澳门,北邻珠海,原为香山县南海中小岛,后因珠江西江三角洲成陆加快,澳门岛与香山县连接。古代澳门有疍民、渔民等水上居民,直至明中叶,澳门并未设置行政性基层组织或军事机构。十五世纪以来,欧洲人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海上探险和殖民扩张,东方大国自然是他们垂涎向往之地,欧洲霸主葡萄牙人首先登陆澳门,经过一番周折,于1553年获准在澳门租住。澳门成为唯一允许外国人居住贸易的港口,吸引大批中外商人前来互市。
广州以中国内陆为依托,为海外贸易提供大量商品,澳门则成为西方国家在东方最大的转折港和贸易基地,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广州-澳门二元中心的贸易体制。
外国商船进入广东沿海港口者日多,由广东起航前往东、西洋的商舶也络绎不绝于印度洋,广州、澳门贸易远及南洋、印度、欧洲和美洲,沉寂二百年之久的海外贸易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开始和世界接轨。葡萄牙人克里斯托旺·维埃拉在广州发信盛赞广东是中国最好的省区之一:这里拥有不计其数的稻米和其他食粮,全国的商品都汇集在这里进行交易,因为它毗邻大海,别国的商品也运到这里来贸易。这里的土地是世上最富饶的,世间的一切业绩都是在广东的地盘上创造出来的。
此时正值世界地理大发现,地球的另一边也在发生着惊天动地的变革,欧洲人征服美洲后,在墨西哥发现巨型银矿,日本本土也发现银矿,而中国本土银产量有限,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福建、广东的对外开放,使得中国的丝绸、茶叶等大量出口,中外贸易存在巨大顺差,世界三分之一的白银涌入中国。中国的市场上,充斥着来自西班牙的“本洋”、墨西哥的“鹰洋”和日本的“龙洋”。白银的流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东南沿海城市发展欣欣向荣,一批新型城镇兴起,为晚明经济改革提供了物质基础。
——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