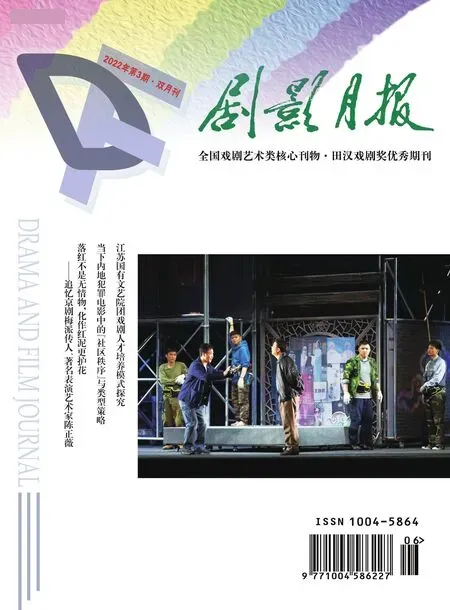戏曲表演中声音的运用与塑造
■钱栋涛
中国戏曲博大精深,是一门极其复杂的学问,正所谓唱腔做打、手眼身法步,而具体到剧中的每一个不同的角色,又涵盖了人物造型、外部形体、内心感受、内在感觉等方面。人们却总会以看戏来形容戏曲演出,台上演员们俊美的扮相、一招一式的功架、各种身段技巧,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相比这些,也有很大一部分观众喜欢“听戏”,听得是声,品的是味。在这一部分观众看来,好演员的声音就犹如一盏香茗、一杯老酒那般,勾人心魄、令人回味。换句话说,如果戏曲演员过不了观众“听”的这一关,那么他的戏就一定好不了。
想想也是,戏曲舞台上好多戏码,都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可想而知声音对于戏曲演员的重要性,没有好听的声音,就不会有好听挂味的道白和唱腔,而戏曲各个行当中的声音更是大相径庭、五花八门。声音是体现人物的最直接的方法与途径,有时同样一个行当,同样一个人物,他年龄的变化,以及所处不同的情境,都会导致声音的大不相同。
在当下的生活中,好多人喜欢听有声小说,一听就是几百集,我想除了小说的故事剧情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喜欢播音员们绘声绘色的语调与声音,他们可以一人分饰多个,甚至是几十个性别年龄完全不同的剧中人。作为戏曲演员的我,真是由衷地钦佩他们,播音员们可以在不借助任何视觉表演的情况下,单单只用自己的声音,就可以把整个事件,所有人物的性格身份等表达得惟妙惟肖,这是他们功力的体现。固然戏曲和影视、播音不属同类,但是我们对于声音的追求和塑造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更好地用自己原声来像剧中人物无线靠近、已达到“以假乱真”。戏曲演员无论是唱还是念,都是需要通过自己的声音来向观众准确的表达人物内心情感的。而根据人物类型,年龄,性格,以及所身处环境,事件的不同。这些声音是千变万化的,下面我就以自身饰演过的一些不同的角色来举例说明。来过无锡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无锡的泥人阿福和阿喜,这本是我们无锡的特有的可爱泥娃,是匠人们想象出来的作品,在锡剧舞台上也是找不到先例的。但在此一剧中,这两个泥人娃娃被赋予了生命。剧中主人公阿炳(华彦君)由于是母亲吴云卿与道士华清何的私生子,他一出生便被迫离开生母,被装进竹篮偷偷送往了生父的道观中,此时的阿福和阿喜是母亲放在竹篮之中的唯一信物,是个不会动的泥人。而当阿炳遇到困难和危险的时候,两个泥人就化作神明、幽灵,暗中帮助,保护阿炳。从扮相来看,阿福的年龄就是三五岁的小男娃,配合可爱滑稽夸张的肢体动作,我演出的时候也似乎渐渐像那么回事了。可唯独这声音把我难住了。起先我一直拿捏不准,我在家就开始反复观察并模仿当时我四岁的儿子说话的语气和语调。经过长时间的模仿排练演出时的反复尝试,我总结了四条要点:一是小孩的声线高而细。所有剧中的台词适当的提高音调,把声音“夹起来”,有些地方需要奶声奶气一些。二是说话不可过于工整。孩子的思维不比大人,语言的逻辑也是不同,经常是想想说说、说说想想。具体体现在声音和台词上就是,要把背熟的台词念出“陌生感”。三是语速节奏不能太稳定。既然是想想说说、说说想想,那么说话的节奏一定是不同的。四是在唱腔声音和运腔的处理上要多用直音,也不可太过追求韵味,虽然是高于生活,但也有贴近生活。
《活捉三郎》是一个移植于昆曲、京剧的经典折子戏,讲的是宋江之妻阎惜娇与张文远苟合,后被宋江失手杀死,她死后念念不忘这位张三郎,鬼魂半夜来到三郎居所,最终带着情郎共赴地府。张三郎这个人物从行当上来说,一般各个剧种都是由丑角演员来饰演的。但我的理解可能稍有不同,我觉得这个人物不是单纯的小花脸这么简单,面上勾白的妆容只是说明他内心的不正面与不健康,而他的形象气质应该是翩翩潇洒的,不然也不会惹得阎惜娇如此迷恋。所以我觉的他的身段和唱腔是可以适当借鉴小生的。具体单就声音来讲,不能一味地用丑行的小嗓,搞笑的声音,需要用小生的真假嗓结合来进行匹配与塑造,给人以“翩翩儒雅文化人”的感觉,哪怕他是装的。尤其出场两句定场诗“摇帘隔窗月,罗绮自相亲”,则要把戏曲小生文绉绉的感觉给念出来。在整个前小半段戏中,由于他还不知道前来的是阎惜娇的鬼魂,一心沉浸在于不知哪家小娘子的言语暧昧时,这种装斯文装儒雅的声音的感觉一直可以沿用。而随着剧情的推动,声音的运用和塑造在这个角色身上有了更高的要求。声音的变化,是这个角色最抓人的地方。比如当他看清来的是阎惜娇的鬼魂时,惊吓将他的声音打回原形,这时倒是可以多用一些丑行的用嗓,惊恐的、有失体面的、滑稽的声音用在这里非常恰当,也对应了他的行当和脸上的妆容。再到他被鬼魂俏丽容貌所魅惑时,他的声音又出现了第三种塑造,得意忘形的、不由自主的,我在这里把前面两种声音来了一次结合,时而文雅,时而又是实在抑制不住的那种“轻骨头”的感觉。我以为,这时的声音是张文远这个人物的标志性声音,也是要演好这个角色必须要去琢磨的声音。戏的最后,三郎被阎惜娇勒着脖子从挣扎到化为魂魄则又是一个强烈的变化,台词处理上他也从说不清到不会说,此时我多用尖叫怪音来表现,直至落幕。
《蘩漪》中的男仆这个人物借鉴了原著《雷雨》中的鲁贵。他五十岁上下,是周家一名卑微的下人,白天像模像样的干活,而到了晚上趁着替老爷巡视家院的时候,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窥视周家主人们的那些不齿的勾当,一边嘴上嘲笑他们、一边却又每晚偷窥看好戏。这是个心理变态、人前背后两面三刀的善变小人。这样的人在对其进行声音塑造的时候,需要增加一点特色,我抓了这几个要点:白天说话可靠沉稳,语速平均毕恭毕敬,音色上要突出五十岁的年龄和厚重感和踏实感。到了晚上偷窥时,说话时则要完全变一个人,要压低声音,并变得尖细一些,露出小人的奸诈。尤其是他变态到还非得拉上女仆一起偷窥的那种畸形的声音处理。此时的笑声也很有讲究,首先一定是奸笑、淫笑、令人作呕的笑声,我经过了反复的练习与试验,最终找出较为合适的方法是:运用笑声小、气声大的手法配合着压到不能再低的尖锐的间断式的笑声,用这种方法来体现人物,并使之更符合人物个性和戏剧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