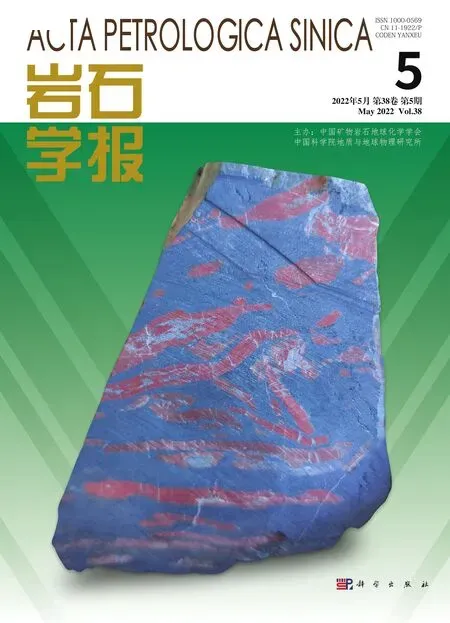青藏高原南部及邻区深部碳释放规模与成因*
赵文斌 郭正府, 3 李菊景 马琳 刘嘉麒
1.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新生代地质与环境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9 2.中国科学院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北京 100049 3.中国科学院生物演化与环境卓越创新中心,北京 100044
全球变暖是当今国际社会和科学界广泛关注的重大议题之一,并被认为与大气圈CO2浓度的快速上升具有密切的联系(Keelingetal., 2005; Gattusoetal., 2015; IPCC, 2021; Shengetal., 2021)。地质历史时期,以硅酸盐风化消耗碳、火山-构造活动释放碳为主体的一级碳循环在地球不同圈层系统之间的物质与能量交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深刻影响宜居地球的形成和演化(Misra and Froelich, 2012; Plank and Manning, 2019; Stewartetal., 2019)。火山活动作为地球深部碳循环的关键环节和主要载体,对长时间尺度的气候变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受到了科学界的密切关注(Mörner and Etiope, 2002; Burtonetal., 2013; Aiuppaetal., 2019; Fischeretal., 2019; Guoetal., 2021)。过去十多年间,在国际“深部碳观测”项目(Deep Carbon Observatory)的支持下,国外学者针对地球深部碳储库以及火山活动与深部碳循环之间的相互联系开展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Orcuttetal., 2019),但是,对不同构造背景的火山深部碳释放规模和机理的认识尚存在很多争议(Leeetal., 2013; Lee and Lackey, 2015; Bruneetal., 2017; Plank and Manning, 2019)。除了洋中脊和板内火山深部碳释放以外(Bruneetal., 2017; Le Voyeretal., 2019),板块汇聚边缘作为地球不同圈层物质与能量交换的主要场所,其火山活动被认为是构成地球深部碳循环的另一个重要的途径(Sano and Williams, 1996; Hiltonetal., 2002; Kelemen and Manning, 2015; Plank and Manning, 2019)。前人关于板块汇聚边缘火山深部碳循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洋板块俯冲造成的岛弧型和大陆弧型火山活动(Sano and Williams, 1996; Lee and Lackey, 2015; Aiuppaetal., 2017; Masonetal., 2017),而对于大陆碰撞-俯冲带火山深部碳释放的研究相对缺乏。
作为印度-欧亚大陆碰撞带的主体组成部分,青藏高原及其邻区分布着众多的新生代火山区(刘嘉麒, 1999; Dingetal., 2003; Chungetal., 2005; 莫宣学等, 2006; 郭正府等, 2014; Guo and Wilson, 2019)。近期研究表明,贯穿整个新生代的青藏高原火山活动深部碳释放控制着新生代大气圈CO2浓度变化,进而影响全球气候、环境的演化(Guoetal., 2021)。高原及其邻区断裂带分布广泛,现今水热活动强烈,具有温泉、喷气孔、水热爆炸等地热活动现象(廖志杰和赵平, 1999; 佟伟等, 2000; 张丽红等, 2017; 周晓成等, 2020),同时还以土壤微渗漏的形式向大气圈释放巨量的深源气体(成智慧等, 2014; 张丽红等, 2014, 2017; Zhangetal., 2017a)。例如,Chiodinietal.(1998)采用密闭气室法调查,估算出羊八井地热区土壤CO2释放通量达每天138t,而高原南部谷露-亚东裂谷的火山-地热区(总面积<20km2)土壤CO2释放通量达到700kt/yr(张丽红等, 2014, 2017; Zhangetal., 2017a, 2021c)。上述研究表明,以青藏高原为代表的大陆碰撞带深部碳释放潜力巨大(Kerrick, 2001; Tamburelloetal., 2018; Guoetal., 2021; Xuetal., 2022),定量研究高原火山-地热区的CO2释放规模及其空间变化特征,对于完善不同构造背景下深部碳循环过程与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地表碳观测是研究火山-地热区深部碳释放的有效手段之一(Burtonetal., 2013; Aiuppaetal., 2019; Fischeretal., 2019)。目前对青藏高原火山-地热区CO2释放的调查主要以点、线型野外观测为主,缺少对高原及其邻区地表碳观测数据的统一分类和整体评价,从而制约了对于大陆碰撞带深部碳循环机制的深入认识。同时,大气圈温室气体浓度的变化是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共同叠加的结果(郭正府等, 2010, 2014; IPCC, 2021),因此在目前我国“双碳”战略背景下,进一步厘清自然过程(包括火山活动、构造运动等)碳释放规模对当今大气圈CO2浓度的贡献对于服务我国“双碳”战略行动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价值。为此,在课题组近十年青藏高原火山-地热区地表观测的基础上,本文综合分析了高原南部CO2释放通量的空间变化特征,并结合前人研究结果计算了青藏高原火山-地热区土壤微渗漏、温泉等的碳释放规模,为探讨大陆碰撞带深部碳释放机理以及进一步确定自然源的CO2排放份额等提供科技支撑。
1 青藏高原南部及邻区新生代火山-地热区的地质概况
青藏高原是特提斯地热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大陆大地热流值最高的区域之一(Jiangetal., 2016, 2019)。新生代以来,青藏高原及邻区具有强烈的岩浆和构造活动(Yin and Harrison, 2000; Dingetal., 2003; Chungetal., 2005; Guo and Wilson, 2019)。前人的研究表明,青藏高原温泉广布,数量超过1700个(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 1981; 佟伟等, 2000; 廖志杰和赵平, 1999),被认为是全球深部碳释放的重要地区之一(Tamburelloetal., 2018, Guoetal., 2021)。
青藏高原南部(主要包括喜马拉雅地块和拉萨地块)的新生代岩浆活动主要受控于特提斯洋俯冲和其后的印度-欧亚大陆碰撞过程,其形成时代主要集中在65~8Ma期间。根据时空分布与物质成分特征,可大致分为如下三类:(1)古新世-始新世林子宗火山活动(65~45Ma,Moetal., 2008; Zhuetal., 2015);(2)晚渐新世-中新世钾质-超钾质火山活动和埃达克质岩浆作用(26~8Ma,Chungetal., 2003; Guoetal., 2007, 2015b; Zhaoetal., 2009);(3)喜马拉雅淡色花岗岩系列(44~7Ma,吴福元等, 2015),岩浆活动的峰期年龄与钾质-超钾质岩火山活动一致(25~8Ma,Guo and Wilson, 2012)。地球物理研究显示,青藏高原南部在深度为15~25km的中地壳广泛存在低速高导层,被认为是地壳增厚导致壳内部分熔融和/或含水流体作用的产物(Nelsonetal., 1996; Xuetal., 2015)。钻井研究结果显示,藏南典型地热田往往存在深部高温热储(赵平等, 2001)。受印度与欧亚大陆碰撞挤压过程的影响,青藏高原南部形成了多种类型的断裂系统,如南北向分布的裂谷系地堑、以喀喇昆仑断裂为代表的走滑断裂、藏南拆离系与高角度逆冲断层等(Yin and Harrison, 2000; Kapp and Guynn, 2004; Taylor and Yin, 2009)。研究区内不同类型的水热活动广泛分布(图1),主要受新生代火山活动与断裂系统的控制(Zhangetal., 2017b)。

图1 青藏高原南部及邻区地质简图与温泉气体He同位素和土壤微渗漏观测点分布简图
青藏高原东南缘新生代火山活动的分布范围比较局限,主要集中在滇西南的腾冲和宁洱-通关地区。该区高钾钙碱性火山活动始于中新世(8Ma;Guoetal., 2015a; Chengetal., 2020),第四纪以来,岩浆活动频繁且规模较大(Lietal., 2020),是我国西南地区有史料记载的活火山区(刘嘉麒, 1999)。位于腾冲火山区东南部的宁洱-通关一带具有小规模的第四纪火山活动(1.0Ma,Wangetal., 2001)。地球物理研究显示,腾冲与通关火山区的地下深部可能存在着部分熔融体,认为是壳内岩浆房(Baietal., 2001; Xuetal., 2018),该区剧烈的水热活动可能是深部岩浆房的地表显示(赵慈平等, 2006, 2012; Shietal., 2020)。在空间上,青藏高原东南缘水热活动的分布还与走滑断裂和逆冲推覆构造相关(图1;Zhouetal., 2015, 2017; 周晓成等, 2020; Tianetal., 2021; Zhangetal., 2021a; Xuetal., 2022),例如川西的鲜水河断裂带、理塘断裂带、龙门山断裂带以及安宁河断裂带,滇西南的红河断裂带与小江断裂带等。上述这些断裂带为深源流体的上升运移提供了通道(Zhangetal., 2021a, b)。
2 样品采集与实验室测试方法


图2 青藏高原南部火山-地热区水热活动特征
在野外采集火山-地热区温泉逸出气的过程中,首先利用塑胶软管连接集气漏斗与采样容器,将漏斗倒置放于水面以下并扣在逸出气泡之上,然后采用排水法收集气体(Sunetal., 2020)。在高温逸出气中,水蒸气在运送过程中易发生冷凝,利用玻璃瓶采样时样品容器内部会存在负压,可在管线中部连接蛇形铜管放入冷水,通过冷凝作用去除水蒸气(Tianetal., 2019),以减少采样瓶内负压给后续实验室的测试造成的误差。土壤气样品采用预真空法进行采集,方法详见Sunetal.(2018)。采集的气体样品应尽快送往实验室进行测试,测试项目包括气体全组分、碳同位素以及氦氖同位素等。
3 CO2气体的野外观测与释放通量
以往研究表明,火山气体的组分含量及其同位素组成(如3He/4He比值、δ13C等)是示踪其来源、探讨运移规律的有效地球化学指标(Sano and Williams, 1996; Hiltonetal., 2002; Masonetal., 2017)。长期以来,前人针对青藏高原及其周边火山-地热区、活动断裂带内的喷气孔、温泉水热气体的特征,开展了挥发分循环机制、来源演化与区域动力学背景的研究(Zhangetal., 2016, 2017a, b, 2021a, b; Zhouetal., 2017; Tianetal., 2019, 2021; 周晓成等, 2020)。基于已发表地表观测数据的统一分类和整体对比研究,依据其碳释放机制与成因的差异,本文将青藏高原南部及邻区的温室气体释放特征分为3个研究区(图1):(1)高原南部火山-地热区;(2)高原东南缘川西火山-地热区;(3)滇西南火山-地热区。
3.1 青藏高原南部火山-地热区CO2释放通量
青藏高原南部火山-地热区土壤气体地球化学特征主要包括,(1)土壤气的CO2含量远高于空气值(Sunetal., 2020, 2021a),(2)He-C同位素组成与温泉气体非常接近(成智慧等, 2014; 张丽红等, 2017; Sunetal., 2020),表明土壤微渗漏是火山-地热区向大气圈释放深部CO2的重要途径(Chiodinietal., 1998; 郭正府等, 2014)。
3.1.1 土壤CO2气体的释放通量
通过累积频率分布对相关火山-地热区的通量释放数据进行识别,剔除对总体平均通量影响较大的异常值,例如异常高值可能代表了土壤喷气孔CO2释放的情况(图2a, b),最后获得有效测点共计1820个(图3)。所有获取的有效数据中,2018年之前的测点采用便携式红外CO2分析仪测量,2018年及之后的测点采用WEST土壤碳通量设备测量,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二者的测量结果在误差范围内,认为两种测量结果是基本一致的(Wenetal., 2011; Zhangetal., 2015),因此,因为测量仪器设备不同而造成测试数据的系统误差可以忽略。

图3 青藏高原南部火山-地热区土壤微渗漏CO2释放特征
对上述数据的综合分析结果显示,青藏高原南部土壤微渗漏CO2释放通量值介于0.3~8794.2g/m2/day之间,平均值为169.7g/m2/day,中值为25.0g/m2/day。通过累积频率法对43个观测区的CO2释放通量进行计算,结果显示,高原南部火山-地热区土壤CO2平均释放通量介于3.9±2.5~791.5±512.5g/m2/day之间(“±”表示95%的置信区间,后同;图4a),最高通量位于谷露-亚东裂谷的宁中地热区(Zhangetal., 2017a),最低通量位于拉萨地块西北部的麻米冷泉区。基于上述的平均通量值,采用反距离加权插值法(Inverse Distance Weighting method)绘制了土壤微渗漏CO2释放通量分布图(图3a),可以看出,高原南部土壤CO2释放通量分布是不同的。位于东部地区的谷露-亚东裂谷(GYR)、朋曲-申扎裂谷(PXR)以及西部的玛旁雍错地热区具有较高的释放通量值,而GYR以东、当惹雍错-许如错裂谷(DXR)以及拉萨地块西北部的火山-地热区具有相对较低的土壤微渗漏CO2释放通量值(图3a)。土壤CO2释放通量呈现出东部高、西部相对较低的特征,这可能与印度板片在东西向上俯冲角度不同有关(Zhou and Murphy, 2005; Lietal., 2008; Chenetal., 2015)。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涉及到的火山-地热区相对于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数量仍较少,精确的土壤CO2释放通量分布状况与深部控制机理仍需更多观测值的支持。

图4 青藏高原南部火山-地热区土壤CO2平均释放通量累积频率分布图(a)和土壤CO2释放量累积频数分布图与总量估算(b)
对火山-地热区土壤CO2的平均释放通量,按照累积频率分布法进行投图,再根据分布曲线的特点和释放通量区域分布图(图3a),将数据以15g/m2/day、60g/m2/day、500g/m2/day为节点划分为4组(图4a):(1)背景通量释放区,其通量值介于3.9±2.5~11.5±9.3g/m2/day,平均值为7.9±3.4g/m2/day,明显高于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区自然过程CO2释放的通量值(0.1~1.4g/m2/day,张宪洲等, 2004),显示出地质源CO2释放的特征,例如当惹雍错-许如错裂谷(DXR)中北部的别拉地热区(图2c),地面覆盖盐华,温泉点附近显示地热异常;(2)低通量释放区,通量值介于16.2±9.0~51.1±34.2g/m2/day,以喜马拉雅地块科作地热区为代表,水热活动以热泉为主,分布于区内相对局限的点位,地面显示出水热蚀变迹象(图2d);(3)中等通量释放区,平均通量值介于67.6±43.7~318.4±106.5g/m2/day,以DXR南部查孜火山-地热区为代表,区内水热活动剧烈,沸泉广布(图2e);(4)高通量释放区,以玛旁雍错曲普地热区为代表,地表水热活动类型多样,分布有喷气孔、水热爆炸区以及多处沸泉和硫磺地面(图2f),本组平均通量值介于509.9±211.9~791.5±515.2g/m2/day,此类高CO2释放通量区同时也是地质源Hg释放的潜在高值区(Sunetal., 2020)。由此可知,青藏高原南部的土壤CO2释放通量高值主要出现在水热活动较强的火山-地热区。

3.1.2 土壤CO2释放规模
火山-地热区土壤微渗漏碳释放总量与区内平均释放通量和释放面积有关(张丽红等, 2014, 2017; Chiodinietal., 1998, 2015),通过卫星影像结合野外实际考察,本研究对每个测区的土壤CO2潜在释放面积进行了较合理估算,进而获得了43个火山-地热区的土壤CO2释放规模(即总通量值,图4b),其中最大释放规模在PXR的查多曲增地热区,每年向大气圈释放CO2约180.1±60.3kt(112.6±37.7kt/km2/yr)(图4b)。青藏高原是特提斯高温地热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沿线分布有大量沸泉、热泉及低温温泉等水热活动区,考虑到目前的观测区不存在选择性考察的问题,因此能够代表区域内不同类型的火山-地热区。本文首先将上述43个火山-地热区的土壤CO2释放量按大小顺序排列绘制成累积频数分布图(图4b),根据频数曲线的拐点将藏南火山-地热区分为4组,分别计算各组的平均释放量和每组的个数及其所占的比例,结合青藏高原南部地热区的总个数将目前已获得的通量推广至整个青藏高原南部,即公式(1):
(1)
其中,F代表青藏高原南部的CO2释放总量,G代表火山-地热区CO2释放量的分组,nG和fG分别代表各组火山-地热区的个数和平均释放量(表1);N代表青藏高原南部温泉区的总个数,本文采用青藏高原科考专著中统计的数据,保守估计约650处(佟伟等, 2000)。利用公式(1)计算的结果显示,青藏高原南部火山-地热区土壤CO2释放的规模为18.7±8.9Mt/yr(表1;图4b),是美国黄石公园火山区的两倍(8.8±4.4Mt/yr,Rahilly and Fischer, 2021),约占全球火山区土壤微渗漏CO2释放量的9.7%~28.5%(47~174Mt/yr,Fischeretal., 2019)。

表1 青藏高原南部火山-地热区土壤微渗漏CO2气体释放规模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结果是青藏高原火山-地热区土壤微渗漏CO2释放量的保守值,原因在于:(1)青藏高原还存在大量未经实地考察的地热活动区,水热活动区的数量可能高于650处(廖志杰和赵平, 1999),此部分并未列入;(2)本研究在计算平均释放通量时剔除了测量异常值,并认为异常高值代表了土壤喷气孔的测点(图2a, b)。以布多地热区为例,这类测点的通量远高于土壤微渗漏1~2个数量级(>104g/m2/day),尽管其所代表的释放面积较小,但类似的情况在高原南部火山-地热区内普遍存在,因此其释放通量不可忽视。前人研究结果也表明,青藏高原南部广泛发育的南北向裂谷是土壤CO2稳定释放的主要区域(Zhangetal., 2021c),如果假设裂谷区的平均CO2释放通量为背景值,即7.9±3.4g/m2/day(图4a),保守估计藏南裂谷区的面积约为11600km2,则裂谷释放CO2气体的量应为33.6±14.4Mt/yr,而整个高原南部通过土壤微渗漏向大气圈释放CO2气体的规模将达到52.3±23.3Mt/yr。因此,青藏高原南部土壤CO2释放规模介于18.7~52.3Mt/yr之间。
3.1.3 温泉溶解无机碳释放通量
火山-地热区温泉水中溶解无机碳(DIC)释放CO2的产率(DIC_CO2,mmol/L)可以通过水化学法进行计算(Chiodinietal., 2004; 郭正府等, 2014; Newelletal., 2008),
DIC_CO2=DIC-(Ca2++Mg2+-SO42-)
(2)
前人针对中国、尼泊尔两国喜马拉雅地区的温泉DIC碳释放通量开展了研究工作,并根据水化学的研究结果,对整个区域内深部碳释放的总量进行了计算(表2)。例如,Beckeretal.(2008)对尼泊尔Marsyandi谷地水热活动的调查结果显示,该地区温泉无机碳释放通量为1.60×108mol/yr,扩展到整个喜马拉雅地区,CO2释放通量达到每年39.6Mt;Evansetal.(2008)对尼泊尔Kali Gandaki地区温泉水化学的研究显示,每年约有1.4×109mol的CO2以DIC的形式释放到大气中,而整个喜马拉雅地区则可能达到了8.8Mt/yr;Newelletal.(2008)通过水化学的研究认为,整个藏南拆离系(STDS)的温泉水CO2释放量达到了30.8Mt/yr,并提出喜马拉雅地块与此相关的CO2释放量达每年1011mol(4.4Mt),与新生代喜马拉雅造山带隆升变质作用释放CO2的量级相当(Kerrick and Calderia, 1999);拉萨地块火山-地热区温泉DIC相关CO2释放研究较为分散,沈立成等(2011)对达格架、郎久地热区脱气量和机理进行了详细研究,郭正府等(2014)根据水化学方法计算了两区温泉水每年释放CO2的规模为170t。

表2 青藏高原南部火山-地热区温泉溶解无机碳相关的CO2气体释放量



图5 青藏高原南部不同地块火山-地热区温泉离子与DIC_CO2脱气速率关系(a)和温泉水温与流量关系(b)
(2)
其中,L和H分别代表拉萨和喜马拉雅地块,F表示温泉DIC相关的CO2碳释放总量,喜马拉雅地块的F值本文采用Newelletal.(2008)中提出的保守估值,即4.4Mt/yr;fr表示不同地块温泉的平均流量值,在处理流量数据时每组剔除10%的极值,以保证选用的数据具有代表性,结果显示(图5b),拉萨地块温泉水平均流量(11.7±2.3L/s)整体高于喜马拉雅地块(7.3±1.5L/s)。
上述模型计算结果表明,拉萨地块火山-地热区CO2释放量为17.3Mt/yr,整个高原南部合计为21.7Mt/yr(表2),与3.1.2节中利用土壤气观测数据模型得到的结果在误差范围内基本一致(表1),表明模型计算结果是可靠的。
3.2 青藏高原邻区川西及滇西南火山-地热区CO2释放通量
青藏高原东南缘的深部碳释放观测研究主要集中在鲜水河-安宁河断裂带以及滇西南腾冲火山区。鲜水河-安宁河断裂带是青藏高原东南缘最重要的走滑断裂之一(图1;周晓成等, 2020),前人通过温泉水、气体多元同位素体系(C-He-Δ14C同位素)的示踪研究,利用质量平衡混合模型识别出断裂带内温泉气体中深部成因(变质作用和地幔来源)碳的贡献达到了80%,仅康定地热区每年通过温泉水向大气圈释放深部CO2的量就达到160t,推算至整个高原东南缘的活动断裂带,温泉CO2释放的总通量约为100kt/yr(Xuetal., 2022),表明高原周边的断裂带具有向大气圈释放CO2的巨大潜力(Sunetal., 2021a; Xuetal., 2022)。
前人通过详细的碳释放野外调查发现,滇西南腾冲火山区深部碳释放类型包括土壤微渗漏、温泉逸出气以及温泉溶解无机碳(成智慧等, 2012, 2014; Zhangetal., 2016)。2012年11月,成智慧等(2014)首次对腾冲北部马站第四纪火山区、热海以及南部的邦腊掌地热活动区开展了野外土壤微渗漏CO2释放观测的工作,获得三个区域平均释放通量依次为42.5g/m2/day、874.5g/m2/day以及25.1g/m2/day,根据地热异常区面积估算,得到三者的释放规模分别为1.8Mt/yr、3.2Mt/yr及2.0Mt/yr,进而提出腾冲火山区每年通过土壤微渗漏向大气圈释放CO2的量为7.0Mt(成智慧等, 2014)。上述的研究结果显示,腾冲热海地区土壤微渗漏CO2释放通量显著高于周边地区。后续针对热海地区开展的详细调查工作结果也显示,热海地区湿季土壤CO2平均释放通量(280±103g/m2/day,Zhangetal., 2016)低于干季(874.5g/m2/day,成智慧等, 2014),表明土壤含水量对深部CO2释放有重要的影响。基于2020年热海地区土壤气观测的新数据,结合前人研究结果,本文获得有效测点182个,利用累积频率法重新计算了热海土壤CO2平均释放通量,结果为366.2±115.5g/m2/day(图6a)。这一通量值明显高于中国东部(例如长白山、五大连池)火山区的释放通量(郭正府等, 2014; Zhangetal., 2015; 赵文斌等, 2021),接近美国黄石公园火山区的土壤CO2平均释放通量(410g/m2/day,Werneretal., 2008)。腾冲火山区内温泉逸出气、溶解无机碳释放CO2的量分别为3.6kt/yr及49kt/yr(成智慧等, 2014)。综上所述,腾冲火山区每年向大气圈释放CO2的总量介于4.5~7.1Mt之间。

图6 青藏高原东南缘腾冲热海地区土壤CO2释放通量累积频率分布图(a)和腾冲热海狮子头水热活动区土壤CO2气体释放特征(b)
本研究最新的结果显示,青藏高原南部土壤微渗漏CO2释放量介于18.7~52.3Mt/yr之间,温泉溶解无机碳释放量为0.13Mt/yr,青藏高原东南缘活动断裂带温泉深源CO2释放的总通量约为0.1Mt/yr(Xuetal., 2022),腾冲火山区总体CO2释放量为4.5~7.1Mt/yr。上述结果显示,高原南部及邻区每年向大气圈释放CO2的规模介于23.4~59.6Mt之间,这一范围与全球其他构造背景火山区深部碳释放的量级相当(图7),表明以青藏高原为代表的大陆碰撞带是地质源CO2释放的重要场所之一。

图7 全球不同构造背景的火山区温室气体释放通量比较
4 青藏高原及邻区火山-地热区温室气体的成因
青藏高原南部火山-地热区温泉气体成分以CO2为主,仅雅鲁藏布江缝合带(ITS)周边及其南部喜马拉雅地块的部分温泉以N2为主(赵平等, 2001, 2002; 张丽红等, 2017; Zhangetal., 2017b)。温泉气体3He/4He比值较低,介于0.01~1.02RA之间(图8a),明显低于地幔He同位素平均组成(8±1RA, Hilton and Craig, 1989),仅拉萨地块西部喀喇昆仑断裂带周边有较高He同位素组成(2.24RA, 赵平等, 2002; Klempereretal., 2013)。谷露-亚东裂谷为代表的南部喜马拉雅地块的气体样品具有典型的地壳氦同位素组成特征,向北He同位素则逐渐升高,指示了幔源物质的含量增多,最高接近20%(图9a;Hokeetal., 2000; Zhangetal., 2017a, 2021c)。气体δ13CCO2值变化范围较大,介于-14.7‰~0.31‰之间(图8b)。ITS往北的气体δ13CCO2值逐渐变重,同位素混合计算的结果显示,气体成分中无机碳酸盐的贡献逐渐增多(Zhangetal., 2017a)。

图8 青藏高原南部(a、b)、川西(c、d)及滇西南(e、f)火山-地热区温泉气体He-C同位素特征

图9 青藏高原火山-地热区富CO2温泉气体3He/4He(R/RA)-XM图解(a)和3He/4He(R/RA)-δ13C同位素图解(b)
川西地区温泉气体成分以CO2为主,偶有N2型出现,例如龙门山断裂带周边温泉地热区(Tianetal., 2021)。释放气体He同位素比值高于高原南部火山-地热区温泉气体,介于0.04~3.80RA之间(图8c),最高值出现在鲜水河断裂带的康定地区(图1),幔源He贡献比例达到30%以上(图9a;Xuetal., 2022),其周边理塘断裂和三江断裂带的温泉气体中存在幔源He的贡献,特别是在不同断裂的相交区域(周晓成等, 2020),指示青藏高原东南缘的断裂体系达到了岩石圈深度(Zhangetal., 2021a)。气体的δ13CCO2值介于-20‰~-1‰之间(图8b)。
滇西南地区温泉气体化学成分和同位素比值均有较大的变化(图8e),有明显幔源He贡献的样品与第四纪火山的空间分布密切相关(图1),表明深部岩浆活动为地表水热活动提供了热能和物质来源(Zhangetal., 2021b)。以腾冲火山区为例,温泉气体3He/4He比值介于0.2~5.3RA之间,气体源区中幔源物质的贡献普遍超过40%(Zhangetal., 2016);滇西南红河断裂带附近温泉He同位素比值明显低于腾冲-通关火山区,介于0.1~0.5RA之间,而远离断裂带的温泉则呈现地壳成因He同位素特征(图1)。温泉气体δ13CCO2值较川西地区与高原南部偏轻,平均值为-8.6‰,显示包含有机质的贡献(图8f)。
为探讨青藏高原及邻区不同区域火山-地热区的深部碳释放模式,本文重点研究了富CO2型温泉气体的地球化学特征(图8、图9),原因在于高CO2温泉气受水热活动分馏或地表过程的影响较小(Zhangetal., 2017b, 2021a)。统计结果显示,富CO2温泉气体较富N2温泉气体具有更高的He同位素和偏重的δ13C同位素组成(图8);另外,三个研究区的He-C同位素也存在明显差异。上述特征表明,高原不同区域深源气体的释放机制与断裂、岩浆水热系统之间的联系不同(Zhangetal., 2017b, 2021a, b; Xuetal., 2022)。
青藏高原南部火山-地热区富CO2温泉气体具有较低的He同位素组成(0.21RA)和较重的碳同位素组成(-5.20‰),表明碳释放以壳内水热系统脱碳作用为主,与区内缺少岩石圈尺度的深大断裂而广泛发育裂谷系逆断层相符(图1; Kapp and Guynn, 2004),说明气体从深部弥散式上升的过程中容易受到壳内高放射成因He的混染(图10)。

图10 青藏高原南部及邻区火山-地热区深部碳释放模式图
川西火山-地热区温泉气体具有中等的He同位素组成(0.33RA),但仍以壳源为主,以及与地幔值(-6±2‰, Barryetal., 2020)比较接近的碳同位素组成(-5.93‰,图8、图9b)为特征,并且断裂带内地热区温泉气体He同位素比值明显高于远离断裂带的区域(图1),表明地幔流体挥发分(He、CO2)的释放与活动断裂的分布有关(图10)。气体在沿断裂上升至地表的过程中,经过了不同尺度的水热系统,并体现为气体地球化学参数的不同。例如,温泉水化学的研究结果表明,龙门山、鲜水河断裂带内流体循环深度、热储温度等均存在明显差异(Tianetal., 2021)。
滇西南地区富CO2温泉气体He同位素呈现“双峰式”变化特征(图8e),较低的He同位素比值代表深源气体的释放受到非火山区断裂带的控制,而高He同位素比值的温泉空间分布与第四纪火山密切相关(图1)。例如腾冲、通关火山区具有显著的幔源岩浆脱气现象(赵慈平等, 2006, 2012; Shietal., 2020)。火山区玄武岩橄榄石斑晶的He同位素组成与地幔值一致(图9a;Zhangetal., 2021b)。大地电磁、地震学等地球物理探测结果均表明,腾冲火山区地下深部存在岩浆房,可为浅部水热系统提供热量和物质(Baietal., 2001; Xuetal., 2018)。这些研究均表明,区内碳释放受到深部岩浆房和浅部水热系统的双重控制(图10)。
5 结论
本文在近年来青藏高原温室气体释放研究的基础上,计算了高原南部及邻区火山-地热区的深部碳释放规模,结合温泉气体He-C同位素地球化学与水热活动特征,探讨了青藏高原南部及邻区的碳释放模式,取得了以下主要认识:
(1)青藏高原南部火山-地热区的深部碳释放以壳内水热系统脱碳为主;区内土壤CO2释放通量介于3.9~791.5g/m2/day之间,气体地球化学模型研究结果显示,高原南部土壤微渗漏和温泉溶解无机碳释放CO2的规模分别为18.7~52.3Mt/yr和0.13Mt/yr。
(2)青藏高原东南缘川西地区的深部碳释放以深大断裂控制的水热系统脱碳为主,而滇西南地区碳释放过程则主要受深部岩浆房与浅部水热系统的共同控制;川西、滇东南断裂带温泉深源CO2释放通量为0.1Mt/yr,腾冲火山区CO2释放通量介于4.5~7.1Mt/yr之间。
(3)青藏高原南部及邻区每年向大气圈释放CO2的量约为23.4~59.6Mt,其规模与全球其他构造背景(如洋中脊、大洋俯冲带、大陆裂谷等)火山区深部碳释放的量级相当,表明以青藏高原为代表的大陆碰撞带也是地质源CO2释放的重要场所。
致谢谨以此文纪念已逝国际气体地球化学家David R.Hilton与杨灿尧教授,感谢他们对课题组火山-地热区深部碳释放观测和气体地球化学研究工作的指导和帮助;在野外考察和实验室测试样品过程中,得到李立武研究员、李中平研究员、张丽红博士、张茂亮博士、成智慧博士和孙玉涛博士的帮助;郑国东研究员、徐胜教授以及俞良军博士对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