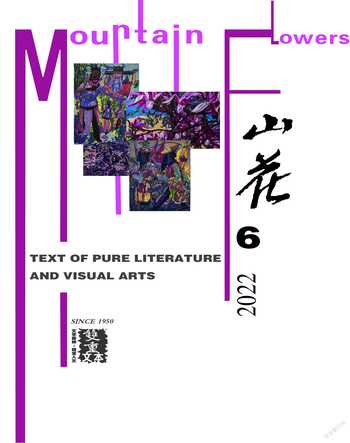被电影渲染的早期记忆
西闪
生命中最闪亮的记忆少不了电影。记得小时候我家附近是日化厂的露天原料堆放场,我童年最美的夏夜故事不少都在那里发生。记忆在发昏的油脂味儿和舒心的松香味儿里交替,那气味似乎现在还偶尔飘荡在鼻息之中。
那时候,住单位宿舍的一个大个子叔叔常为孩子们放映他自己制作的幻灯片。红红绿绿的画面投映在斑驳的外墙上,于我而言是电影的启蒙。
大个子叔叔是我父母的同事,喜爱绘画,常被电影院借调去画大幅的电影宣传画——过去所有的海报都是手绘的。我见过他在地委大礼堂工作的样子,还去过他家。他单身,屋子里没什么摆设,桌子上乱七八糟堆着画笔颜料,墙上贴着各种石膏素描、水粉风景。不知怎么的,我很喜欢素描的碳粉味儿。打那以后,我就暗下决心,未来的某一天,我要像他那样,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提着颜料桶,用刷子飞快地画出《黑三角》里白衣白帽的公安形象。
之前我可不这么想。大概四五岁时,我跟父母去看了一部外国电影,片名叫《爆炸》。具体的内容记不清,但货船甲板上即将爆炸的气瓶,滴答滴答的钟表倒数声,还有沉闷而急促的汽笛声,都让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真正的恐惧。很长时间,每个黑夜,我不敢入睡,也无法入睡。一闭上眼睛,屋内钟表的滴答声就会涌入双耳,无数的气瓶在脑海里碰撞滚动,连我一向喜欢的轮船汽笛声也让我不得安宁。我甚至不敢翻身,因为枕头发出的沙沙声实在像钢瓶泄漏。那时候我才明白,漆黑的夜晚不可怕,大人杀鸡的场面也不算什么,什么也做不了,就这样等着一个毁灭的时刻,那才叫真可怕。
印度电影《流浪者》也是我幼小心灵的一块阴影。我记得是外祖母家的邻居带我去看的。当年邻居应该还很年轻,约莫三十五岁吧,辈分却不低,我管她叫谭婆婆。
谭婆婆和地委大礼堂一楼的一家住户好像很熟,每有新片上映,她就领我穿过那家住户的屋子,从一扇小门钻进大礼堂的放映厅。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那家人西式阳台上的花草,以及明亮宽敞的客厅,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能正是因为客厅的明亮,一走进放映厅的黑暗中,我就被《流浪者》里满幅的积雨云镇住了。当我在陌生而古怪的印度歌曲里摸索着找到空位,一抬头,眼睛里就塞满了厚重如铅的云。它似乎纹丝不动,又似乎正在升腾,逐渐扩大,缓缓地朝我挤压过来。它大体是不同层次的灰黑,边缘却闪耀着夺目的白光。就像《爆炸》里钟表的滴答声一样,它预示着某种我难以理解也难以把握的未来正逼向我。到后来,它和电影里那句“去偷!去抢!去杀人!去放火!”的经典台词组合成一个压抑的图景,在某些莫名其妙的暗示下,常常闪回在我的脑袋中。
今天的神经科学提醒我,恐惧源于大脑中一对特定的结构,名叫杏仁核。记忆在杏仁核(包括别的神经结构,例如尾状核、纹状体,乃至嗅球)的渲染下,因情感的色彩而鲜亮。与此同时,强烈的情感也在塑造记忆,使之远离事实与真相。所谓闪光灯记忆,就是如此。人们往往以为,生动的记忆细节更饱满,情形更准确。神经科学却再次提醒,无论是记忆量还是准确度,闪光灯记忆跟一般记忆没什么区别。
那么我的记忆如何?是因情感而生动,还是因情感而扭曲?我不知道。回看电影,查阅资料,一直以为《爆炸》是土耳其电影,原来是罗马尼亚出品。《流浪者》也不是那时候首映,20世纪50年代就引进国内了。我还查到当年地委大礼堂的图片,就在那里,1600名小学生被《405谋杀案》的开头吓得齐声尖叫。如今它远没有记忆中那么巍峨,考虑到我当时小小的年纪,这也很正常。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偏离事实的太多迹象。然而我终究不能像纳博科夫那般,像总经理听取属下汇报那样自信满满地命令:“说吧,记忆。”
好在神经科学家又讲,由于情感的因素,比起一般的记忆,闪光灯记忆的维系时间的确强而持久——这一次,他们用实验确证了常识。然而他们没有解释清楚,同样不乏强烈的情感,婴儿为什么稍长几岁就不再记得自己为何而悲喜?弗洛伊德把人类这种普遍的生理现象命名为“婴儿失忆”(infant amnesia):极少有人会葆有自己两三岁时的记忆。
我记得一部名叫《天才宝贝》(Baby Geniuses)的美国故事片给出了一个美妙的答案:每个婴儿都是天才,他们使用一种成人无法理解的语言相互交流。但随着年龄增大,这种语言终会消失,儿时的记忆也就随之逝去。这个答案可能借鉴了心理学的观点,事实上的确有某些心理学家认为,记忆与语言密切相关,可惜这个观点缺少充分的证据。
我询问过不少人,他们的儿时记忆尚存多少。一位记者朋友说,他初中之前的记忆都很模糊。这让我立刻想起动画片杰作《头脑特工队》(Inside Out)。片中那个叫Riley的小女孩,正是在初中阶段,彻底忘记了童年时期想象出来的伙伴BingBong。不得不承认,看到BingBong在大脑的“陌生山谷”里化作随风而逝的细尘,我内心泛起了感伤的情绪。我不晓得,孩子们看那段情节作何感想。
另一位朋友是画家,她说她同样记不住青少年时期的事情,但是她能记住当年的很多情绪。后者的话提醒了我,对于我们而言,相较于记忆,情感才是更基础的东西。没有了它,我们就像没有了基座的石像,必将倾覆。毫无疑问,电影《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里的Hannibal Lecter 学识渊博,记忆力惊人,但是他不知道恐惧为何物——要么是内心没有恐惧,要么是无法辨识恐惧或理解恐惧,正因如此他成了一个心理变态者。有人曾经拿一组照片给一个囚禁中的变态杀手看,结果她一次也没有认出人们脸上的恐惧表情,直到最后她才恍然大悟:“我知道这是什么表情了。在我拿刀捅他们之前,他们就是这样一副表情啊。”
哲学家以赛亚·伯林说,他毕生无法忘记的,是八岁那年目睹一个濒死的警察被暴民在大街上拖行的可怕情景。他把那段記忆称作“终生不灭的对肉体施暴的恐惧”,而我能在他的哲学中理解恐惧。我相信,正是从童年时期的电影里感受到的恐惧,很早就帮助我试着去了解、去反对、去同情。
和有些朋友们不同,我还保存着不少儿时的记忆。我没有忘记,那时候的孩子大多独自去上幼儿园。就在我必经的小巷口,贴着电影海报,也贴着法院的布告。站在下面我仰头看院长的签名、大红的公章,往上是犯人的姓名和罪行,还有名字下用红墨水画出的短线。以前大人讲过,勾了红线的就要枪毙,当地人叫做“敲砂罐儿”。紧挨着的便是电影海报。
电影与现实,形成了一种对应。记得夏天的某个晚上,我和同学们看完《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学生包场从电影院出来,听见身后杂乱的脚步声由远至近,我近乎本能地猜到了那是些什么人。当她们跑过身边,路灯下我忽然发现,她们就像从我刚看的电影里跑出来的角色,一样年轻,一样焦虑。之前我见过她们,背着装满竹器的背篓,手上挽着四五个藤编的果篮,从乡村来到城市,准备在码头上和游客做买卖。姑娘们一般在桥洞下歇息,游轮夜里一靠岸,她们就到趸船边怯怯地逡巡,期望卖掉一两件手工艺品。更多的时候,她们四下奔窜,躲进一条条黢黑的巷子里。
如果晚生两三年,我可能就不会见识到那些场面了。两三年后,《雅马哈鱼档》里的“社会闲杂人员”也可以有立足之地。再过几年,正面描写个体户的《珍珍发屋》已是波澜不兴。压抑的东西开始消退,以稍有距离的方式出现在电影里。譬如《芙蓉镇》《少年犯》,譬如《人生》《老井》等等。记忆是高度情境化的,回想起来那时候我的内心似乎真的少了恐惧。
然而差不多同时,观众对电影的热情也在消退,电视很快取而代之,成为更主流的观看方式。影院里的新片越来越少,到后来主厅大门紧闭,偏厅干脆改成录像放映。随着欧美港台既新奇又粗糙的影像大量出现,我学会了逃课,也学会了在《杀人蜂》《猛鬼街》《第一滴血》中远距离地享受恐惧。录像厅门口,我经常碰见另一个逃课的同学。他喜欢所有的琼瑶片儿,竭力向我推荐林青霞,什么《我是一片云》,什么《雁儿在林梢》《彩霞满天》,我却对他说,你的选择比恐怖片还恐怖。
为了省钱看电影,我用光了零花钱,午餐也省到了极致,成天还琢磨怎样逃票混进影院的门路。我记得市文工团比较好混,它的一扇小门就开在街边,穿过一条逼仄的过道,我能够悄无声息地溜进乐池。一想到好几部电影我都是在乐池里仰着头看完,脖子酸痛的感觉复又泛起。
有一天我在文工团的大门口看见一张巨幅的海报,上面写着本剧院即将上演曹禺的话剧《原野》,导演张辛欣,这让我非常吃惊。张辛欣的大名我在《文汇月刊》里见过好几回,很新潮的一个女作家,她怎么会到这个小地方来执导一出话剧呢?我当然想溜进去看看。可那是话剧呀,我没机会躲到乐池里去。我不甘心,在那扇小门前几度徘徊,某天下午,我竟然进去了,看到的却是电影版的《原野》。
晚上或者周末,像《神秘的黄玫瑰》《伦敦上空的鹰》《野鹅敢死队》和《逃往雅典娜》这一类的译制片依然吸引着大批观众。但是平常日子里,尤其是白天,各个电影院门可罗雀。不久我注意到,正是这萧条的缝隙,给了国产电影成长的机会。电影院的海报栏里,开始出现陌生的导演和新奇的片名。高中那三年,我和几个一起翘课的哥们儿,成天晃荡在电影院门口,一边玩着街机,一边等着进场看“探索电影”——那是《大众电影》里一篇文章给出的概念。张暖忻的《青春祭》、陈凯歌的《黄土地》、黄建新的《黑炮事件》,还有《假脸》《红衣少女》《城市假面舞会》《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等等,都是在那段日子里看的。空空荡荡的影院,只有我们几个少年人。打那以后,电影给我的情绪,就像某个雨后清凉的夏夜,我们看完《最后一班地铁》后的感觉,多了一丝可贵的迷惘,也多了一份醉人的寂寞。
印象很深的还有八十年代末公映的《黑楼孤魂》。看惯了录像带里的恐怖片,我倒未被其中的桥段吓到。只是那以后,我对电影的兴趣没那么大了。也不知是否巧合,自那以后,“探索电影”也接近了尾声。
待我意识到这一点已是多年后。一个名叫“The The”的英国乐队这样唱道:“救救我,救救我……為什么爱情总是不如恐惧那么深入人心?”不知为何,我忽然明白,就在那时,我的少年观影史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