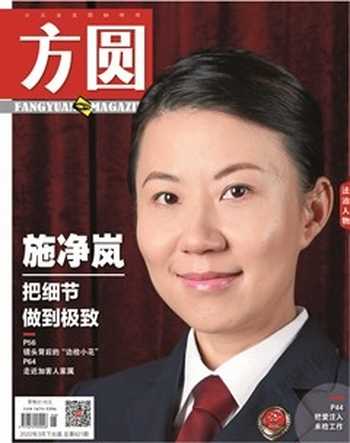盲人跑团的助跑员
李婷婷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里有一支盲人跑团。他们大部分是半盲,眼睛或多或少有一些光感,余下的全盲盲人里,有一部分因为先天失明,从小没跑过步。但到了奥森,只要有助跑员,他们就能以最快的速度奔跑起来
想象一下,当闭上眼睛,你要怎么跑步?
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就被蒙上眼睛,在另一个人的陪同下跑了100米。那绝对是我这辈子跑过最惊心动魄的100米——我扒着旁边人的手,整个人摇摇晃晃,就像踩在一颗球上,每迈一步都哆嗦。
我是以助跑员的身份加入了一个助盲跑团。在一份全国百大跑团名单里,这是唯一一家由1000多位盲人和1000多名助跑员组成的公益跑团,每周在奥森晨跑两次。蒙眼跑步便是新助跑员的培训内容之一。当体会过闭眼跑步有多吓人——哪怕是踩到一个凹凸不平的井盖,就够让人心慌的,而奥森5公里跑道上有32个井盖——你就知道作为一名助跑员责任有多重大。
但第一次参加晨跑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低估了盲人。实话说,如果不仔细观察,你很难辨认出谁是盲人谁是助跑员,只有团服背后的字样把他们区分开:一部分写着“视障”,一部分写着“助盲”。大家两两分别握住一条绿色绳子的两端,绳长30厘米,没有弹性,柔软不勒手,两端做成手环状——助盲绳摆动起来,跑步也就开始了。
我跑在了速度最慢的五队的最后面。不是我不想往前跑,而是我根本跟不上前四队的速度。我甚至得感激这天新来的一位盲友,为了照顾这位第一次来跑步的盲友,他和他的助跑员只需要慢跑3公里,我跟着他们俩跑,其他人则要跑5公里、10公里、15公里甚至20公里。
开跑前,助跑员先问他的视力情况,“我是全盲。”他说。助盲团里,70%的盲友都是半盲,眼睛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光感,余下的全盲盲友里,有一部分因為先天失明,从小没跑过步,“以为跟走路一样,走得高一点就是跑步了。”一位助跑员说。有一位盲友平时用惯了盲杖,突然撤走它,路也不敢走了,助跑员用手掰着他的腿,教他先抬腿,再往前迈,一切得从走路学起。
出乎意料地,新盲友跑得非常顺利。虽是第一次跑,但他完全不害怕。助跑员一左转,他通过助盲绳就能捕捉到左转的信号,身体也自然地左转,几乎不需要言语上的指引。当踏过第一个井盖,助跑员问需不需要提醒,他说不用。唯一异样的是拉着助盲绳的左手,无论助跑员怎么提醒,盲友的左手始终不能像右手那样自然地摆动。后来我才知道,新盲友是一位按摩师,之前他在广东一家按摩店上班,总跟着视力正常的同事去逛街、爬山,左手习惯搭在别人身上。出门多了,胆子就练大了,也敢一个人出门,但今年10月他搬来了北京,人生地不熟,出门是不敢的,只好在按摩店里来回踱步,直到和一位同事聊起来,“他说他参加的一个跑团还不错,我说那就去看看嘛。”
大部分盲友都是按摩师。他们平时分散在北京各家按摩店里,为了今早的跑步,有的因为按摩店在郊区得提前一晚住进市区;有的不善出门,花30分钟才走进地铁站;胆大的独自拄着盲杖就来了,也有的需要两两搀扶。但到了奥森,只要有助跑员,他们就能以最快的速度奔跑起来。
团长何亚君是助盲团里跑得最快的全盲盲友。他41岁,跑15公里的平均配速是4分44秒,当他跑起来时,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通过那根30厘米长的助盲绳,助跑员抬一下胳膊,他就知道前面有一个减速带。

何亚君也是一位按摩师,7年前开始跑步,是一位顾客邀他到奥森参加一场助盲欢乐跑公益活动。当时他在北京待了12年,不仅跑步是第一次,连走进奥森都是第一次。很快,身高1米76、体重190斤的何亚君拽着助盲绳跑了起来,越跑越兴奋,5公里跑完,何亚君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旁若无人地在终点处喊:“我没跑够!我要继续跑!”
而今,何亚君瘦了50斤,带着助盲团在有952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奥森公园里跑了6年。奥森分南北两园,道路曲折、有挑战性的南园才是他们的主场。对盲友而言,仅凭脚感和声音就可以辨认奥森——第一公里有一个缓缓的上坡,会经过一座桥,桥下有流水声,两公里处有一个左转弯,三公里处又有一座桥,快到四公里则有一片芦苇塘。
早上8点半,跑出去的盲友和助跑员又回到了奥森南门口。有盲友来不及换掉汗湿的衣服,也来不及做拉伸,套上外套,背上背包,就匆匆往地铁站赶,10点按摩店就要开张,今天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晨跑结束后,我跟着盲友刘冲一起坐地铁回了按摩店。
刘冲很腼腆,36岁,总是笑呵呵的,跑完步,他掏出装在背包里的小面包,分给了我一个。他一出生眼睛就只有一点光感,能模糊看到我穿的是白色上衣,手机凑到脸边也能看见。等地铁时,他找了一根柱子,脚掌压在墙面上开始拉伸。这天他跑完20公里后已经9点多了。

2020年12月,刘冲和盲友南倩结了婚。两人因为跑步才热络起来。南倩也是按摩师,但和刘冲不在一家店里。 夫妻俩性格迥异。刘冲不爱出门,除了去奥森跑步,他就待在按摩店里,听新闻、听小说,前段时间刚听完莫言的《生死疲劳》。他最害怕逛商场,“跟迷宫一样,有时候进去了,出来还是个问题。”南倩外向得多,虽是全盲,但她是那种去海边玩会拉着绳走到海中间的胆大姑娘,最开始跑步也是为了去奥森玩。她出门不带盲杖,理由是她不太会用,而盲杖只会让更多人注意到她是个盲人,有几次她听到路人议论她是瞎子,“我的自尊心非常抵触。”
关于出门这件事,夫妻俩争执过几次。刘冲的意思是,让南倩找个看得见的朋友带她出门,但南倩就想二人世界。一次夜里10点下班后,夫妻俩出去吃宵夜,两人走着走着,刘冲突然从快一米高的马路牙子上掉了下去,虽无大碍,但吓得南倩不敢再勉强他出门。
那怎么还敢跑步?我问刘冲。他一时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列举了很多理由:按摩师的工作只动上半身,下半身都生锈了;经常吃宵夜吃出了小肚子;体质差,总是感觉很累。直到他说起自己真正的第一次跑步,不是在奥森,而是在南京大学的操场上。当时他上班的按摩店就在附近,一天早上,无来由的,他摸索进了南大,学生还没起床,他在操场上突然撒丫子跑了起来,腿还有点外八,三四圈之后,“又累又喘,但感觉还挺好。”
7年前第一次跑步的时候,何亚君已经是一家按摩店的老板。虽是全盲,他还能切菜、做饭、拧螺丝,给刚出生的儿子洗澡。
我第一次见到何亚君那天,碰巧是国际盲人节。当时他刚做完一场按摩,坐在按摩店前台吃外卖。为了方便跑步,他把第二家按摩店开到了奥森对面,连招聘员工,其中一项要求都是愿意跑步。那天,他的手机不停发出读屏软件的声音,语速比常人快了五六倍,他把手机放在耳边听,对我说,“群里有人说节日快乐,今天是国际盲人节嘛,我说过什么节啊,我们和别人没什么不一样,我们眼盲心不盲,我从来不把自己定义成盲人,所以该玩的玩,该吃的吃。”
2002年刚到北京头三个月,何亚君只挣了150块钱。当时他22岁,一个人从四川老家来北京学按摩,他住在按摩店里,北京的亲戚问他,有钱花吗,他硬气地回,有钱花。第一个月挣到的钱,他全部寄回老家给了父母。尽管对于父母当年因为付不起2万元手术费以致他15岁眼睛彻底失明这件事,他始终耿耿于怀,至今都无法当面喊出爸妈这两个字。在北京的头三年,他春节也不回家,一个人在几百平米的按摩店里躺了7天,每天吃泡面,听屋外喧闹的炮竹声,然后莫名其妙流眼泪。
“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被打垮以后,那真的是太可怕了。”现在的何亚君已经能云淡风轻地讲自己的故事,坐在自己参与设计、墙面是竹纤维板的按摩店里,他说,“所以我才要跑步,我认为跑起来的不是身体,首先精神世界要跑起來,才能带着你的肉体一起跑。”
盲友周玲就是在2014年那场助盲欢乐跑公益活动上认识了何亚君。她记得受邀的盲人只有5位。当时51岁的周玲是被助跑员哄着跑完的,累得“那腿都不是我的了”。但接下来的每一个周六,周玲都拄着盲杖,坐3站公交,倒4站地铁,一个人来到奥森。
那时何亚君还没成立助盲团。在奥森,周玲收起盲杖,找到跑道和水泥路中间凸起的路缝——她的眼睛尚能感知到一米内的事物,看不见彩色,只有黑和白——她踩着路缝慢慢走,听到旁人的跑步声,她就慢慢地跟着跑起来,那声音就像助盲绳一样牵引着她,直到别人跑远,她再停下来慢慢走。
“能享受一天,就是这种还能看到一点光的日子,我就出来,说不定哪一天连这些都享受不了了,对不对?”周玲说。23岁那年她确诊了视网膜色素变性,当时她已经是一名护士。视力逐步变差后,她的岗位也不停调转,从冠心病监护病房,到心电图室、内科门诊部,最后是电话咨询部。她当然为此痛苦过,但“最重要的,还是社会里有一个自己的位置”。为了证明自己能行,她什么事儿都自己做,独自一人带着盲杖上班,下班就去菜市场买菜,用手摸出西红柿的甜度。仅有的一次,她不得不打电话让丈夫送她上班,当时她误入了小区乱停的车堆里,被困了半小时,最后发现,离平时的路线只错开了1米。
宋海峰当了5年助跑员,准则是“让盲友提起你就想笑”,为此他还真准备过段子、笑话、脑筋急转弯。但在3万人开跑的北京马拉松赛道上,当一个合格的助跑员并不容易。为保证盲友安全,4个助跑员要围住1个盲友,一人用助盲绳牵引盲友,其他人则要中途变速去补给站取水。
“有一次,那人就永远在我5米后,水就那么拿着送不上来了。”助跑员鱼哥说。鱼哥51岁,是一名律师。在助盲团里,鱼哥是出了名的好脾气。一位半盲盲友想报名厦门马拉松,对他说,“我想在眼睛完全失明前去看大海,看鼓浪屿。”他当即决定自费去陪跑。到了厦门,他先带盲友去摸了摸海水,盲友还兴奋地“试喝”,“鱼哥,海水真是咸的。”听到这句话,鱼哥有点伤感,“我们正常人唾手可得,甚至忽略不计的东西,对许多盲友来说却是梦想。”
如今鱼哥已经助跑过不下15个全马。2019年的北马,他撺掇一位在北京当按摩师的女盲友和她在河北老家照顾老小的丈夫一起跑马,“在马拉松的赛道上你们携手出现,以后在生活的马拉松也照样一起走到终点。”他组了一个8人助跑小分队,艰难地协调所有人的配速,安全地把夫妻俩送到了终点线,“我就觉得这个北马是最幸福的。”
每回晨跑,除了跑步的人,助盲团里还有看包、倒水、手工编助盲绳的后勤组。61岁的贺姐曾是其中一员,在跑团里得到了“贺铁腿”的称号。“我爱参加这些志愿活动你知道吧,干点活什么的,别让我管事,你让我干活行。”
鱼哥陪团长何亚君跑过两次全马,但现在,他的速度已经跟不上何亚君了。刚跑步半年,何亚君就参加了第一个全马,到了终点累得口吐白沫,歇了一小时才缓过来,如今跑了七十几场马拉松后,“跑完一个马拉松回去还能连续做十个(按摩)”。但这次北京马拉松,何亚君征集了半个月也没找到助跑员。他的全马最好成绩是3小时25分。眼下正是最尴尬的时段,只有3小时以内的跑者才能给他助跑,这样的跑者算是马拉松高手,每跑一次都想破自己的纪录。
何亚君也想突破自己,不愿意降速,哪怕是平时的奥森晨跑也要全速前进。在奥森对面开了第二家按摩店后,他碰巧遇到一位住在按摩店楼上的60岁退休警察,警察也陪他跑过一段时间。何亚君最信任的助跑员狼哥,助盲团一队队长——可以做到助跑时不绷紧助盲绳,让盲友感觉不到绳子的拉扯,就像在笔直、平坦、无人的大马路上尽情奔跑一样。
10月底,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奥森晨跑取消了。不能去奥森跑步的日子,58岁的周玲就出门爬山,或者在家小跑1小时。在发给我的视频里,她手舞足蹈地在家里的瓷砖上原地踏步。
北马延期之后,何亚君一个人坐飞机去了成都,参加盲人医疗资格证考试,他还学会了游泳。但何亚君依然喜欢户外。他爬过19座大山,还和朋友包车在滇藏线玩了9天,借助风声,他能感觉到四周辽阔,整个人由此变得无比放松。他跑过最远的一个全程马拉松,是2016年受邀参加的西班牙巴塞罗那马拉松。他对弥漫在那座城市的香气印象深刻,“跑到哪条街都有一种香味。”在足球场里,他还看了一场梅西上场的比赛。
那些跑马拉松得来的七十几块奖牌,曾并排挂在何亚君开的第一家按摩店里,像一串珠帘似的,拨动一下就叮叮当当。所有比赛里,他最喜欢北京马拉松,因为比赛的起跑点就在天安门广场。31年前,他只有10岁,跟着父亲从四川老家来北京治疗眼睛,顺便去了一趟天安门广场。那时他的眼睛还有一点光感,“我隐隐约约走到跟前看,地上摆了很多花团,各种花,各种彩灯、彩旗,我特别喜欢那种气氛。”当何亚君再一次站上天安门广场,置身3万名跑者之中,和所有人高唱国歌,制造出巨大的脚步声,终于,他也成了这声音的一分子。(本文由“谷雨实验室”特约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