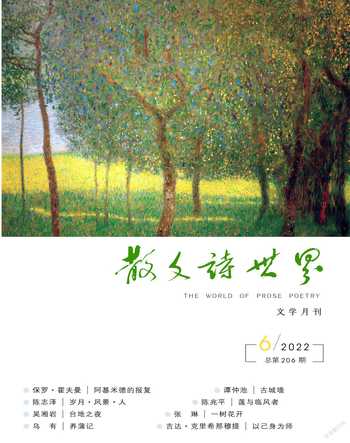岁月·风景·人 七章
陈志泽
走进天后宫
在湄洲岛,在你的升天处,我寻不见你远行的身影。但我知道,你播下的福佑随着大海的波涛没有边际涌溢漫流。
在中国沿海和东南亚一带,为祀奉你而建造的“顺济宫”寻常可见。一位赤贫如洗的农家女,被尊称为妈祖,进而天妃,进而天后,成为拥有最多“房产”的天下最富有、最高贵的女性,真有点不可思议。
泉州天后宫成为闯海人心目中的女神最高规格的居所——
矗立在大海的惊涛骇浪之上,在妈祖的圣名与传奇故事之上。
牌楼式的山门,门后筑有戏台,仿佛随时锣鼓声响彻。热烈,吉祥,迎来虔诚的膜拜。
山门两侧秦宫汉阙的构筑,浮雕麒麟,似乎从未停止过跳跃。雄伟、华美,引人入胜的立体歌谣。
正殿内34根圆形粗大的花岗岩石柱,托举起排除人间疾苦的信念,在殿中央天后神像的光辉里壮丽耸立……
安平桥
千钧重石一块块从水中浮起,铺排出五里长桥。
八百年岁月之水漫流不息,涟漪的游鱼在石板上轻漾。从不间断的脚步,蹚着时光的波浪穿行,磨砺出石板光亮如镜……
不必细说安平桥是世界上中古时代最长的梁式石桥,也不必称颂它是中国现存最长的海港大石桥,望一眼这“天下无桥长此桥”的杰作,想象宋时此地繁荣昌盛。在桥上穿梭,谁不心潮澎湃,血脉贲张?
肆无忌惮的恶浪撕扯不了牢固的桥墩,随心所欲的雷电炸毁不了岩石的坚硬。
什么样的风云没有从桥上滚过?战马的铁蹄、百姓的赤脚,商贾、渔人、农夫、“过番人”的笑声抑或泪滴不曾在桥上印染?
安平桥是一架巨无霸的琴,八百年弹奏着多彩的旋律。
安平桥是劳动者双手安放的壮丽通道,今日沐浴着新时代的阳光,人间的欢乐随意通行……
镇守
一尊依山而琢的寻常石像。一位裴氏道人盘腿而坐,目光在一处岩洞口燃烧,目光探照幽深的洞,目光翻遍四面八方的风吹草动,目光穿透前方叠嶂的山、迷茫的水……
自宋至今寸步不移坐于原地,未曾熄灭搜寻的警觉。
到这里来的敬仰者谁不赞叹,这一位裴道人追捕吃人的大蛇,直至把蛇逼进洞穴并且索性就在洞口坐化了——从此他用他的魂永远镇守。
这一个人称蜕岩的岩洞,千百年矗立,无异于裴道人的一座丰碑。
林木因它而肃穆,野花因它而红艳。
夜晚,星月落下最后的泪珠隐去;清晨,白云垂挂洁白的素绢……
一种坚如磐石的镇守,一种对于害人虫永远的警醒,照耀千古。
一位女全科医生
她是这块小小土地的一棵绿树。她是社区人们大拇指上的最美医生。她的名字叫“阳阳”。即使是患者病痛如山,她的明丽也会推倒重压殷殷映照。即使是疫情如铁,她的光和热也会进击坚硬而挺立。
亲切的凝视瞬间就消融了求诊者脸上厚厚的愁绪。
专注的问诊三言两语就驱散盘踞在病人心头的烦恼。
宽慰是她医者仁心的由衷滋润,医术是她清除瘟神作祟的利器。
听诊器展开明亮的触须探测人体内哪怕是隐藏在暗处的声音,冷静的辨析扫却了遮蔽病情的哪怕是一丝半点云翳——作为一位久经磨练的全科医生,这样那样的难题她都能对付,处方笺刷刷划出疗治的精准判断。
许多人直呼其名,把她看作自家人。她那很阳光的微笑可是源于她响亮的名字?她那暖人的询问与叮嘱可是来自她名字里那后羿射不落的火球?她的全科通吃的“全”,可是因了当年医科大学的攻读早已刻下了理想的谱系?或是得到过什么神医的稀世真传?依我看这是艰苦繁杂的基层医疗工作干出来的,更是因了怀揣“为人民服务”的太阳使然……
黑与白
长街上与一位老友不期而遇,我仔细端详他好久。
他的圆脸边上,一圈白发鲜明地显现在浓重的黑发中,犹如晨光驱赶着黑夜,像是冰雪驱赶着土地上的芜杂……
黑白之间,我看到了一种从根部生长的强大的白,而黑正在无可奈何遁逃。
未等我开口,老友笑着叹道:“不染了”。
黑白之间,我看到老友生命力的旺盛,更看到他对于美的探索与追求。
我不自觉地抚一抚自己头上那些黑不黑、白不白的稀疏枯草,幽默道:“我指望早日一片光明。”
长街上我俩一阵朗笑荡着太阳的俯瞰,边走边聊,踏出长风……
老
生气勃勃绽放了一脸黑蜡梅,老在深深的皱纹里很有气势地流淌。
头顶上的银丝挑逗着阳光,浓密在嬗变为稀疏,为了腾出更多空地接纳天上的飘流物。
脚步轻重缓急敲打石板路的琴键,奏响悦耳的旋律,一不小心,踩响了一个雷,毁了杰作,但毫不气馁,又从容不迫踏着五线谱,续写生命的约稿。
大清早,一只鹧鸪浑厚的啼鸣和一位老人粗重的呼吸相应和,在晨练中断断续续,起起伏伏。
入夜,一位老人陷在沙发里,打盹的头有力地叩问人生……
一个男人的命运
得了重症,就躺下了。把无用的烦恼睡干净,把山摇地动睡安稳。
睡,睡,妻子只能在他床前丢下影子,摇摇头走开。
女儿无法忍受家里的死寂,撞进歌舞厅的热烈,让强音冲洗烦恼。
睡,睡,一种醒着的睡,一种睁着眼睛的睡,一种咬着牙的睡。
女儿日夜探戈,探了个哥就很少回家。妻子到外头寻找指望去了。
家里空了,空得只剩下一个爱睡的男人——他把一切遗忘,一切也把他遗忘。
倒是人们没有遗忘他——有一天社区的人员进入他的家门,把他唤醒——养老院添加了新成员——没多久,他每天在护理人员的搀扶下,走向大楼的走廊——在明亮平坦的道路上,一趟趟往返,丈量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