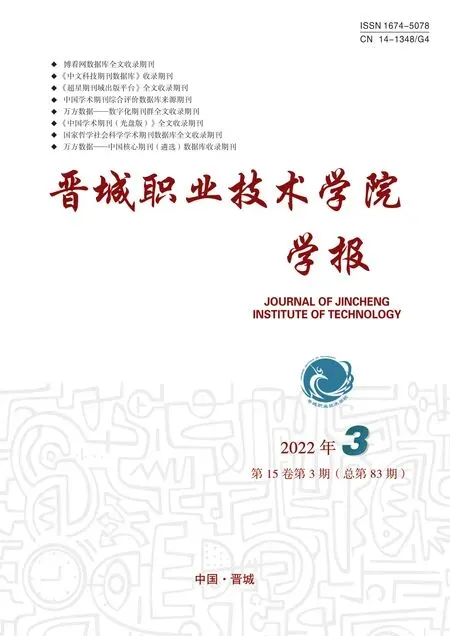大学生心理骨干感恩与助人行为的关系: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
陈 梅
(广州华商学院,广州 511300)
随着新时代的发展,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一项关于“〇〇后”大学生心理普查结果显示:近半数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1],自杀是大学生第二大常见死亡原因[2]。而当大学生出现心理问题时,首选倾诉或救助对象是朋辈群体。[3]大学生心理骨干由心理组织干部、班级心理委员等组成,由于同龄人的天然优势,在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工作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是高校心理健康工作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力量。大学生心理骨干从事的工作是助人自助的过程,目前从助人行为的角度来探讨大学生心理骨干的研究比较少,因此探讨大学生心理骨干助人行为的影响机制,强化其助人行为,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感恩是指当个体受到他人恩惠时,个人内心产生对他人的感激之情。[4]感恩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热点,感恩作为人类的积极情感,具有道德激发和道德强化的功能[5],对个体的助人行为起到积极的作用[6],提高个体人际关系质量,提升个体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水平[7]。根据艾森伯格的亲社会行为理论模型,感恩作为一种稳定的积极的人格特质,是助人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8]已有研究表明,感恩是个体助人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9],相对于低感恩水平的个体,高感恩水平的个体有更高的助人行为。
感恩和助人行为的关系已被以往的研究证明,以往有关感恩和助人行为的研究往往从共情[10]、社会支持[11]等角度来探讨其中介过程。例如感恩不仅直接影响助人行为,还通过领悟社会支持间接影响助人行为。[11]而生命意义感可能为解释感恩和助人行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生命意义感(Meaning in life)是指个体感受到自己的生命有意义和价值,以及意识到自己生命的目标和使命,包括两个独立又互补的维度,拥有生命意义感和寻求生命意义感。[12]根据生命意义感理论,生命意义感是助人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13]现有相关研究表明,生命意义感和助人行为密切相关[14-15],生命意义感高的个体,有更高的助人行为。刘亚楠等人研究亦发现感恩与生命意义感存在正相关关系。[16]这提示了生命意义感可能在感恩和助人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鉴于此,本文推测感恩通过生命意义感来影响大学生心理骨干的助人行为,并提出假设:生命意义感在感恩和助人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本文以大学生心理骨干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感恩对助人行为的影响机制,考察了生命意义感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以期强化大学生心理骨干的助人行为,提高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2021年9~10月,采用整群取样法,选取广东省某高校的大学生心理骨干作为被试。通过线上问卷调查的方式,发放给学生作答,剔除无效问卷(在问卷中设置题目:请选择“完全同意”选项,没有按要求填写,视为无效问卷。),共回收527份有效问卷。在527名被试中,男生88人(16.7%),女生439人(83.3%),被试年龄17~24岁。
(二)研究工具
1.中文版感恩问卷
选用2002年我国学者魏昶、吴慧婷修订的中文版感恩问卷[17],共6个题目。采用七级计分法,分数越高代表感恩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为0.826。
2.生命意义感量表
选用刘思斯和甘怡群修订的生命意义感量表[18],分为拥有生命意义感和寻求意义感2个维度,共9个条目。用七级计分的方法,分数越高说明个体的生命意义感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α为0.804。
3.助人行为倾向问卷
采用2006年付慧欣编制的助人行为倾向问卷[19],问卷设计了8个需要帮助的情境,每个情境后有一道题目。采用四级计分的方法,每道题目分数相加即是助人行为倾向的总分,得分越高代表个体助人行为倾向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α为0.632。
(三)统计处理
本研究采用SPSS19.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并使用Hayes编制的PROCESS进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采用Harman单因素法来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有5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其中第一个因子方差解释率为24.76%,小于40%,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二、研究结果
(一)感恩、生命意义感和助人行为的相关分析
对助人行为、感恩、生命意义感进行相关分析。由表1可见,感恩、生命意义感与助人行为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p<0.01),三者之间的关系密切。

表1 感恩、生命意义感和助人行为的相关分析
(二)生命意义感在感恩与助人行为的中介作用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感恩、生命意义感和助人行为两两正相关,可以进行下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以感恩为自变量,助人行为为因变量,生命意义感为中介变量,以人口学变量性别为控制变量,利用Process宏程序中的模型4对中介模型进行多层次回归分析,重复取样5000次,计算偏差校正的Bootstrap95%的置信区间。
结果表明:感恩对助人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β=0.1759,P<0.001),当放入中介变量生命意义感后,感恩对助人行为的预测作用依然显著(β=0.0918,P<0.01)。感恩对生命意义感的预测作用显著(β=0.6090,P<0.001),生命意义感对助人行为的预测作用也显著(β=0.1381,P<0.001)。感恩对助人行为的直接效应和生命意义感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括0,表明感恩不仅能够直接预测助人行为,而且能够通过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预测助人行为。直接效应(0.0918)和中介效应(0.0841)分别占总效应(0.1759)的比例是52.19%和47.81%,见表2、表3和图1。

表2 大学生心理骨干生命意义感在感恩和助人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表3 生命意义感的中介效应

图1 中介效应模型图
三、讨论
(一)感恩、生命意义感和助人行为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心理骨干感恩与助人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正向预测助人行为。根据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在积极情绪状态下,个体能够理解他人的困境,增强同理心,进而产生助人行为。[20]感恩是个体能认识到他人对自己的帮助,个体内心产生感激之情,是一种重要的积极情绪,能调动更多积极的心理资源,容易理解他人的需求,对他人产生移情,对他人的不幸事件产生强烈的共情反应,从而激发个体助人行为的内在动机,促进助人行为。感恩与助人行为关系密切,具有高感恩水平的个体会有更多的助人行为,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均证明了感恩是助人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21][22]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心理骨干感恩和生命意义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23]感恩是一种积极的个体资源,高感恩水平的个体有更多的活力、更少的负性情绪、乐观,对生活满意度更高,更容易、更频繁地经历和表达感恩之情,更加明确地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提高了个体生命意义感。
本研究还发现,大学生心理骨干生命意义感和助人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近年来很多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了生命意义感和助人行为之间密切相关,生命意义感正向预测助人行为。[15]生命意义感是人类的基本动机之一,对个体身心健康有重要的影响。较高生命意义感的个体,心理健康水平更高,更多关注他人和社会需求,激发内在的助人行为动机,从而产生更多的助人行为。
(二)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感恩对大学生心理骨干的助人行为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且感恩会通过影响生命意义感间接影响助人行为,生命意义感在其中起中介作用。感恩作为一种积极情绪,可以启动和拓展个体的认知,能够扩大个体的注意范围,增强认知灵活性[24],提升了个体的生命意义感。根据认知行为理论[25],个体对事件的认知决定了个体的情绪和行为,生命意义感属于自我认知的内容,对助人行为起重要作用。柯维和史密斯认为,生活的意义与助人行为密切相关,帮助他人、服务社会其实是个体追求和实现幸福的过程。[26]由此可见,生命意义感对促进大学生心理骨干的助人行为起关键作用,在感恩与助人行为之间起连接作用。生命意义感中介了感恩对助人行为的影响,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可以从直接路径出发,通过提升感恩水平,促进大学生心理骨干的助人行为,还可以从间接路径出发,通过开展生命意义教育提升大学生心理骨干的生命意义感,以便在激发其感恩的情境下来增加助人行为。
四、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发现,生命意义感在感恩和大学生心理骨干助人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即感恩不仅对大学生心理骨干的助人行为产生直接影响,还通过生命意义感间接影响大学生心理骨干的助人行为。
大学生心理骨干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起重要的作用,因此促进其助人行为,对推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高校教育工作者可以从感恩和生命意义感两方面入手,开展系统的感恩和生命意义感为主题的心理训练和团体辅导活动,以此促进大学生心理骨干的助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