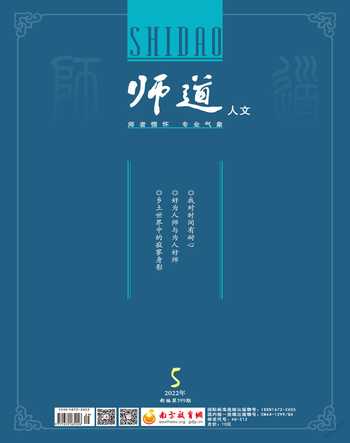流行语镜像中的文化面相(三十八)
古北
“爹味”上的可不是什么好菜。在家庭饭桌上,它原本就是一道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菜肴,只是面前区区几盘,不容你忽视或躲避。但在社交聚餐中就不一样了,美食繁多,对吃不下看不惯的“爹味”,完全可以置之不理,转啖其他心怡菜品,舌暇或再对之鄙薄一番。“爹味”如何叫人反胃?其堆叠的是陈旧的学识,吹嘘的烈火烤就焦黄的外皮;浇头的是自恋的蚝油,绕几圈往事兜转意难平;飘浮的是“为了你好”的一缕热气,隔绝的却不只是一个世纪的互为陌生。一匙于口,只觉厌腻,咬之更是老柴難咽。
“爹味”一词成为流行时间并不长,然而“爹味”的气质早已是流布广泛,根深蒂固。或是做爹后方才激活的某种遥远记忆,口吻突然间对上了其父之口型,自觉亲切流利,势如破竹,奇迹般屏蔽早年在他口水下的湿漉难堪以及眼前这位新少年的手足无措。或是未做家长就“父魔”上身,侃侃而谈,头头是道,自觉少年老成,志得意满。此等好为人师者,常以苦口婆心自我感动,径视闭目塞聪或反唇相讥者为懵懂顽固之徒。最讽刺莫过于浩叹观众“怎么就听不进去”,殊不知将自己围囿起来的正是“听不进去”,而失却自我反省之力,也使“爹味”在“叛逆儿女”的漠视和反攻下越演越烈。
“爹味”的流行,使以热衷指示为基本特征的“官样”受到人们更多的注意,其从家庭到公众、从男性到女性的扩散,更使人意识到这种喜欢摁着别人的头的控制欲蔓延极广,展转无穷,在暗地里悄悄支配着人性。“爹味”的一触即发使“人均爹数”超标,互相尊重几近可遇不可求。那张在“爹味”蒸腾中拉扯得变了形的面子,拾掇起来手忙脚乱,唯一的出路就是让它继续摊放着——“栩栩如生”的“爹味”没有规则,没有边界,只有“我”的声嘶力竭和“前浪”的死有不甘。
“爹味”的弥漫和带来的广泛批评,也使人更有机会关注和追索“爹味”的始发地,对在父子关系中伤痕累累的那个孩子更具同情。当人们认为“爹味”发射塔的根基来自原生家庭的家长作风时,这个问题也有了关于新旧两代人观念必然交战的讨论分翼。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父方在辩论场决胜的筹码,常不是理智的思辨,而是腐朽的蛮力。或许,眼看着新的价值体系慢慢建立,“老爹”们的担忧和害怕需要转嫁,并不是他们的立场毫无道理、他们的经验毫无价值,而是他们灌输的内容几乎无视年轻人自身的判断力,这样“高人一等”的说教在第一个字开启时就令人警觉和反感。总之,“爹味”的屡批不止,使那些“没有‘爹味”的公众人物更有希望成为优质偶像。而家中手持仙拂的那位到头来总落得寂寞的下场,越寂寞越伺机释放“爹醛”,像一个死局。72232DEF-F64D-401B-8CE7-D6C5B9B553A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