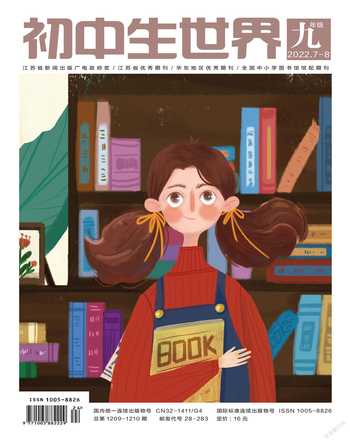走着,走着
董力源


母亲年轻的时候在服装厂工作,每天一大早便要摸黑过去,半夜要披着夜色回来。那时她年纪小,怕黑,再加上村子荒凉,月色映下了道旁树的影儿,在曲折的小路上如鬼魅般黑黢黢的。风,呼啸着,树的枝儿是光秃着的,好像神话里夜叉手中的那把大戟。
月,映着雪地,发出惨白的光。
母亲悄悄地跟四姨说自己怕黑,四姨倒是爽快:“那,咱姐儿俩一块去吧,也算是有个伴儿。”
去县城的路远,母亲与四姨相伴着去,轻松了不少。
那日,雪下得紧,四姨病倒了。母亲心中是怯的,总不肯出门,待雪小了些,才心一横,骑上车子赶往单位。
一路上,她疑神疑鬼的,总觉得有人跟着她,她也不敢往后看,只是加紧向前骑去……
晚上,是舅舅把母亲接回家的。
回到家,正见着外公给外婆拿药。
外公再出来时,母亲问他:“爸,妈怎么病了?”
外公点了支烟,却又很快把它捻熄了:“嗯,忘了这档子事儿了。”大概是母亲对烟味过敏的事。
母亲见外公答得含糊,也没有追问下去,只是一五一十地将早上的事告诉外公。
外公搓了搓大手,呼出了一团白气,目光扫过外婆的房门:“那人是你妈。”
“我妈?她跟着我干吗?”母亲似是有些不满,嘟囔了一句。
“小声点,你妈不让我告诉你。你们兄妹几个,你年纪最小,也最要强,明明如此怕黑,可偏偏不肯晚一刻钟去上班。每天你去上班,她总会默默地在后面跟着,跟到村口。她说啊,村里太黑,送你一程,她才放心。”说完,便又瞥了一眼外婆的房门。
母亲的泪,不觉涌了出来。
后来,母亲长了个心眼,每次去上班,拐过了大路,都会在一棵树下停住,偷偷回看,那熟悉的身影,在黑夜中站着,好似从未离开过一样。
再后来,母亲结了婚,去城里定了居。外公早已亡故了,母亲两次三番地劝外婆来城里住。外婆也来了一次,只是没住几天,便嚷着要回去,说是楼高不好上。
外婆回去的时候,是我送外婆下楼的。我跑得快,一溜烟已下了一层,回头再看时,心头好似被重重地砸了一下:外婆微笑着,扶着栏杆,蹒跚着,一步一步走下台阶。母亲刚出了门,站在上面扶手前,眼圈儿通红。
母亲抹了把泪,赶上几步:“妈,您慢点儿。”说着,她扶住了外婆。外婆只是笑着:“人老了,走不动喽!”
再见外婆时,已是两年后了。我们刚从南京回来,那时的外婆精气神儿明显不如以往,在平地上走着也是步履蹒跚。
她拉我和母亲去屋后的枫树林,笑呵呵地对我说:“你妈像你这么大时,还只有我胸口高,就爱在这树林子里乱跑。那时你妈还走不过我呢,她走两步就累了,我总是会回头叫她‘快点,快点。如今啊,我这老胳膊老腿的,是走不动了!”
外婆笑着,母亲也跟着笑,只是笑着笑着,泪珠就滚下来了。
该回家了,外婆照例将母亲送到村口。
我从车上回看,外婆就像一枝几近枯萎的向日葵,向我们望着,望着……
突然,我想起了龙应台在《目送》中的一句話——
“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我们就这样走着,走着,然后,渐行渐远……
(指导教师:张继东)6F173DBC-5E0E-4456-8EDA-520B1FEBBD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