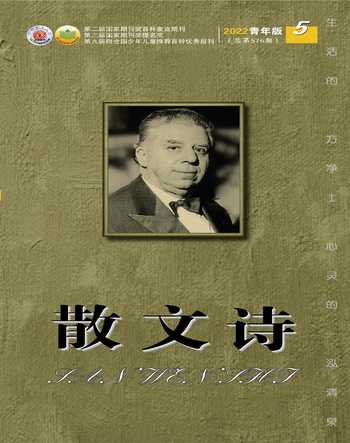雨的鸣响
陈美桥
寻 雨
雨打湿高粱吐出的火焰,旗帜举过头顶,飘展粗糙的真理。
父亲同高粱,在雨中,交替昂扬。
玉米的牙齿,吸饱雨里的钙质。而父亲刚掉的几颗大牙,迁徙到灶孔里,询问灰烬。
一颗饱满的玉米,也许能短暂填补岁月的坑洞。但老化的纤维,在齿间的磨合中,怎么都抹不平褶皱。
父亲与稻子,一样躬身。谁也追不上一滴雨的脚步。
他们善于对一场大雨,使用祈使句。谦卑,可以减少霉变的可能性。
庄稼在雨中涌动。父亲却卧倒原地,轻盈得不留痕迹。
缩小的父亲,要在旷远的大地中,寻觅一滴雨,跌落的尽头。
春 雨
雨中,氤氲着艾草的香气。
去年的刀口上,长出新苗。叶片打开的,是苦难和治愈。
苔藓裹住虫豸的肉身。绵延的雨,滑过鸟兽的沉默。田地里,有琐碎密语。
犁头上的雨,与巉崖比肩。雨,攀沿高处,也随波逐流。
老牛,把姿态放得很低。牛蜱在耳内蛰伏,那么多的痛痒,隐秘而又难言。
蹄子深入泥土,蘸蘸春雨。在前进中,改写听过的故事。
耕种的齿痕,梳理掉一些可有可无的情节。
脚下,那些深深浅浅的铺垫,是大地的肺叶,在雨中咳出的赞许。
秋 雨
在雨中,种下玫瑰。
手里涌动的热浪,会遭遇扎心的针芒。
泪滴匍匐。体内深掘的盐粒,蜂拥而至。每次悔悟,都如刮骨疗伤。
雨点砸向秋风,有些花瓣顺势而动,白出坡度。
花瓣也会凝结阵痛,耳畔鸣啭的枯萎,容不下一个“红”字。
雨滴挤进罅隙,巧妙地屏蔽,那些纠结的嗓音。
隐痛沦陷。看满坡翠绿,终究会为谁红?
当骨节一天天变硬。泥土的酸堿和湿度,不再温柔地附和。
谁还能在秋雨中,种一朵合格的玫瑰?
冷 雨
想念一个人,就像把蚂蚁放在胸口,听雨。
每一声滴答,都会在心尖,痒痒地开出花朵。
把爱从圈里牵出来,用指尖去宽恕放任的罪过。
一场冷雨,或许能稀释夜里的意乱情迷。
就像冲淡一滴蚜虫甘露,让蚂蚁不再尾随剔透的甘甜。
那些四处张望的幸福,要回归最原始的理性。
想念的人,是冷雨里,求而不得的大伞。
后背烙下的姓名,撑不起一把负重的骨架。
发肤被提示过的敏锐,在瓦楞上,叮咚作响。
把忏悔扶正,在冷雨的掌纹间,川流不息。
只有蚂蚁的嗉囊里,有一粒爱情的遗骸。
心 雨
蜗牛凄恻。雨中的触角,没有阳光映射,为难地贴近肉身。
雨的速度,偶尔会变成蜗牛的速度。
我们的行走,那样缓慢,像蜗牛把壳扛在身上。
雨能淋湿的,是生活的土壤。唯有虚张声势地填埋种子。
地铁口蹿出来的那些秧苗,多么单薄,而又疲惫。
路灯泛出的光束,是黑夜订制的外壳。
不分高配,还是低配,雨丝倾慕而来。在清洁工的脊背,弧形跨过。
一个喷嚏,不像身体发出的警告。而是雨,想寻找归途。
车轮下飞驰着雨阵。晚归的人,不敢吐出烟圈,指指点点。
黑夜,像循环不断的虚空,分不清每一场雨的来处。
那一副躯壳里生根的心雨,会不会在岁月里翻江倒海?
暴风雨
一束风的张狂,在雨中组建错误的词组。
雨还没学会内敛。风雨交织的热烈,会分娩“不幸”的后代。
于是,一条街有了河的血脉。青蛙在树杈上,诊断时间的脉搏。
当视野出现浑浊,就像眼底生了黄斑病,惊恐也汇集成雨。
趟着泥水过路,要把一双手,握成救命稻草。
风雨喋喋不休,吹捧着锅碗瓢盆。人浮于世,自当远行。
有暗影浮动,昨日与今朝,在得失之间,迂迂回回。
暴风雨,教会我做一个咸淡适宜的人。
不在这碗汤中添油加醋,不在那盘菜里偷工减料。
对于生老与病死,自然与构建,始终保持敬畏和警醒。
泪 雨
雨滴,浇灌一把镰刀对于前世的觉醒。
矿石向下,热风向上。岁月像巨大的高炉,滚滚燃烧。
铁水,喧嚷、沸腾。要趁热,敲打它的激情。
雨的冷漠,淋出一把镰刀的雏形,不灭的肉身。
雨虽无骨,却让皈依的铁,长出软肋。铁也落泪。
一滴红泪,融进青草的血液。镰的唇齿,还挂着韭菜的残羹。
废弃的土墙房,永别的人,在瓦灶间一枕黄粱。
熄灭手中的旱烟。让泛黄的手指,轻舞烟卷。
目光黯淡,仿佛前世,在倾盆大雨中微弱的灯盏。
镰的泪水,其实与雨无关。越来越模糊的双眼,被电子装备填满。争分夺秒地发射,数不清的虚拟枪支和弹药。
双手紧握着,夜里的激情。一旦摊开,就是白天的困倦。
求 雨
有时,雨滴别出心裁,将爱情的肉体,巧妙伪装。
当它落在爱人的唇上,彼此就有了滋润的欲望。
泥土的干涸,和内心的枯竭,同样焦灼。
让羊群铺满大地,绵延成空中的云朵,结出温柔的棉团。
让它们一次又一次,饱吸那些潮湿的企盼,轻易地被风,挤出水来。
稻桩,就会绽放新绿,抽出新穗。
求雨,就要做一个与时光赛跑的人。
雨,在每一枚叶片上的纵横交错,都有奔赴的经度和纬度。
雨,是无数条河流,分离过后的复归。
求雨,就不用追问爱憎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