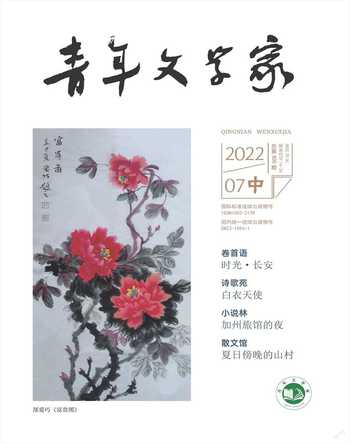从结构主义视角赏析《春夜喜雨》
阳子芯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杜甫《春夜喜雨》
《春夜喜雨》作于唐上元二年(761)春,杜甫历经“安史之乱”后,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草堂安定了下来。此时,杜甫已经在成都草堂居住了两年,当时的杜甫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亲自躬耕于田地之间,农耕的生活拉近了诗人与农民之间的距离,也使诗人有机会亲身体会农民耕作之苦。从上年的冬天到次年的二月间,成都一带发生了旱灾。经历过旱灾的人,最懂得雨的可贵。所以,当春雨来临之际,杜甫欣喜异常,以久旱逢甘霖的心情,描绘了春夜雨景,讴歌了春雨滋润万物之功。
作为杜甫最为重要的五律之一,关于这首诗的赏析可谓著述颇丰。但历来各家大多从传统的诗论的角度出发,或停留于字词训诂,或关注诗歌与作者生平、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往往忽略了对文本自身结构的细致分析。本文采取语言学批评的方法,从诗歌结构主义批评的视角,探索《春夜喜雨》阐释新的可能。
一、批评方法与文本选择
为什么要选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批评方法?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家托多罗夫提出:“世界各国的文学研究,都没有摆脱与社会发展史、思想史、创作心理学、创作社会学等学科的纠缠。”如利奇认为:“如果要对每一实例进行透彻的、卓有成效的分析,就必须了解每首诗的背景,包括作者的生平、文化背景、社会背景等。”此一观点便是文学传统研究方法的代言。现象学文论家希利斯米勒不满于离开诗歌文本研究诗歌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诗渐渐地消失在众多的组合中,诗不是自给自足的实体,而只是流行于产生诗的文化中的念头与形象的现象”(赵谦《杜甫五律的艺术结构与审美功能》)。他打了个比方,作为研究对象的诗“对环境的关系是向外辐射的,就像掉在水中的石头所引起的中心圆。这些圆圈无限地倍增,以至学者被迫沮丧地放弃给它们开个清单的企图”(威廉·K·维姆萨特《“新批评”文集》)。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文学回归本体研究的重要性。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角度看,“依经立义”、比附政治或带有现实功利目的文学批评曾产生过重大影响,而关注字词意义的训诂研究亦是显学。中国诗歌阐释长久停留于历史传统中而呈现出停滯不前之态,与其他人文学科纠缠的现象尤为严重,故新批评方法的引入是发展的应有之义。
当然,语言学批评方法的引入并不是为了要颠覆传统诗论的结论。无论这些观点有何不足,那些论诗者毕竟在时间和文学习惯上更接近杜甫。“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观点一致时,我们的任务仅仅是指出在特定的语境中产生这种观点的语言特征;而当他们的观点分歧又没有明显的证据可以平衡时,我们几乎可以断定那引起争论的词或句子具有内在的歧义。”(高友工、梅祖麟《唐诗三论:诗歌的结构主义批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关注对语言特征作出精确的描述,使现代语言学的方法和研究成果付诸实践。罗兰·巴特曾说过:“我们重建客体,是为了使某些功能显现出来。”以“新”视角看待“旧”诗歌,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式重构客体,揭示传统批评视角下忽略的细节。
为什么要选择《春夜喜雨》作为研究文本?高友工和梅祖麟在《唐诗三论:诗歌的结构主义批评》中运用结构主义语言的方法,对杜甫的《秋兴八首》组诗展开了精彩的论述。故本文延续这种批评实践,选取杜甫五律代表作《春夜喜雨》进行分析,与传统诗论形成对话。杜甫五律大多是“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文心雕龙·章句》)。关于诗歌形式的探索在南北朝时期已有体现,永明声律说对近体格律诗的创作打下了基础。近体格律诗发展至杜甫已日臻成熟,在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努力下,律诗既符合严苛的格律规定,又有着意出笔端的自由变化之态。关于五律的结构,前人论述甚多,不外是起、承、转、合之法。而杜甫所要做的是突破单一的一元结构,在已定型的形式内安排物象,同时对结构和功能进行重新分配,使此种诗体艺术产生丰富的可变性。故杜甫的五律既有诗体规范作为参照,又体现着杜甫超越规范的精巧之思,而《春夜喜雨》作为五律的代表作之一,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二、格律造虚实
传统诗论的共同看法是,全诗前三联或议论或描绘黑夜中眼前的景致,而最后一联是诗人发挥想象,想象第二天日出天晴后锦官城中花团锦簇的艳丽风光。如《唐诗鉴赏辞典》提到,“尾联诗人驰骋想象如果好雨下上一夜,万物都得到足够的水分滋长繁荣起来了,万物之一的花、最能代表春色的花也就带雨开放,红艳欲滴”。莫砺锋也提出:“面对着一场如此绵密丰沛的好雨,诗人不由得浮想联翩:天亮之后无数的花枝上堆满了沾着雨水的鲜花,整个锦官城里将变成一片沉甸甸的花海!”可问题在于,诸位批评家只是给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想象之词”究竟从何而来,我们无从知晓。如果仅仅关注字面意义,诗人并没有给出任何“想象”的证据,我们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全诗是时间线的自然延续,诗人在夜晚见证了春雨之后,次日清晨早起,看见了“花重锦官城”的景象。故成为最后一联亦是诗人眼前所见的实景。但实际上,当我们将注意力移到诗词的格律与节奏,会发现诸家提出的“想象”之论更为精妙贴合。
《春夜喜雨》全诗的用韵形式为: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五律标准的四种格式为: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观察《春夜喜雨》的平仄会发现,前三联是极为标准的基本格式,而在最后一联出现了可以允许的平仄错误。“晓”是仄声,却出现在了平声的位置上,故下联相对的位置只好采用“花”这个平声字。虽然在“一三五不论”的规律之下,这种变化可以容忍,却打破了对诗歌应有韵律的期待。且诗歌韵脚选择“庚”韵,后鼻韵母,其发音过程较长,客观上拖慢了整首诗涵咏的时间和语调,呈现出舒缓之态。而前两联的流水对,使得春雨的神韵跃然纸上,颇为流畅。行至最后一联,本应延续此种舒缓流畅之感,诗人却突然以短促的仄声起调,舒缓变为急促,流畅变为滞涩。诗人仿佛是在刻意提醒读者,此处将有转折变化。
另外,从诗歌节奏的视角,五言律诗的节奏是严格的两个双音部加一个单音部,且单音部是只能出现在句中或句末。前三联中各句的節奏都是2∶1∶2,但到了最后一联,节奏却变为了2∶2∶1,体现出一种整体节奏不一致的特点。这种不对称的现象有着一种后趋向运动,前三联的节奏几乎连续一致造成雨夜的宁静昏沉之感,而尾联节奏忽变,全诗的力量蓄积于此,成就了白日的清新明媚、雍容繁华之感。
据此分析,尾联在声律和节奏上都呈现出与其他部分颇为不同的特点。如果只是时间自然延续,由黑夜过渡到白天,过于单调贫乏。况且诗歌本身的景物变化已经可以突出黑夜与白天的差异,诗人又何以煞费苦心地安排声律和节奏的突变?故此背后一定有更为深刻之意。将尾联理解为诗人想象之作,一虚一实,实际时间聚焦于当下,心灵时间却已飞向未来,由眼前世界入头脑世界,境界便拓展开来。并且,眼前是雨夜黑暗沉闷之景,心中却是天晴阳光明媚、繁花似锦之画,差异聚焦于时间轴上的同一点,更能将诗的张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结构添诗意
上一部分主要关注声律与节奏的变化,暗指诗歌的理解层次,此一部分将从结构的视角,关注一联中的两句诗、四联组合成的诗歌整体如何通过各自的语法结构相互影响。
首先看“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这两句诗形成了一种双向的结构,可以看作两个并列的独立句子,分别描述野外天空的情况和江面上的情况,二者形成了对照;也可以看作一个连续的句子,正是天空乌云密布、春雨绵绵,才使得江上模糊一片,只能看见点点渔火。并且,上下句内部也可以各自有两种解释。理解其一:“野径”和“江船”各自点出地点,在野外小径的上空大片大片的云朵乌黑一片,在江上的渔船只有挂的渔灯可以被看见。“俱”与“独”是针对“云”和“火”而言的。理解其二:野径与乌云,江船与渔火两种意象产生了联系。在绵密的夜雨中,野径和乌云都是黑压压的一片,看不清,故曰“俱”;江上烟雾弥漫,雨水轻打江面,在夜色中船身是看不见的,只有渔火可以被远远看见,故曰“独”。由此形成了两组对照的关系,横向而言,野径和乌云对照,都是昏暗不明的,江船和渔火对照,只有渔火是明亮的;纵向而言,上下句的明与暗形成了对照。此时已经很难再将两个场景分开来了,当诗人雨夜推门而眺望远处时,在湿润的空气和一片黑暗朦胧中,只能看见远处锦江上的点点渔火。故此种对照看似分离,却将空间中分隔的两处景象融为了一体,变立体为平面上的一幅画了。此一联形成了歧义对句—“对句中每行有两种不同语法结构,而且这种结构两两成对”(高友工、梅祖麟《唐诗三论:诗歌的结构主义批评》)。歧义对句的使用不仅是为了追求经济表达,而且是“通过这种平行力场及其对句的相互呼应,诗的效果将会成倍地扩大”(高友工、梅祖麟《唐诗三论:诗歌的结构主义批评》)。律诗的中间两联要求对仗绝对工整而显得地位非凡,歧义对句形成的多义与暧昧才对整首诗的意味起着重要作用。
当然,此联诗意的营造还可以从雅各布森对等原则的角度分析。雅各布森对等原则的提出可以追溯到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索绪尔提出了横组合和纵聚合的关系,雅各布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选择”“组合”与“对等原则”三个重要概念。选择指的是“在一套由不同程度的相似性而联系在一起的符号集合中进行替换与选择,这种相似性或因同义而具有等价关系,或因反义而享有共同内核”(田星《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理论与中国古典诗歌》)。组合则是“处于同一语境下的各组成部分的连接。它依靠的是邻近性,这种邻近性与语言的规则有关,受语言结构的逻辑制约,而体现为空间位置上的序列”(田星《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理论与中国古典诗歌》)。对等原则就是指从选择轴投射到组合轴,“诗的作用是把对等原则从选择过程带入组合过程”(高友工、梅祖麟《唐诗的魅力》)。“枯藤老树昏鸦”便是对等原则造就诗意语言的最好体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这一联诗意盎然,为全诗增色不少,也正是运用了对等原则。“野径”“云”“江船”“渔火”,本是属于选择轴,诗人却将它们并置,投射到了组合轴。但是这一联的投射与“枯藤老树昏鸦”的类型又不太一样,不是单纯运用这些“直观语言的精华”取消句法传达诗意,而是将投射与句法在一句诗中结合,从而形成诗的漫游与散文的抽象相结合的风格。我们只看“野径”“云”“江船”“渔火”,并不能领悟到想要表达什么,等读到“俱黑”“独明”的时候才明白传达的意思。但此联又不是完整严谨的句法,正是这种句法的部分取消才形成了上文提及的“歧义对句”,具象与抽象的结合营造了诗意。
再来看“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一联。表面上看来这一联无论是在结构还是节奏上对仗是颇为工整的,但是深层看来却没有那么工整。“晓”作为副词,修饰动词“看”,“看”明确指向“红湿处”,对句却没有这么简单。“重”可以指向“花”,雨水使得花沾染露水而显得雍容沉重,此种情况下“锦官城”仅是点出的“花重”的地点而与其联系较为松散。如果“重”理解为使动,那么“重”与“花”和“锦官城”都会产生紧密的联系,露水让花显得娇艳欲滴,繁密而沾满露水的花也将锦官城衬托得雍容华贵了。“一个句子中的语法关系包括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两部分—只有后者是与语义解释直接联系的。”(高友工、梅祖麟《唐诗三论:诗歌的结构主义批评》)分析该句的深层结构指向的语义会发现,“看”和“重”两个动词的指向以及包含的意义对仗上是不太工整的,正是属于假平行的范畴。假平行(pseudo-parallel),“即一联中的两行在词或短句的层次上存在着对仗关系,但在深层结构上则可能是不对仗的。如果把对句看作是双筒目镜,那么,歧义对句有两个焦点,而假平行对句则根本没有焦点”(高友工、梅祖麟《唐诗三论:诗歌的结构主义批评》)。虽然这种平行有着虚假的一面,但是客观存在的平行力场却会“将假平行转变成歧义性对偶,并以一种令人瞩目的意象产生特殊的效果”(高友工、梅祖麟《唐诗三论:诗歌的结构主义批评》)。在“重”上体现出的歧义,正是诗歌意出言外、值得玩味之处。
最后看整首诗的结构。清人黄生在《唐诗摘钞》言:“雨细而不骤,才能润物,又不遽停,才见好雨。三、四紧着雨说,五、六略开一步,七、八再绾合,杜咏物诗多如此,后学之圆规方矩也。”这便是错综句法的运用,所谓错综,“就是在一个短暂分离之后,又回到原来的主题”(高友工、梅祖麟《唐诗三论:诗歌的结构主义批评》)。五、六句诗人略开一步,并没有直接提到雨,而是描写雨夜所见场景。四处黑压压的一片,远处只有些许渔火可见。但是诗人却并没有离开雨的主题,乌云密布证明春雨持续的时间长,渔火独明正是春雨迷蒙的体现。一明一暗却是从侧面写出了雨的情状。这种不离主题的错综与跳脱打开了诗歌的境界,更加妙趣横生。另外,学者赵谦提出此诗还有着明暗双线结构。诗的标题是“喜雨”,全诗却没有出现“喜”字,故诗人的情绪作为暗线被隐藏了起来。“明线,夜雨:发生时节(起)→发生方式(颔)→发生趋势(颈)→发生效果之一(尾)。暗线,情感活动:春雨终于发生(始喜)→雨之润物不知不觉(又喜)→雨将继续(三喜)→明朝锦城春色可悦(四喜)。”(赵谦《杜甫五律的艺术结构与审美功能》)如果错综句法的使用延伸了诗的广度,那么明暗线的交织形成的复调结构则扩展诗的厚度。这种相互制约形成的整体性功能,正是杜诗“虽小而大”的体现。黄生才会在《杜诗说》中感叹:“少陵如大将用兵,所向无不如意。材之所取者博,而运以微茫窈渺之思;力之所自负者宏,而寓以沉郁顿挫之旨。”
本文选取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批评方法,借鉴高友工和梅祖麟针对唐诗的批评实践,对杜甫的五律名篇《春夜喜雨》进行重构,以期从语言学的视角与传统诗论形成对话。对声律和节奏的探究可以发现杜诗虚实相生的秘密所在,回应对最后一联含义的争论。而从结构的角度,五、六句采用的歧义对句和对等原则,七、八句化用的假平行,以及全诗错综句法和复调结构的使用,凸显着语言上的朦胧暧昧和诗意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