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沛霞:在历史细微处理解中国
李菁

最近,电视剧《梦华录》成为文化热点,这部戏从女性视角出发,讲述了三位宋朝女性的故事,颇有“现代女性”觉醒的意味,也让人们在观剧之余把视野放在宋朝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的女性的真实生活状况。
其实早在二十几年前,美国学者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就在她的《内闱》一书里生动地重构和再现了宋代女性的生活状况。在她的著作里,女性并不是传统历史叙事里被遮蔽于父权与夫权阴影下的“受害者”,相反,她们积极地、“能动地”掌控着她们的生活……
“女性史”只是伊沛霞近半个世纪学术生涯的课题之一。早年求学于芝加哥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的伊沛霞目前是华盛顿大学荣休教授。半个世纪以来,她对史学理论发展不但自始至终保持着高度的关注与敏感,并且积极地付诸具体的中国历史研究实践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一位“多变”的历史学家,既不安于固守已有的方法论,也不囿于单一的研究领域,在漫长的研究旅途上,她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不断拓展新局面。
“大话题”的中国史
在西雅图这座漂亮的城市,我们相见于伊沛霞的书房。单看她书房的陈设与书架上摆放的书,会恍惚以为置身于国内某历史学教授的办公室——无论是客厅里的屏风、卷轴画,还是书房里挤得满满的《宋史》等历史典籍,都是浓浓的中国风。
作为一名“局外人”,与中国历史结缘近半个世纪,深入到浩瀚的中国历史细部,以另一种视角观察、分析、研究中国——这一切的起点是什么?这几乎是伊沛霞必然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你是如何对中国产生兴趣的?”
1947年,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出生于美国东海岸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曾在报社工作。在这样的环境里,大量的阅读是家庭生活的常态。她是典型的美国二战后“婴儿潮”的一员,在她长大的那座一万多人的小城里,很多同学的父亲都参加过二战,其中一些人从日本娶妻归来。这些被称为“战争新娘”的日本人,是少时的伊沛霞与亚洲极其微弱而遥远的关联。而“中国”,更是一个遥远的词。“直到越南战争发生,‘亚洲这个字眼似乎才显得具体且重要起来,”伊沛霞回忆。
1960年,年轻的民主党人肯尼迪的当选,给13岁的伊沛霞带来了一种她后来称为“政治觉醒”的东西。她还记得,有一次她和同学们都举着自制的标语牌,拥到机场附近去欢迎到访的肯尼迪。在众人羡慕的眼光中,她幸运地得到了肯尼迪的签名,“我也不记得牌子上写了些什么。”虽然她不认为自己是“政治上非常活跃”的那种学生,但身在那个时代大潮中,政治似乎成为那个时代的一部分。她还曾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去华盛顿参加过反越战大游行。
1965年,伊沛霞进入芝加哥大学就读。在这所著名的学府里,她遇到了很多优秀的学生和老师,“他们讨论问题的方式、关注的问题,都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初入大学的伊沛霞对社会科学颇感兴趣,不过芝加哥大学有一项特殊要求:如果选社会科学专业,则必须修一门“非西方文明课”,可选择的课程有俄国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我觉得同属基督教文明的俄国有点太‘西方;印度嘛,宗教意味太重;日本文化又更多来自中国……”多重考量之下,“中国”成了一个当然的选择。
从大二那年起,伊沛霞开始修“中国文明”,课程由芝加哥大学的三位资深教授主讲:著名汉学家顾理雅(Herrlee Glessner Cree)讲“早期中国”;柯睿格(Edward A. Kracke Jr.)主讲宋朝;何炳棣则从明代开始“接棒”。
被问及对何炳棣的印象时,伊沛霞沉吟了一會儿,似乎在努力寻找合适的措辞:“作为学者,我认为他是一流的。他的很多研究回应的都是大问题、非常重要的问题。作为老师的何炳棣……”陷入回忆的伊沛霞忍不住微微一笑:“他在第一天来给我们上课时就说:‘你们好好读我的两本书(注:指《明清社会史论》、《中国人口研究》),就足够了!”学术圈里流传着不少有关“恃才傲物”的何炳棣的“传说”,伊沛霞这里也有极其生动的回忆。每次开课前,何炳棣直接问下面的学生:上次我讲到哪里了?下面的同学给他一个提示,他似乎无须准备,就自如地从这个话题切入进去。“我在猜测,他想,以他的历史知识,应对我们这些本科生完全没问题——虽然他本人并不是中国历史的博士,他拿的是欧洲史的学位。他是自视甚高的一位学者,当然他也是有资格的,他是庚子赔款的留学生,极其优秀。”她停顿了一下说,“他给我们的指导是不一样的。”
大二结束时,伊沛霞做了一个影响一生的决定——研究中国历史。促使她做此决定背后的观察和权衡也很有意思:“其实我当时对‘西方文明课程也非常感兴趣,而且觉得它比‘中国文明课程更为成熟。但是,如果你学‘西方文明,写论文全是小话题,比如,关于法国孤儿院系统就可以做个40年,可是研究中国史的话,里面全是大话题——何炳棣一写就是明、清两个朝代的社会流动史!”被“更大话题”的可能性吸引,伊沛霞自此开始了与中国历史近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不过,现在的情况与当年比又有很大变化。浸润中美学术圈多年的伊沛霞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对比:当年,在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倾向于写“大话题”,但是因为现在在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大多数来自中国,他们的目的是尽快在中国用中文发表论文,所以又选择“小话题”,“写中国历史的论文,用中文写与用英文写,选择的内容会很不一样,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异。”
“越战一代”
既然选了“中国文明”的课,伊沛霞又再次挑战自己:“我想,好吧,学汉语应该也有意思!课程里既有‘现代汉语也有‘古代汉语,我去咨询系里的老师,他说‘你从古代汉语开始学习吧!——我想美国大学里很少有像芝加哥大学这样教中文的学校,先从古代汉语开始学起!”
现代汉语对美国学生来说已是一个巨大挑战,更何况是古汉语,几乎每个学期都有学生退出,伊沛霞却发现自己很喜欢古汉语课,这或许与芝加哥大学独特的教学方式有关:“教材是顾理雅自己编的,他不讲语法,只要你选了这门课,就跟着他学习典籍,比如我们是从《孝经》开始学起,之后学《论语》。”

何炳棣
1968年,伊沛霞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继续深造。正是在哥大读书期间,一位来自中国的中文老师给她取了“伊沛霞”这样一个特殊而有意蕴的中文名字。
哥大东亚系是美国最早建立的汉学系,是美国的中国研究重镇之一。它不仅有丰富的藏书,也拥有十分强大的师资力量。在哥大,伊沛霞的古汉语训练得到进一步加强。当时的研究生中,母语是中文的学生所占比例很小;古文讨论班课通常是一行一行地研读,以准确理解句子的意义为起点。伊沛霞回忆说,当她后来准备哥大的博士资格考试时,哥大的要求是“熟悉过去四五十年中出版的所有有关中国史的论著”。“当时复印机还没有普及,我坐在图书馆里翻遍所有的重要期刊,寻找有关历史的文章,做笔记,居然也应付过来了。”
而求学早期这种扎实刻苦的训练,让伊沛霞未来的学术之路受益匪浅。当被问到如果打开任何一部中国历史典籍——比如《唐史》或《明史》,可以立即无障碍地阅读吗?伊沛霞毫不犹豫地说:“可以!”
伊沛霞开始学习中文的这一年,遥远的中国爆发了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伊沛霞还记得,芝加哥大学一些学政治科学的学生还组织会议专门讨论,这些年轻人都非常兴奋:中国在发生着什么?什么是“文化大革命”?学生们对这场红色风暴都持非常积极的态度。那时的伊沛霞,对他们眼中“红色中国”发生的一切,也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想象。
几年后,当伊沛霞开始进入中国历史的时候,尽管外部世界与中国的通道是隔绝的,但是“有关中国研究的英文著作已经相当可观”,她后来评论说。与此同时,美国的中国研究也正在逐渐发展,已有几十所美国大学设有中国史课。
“美国的中国史领域是否比其他历史领域发展得更快?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这或许与时代背景有关。“在我1966年至1971年间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修中国史课时,我的教授们选择研究中国的原因颇为特别。”伊沛霞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详细梳理了美国的中国学。“许多人在二战或朝鲜战争中在美国军队受东亚语言训练,有的参与情报活动,还有一些则曾在美军驻日期间在日本工作。受此背景影响,这一代的教授一般从冷战的角度来看全球态势。”
“与这些学者年龄相当的美籍华人则组成了当时美国最领先的中国史课目的第二批教授。” 伊沛霞說,这些学者包括萧公权、许倬云、何炳棣等人,他们不仅是有传统的人文学家,还有不少是深切关心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希望借助西方理论和观念来探究中国。当时正是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占绝对优势,许多历史学家受法国年鉴派的理论影响,将研究的焦点放在平民百姓生活,并力图发掘能用于计量的史料。在伊沛霞看来,何炳棣于1962年发表的《明清社会史论》即是此类范畴的杰作,“他以进士名册为据,考察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及其影响,进而提出明清时期上层社会的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伊沛霞说,虽然何炳棣的一些结论当时引起一些争议,但是他寻找资料的路径和方法都是被称道的。
伊沛霞曾把自己这一代中国史学者称为“越战代”(Vietnam War generation )或“国防外语奖学金代”(National Defense Foreign Language Fellowship generation)。她解释说,1963年前后,也是因为越战的影响,政府开始鼓励人们学习当时对美国人来说并不常用的一些语言,比如汉语、日语、越南语、俄语、阿拉伯语等等。
“随着政府奖学金机会的增加,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中国史的学生数量骤然上升。不少反对越战的青年视亚洲研究为真正改变世界的切实可行的途径之一。”伊沛霞回忆。
进入中国史研究领域之后,最初几年,像很多同时代的学者一样,她也是“曲线救国”,选择到日本或中国香港、台北查找档案,为研究课题寻找资料。她还记得在香港的时候,与许多游客一样,在深圳与香港的边界线上,通过望远镜远远地眺望中国内地这一端——镜头里是开阔的农田和耕作的农民。
1978年夏天,伊沛霞与同在伊利诺依大学工作的丈夫在日本访学。有一天,他们偶然得知,可以从香港参加一个前往中国内地的观光团,他们立即加入。这是伊沛霞第一次踏足中国内地。他们先是坐火车到达广州,然后去了桂林和南宁。当时中越在边境上有一些军事冲突,沿途他们看到很多军用卡车来来回回穿行。1980年,伊沛霞与丈夫再次有机会到中国访问。让她印象深刻的是,他们遇到的很多中国人会过来捏孩子的脸蛋以表达对孩子的亲昵和喜爱,这是她切切实实地开始从书本之外的层面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
“多变”的研究者
1973至1997年间,伊沛霞在伊利诺大学东亚系和历史系执教。这25年间,她从一位默默无闻的临时教员起步,最后成为伊大的杰出终身教授和美国中国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尽管伊沛霞后来在中国因宋徽宗及宋史研究而在大众层面获得更广泛的认知度,但实际上,在她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半个世纪里,她的领域发生了很多次转向,而每一次转向,都一定程度折射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范式的变迁和代际转换。
伊沛霞在学界“初出茅庐”的1970年代,正是社会史方法论兴起的时代。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正是对社会史方法论的积极回应,也使得她成为最早从社会史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之一。

宋徽宗《 题李白上阳台帖》 图/Fotoe
若干年后阅读这部即便对中国人来说也非常冷门的学术著作,不禁令人感慨:50年前,在与中国的通道如此不畅的条件下,她竟然能做出这样一份材料扎实、论证精彩的个案研究。随之而来的一个好奇是:她是如何搜集到这么多材料的?“我当年去台北做研究时,在中研院发现了很多崔氏的墓志铭,上面有详尽的个人资料,”她回忆说,尽管其中一部分还没有出版,但工作人员还是热心帮助她复制了这部分材料,“根据上面的信息,我们大概可以重建当时妇女的生活。”
1978年,在此论文基础上形成的专著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被收录到在西方学界颇有声望的“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在这部专著中,伊沛霞将社会史方法与人类学方法相杂糅,成功地以博陵崔氏家族为个案,透视整个精英阶层的发展轨迹,开创了个案贵族家庭史研究的先河。1982年,北大周一良教授首次向中国史学界介绍这部著作,肯定了伊沛霞士族个案研究法给中国学界带来的参考价值。这篇书评的发表直接推动了1980年以来中国士族个案研究的兴起。
“第一本书完成之后,我一直在思考:下一步我真正有兴趣、想投入的工作是什么?”本想开始做唐代研究的伊沛霞,发现自己开始对家庭史产生浓厚兴趣。“家庭史研究是欧洲史常见的一种类型,”伊沛霞回忆,家庭的重要性对于普通中国人的意义毋庸置疑,但中国的家庭史研究却非常少见——意识到这一点后,她开始了对中国家庭制度和婚姻制度的研究。另外,从客观上说,伊沛霞很早就发现,宋代的史料比唐代更丰富、也更全面,“首先是印刷术的推广使得很多宋代典籍得以存世”;尤其墓志铭这样的史料,有助于后人重建有关宋代家庭的历史;此外,宋代笔记中也有大量关于普通人的记录,其中包括很多关于宋代仆役和女性的记载。

《听琴图》(局部) 传为宋徽宗赵佶创作的绢本设色工笔画,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有说法认为弹琴者为宋徽宗本人,两侧红衣为蔡京,青衣为童贯 图/Fotoe
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伊沛霞对史学理论发展的高度敏感与关注,贯穿她学术生涯的始终。随着社会思潮的转变,到了1990年代初期,伊沛霞的研究兴趣开始由中古时期的贵族家庭转向妇女史领域。“我进入妇女史研究领域,绝对是因为受了美国妇女史和欧洲妇女史研究的影响。”伊沛霞回忆。“回到上世纪60年代,当时的社会思潮不仅有民权运动,也有妇女运动。当这些运动发生时,人们思考:‘我们需要把妇女运动也写进历史。因为女性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我想这也影响了我。”此后一段时间,伊沛霞以妇女的生活细节为楔子,进入到纷繁复杂的中国历史的深处:她与同时代另一位著名学者高彦颐(Dorathy Kuo)等人一道,被公认为西方学界第一批研究中国女性的学者。
实际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经历了从“西方中心”到“中国中心”的转变。而美国中国学的范式转变成为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的重要学术资源。中国学领域妇女史的研究也呈现出从“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对中国女性权利地位的关注”,到“将妇女置于社会进程中探究其积极作用”的变化。
1993年,伊沛霞出版了《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此书后来被誉为“海外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伊沛霞在这部作品里生动地勾勒出宋代女性的真实生活场景。她用扎实的史料考察了宋朝这样一个纷繁复杂、充满变化的时代,女性真实的婚姻家庭生活:一方面,缠足开始流行,士人开始倡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宋代女性的法律地位有了很大提高,突出表现在女性对家庭财产的所有权与支配权,极大地提高了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
“以往西方对中国古代女性的刻板印象是‘温柔的、顺从的;而中国传统话语体系里则被‘五四妇女史观笼罩——也就是说将女性受压迫看成是中国封建父权最突出的特点。或许我们该超越那个视角,看到她们‘主动地、‘积极地做了什么,而不是仅仅把她们当成被动的角色。”伊沛霞说。
“在我们努力地思考了女人在哪里以后,中国历史和文化看起来就不一样了。”在被问到试图将何种新的视角带到中国女性的观察里时,伊沛霞回答:视女性为“动因”(agent),“她们自主地发挥自我。”她详细解释说,如果深入到历史细部,会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观察,比如说,女性绝不仅仅是家庭关系里的被动角色,她们在养育子女这件事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子女的婚姻中,她们也经常起到主导作用,等等。“如果她们愿意,她们也可能改变一些结果。”“所以对中国女性的观察也需要转换视角,让我们看看她们做了些什么,而不是外界在她们身上做了什么。”
有评论说,伊沛霞“最先在中国史研究领域提出了妇女是构造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能动主体的观点”。西方主流学术界也给了这本书极高的评价。1995年,《内闱》一书获亚洲研究协会(AAS)专门为中国研究领域颁发的著名的列文森著作奖。
伊沛霞的中国女性史研究的确与她自身的女性意識的觉醒密不可分。她回忆,在哥大读博士课程时,整个东亚系只有一位女性教授。伊沛霞发现,大家习惯以Mrs.(夫人)来称呼这位女教授,而用“Professor XX”来称呼男教授。“好像大家都不太习惯于将‘教授的头衔与一位女性联系在一起。”但那时学生中的女性比例要远远超过哥大教授中的女性比例。
“我1973年刚到伊利诺大学执教时,整个亚洲研究课程(Asian Studies Program)没有一个女教师,而历史系也好像只有两位女性,其中一位还是当年刚招的。“我感觉男教授们发现自己好像很难适应有一位女性同事共事,”她笑着回忆。“在许多场合中,我感觉到男教授们真希望我自动提出不参与他们的活动。不过,我觉得是时候让他们习惯我的存在。”柔声细语的伊沛霞回忆至此,忍不住呵呵笑了起来。“有时候教授们一起到餐馆聚餐,男士们会点啤酒,我无法喝了啤酒再去工作,所以我就点了咖啡。三个月之后,我发现男教授们也开始点咖啡,似乎在说:‘OK,这也是可以接受的。”

宋徽宗赵佶。图/Fotoe
妇女史之后,伊沛霞的学术生涯再次发生重大转向——她开始转向宋朝,转向与以往研究对象“相悖”的领域与人物,最终拿出一部厚重的《天下一人——宋徽宗传》。
“天下一人”宋徽宗
回想起来,伊沛霞对历史人物的兴趣,多少与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有关。自1970年代中期开始,史景迁出版了一系列中国人物传记。伊沛霞被他讲故事的方式所吸引,“无论是他写康熙皇帝,还是17世纪的一位非常普通的乡村妇女的生活(注:《王氏之死》),虽然不是鸿篇巨著,但都非常有意思。他的书一出来,我就会去读,读他的书很愉悦。他的读者超出了专业范围,被普通大众所接受。”
在很长时间内,写一本中国历史人物传记的想法萦绕于伊沛霞脑海中——选择范围当然还是她最熟悉的宋代:“苏轼当然是一位很有趣的人物,但林语堂已经写了一本非常好的传记”,而像欧阳修这样她感兴趣的人物也早就有了传记;也考虑过“有足够多的材料”的南宋诗人刘克庄,他著述颇丰并在朝中担任要职,卷入过南宋末年的政治风波。
但是在研究与教学过程中,敏锐的伊沛霞开始注意并思考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字与视觉的关系。伊沛霞对视觉层面(visual side)的敏感与关注由来已久。向来喜欢参观博物馆的伊沛霞回忆,自从开始研究中国历史之后,就开始对中国文化中的视觉艺术愈发感兴趣。上世纪80年代有机会访问中国时,她与丈夫经常去文物商店看看,也经常发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文物,当时19世纪的中国画的价格非常低——其中一些成为她现在的书房和客厅的一部分。
1990年代以后,随着图像学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崛起,伊沛霞对历史研究中的视觉对象和视觉方法的兴趣日渐浓厚。“之前的历史学家都过于依赖文字材料来研究历史,过分关注文化的言辞表述,我开始阅读与视觉艺术有关的研究,开始考虑在宋史研究中有什么课题可以让我去探索这些问题。”
她注意到,每个教宋史的人都会用《清明上河图》。“虽然这张画内容丰富,我们还是有很多东西没有探讨过。”她开始试图考察衣服的颜色、人们在各种仪式中站立的位置等等。伊沛霞写过一篇有关皇帝出游仪式的文章,她发现能找的有关皇宫的视觉艺术资料远远超过宋代社会的其他方面,宋代朝廷是否可以作为下一步的研究对象?她开始思考。
在伊沛霞看来,历史不仅仅存在于言辞,城市的空间布局、礼仪的制式、建筑的样式、书画的内容以及风格,都承载了历史的叙事。作为画家、书法家、收藏家以及宫廷艺术家赞助人的宋徽宗,进入了她的视野。 “是的,这看起来有点自相矛盾,”伊沛霞笑着回应。作为深受1960年代社会史思潮影响的历史学家,“帝王将相”似乎从来不在他们的研究名单里。但这一次,她被宋徽宗这位充满戏剧性的皇帝的故事“牢牢吸引”。她的研究越深入,对宋徽宗的兴趣就越浓烈。
2006年,伊沛霞与他人合编的《徽宗与北宋后期:文化政治与政治文化》一书,收录了国外13位学者从不同维度对宋徽宗展开的讨论,这部论文集被看作“西方学界试图重新全面认识昏庸之君宋徽宗与他的时代的一种努力”;2008年她又出版了关于宋徽宗收藏的文物与艺术作品的专著——《积淀文化:宋徽宗的收藏》,此书后来拿到东亚艺术史上最佳书籍的岛田奖。2014年,《天下一人——宋徽宗传》正式出版,以此为她的“宋徽宗三部曲”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伊沛霞透露,实际上,后两本书是同时进行的:“在准备写徽宗的传记时,我想:‘从他的收藏开始入手吧!结果我发现了很多材料,越来越多,而一本传记容不下这么多材料,我想,那干脆另写一本谈他的收藏的书吧!”
宋徽宗大概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充满话题性的皇帝。一方面,他有举世公认的艺术造诣和艺术品味;另一方面,他又是以极其戏剧性及悲剧性的方式,成为亡国之君。
“我是想强调他命运里的一系列意外偶然。”被问及宋徽宗身上最吸引她的一点是什么时,伊沛霞略一思考之后回答。她解释说,当年的赵佶未曾想自己会成为皇帝,如果不是哥哥宋哲宗在23岁突然去世且没有子嗣,他绝不会成为皇帝;如果不是他的继母(神宗的皇后向氏)选了他,他也不会成为皇帝;如果契丹能够平定女真叛乱,女真绝不会入侵宋朝,宋徽宗在皇帝的宝座上可以再统治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在中国正统的历史叙事里,徽宗是“玩物丧志”的典型人物,这个评价有失公允吗?
“绝对是!他非常聪明,非常有才华。如果你仔细看历史材料,徽宗并不是让别人来做决定。在做决定之前,他会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然后花很长时间来考虑采取合理的决策。比如他花了很长时间来考虑是否与金联盟的事——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这个决定,有的人支持,有的人强烈反对,他一直都非常关注各种意见。”
作为一位中国历史的“外人”,伊沛霞说,中国传统的历史叙事容易存在从结果反向推导一个人的倾向,由“亡国”的结果反观宋徽宗,从而对他充满了“后世之见”。“我们是否可以进入真正的历史来看一下徽宗的处境,进而考慮他为什么做出那种选择?”伊沛霞的《宋徽宗》一书,对内,把各种势力的政争;对外,把宋与辽、金之间的分分合合、结盟与分裂,都客观地梳理得非常清晰,让人读罢也会对徽宗在政策选择上的犹豫多几分理解,进而对他的悲剧性命运也多了几分惋惜。
不管后世对宋徽宗有什么样的政治上的评价,他在绘画、诗歌、书法等领域的造诣是举世公认的。但即便如此,伊沛霞还是用不少的笔墨来提醒我们:对于宋徽宗对中国艺术的深远影响,我们的认识也许还不够充分。比如宋徽宗对建筑有极大的兴趣。在他还是端王的时候,赏识并重用建筑天才李诫。在他继位第一年,李诫开始修订对后来有极大影响的官方建筑指南《营造法式》;“画院”虽然并不是在宋朝首创的,但绝对是在宋徽宗时期达到了艺术高峰。徽宗对宫廷艺术家的作品要求非常严格,也极其挑剔,以至于著名艺术史家高居翰评价说,徽宗坚持正确画出细节的故事说明,“在中国绘画史上,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将艺术真实性的标准认真向前推进的机会。”
宋徽宗对自己的文化修养和造诣无疑也是自信的。“到了19岁的时候,他就很自信可以开创一种非常特别的风格。他不想模仿王羲之或王献之,非常有创造性,也非常独特。”令人感慨的是,灭亡北宋的金国皇帝章宗,就是宋徽宗的粉丝,他的书法“悉效宣和字(瘦金体)”,几可乱真,许多人第一次看到金章宗的书法作品时,都误以为是宋徽宗手笔;章宗还刻意模仿徽宗的绘画偏好,听说徽宗作画“以苏合油烟为墨”,也高价购来同样的墨。
在伊沛霞看来,徽宗并非只是沉溺于艺术的昏庸之君,相反,他在文化上、艺术上所做的努力都有意识地与政治功能相联系。宋徽宗在文化上和艺术上推行的种种举措,实则是为政治服务,而他的艺术家形象也有助于增加他作为帝王的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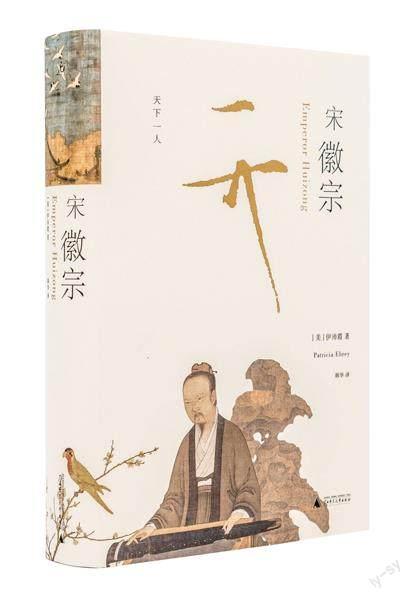
伊沛霞的书里也细致入微地刻画了蔡京、童贯这些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几乎被脸谱化的人物,比如在家喻户晓的《水滸传》里,蔡京就直接被定性为“奸臣”。宋徽宗对蔡京的信任和倚赖被后世所诟病。真实历史里的蔡京是什么样子的呢?又该如何看待徽宗对蔡京的信任呢?“徽宗信任他是完全有理由的。蔡京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是一名非常高效的行政管理者和财政管理的奇才,是他让这个系统运转起来。” “蔡京能够从禀告给皇上的大量问题中迅速理清头绪,找出其中的重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或许为了让现代读者对几百年前的历史人物有一个更为直观的理解,伊沛霞把蔡京比喻成现代企业里CEO类型的人。
伊沛霞另一个角度的观察也很有意思:“我感觉徽宗对蔡京的感觉有点像对父亲——他父亲(神宗)死时,他才3岁。蔡京和他父亲的年龄相仿,他们对文化的兴趣和审美上的品味也非常相似。”徽宗对蔡京的信任,还有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与彼此欣赏。实际上,蔡京一直不同意与金国结盟。当后来局势恶化时,宋徽宗对手下说,蔡京是唯一一位自始至终反对北伐的人。
熟悉和喜欢宋史的人能在《宋徽宗》一书里找到很多“老朋友”,比如苏轼与王安石等人的政治歧见,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也都写一手好文章。但是他们对时局的看法不一样。互相争斗。这种情况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一个党提出一个意见,另一个党就反对。”提到苏轼,伊沛霞说,她对这位大文豪有“非常正面的看法”。“我的理解是,从某种程度上说,徽宗有点为那么多人喜欢苏轼而不快,”这是另一种文人之间的嫉妒?“我想即便是现在,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一些优秀的作家也许有类似的感觉。这也许是人的共性吧!”她笑着回答。
伊沛霞直言:“我对徽宗的诠释比传统的历史学家更具同情心。”的确,“以史为鉴”的修史思路,容易出现剪裁历史、以是非遮蔽史实、忽视历史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伊沛霞对宋徽宗的“同情与理解”,有助于我们摆脱单一视角看待这位个性明显的北宋君主。虽然,有学者认为伊沛霞对宋徽宗的某些辩解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但也都承认,她对宋徽宗的整体还原是成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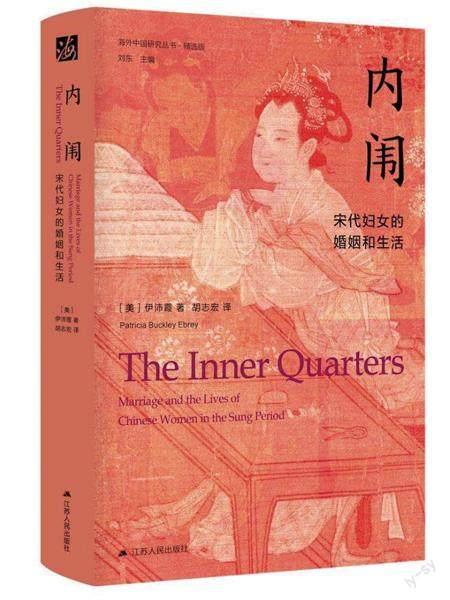
宋朝文化上的繁荣与军事上的衰弱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否也是这个王朝的悖论?“宋朝的开国者视军事为一种危险,这与欧洲一些王朝不太一样,欧洲的王朝通常会有一位退役的军事将领在内阁中。但是在宋朝政府里,是根据文艺的才能——比如写诗的好坏来选拔官员的。这是不同的管理方式。”
实际上,如果我们站在全球史这一更大的历史空间来看,对北宋与“末代皇帝”徽宗的命运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理解。“是的,在相对简化的故事中,我们会认为宋是唯一的主角,但事实是,当时的辽和金也同样强大。这段时期,北宋面临相对于汉唐时期军事上更强大的邻国。”如果以此为背景,我们能否进一步假设:即便徽宗当年做了正确的选择,是否只是延迟而无法最终逃避北宋被灭亡的命运?
“对,这是我说的另一个偶然性的意思。虽然金灭了辽、北宋,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被蒙古大军灭掉的命运。”
有趣的是,在宋徽宗传记中,伊沛霞也时常将这位传主置于跨文化的角度下来观察。她说,中国读者批评宋徽宗建大园林、收藏那么多的画,但是“建筑、装饰和收藏的欲望在全世界的君主中都非常普遍”,她说,与其他地方的皇室相比,徽宗为了加强皇室威严而投入的花费不算出格。
又比如,欧洲皇帝有狩猎的传统,一方面熟悉军事,一方面可以保持与外界、与下层社会的沟通,这也是皇帝加强、维护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与政治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手段。“但中国的情形不太一样。因为远离一线,前线将领往往不敢将失利的真实情形汇报给皇帝,即使汇报了,也是非常迟的,导致他的应对策略既滞后又误判。
“将领们可能希望明天战况有好转,这样他们就不把今天的失利报告上去。”如何得到一线即时的、真实的消息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中国这么大,需要更长的沟通和交流时间。在高宗时期,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他要给他们多大的自由空间,让他们自己做决定?将领们经常说,如果不让我根据形势来做处理,那我通常会失败;而统治者又感觉被冒犯了。
如果以开启宋徽宗的研究为起点,这本《天下一人》到最终出版前后用了15年的时间。伊沛霞坦承这本书本是为西方读者写的,但结果证明,它在中文世界里收获的读者,远远超过英语世界的读者。宋徽宗传记在中国的成功,让伊沛霞多少有些意外。“说老实话,我到现在都不太知道这本书到底卖了多少。虽然是翻译过来的书,但中国的读者远远比在美国的多。”她笑着说,“也许因为他是中国的皇帝吧!”
当被问及写这部书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伊沛霞回答:材料收集。宋朝的材料不可谓不多,但很多都是后世根据自己的主观需要,难免有所剪裁,并且充斥着训诫味道。她举例说,《宋史·蔡京传》是根据弹劾他的奏章写的,而要了解蔡京在徽宗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就要仔细分析那些通常带有偏见的证据。为此,“我转向最早的、后人改动最少的原始资料”。早年扎实的古文功底使得伊沛霞可以直接阅读大量原始材料,包括宋徽宗颁布的诏书、呈递给徽宗的奏章、笔记和各类传记。她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几乎一切与徽宗时代有关的史料,这需要的除了耐心和毅力,还有功底、眼力和判断力。

解讀中国
早在大学二年级时,伊沛霞就把自己未来的职业选择与学术和教育联系在一起。伊沛霞教授是位勤勉的学者,美国学界也以一系列的奖项对她的努力予以肯定和回报。2014年,为表彰伊沛霞在学术研究上的贡献,美国历史学会(AHA)为她颁发终身成就奖。她还获得了2020年度的"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s to Asian Studies)。
除了大量的学术专著外,伊沛霞还撰著或合著了6本广为使用的中国史、东亚史、世界史、史料教科书,其中最为中国读者熟悉的,是《剑桥插图中国史》(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 )。
有趣的是,当年轻学者伊沛霞逐渐在学界闯出名气时,出版社找到她,请她来写《剑桥插图中国史》——伊沛霞并不知道是谁在背后推荐了她,但出版社提出的初版印数18000册让她非常动心,“在这之前不久,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著作,当时只印了850册”,她笑着说。《剑桥插图中国史》的成功令伊沛霞非常意外,它一直被哈佛大学、伯克利大学等学校当作教材在使用,也被翻译成好几种语言,在中国也很受欢迎。“可能是大家想看一个西方人写中国历史的角度吧。”
在这本面向西方普通读者的书中,伊沛霞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讲述中国这个历史漫长的国家。伊沛霞说,她试着勾画一两个有关中国的最紧要的问题,比如“它的巨大和历史连续性”。伊沛霞向西方读者发出这样的疑问:这十多亿人口——比东欧、西欧和北美人口的总和还多——逐渐认为自己拥有相同的文化、享有认同感,这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他们没有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那样,因在方言、宗教或生活方式上的差异而分裂成一个个相互猜忌的群体?对此,伊沛霞尝试着做出自己的解释,包括中国的地理位置,它的形声书写系统,以及强大统一政权的长期经验。“中国是一个长时间使用一种语言的国家,而欧洲不一样。直到19世纪,欧洲受过教育的极少数人说拉丁语,但它切断了同普通人的联系。在中国,即便是金朝,它也使用与宋朝相似的文字,即使王朝更替,构成文化基础性的元素,也有极大的相似性。”
“如果你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就不会理解现代中国。” 这是伊沛霞在西方讲授中国历史时,通常所用的开场白。“我们那一代学者的目标是让美国公众更好地理解中国。”这大概也是这位学者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
——《宋代徽宗朝宫廷绘画研究》评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