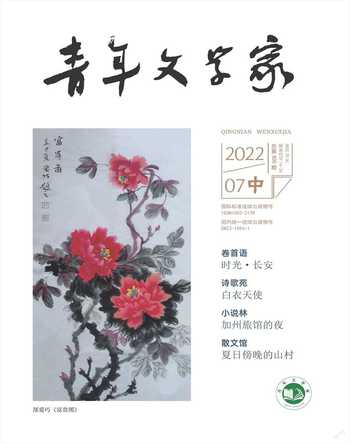安六爷
黄曦
我第一次见到安六爷是在义诊诊所。
在这片不甚发达的土地上,诊所寥寥无几,到镇上的医院要跋涉数十里。村民的病几乎是靠赤脚医生维系。义诊队的入驻对他们来说是莫大的福音。临时搭起的板房每天门庭若市,从皮外伤到头晕、胃痛,都要上这里来瞧瞧。
安六爷是在一个傍晚来诊所的。挺慈祥的一个老人,灰色的对襟衫松垮地套在瘦瘦的身躯上,下搭一条黑色长裤,脚上趿着一双凉鞋,衣服不贵,但都洗得很干净。几绺灰白的刘海儿散在额前,更添几分慈祥,看起来有七八十岁,精神还很好,除了耳背很严重。
那时正是饭点,诊所人不多。安六爷进来,一位同事上去询问状况,安六爷伸出裹着布条的左手:“小先生,麻烦你给俺看看这手。”同事为他拆开布条,我正好在一旁。老人左手上有一道被利器划伤的口子,伤口挺深,有些血已經凝固了,但新鲜的血还在流,伤口近旁还有一些污物。
同事把安六爷引到换药室里,安六爷听力不好,沟通很费劲,一个简单的配合需说上三五遍。伤口有点儿深,又沾了污物,同事用裹着消毒水的卫生棉仔细清洗。“大爷!您忍着点儿,要清洗干净,伤口才不会感染!”安六爷“哎哎”地应着。在清洗的过程中,安六爷没有叫唤,只是偶尔“呲……”地倒吸一口凉气。从他因痛苦而拧在一起的五官和紧紧攥得发白的指节上,可以看出他的隐忍。
告别的时候同事凑近安六爷的耳边叮嘱道:“大爷,您下次来,叫个家人陪着吧。”“什么?”同事又大声重复了一遍,安六爷总算听清了。他小声呢喃着,像说给我们听,更像在一个个排除选项:“我孙子在A城工作,一年回来没几次,儿子在B城做帮工,也不常回。两个女儿远嫁……”安六爷越说越小声,对儿孙的不在身边,他并无怨怼,但说到最后,发现连一个陪自己来诊所的人都没有时,语气里有一股淡淡的失落。
后来的几次换药,安六爷也是自己来。他的耳背还是很严重,沟通还是很费劲,但来得多了,便熟起来。他也会跟我们唠嗑,讲他年轻时的经历,讲他读大学的外甥女和他进入国企的孙子。说到孩子们时他的眼里有藏不住的骄傲,我们也会竖大拇指夸赞,安六爷会朴实地咧嘴一笑,露出一排有点儿歪扭的牙齿。
安六爷的手好了之后,偶尔也会到诊所来跟我们唠嗑,大概是没有人陪他聊天儿,来我们这图个热闹吧。我有时散步,也会去安六爷家坐坐。他独自住一栋两层小楼,常搬一张竹椅坐在电视机前,电视里很大声地播着戏曲,他听着听着便头半靠在肩上打起瞌睡,有人进去了还毫无知觉。轻唤他几声,他会一时间想不出我是谁,怔怔地看着我。人老了,总会很像一棵枯木,呆呆地杵在那里,长不出绿叶,冒不出新芽,也没了生气。
去安六爷家有时也会遇到玩闹的小孩儿。安六爷手很巧,听说年轻时是个木匠,小孩子们会拿着木料跑到安六爷家请他做木剑。他也很乐意帮忙。拿到成品的小孩子们会很大声地说:“谢谢六爷爷!”这时,属于孩子的那份活力总会爬到六爷的脸上,他笑到所有的皱纹都挤到头上和鬓角。拿了枪剑,小孩子们有时就在安六爷家玩了起来,爬到楼梯口躲在护栏后假装射击,猛地跳起扔一颗并不存在的手榴弹……安六爷总笑盈盈地看着,也不阻拦。小孩子们在,这栋房子才多了一些生气。
在咿咿呀呀的戏曲声和小孩子们的笑声里,三年过去了。我见到安六爷的亲人回来过几次。那段时间,安六爷的语气都扬了几分,笑声也爽朗了许多。但更多的时候,安六爷的小楼里响的是咿呀的戏曲。安六爷的生命似乎也跟着这声音在岁月里流淌,他的头发更白了,脸上的皱纹更深了,耳背也更严重了。
后来驻村时间到了,我们在乡亲们的欢送中离开了村庄。安六爷也来了,还是那件灰色的对襟衫、黑色的长裤,凉鞋倒像是换了一双,步伐没了之前的稳健,耳背也更严重了。坐上车时,我看到他似是张了张嘴,但说的什么话已听不清了。
时隔两年,一次出行经过村庄,便去看看。义诊所的板房已经拆了,建起一家真正的诊所,村里人的大病小疾终于有了一个求助地。我到村里转悠,很多人都还认识我,热情地与我寒暄。小孩子们围着我笑闹,几位妇人也与我闲谈。经过安六爷的小平楼时,我发现平日一直敞开的大门紧闭着,屋里也没有响起戏曲声。
“大妈,怎么没见六爷?”我问同行的妇人。
“姑娘,你还不知道吧?六爷四月份归西了。”其中一位大妈轻轻叹息了一声开口道。我张口想说出什么,最后也只憋出一句“这样啊……”
“往日八点多,六爷就会关电视休息。那天都十点多了,六爷家的电视还响着。俺寻思着有点儿怪,就去看看。俺们家小顺屁颠屁颠地先进去了。”正在跟小伙伴玩的小顺听到自己的名字,跑到我们旁边,倚在自家奶奶身上。其他几个孩子也停止了玩闹,静静地站在一旁。
“俺进了屋见六爷爷在竹椅上打瞌睡,就喊了他几声,六爷爷都没应,俺就跑回家喊来爷爷奶奶。”
“俺跟老头子过去看,也是叫不醒。老头子赶紧上诊所去叫先生。先生把了把脉,又掰了掰六爷的眼皮。俺们也不懂这是干啥,问先生六爷这究竟是怎么了。医生没有回答俺,而是问俺们六爷这样睡了多久了。俺们也不知道呀,就把事情跟他讲了一遍。先生摇摇头,叹了口气,轻声说了句:‘这六爷怕是没了几个小时了。俺们便赶紧通知六爷的儿女回来,唉,你说这,一提到还是让人觉得有点儿鼻子发酸。”
“唉,六爷也是可怜人哟,儿孙有出息,盖了大房,可是自己住呀,它没有人气。连过世都没有人知道……”另一位妇人感叹道。
说到这,大家都有点儿愣神儿,静静地站着,谁也没有接话。我呆呆地看着眼前的空屋,心里很不是滋味。那位老人,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了。耳背把他与外界断绝,但他从来都没有与大家隔绝。他向大家诉说他心中的丰富世界,又努力根据别人的举动给出一点儿回应。但最终,大而空的房子,还是把他与外界隔开,在戏曲声的掩护下,他悄无声息地走了。
我怔怔地看着眼前的大房子,想着那个慈祥而又坚忍的老人,呆愣了很久,深深吸了一口气,双手合十,朝村西墓地的方向默念:“六爷,祝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