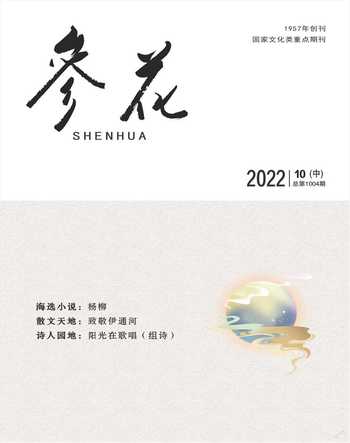中印美学中的“味”“韵”和物我合一
中印美学范畴中存在着三组极为相似的概念。婆罗多的“味论”与钟嵘的“滋味说”都强调读者接受过程中的超越性艺术审美体验,欢增的“韵论”与王士禛的“神韵说”皆认为,诗人应当创作具有言外之意的作品,新护所推崇的“梵我合一”的“喜”与庄子追求的与道合一的“逍遥”,在本体论意义上达成了一致。对这些概念的对比研究有助于明晰中印两国的美学特质,为东方诗学提供更多更有意义的内容,同时,在与西方文论进行对比研究时,更有理论自信。
一、中印接受理论概念——“味”
(一)印度美学的“味”
“味”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古籍中记载了四类“味”。到了公元前700年左右,精神的味取代了物质的味,其中“这是味,得味者欢喜”对文学理论的影响很深。作为文学理论的“味”形成于公元前3世纪左右,之后经过发展,约公元2世纪左右,婆罗多牟尼作《舞论》标志着“味论”正式成熟。
《舞论》系统地总结和阐释了“味论”,具体论述了戏剧的艳情、滑稽、悲悯、暴戾、英勇、恐怖、厌恶和奇异八种味,这些味产生于别情、随情与不定情的结合,各味又有各常情。“情使这些与种种表演相联系的味出现”,由情生味,情与味相辅相成,“正如善于品尝食物的人们吃着有许多物品与许多佐料在一起的食物,尝到味一样。智者心中尝到与情的表演相联系的常情的味。因此,这些常情相传是戏剧的味……有正常心情的观众尝到一些不同的情的表演所显现的,具备语言、形体和内心的表演的常情,就获得了快乐等戏剧的味”。[1]《舞论》中论述的“味”是艺术之生命,美之本质,“没有任何(词的)意义能脱离味而进行”,[2]这种“味”指向创作、表演与鉴赏中的感情,更倾向于审美体验。
之后,大约10至11世纪,新护的《舞论注》在前人基础上,创造性地阐释了婆罗多的味论,成为梵语诗学家大多采纳的理论,并为现代人所推崇。新护在洛罗吒“强化展示论”、商古伽“模仿推理论”、那耶伽“品尝论”三种味论的基础之上,[3]提出具有鉴赏力的观众在观赏戏剧时,通过演员表演等各种艺术手段,戏剧内容与真实存在互相抵消,观众形成一致性感知,被戏剧中普遍化的情由、情态和不定情唤醒心中潜伏的常情,由此产生一种超越文字和语言的感知,就是味。观众品尝到的味由常情产生,但常情有快乐,也有痛苦,而味永远是愉快的,因为味是超越世俗束缚的审美体验。并且,新护还在婆罗多八味说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九味——寂静味。至此,印度美学对味论的研究达到最高成就,“味论”也形成了全面体系,成为占据核心地位的美学思想。
(二)中国美学的“味”
中国的“味论”从先秦就开始了,不过主要是以“味”论政或论乐。《左传·昭公·昭公二十年》记载“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以“五味”喻政德,将味的概念限制在政治领域。而《论语·述而篇》有“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礼记·乐记》有云,“是故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飨之礼,非致味也。《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4]都将味与乐联系了起来,使味的概念进入审美领域。
到了南北朝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味论诗。陆机的《文赋》以味品诗文偏重文采,刘勰的《文心雕龙》直接将味与情采联系,但只是旁及,未将味视为独立概念,理论价值不高。真正建立诗味说的是齐梁时期的钟嵘,他第一个明确提出并全面论述了诗之味。钟嵘建立的“滋味说”的核心内容有两点:一是好诗须有滋味,这种滋味来自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其《诗品序》谓五言诗当为“众作之有滋味者”,原因就在于其“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而不似玄言诗的“理过其词”和宫体诗的“词繁意少”。将情真意切与文采华茂结合,才能产生有滋味的好诗。二是把“味”当作评判诗歌好坏的艺术标准,有滋味的好诗才能“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心动”,引起读者的审美愉悦感。由此,钟嵘建立的“滋味说”开始作为重要概念影响后世美学,晚唐司空图进一步将滋味说发展为“韵味”说,将滋味说引向了更高的审美领域。
综上所述,中印美学中的“味”都指能产生审美愉悦感的接受心理,形成与感知流程基本一致:先是作品提供引起艺术感知的前提,然后通过作者的表述或演员的表演,使接受者获得普遍的情感体验,由此,接受者达到超越性的艺术审美境界。在这一过程中,“情”非常重要,中印美学都强调以情感味,由情生味,但“情”的含义不大相同。印度味论中明确规定了“情”的各种类型,含义广泛且不固定。中国味论所说的“情”即为感情,只强调真实性而不进行详细划分。印度的味论更偏重戏剧这一舞台表演形式,而中国的味论主要限制在诗文领域,受不同传播媒介的影响,接受者所感之“情”也不太相同。然后,中印美学的“味论”都趋向了更为复杂的审美和哲学境界,如新护以“喜”解味,中国的滋味说经由司空图发展为“味外之味”,最后在王士禛那里发展为“神韵说”,之后进一步发展为代表中国美学核心的意境说。印度的味更多地走向了宗教领域,而中国则将其限制在艺术审美领域。
二、中印创作理论概念——“韵”
(一)印度美学中的“韵”
提出“韵”这一术语的是公元八九世纪的欢增,在此之前,“韵”是一个语言学概念,是指通过语音展示词义的一系列发音过程。欢增的《韵光》将“韵”从语言学领域转换到诗学领域,容纳庄严论、风格论和味论,构成了“韵论”完备坚实的体系。
《韵光》中指出诗的意义有表示义和暗示义或领会义两类,诗的本质是后一种,暗示义“不能为仅仅具有词和义的学问(一方面)知识的(人)所知晓,而只能为懂得诗的意义的真义的(人)所知晓”,[5]因而这是由暗示和超越所得的诗的灵魂——“韵”。在欢增的论述中,韵既指具有暗示意义的诗,也指在诗中起暗示作用的因素和所暗示的意义,其“实质是词(以及由词组成的句和由句组成的篇)的暗示功能和由此产生的暗示义”。[6]同时,欢增将韵分为“非旨在表示义”和“旨在依靠表示义暗示另一义”两大类,两类之下,又有“味韵”“情韵”和“庄严韵”等若干小类,建立起细致全面的体系。此外,欢增还将诗分为韻诗、画诗和以韵为辅的诗三类。他推崇韵诗,认为诗人通过巧妙刻画别情、随情和不定情形成暗示义,将事物的本质和灵魂隐藏在外在形式之下,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以透过事物的表面领悟真理,这种领悟是与梵我合一极为相似的境界。欢增所建立起的这套以“韵”为中心的诗歌艺术理论,将诗歌视为一个有机体,走出了语言学的桎梏,为印度诗歌理论的发展带来了新思路。之后,大约10至11世纪,新护的《韵光注》进一步发挥了欢增的“韵论”,同时,曼摩吒的《诗光》也谈及了词的字面义、内含义、暗示义和韵的分类等,使“韵论”成为印度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
(二)中国美学中的“韵”
与印度美学相称的中国美学中的“韵论”为“神韵说”,其来源与庄子的“得意忘言”论密切相关。庄子认为道无形,故不可言,所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但他也认为言可间接“渡”意。对于这种间接性,王弼给了通达的解释:“立言以造象,立象以传意”,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因此,庄子的“得意忘言”之论强调了言语作为象征性工具的作用,但同时也涵蕴了形象大于语言文辞的意思,这就可以悟出形与神的问题。在这之后,钟嵘提出“文已尽而意有余”,皎然论说“意中之静,意中之远”就顺其自然了。这些理论都是在庄子“得意忘言”基础上的进一步阐发,在此之上,司空图提出了“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形成了神韵论的雏形。
司空图的《与李生论诗书》以饮食为喻,主张诗歌应写得含蓄蕴藉,做到“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具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这一论说直接启示了王士禛。王士禛继承了司空图“X外之X”的结构和“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理论,认为象外之象的组织结构促成了味外之味的艺术效果,正式确定了“神韵论”这一概念。“神韵论”即诗人以简易笔墨、虚实之意象和含蓄蕴藉之语言,造既富生机又表意深远的意境,借此含蓄表达作者的真挚情感和幽深意绪,以促使读者从中体会“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意蕴。
梳理中印韵论可以发现,两者都将“韵”的暗示性和超越性作为核心特点进行理论建构。印度韵论转借语言学概念,强调语言的言外之意,以为这才是诗之灵魂,中国的神韵说同样强调要用有限的语言表达无限深远的意境。中印韵论都是对诗人创作的规定,认为诗人应通过一系列技巧和手法创作出具有韵的诗,这样的诗才算好诗。但两者的体系却完全不同:欢增详细规定了韵论的含义及分类,建构了一套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中国韵论的建立和发展都很随性,概念模糊,理论凌乱,对于这一点,中国文论应合理扬弃。
三、中印艺术境界:物我合一
(一)印度美学——“喜”
10至11世纪,新护在《韵光注》和《舞论注》中提出了“喜”,指艺术品的“味”“韵”必须达到“物我双亡”、主客合一的“喜”的境界,即“梵我合一”。这一概念与印度一贯的美学追求相符合。古代印度把世界分为现实的物质生活领域和超验的精神生活领域,这种灵肉二元的观点贯穿印度美学的始终,使印度人不仅积极享受人生的欲乐悲苦,同时,又充满了对现实的超越之情。“梵”即是这种灵肉二元合一的最高境界。新护所提出的强调梵我合一的“喜”,就是要求人们透过物质现实领域的美去领悟精神世界梵的真,这种经验美和超验美的和谐统一,是印度独特的灵肉双美的艺术风格。
同时,新护受印度吠檀多“不二论”影响很深。吠檀多“不二论”分“不二一元论”派、“制限不二论”派以及“二元论”派,三派中的“不二一元论”派是主流学派,主要观点为“梵我不二”,即梵与“个我”合一。新护认为,好的艺术作品可以使读者实现“梵我合一”的境界,很明显与“不二一元论”相符合。可见,在美学层面,印度始终贯穿灵肉双美的思想追求。由此,“喜”作为融合了传统美学思想的核心概念,强调“不受阻碍的艺术感知”,能使欣赏者“不厌倦和不间断地沉浸在享受中”,始终追求一种在有限之中达到愉悦的无限境界。
(二)中国美学——“逍遥”
吠檀多派将世界的本源和终极都归于“梵”,道家则认为世界的根基是“道”。在本体论上,二者达成了一致。新护以“不二一元论”为核心,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乃是“梵我合一”的“喜”。在道家思想中,同样强调与道合一的是“逍遥”。庄子提出逍遥的核心是“无己、无功、无名”之后的“无所待而游于无穷”,这是一种与道合一,精神与身体都绝对自由的境界,要达到这一境界,须“心斋”“坐忘”。
庄子所谓的“心斋”即“虚静”,是认识和审美的心理要求和状态,指排除内心杂念之后的大清明。“坐忘”即忘却外物,忘却自我,心物无二,物我合一。“心斋”“坐忘”的实质都是摆脱身心欲求,保持心灵自由,通过主客一体的浑融进入审美状态,这是创作者和欣赏者都应该具备的审美态度或修养方式。如此之后,“物物而不物于物”“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最终实现有限人生的无限自由。中印美学在物我合一这一概念上达成的一致令人赞叹,他们皆看到人生活中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存在,也共同强调对二元世界的融合,既肯定现实美,同时,又追求精神的超越,这种和谐之美是中印两国共同追寻的美学精神。但印度走向了神秘的超验世界,而中国走向了现实的艺术。
四、结语
印度文艺思想成就很高,但探讨印度文化或美学所能依据的文献资料断续不全,集成的著作一出,零散的前驱就散失。因此,无法对印度美学做全面系统的了解。但本文选取的这三个美学概念,作为印度美学的核心概念,资料相对丰富,因而笔者才能与中国文论对照,在彼此关照中,发现中印两国不同又相似的美学特质,为东方诗学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内容,丰富东方文论的研究。同时,在与西方文论进行对比研究时,也能更好地找准定位,树立理论自信,建立东方文论体系。
参考文献:
[1][2][5]曹顺庆,主编.东方文论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3]尹錫南.梵语文艺理论家新护对《舞论》戏剧论与乐舞论的阐发[J].南亚研究季刊,2020(02):62-68+100+5.
[4][元]陈澔,注.金晓东,校点.礼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6]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张明月,女,硕士研究生在读,天水师范学院,研究方向:文艺学)
(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