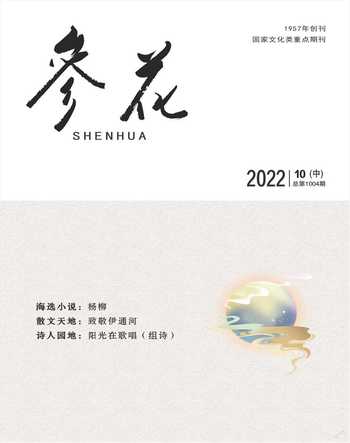浅析勃洛克抒情诗创作第一阶段中的“梦境”
一、引言
“梦境”研究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热门话题之一。众多学者经常提及“梦境”,并试图以自己的方式阐释这种状态。无论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还是荣格的相关著作,都是这一时期解读“梦境”的代表作品。关于“梦境”的研究,引起了许多诗人,尤其是象征主义诗人们的注意,其中就包括勃洛克。“梦境”常常出现在勃洛克的诗歌里,这让他的抒情诗从整体上具备了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魔鬼告诉伊万·卡拉马佐夫的“梦境”相媲美的特质:“……人往往会做一些精美绝伦的梦,看到极其复杂而又真实的生活,看到许多事件乃至整部历史,其中贯穿着苦心设计的密谋,连带着意想不到的细节,大到可歌可泣的壮举,小到胸衬上的一粒扣子……”
勃洛克在生前自编的抒情诗三卷集,即1916年版本,是目前学者们普遍遵循的版本(第一卷收入了1898—1904年的作品,第二卷收入了1904—1908年的作品,第三卷收入了1907—1916年的作品),它常常被视为划分勃洛克抒情诗创作阶段的参考文献。虽然上述每一卷的作品中都有“梦境”出现,但是相比之下,与“梦境”有关的主题在第一卷和同时期未被收录的诗歌作品中,被提到的次数最多,因而值得关注。
勃洛克抒情诗创作的第一阶段,作品繁多。它们有一些被收录在卷集中,卷集包含三个组诗,依次是《黎明前》(1898—1900)、《美妇人集》(1901—1902)和《岔路口》(1903—1904)。当然,也有一些未被收录的佳作。随着诗人思想的不断深刻和技艺的纯熟,“梦境”在这一阶段的诗歌作品中,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并愈发积极地与现实互动起来。
二、美妙之梦与现实的两分
勃洛克在其早期創作的诗集《黎明前》中,就已经开始呈现“梦境”这一主题:“我追求富丽的自由/我向往美妙的异地/那辽阔纯净的原野/如梦似幻,令人心旷神怡……”(《我追求富丽的自由……》)勃洛克认为,人类生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并把美好的世界视为“梦境”。这种二元性的观点,是浪漫主义者重要的美学思想之一。它深刻地影响了勃洛克,这才使得勃洛克眼中的“梦境”呈现出类似《我追求富丽的自由……》中所体现出的特征:梦中的世界与现实生活截然相反。“梦境”被视为从繁乱的生活中脱离出来后,进入的和平且安静的空间。就像诗歌里写的那样,抒情主人公所渴望的“美妙的异地”是“如梦似幻,令人心旷神怡”的。那里就像一个乌托邦,它是抒情主人公最原始和真实的诉求。类似的描写在其他作品中也经常出现,尽管有些作品并未被收入抒情诗第一卷中。例如在《这是沉醉于幸福美梦的时辰……》中,他写道:“这是沉醉于幸福美梦的时辰……周围一片静谧。你听:窗外/夜莺是否在为我们把幸福预言……”
为了更好地证明“梦境”是一个能够摆脱世俗,以慰藉精神的出口,勃洛克还常常将“梦境”与“神圣的殿堂”联系起来。在那里,人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精神的力量,探索生命的奥秘。为此,他在作品中呼唤:“呵,相信吧,我将向你献上我的生命/请你给我这个人不幸的诗人/打开进入新的神殿的大门,指出一条……”现实生活虽然不同于美好的“梦境”,但它能给人无限的真实感,唤醒人类的感情。勃洛克清晰地知道,现实与“梦境”的两分,他曾经在组诗《黎明前》里的另一个作品中写道:“为了眼前这短暂的/而明天将逝的梦/年轻的诗人准备着……又是恐慌,又是向往/又一次想要倾听/生活全部决战的交响/直到新的梦来临!”(《为了眼前这短暂的……》)
三、神秘之梦与现实的联结
渐渐地,“梦境”变成与现实生活不完全相对的存在。它在诗人的笔下与现实建立了一种全新的联结。这种联结的建立,在《黎明前》中的一些诗歌里已经初见端倪。例如下面这首诗所描绘的,诗人发现自己命运的“艰涩”,生活好似一场“忧郁的梦”,无法被控制,让他备受折磨:“我是衰老的灵魂。某种艰涩的命运——是我辗转的轨线/忧郁的梦,面目狰狞又久久不散/这让我的胸口窒息难安……”(《我是衰老的灵魂。某种艰涩的命运——》)
慢慢地,勃洛克开始站在“梦境”与现实的交汇处,他笔下的抒情主人公也因此经常进入半梦半醒的状态。他感觉不到时间的运动,时间对他而言是冻结的。在这种状态下,“梦境”与现实开始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他在《寂静的午夜。锁链……》中写道:“寂静的午夜。锁链/套牢沉睡的灵魂/我徒劳地渴求灵感——枯败之翼跳动不再……”
在组诗《美妇人集》里,勃洛克终于找到了联结“梦境”与现实的方式。深受索洛维约夫提出的索菲娅学说影响的勃洛克,在《美妇人集》里创造了一位神秘的女性。虽然她拥有多样的面孔,但无论如何变化,她都是索菲娅的代表。索菲娅既是神的化身,也是理想化的人类的象征,既是彼岸世界的象征,也是生活在尘世里的美丽女郎。索菲娅是一个中介,一个连接现实世界与彼岸世界的纽带。正是索菲娅的出现,加速了勃洛克笔下的“梦境”与现实的联结。正如《美妇人集》中的诗歌《有谁在窃窃私语,在笑……》中写的那样:“……又是窃窃私语——这私语/饱含着谁的温存,恍然如梦/这不知是谁的女性的呼吸啊/我永恒的欢乐显然就在其中……”
在诗歌《我走出家门。冬日的黄昏……》中,勃洛克进一步刻画了“梦境”和现实的联结:“……啊,这些有过美好年华的人/伴着你们来自深处的歌声/黄昏在大地上降临/永恒的梦随之苏醒!”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不仅致力于抒写诗人心中的“梦境”世界,打开通往“永恒”的大门,而且还极大地引发了读者对“梦境”与现实的联结的关注。在这首诗中,现实世界的黄昏和“梦境”的形象是息息相关的。因为“黄昏在大地上降临”之时,“永恒的梦”才会“随之苏醒”。
对于勃洛克而言,虽然“梦境”好似被迷雾笼罩,掩盖了一些神秘的、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但是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没有舍弃看似“不存在的思想”和“不存在的幻觉”。正是因为他灵魂中的诗意和敏感,才能让他立足于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彼岸世界的边界。与此同时,勃洛克进一步探索了诗人的使命。他在“梦境”的指引下,获得了新的启迪。因此,人们才会在勃洛克于1900年创作的诗歌《沉默无语的梦幻有时……》里看到,诗人的使命是创造一种“沉默的梦境”,并将它带入他人的意识中:“沉默无语的梦幻有时/诞生于幻想/它们闪耀在太阳和你之间/映照着春光……”
四、沉重之梦与现实的融合
从1901年开始,勃洛克的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他逐渐意识到理想的不可实现性。虽然此时诗人笔下的“梦境”,大多还有着明亮的、甜蜜的、温柔的特点,但是“沉重的梦境”也出现了。勃洛克因“沉重的梦境”而备受煎熬。在茹科夫斯基的《斯维特兰娜》的巧妙变体《除夕夜》一诗中,勃洛克把“梦境”与“秘密游戏的幻想”以及“低语和嬉笑”关联起来,“梦境”甚至获得了欺骗属性:“冰冷的雾气私下弥漫/暗红的篝火在燃烧/斯维特兰娜寒冷的灵魂/沉溺在秘密游戏的幻想中……有人在低语和嬉笑/而篝火正燃烧,燃烧……”
在《不曾存在的沉思之梦……》中,勃洛克直接对“梦境”发出了质疑:“所有梦幻都那么短暂——我还会相信它们吗?可是,我这偶然、可怜、易朽的人,或许,还会得到/宇宙的女王/无言之美的垂青……”而在《老者》这首诗中,勃洛克失去了昔日对“梦境”的追求和对光明未来的信念。“梦境”的沉重之感进一步加深:“在忘却了圣物的衰迈之年/我凭借枯竭的记忆生活/曾经——在那里——我俩在一起/可那是在梦中——并非现实……”
在《房屋犹如愿望似的生长……》一诗中,勃洛克借古希腊神话中吟游诗人奥尔甫斯的形象,诉说现实带来的痛苦。它们击碎了“梦境”承载着的理想之美:“房屋犹如愿望似的生长/可是,你若突然往后一瞥/在曾经有过白色建筑的地方/你将看见一座黑色的厕所/一切事物就这样相互易位/悄悄地消失在高空中/你,奥尔甫斯,失去了新娘/谁对你低语:‘回头看一下……”根据神话记载,奥尔甫斯为了他去世的妻子欧律狄克,乞求冥王和冥后把妻子还给他。但是在返回人间的路上,奥尔甫斯不顾禁忌,回头看了一眼,由此,永遠地失去了欧律狄克。奥尔甫斯的回首与抒情主人公“梦境”的毁灭相关,诗歌与神话内容形成紧密的互文感:当诗歌里的抒情主人公一回头,他发现自己身处的现实是一个“黑色的厕所”。美好的“梦境”在片刻之间破碎、瓦解。
在组诗《岔路口》中,“梦境”开始被赋予更多的负面含义,它变成了黑色的、沉重的,而不是神圣的、蔚蓝的、温柔的。就如同组诗的名字一样,“岔路口”很容易让人把它与“艰难的选择”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无论从它本体的特点看,还是在它所承载的象征含义上体会,它在勃洛克笔下指代的,并不是一种相对顺遂的生存状态。例如,在《当我开始衰老和冷漠时……》中,诗人写道:“……糟糕的梦!我的预言诗歌里/糟糕的时刻……”
除此之外,在组诗《岔路口》中,“梦境”被注入了更多有关现实的元素,例如人物或者人物的行为举止。这让它和现实世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交融: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从那时到如今
谁也不知道过去了几多岁月。
我们很少见面也很少交谈,
彼此间往往是很深很深的沉默。
一个冬日夜晚,相信了自己的梦,
我走出人声鼎沸的明亮的舞厅,
在那里,闷热的面具对着歌女微笑,
我的一双眼睛把她贪婪地紧盯——
…………
一个阳光明媚、寒冷而美好的白天,
我们相会在悄无声息的教堂,
深深的寂静使多年沉默豁然开朗,
我们懂了:过去的一切发生在高高的地方。
…………
《那时她才十五岁,但凭心跳……》
这首有关勃洛克的爱人——门捷列娃的诗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诗歌中出现的“自己的梦”,其实暗指了诗人的生活经历,因为在“梦境”里出现的舞厅、歌女、微笑……还有关键的“她”,均是来自现实生活的元素,几乎不带有明显的象征主义色彩。门捷列娃在她的回忆录中提到了这段经历:“在神话般的树林里(鲍勃洛沃附近教堂的树林,聚会在门捷列夫家的青年人常去那儿散步)并肩而行,沉默不语——这在我们见面的时候真是无声胜有声”。而且,诗歌中的“一个冬日夜晚”和“一个阳光明媚、寒冷而美好的白天”都有具体对应的日期:1902年11月7日和9日。它们分别是女校的学生在舞会结束后,勃洛克向门捷列娃求爱的那个夜晚和在喀山大教堂约会的那个白天。诗歌真实而含蓄地描绘出了二人爱情的坎坷,尽管门捷列娃朗诵时会产生“似我非我”之感,但是她仍旧能够体会到“那里的一切是悦耳动听且令人回味无穷的”。
五、结语
楚科夫斯基把勃洛克称作“梦境的歌者”:“……他早期的诗歌中没有明确的格式,只有幻象的碎片,事件的片段,阴霾形象地拼凑,就像不安的梦境”。应该肯定的是,勃洛克抒情诗创作第一阶段中的“梦境”确实影响了诗歌的主题。只不过,它不仅影响了一首诗,影响了一部诗集,更影响了诗人这一时期创作的历程。“梦境”不但是诗歌中所呈现的意象,还是勃洛克思想的“代言人”。
参考文献:
[1][俄]亚·亚·勃洛克.勃洛克抒情诗选[M].丁人,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2][俄]亚·亚·勃洛克.勃洛克诗选[M].郑体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3]汪剑钊,主编.[俄]勃洛克,著.死亡的舞蹈——勃洛克诗选[M].汪剑钊,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14.
[4]亚·勃洛克.知识分子与革命[M].林精华,黄忠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5]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1890年代—1920年代初(共4册)[M].谷羽,王亚民,等.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
[6]图尔科夫.光与善的骄子——勃洛克传[M].郑体武,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93.
[7]于胜民.美妇人形象的原型世界——《美妇人诗吟》解读[J].外国文学研究,1998(04):
106-111.
[8]于胜民.试析《美妇人诗吟》抒情主人公的象征形象[J].外国文学研究,2004(01):81-86+172.
(作者简介:王乔,女,硕士研究生在读,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