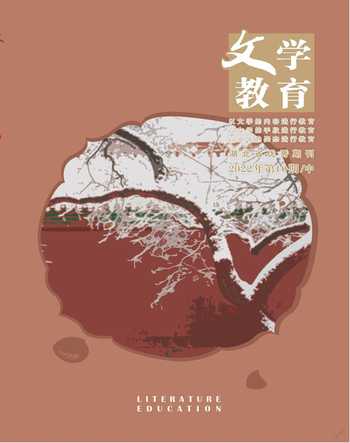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域下的《日瓦戈医生》
蒙瑶
内容摘要: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作为俄罗斯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他以俄国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大变革为背景,写出了“半自传体”小说《日瓦戈医生》,并因此获得了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除了主人公尤里·日瓦戈,帕斯捷尔纳克在小说中塑造出无数个鲜活的俄罗斯人物,尤其是充满俄罗斯精神的女性,她们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大放异彩,呈现出了俄罗斯民族心理,也见证着俄罗斯苦难、深重的历史。
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日瓦戈 俄罗斯文学
《日瓦戈医生》作为一部俄罗斯史诗级的作品,生动地展示了俄罗斯那个新旧交替、政治格局动荡不安的特殊年代。这种形势下,像日瓦戈这样的知识分子都陷入了精神危机,更何况是社会地位不高、势单力薄的女性。但是在《日瓦戈医生》中,许多女性往往以强大的精神和坚韧的心灵,在腥风血雨中发挥出了女性的惊人力量与过人的智慧。她们对于家庭、伦理的思考,个人爱情的体悟以及对社会现状的见识,都不输于书中的任何一个男性角色,展现了战争年代下的女性魅力和不屈不挠的俄国精神。
一.伦理与爱情之间的女性认知
在小说中,作者塑造了许多女性人物,她们个性鲜明却又同样命运多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与日瓦戈息息相关的三位女性人物,分别是冬妮娅、拉拉、马林娜。冬妮娅是日瓦戈的第一个妻子,她与日瓦戈是青梅竹马,这个充满“天真无邪的童稚气味”的姑娘带给了日瓦戈温馨的家庭生活。冬妮娅和日瓦戈结婚后不久,正好赶上了战争爆发,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时期,她极少抱怨命运的不公,当丈夫日瓦戈不知去向时,她又以坚强的意志,撑着刚生完孩子虚弱的身体,带着一双儿女还有年老的父亲,从瓦雷金诺赶往莫斯科,随后又不幸受到政治牵连,全家都被驱逐出境。这一系列的磨难不仅没有让冬妮娅失去信心,反而让她在一次又一次的痛苦中向更多人传递她的母性关怀。即便当她知道了日瓦戈已经爱上了拉拉,她也对此表示理解,她在信中动情地说道:“一切我都不怪你,不责备你,照你的意思去活,只要对你好,我就快乐”[1]。日瓦戈第三任妻子马林娜也是如此,她虽然只是门房马克尔的女儿,但她是发自内心地深爱着日瓦戈,哪怕日瓦戈给不了她一个妻子的名分,她也在日瓦戈穷困潦倒的时候给予他无限的关怀,甚至不惜辞去邮电总局的工作,“原谅日瓦戈的古怪,忍受他的牢骚,他的脾气,他的神经紧张”。
冬妮娅和马林娜都把家庭放在了首位,从而不断地牺牲自我,她们对自己认知是妻子、母亲,因此她们认为承担家庭责任是义不容辞的。在战争和炮火面前,照顾孩子、体贴丈夫依然是她们的生活中心。列夫托尔斯泰曾经在1868年一篇《论婚姻和妇女天职》中谈到他对于婚姻家庭的思考,他说:“男人的天职是做人类社会蜂房的工蜂,他是无限多样化的;而母亲天职呢,没有她们便不可能繁衍后代,这是确定无疑的”,在托尔斯泰看来,“一个妇女为了献身于母亲的天职而抛弃个人追求越多,她就越完美”[2]。冬妮娅和马林娜便是如此。即使冬妮娅明白她和日瓦戈之间存在“我爱你而你不爱我”的问题,她也选择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认为“不能够把这个打击加在任何人头上”。除了冬妮娅和马林娜,在小说中还有很多女性,她们饱受战争折磨,可还是不忘孩子和丈夫。就像书中帕姆菲尔的妻子一样,她只有两个烦恼——“母牛和丈夫”。这些犹如冬天里常青树的母亲们、妻子们是俄罗斯女性的时代缩影,永远凝结着一种女性永恒之美。
相对而言,拉拉是一个特殊的女性形象。冬妮娅曾经这么评价拉拉,“我(冬妮娅)生来就要使生活简单,寻求理智的解决,而她,总是把生活弄复杂,制造混乱”。冬妮娅代表了传统意义中的俄罗斯女性,而拉拉则是从悬崖峭壁生长出来的向日葵,注定了她的不平凡。在拉拉不谙世事的时候,她就被母亲的情人科马罗夫斯基诱奸。她一面在情欲中沉浮,享受被男人欣赏的得意,一面又暗自谴责自己,在道德和乱伦的折磨下痛苦不堪。但当拉拉意识到科马罗夫斯基“悲剧式的空洞誓言”后,她便义无反顾地决定靠自己的力量离开科马罗夫斯基的控制。从这个时候开始,拉拉完成了女孩到女人的蜕变,她成为了像冬妮娅一样具有传统美德的女性。有所不同的是,冬妮娅出身良好,她的美德是从小培养的,而拉拉却是在历经了精神折磨和身体屈辱后,从堕落走向了女性觉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拉拉更具有抗争意识。一段良好的婚姻会成为女性的规范,让女性按照妻子、母亲的身份来行动。结婚后的拉拉也因此逐渐成熟起来,她把爱情融入照顾家庭这一责任和义务当中,在帕沙参军失踪后,她把孩子交给亲戚抚养,孤身一人去了战区当护士,寻找帕沙的下落。她和日瓦戈在一起后,经常帮着处理家务琐事,让日瓦戈感受到了女性的魅力和久违的家庭温暖。在这一点上看,拉拉和冬妮娅并没有什么不同,她们都是把家庭责任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勇于追求爱情的同时也不忘身上伦理、道德,清醒而又克制,寻求心灵的宁静。
在“所有的习俗和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家庭和秩序有关的一切,都在大动乱和重建中化为尘埃”的时候,像拉拉、冬妮娅、马林娜这些被时代裹挟的女性依然坚守着家庭阵地,“把其责任融入到了一个更加完全的生活”,升华到了近乎无私、时刻准备牺牲自我的地步,这种精神是俄罗斯女性在白银时代的真实写照。
二.战争中的女性力量
小说涉及到了俄国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穿插了很多历史著名的大事件,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二月革命等,这就注定了小说当中的人物都被暴露在残酷的战争当中,让读者在绝境之下看到女性迫于生存而爆发出的力量和智慧。长期以来,在人们的潜意识里,男性通常在战争中占据主导力量,但在小说当中,帕斯捷尔纳克把女性塑造极具“战斗精神”。当游击队击破白军之后,难民纷纷涌入营地过程中,“女人们发挥出了不可思议的机智与奇迹”,她们砍伐树木,架桥铺路,砍开一条三十俄里长的路,让负责接待妇女难民的斯维利德不得不感慨,“还能说她们是娘们吗?她们做了我们三十个星期才能做得完的工作”。
女兽医库巴丽哈在其中是个富有女性魅力的角色,她敢于在军营唱一曲忧伤的俄罗斯民歌,传达了激昂的战斗情绪,充满对侵略者的憎恨,还隐藏着战士们强烈的归乡情感,安慰了不少士兵们包括日瓦戈在内失落的心灵。库巴丽哈把红色军旗当做“亡女的紫色手帕”,认为内战给人民带去了痛苦、灾难,让人不得不去反思这场战争是否真的有益于国家,显露出了女性对整个历史敏锐的洞察力。在小说的结尾,甚至还涌现出了赫里斯金娜这样的女战士,她勇敢地潛入了德军防线,却因此被生擒绞死,这种超越了家庭和个人生活,具有大无畏、爱国精神的女性令人钦佩不已,体现了俄罗斯女性在残酷战争和强烈求生欲望下的巨大力量。
女性“由于历史的剧烈变动而每况愈下的命运,就不会仅仅是她一己遭遇,而是那个动荡时代强烈影响个体命运的一种典型性的艺术反映”[3],书中的“多灾多难的俄罗斯女性”已经成为战争中反复遭受折磨的弱者与时代对话的一种象征。这里的“弱小”是面对时代洪流来说的,同样,男性也不是全能的,他们也并不能在战争中幸免。我要说的是,女性因为身处父权制或者男性偏见中,而被常常忽略掉她们身上的女性力量。波伏娃曾在《第二性》中谈到“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还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4]。“脆弱”“无知”“受保护者”等定义是男性强加给女性一种标准,或是对女性力量的变相恐惧。当斯维利德跟利韦里说妇女们惊人的工作能力时,利韦里冷酷地打断了他的话,在利韦里这样的男性长官看来,难民本身就给他们行军添加了很多压力,更何况是一群妇女,他把女性的弱小和无能这些缺点无限放大,以至于直接忽略女性们所做的贡献。换句话说,承认女性们在后方做出了巨大贡献,相当于否定他们男性的军绩,变相地承认他们突围的无能。如果跳出了传统定义的视角,女性展示的力量是颠覆性的,因为这种力量是突破生理上的差异和权力的不平衡而换来的。在渴望生存的强大动力之下,女性潜在的力量会让她们暂时忘记社会强加给她们的“女性身份”,女性也并非像男性定义的准则那样缺乏能力,只不过由于社会过于把女性束缚在比男性低一阶级的地位上,从而限制了女性才能,进而又加深男性对女性的认知固化。
三.父权制文化下的女性抗争
拉拉被科马罗夫斯基诱奸后,产生了极大的乱伦和背德感,拉拉无时无刻都想摆脱这种思想包袱。当拉拉在斯文基茨家的舞会中,看到那个曾经伤害自己的人正在使用花招诱骗其他女孩时,她仿佛看见了曾经那个堕落的自己,“一个新的牺牲品”。于是为了维护人格尊严,她拿出了提前装好子弹的手枪射向科马罗夫斯基,正如文中所说的“这一枪射向科马罗夫斯基,射向她自己,射向她的命运”。拉拉从她的原生家庭开始,就注定了不幸。拉拉是贫困人家的女儿,她的母亲吉沙尔夫人只知道依附男人。拉拉很清楚自己是无罪的一方,和母亲的情人在一起这件事是有违道德伦理的,但她不理解为什么自己总是屈服于科马罗夫斯基的淫威。正如日瓦戈所说的“人性,特别是女人性情,总是那么不可理喻且充满矛盾的,或许就在你的厌恶中,有些东西使你愿意屈从于他,还超过你爱任何以你的自由意志所爱的男人”。
由此看来,拉拉从小就得不到正确的性教育,并且长期得不到父亲的关怀,使她无法直面自己内心深处,于是不知不觉地陷入科马罗夫斯基的陷阱,“不断地从他者身上寻找以便补充这种缺乏”[5],一方面,科马罗夫斯基有着金钱和权力,他用经济压迫、精神控制禁锢着拉拉,让拉拉成为他的奴隶;另一方面,在父权制的社会语境下,拉拉有一定程度的“厄勒克特拉情结”,她对母亲充满了失望,而科马罗夫斯基这时又以拯救者的身份出现,帮助了她们一家。就这样,拉拉不断地从科马罗夫斯基身上寻找这种男性关爱,从他的眼中看到“廉价、扭曲的一面”,再加上在父权传统中,女性总是被认为从属于男性地位,因此童年时期的拉拉多次纠结两人的不伦感情,却又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所幸的是拉拉还是从男性欲望的牢笼中逃离出来,以一种少女罕见的决心争取到了独立、自由的生活。这种抗争是极为宝贵的,因为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俄罗斯女性依然束缚在男权至上的家庭格局中,尤其是深受基督教影响的俄罗斯民族,大多数女性几乎是不可能冲破这种精神枷锁。在社会经济、权利远远不如男性的历史进程中,女性是处于弱势一方,要时刻担心名声受损。如火车上少女佩拉吉娅,她深爱着一无所有的普里图利耶夫,即使他被捕,不得不四处颠簸,佩拉吉娅也不离不弃,甚至以一颗母爱的心去照顾普利图里耶夫的侄子瓦夏。可就是这样无私奉献的女性,却被认为和少年瓦夏有私情,被无数人说闲话,最后她只好逃出来,暂时去已婚姐姐家躲避。还有加卢津娜,作为年轻时受到很多青年人喜爱的她,看到战争带来的破败而痛心疾首的同时,又不得不陷入道德漩涡,不敢一个人深夜在街上转悠,因为容易“让人说闲话”,并安慰自己“不是坏人”,“是个好女人”。这种反复的胡思乱想正体现了男权压制和传统道德下女性对自我约束。实际上,当时很多女性都曾集体无意识地倒回到传统父权制文化下的行为规范中,因为长期浸淫在男性主导的社会话语权下,女性被动地被男性误导,辨别不清其中的性别偏见,还被男性塑造出来女性形象给蒙蔽,最后不得不自觉地将其内化为自身标准,成为了时代的牺牲品和男性的所属物。
《日瓦戈医生》塑造了一群“多灾多难”的俄罗斯女性,在特殊年代生活着的她们为了家庭做出了巨大牺牲,展现出了女性无私、奉献的一面,出色地完成了女性的社会功能;同时,她们理智对待感情,对男性话语权勇敢地说“不”;在俄国秩序混乱、动荡不安的“恐怖时代”依然保存着至高无上的人道主义,用一颗“俄罗斯的心”包容、温暖着伤痕累累的民族。除了小说中的男性角色,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拉拉、冬妮娅等女性也同样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灭的痕迹,成为俄罗斯精神的代表人物,让读者们为帕斯捷尔纳克的家乡“俄罗斯的美丽哭泣”,为这群伟大的俄罗斯女性所深深地感动。
参考文献
[1](苏)帕斯捷尔纳克著;黄燕德译.《日瓦戈医生》[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8(2015.4重印).
[2](俄)列夫·托尔斯泰著;陈琛主编.《列夫托尔斯泰文集(1-4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6.
[3]汪介之著.《诗人的散文:帕斯捷尔纳克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4](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桑竹影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5]柏棣主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论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