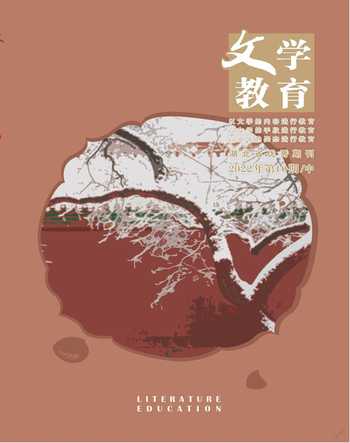十九世纪早期法国文学中的丹蒂想象
范晶
内容摘要:旧制度下的法国在宫廷文化中孕育出了以追求奢华为主要内涵的贵族风雅。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早期,受激进革命的冲击和英伦风尚的引导,法国出现了一种不同以往的风雅之士——丹蒂。这一群体不再局限于贵族,其成员来自社会的中上层。本文从巴尔扎克、欧仁·苏、司汤达等人的小说作品入手,剖析当时法国丹蒂的文学想象,并尝试解读民众对这一群体的社会心态。
关键词:丹蒂 法国文学 贵族文化 社会心态
十九世纪早期,随着法国复辟王朝的建立,诞生于英伦的一股新兴潮流——丹蒂(Dandy)[1]风尚——借由赴法的英国时尚人士和归国的法国流亡贵族,逐渐传播至法国。它与法国本土源远流长的风雅观念相结合,最终孕育出法国丹蒂群体。这一群体的特征包括:穿戴简约而精致的服饰,讲究优雅的言行,培养悠闲而无用的嗜好,内心保持无动于衷、冷漠自恋,追求独一无二。
在主流历史书写中这一群体未曾占据重要位置,但实际上人们很难不注意到这个群体:“丹蒂以他们优雅的外表,精致的服装和一丝不苛的修饰,成为十九世纪法国社会不可忽视的一类人”。[2]当时,资产阶级男士通常在着装上选择黑色、白色等色彩,他们致力于生产性工作,不需要展示身体。然而,延续了贵族风雅的法国丹蒂群体则完全不同。在套裤、蕾丝、假发日渐消逝的民主时代,身穿简洁三件套的他们依然保留了贵族服饰的一抹艳丽,青睐使用明亮的色彩突出自身与众不同的优雅外观,例如奥尔赛伯爵偏好蓝色,巴贝·道勒维热衷红色。丹蒂亲自上蜡的鞋子,适度磨旧、磨薄的镜片,只有剪刀方可拆解的繁复领结都塑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别致,比资产阶级希望的得体、整洁更胜一筹。这一群体从本质上拒绝工作的功利性,即赚取钱财,发家致富。他们把礼节、品味、生活方式当作社会竞争的筹码,希望生活、爱好成为其主要的工作。归根到底,这是贵族“无用”性的延续。在旧制度下,“贵族不需要工作,他们是什么远比他们做什么更重要。他们拥有高贵的封号,至于是否具有功能对他们的天赋特性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当丹蒂活跃于法国的各个公共空间时,其衍生品——文学想象中的丹蒂也在众多小说中应运而生。十九世纪早期,这些介于虚构、真实之间的人物逐步构建了一个关于丹蒂的传奇神话——无所畏惧的“冷漠纨绔”。
要研究十九世纪早期的丹蒂文学想象,欧仁·苏、司汤达、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不可或缺。德·玛赛、吕西安·夏同、圣雷米子爵[3]等人物均复制了现实同类的高傲俊美,考究衣着,潇洒举止,或在杜伊勒里公园无所事事地漫步,或在自家安乐椅上懒懒散散地晒太阳。不过除此之外,他们身上还具有一些夸大的特质,其中就隐含着民众的看法。
一.雌雄莫辨
巴氏笔下的“丹蒂之王”德·玛赛是一位英国贵族的私生子,他拥有“浓密的栗色卷发,少女般的肌肤,贵族气派的瘦高身材,非常漂亮的手”,[4]外貌阴柔,曾被心怀嫉妒的外省青年吕西安暗地讥讽为“人妖”。拥有贵族血统的吕西安其实也不够孔武有力,他“个子中等,细挑身材,看他的脚,你会疑心是女扮男装的姑娘”[5]。与两人均有相识的年轻伯爵德·脱拉伊则“穿着一件紧贴腰肢的外氅,像一个美丽的女人”[6]。
这种雌雄莫辨的形象与现实情况有所出入,穿着简雅的法国丹蒂虽然不及昔日的尚武贵族英勇,但绝非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并且,自视甚高的丹蒂始终排斥女性,因为他们认为女性保留了难以自控的动物属性,与其“自我升华”的贵族气质相悖。在本雅明、巴特等现代学者的研究中,法国丹蒂一直是纯粹的男子群体[7]。不过,如果站在民众的角度,可以发现他们很难达成所愿从而划清与女性的身份界限,甚至在“某些方面的确如女子”。首先,丹蒂热衷征服女性,这种缺乏情爱的行为或许只是为了满足虚荣心,但也证明只有女性的美丽才能与丹蒂的优雅相媲美,并博得丹蒂的青睐。在学者杰西卡·弗尔德曼看来,优雅、美丽分别专属于男、女两性,优雅的魅力弱于美丽,气势却强于美丽。事实上,丹蒂身旁女子的美丽更能衬托出他们独具一格的男性优雅,当时的人们经常能在林荫大道上看到这些结伴而行的风姿绰约的男女。其次,“对丹蒂和女性来说,自我展示即生存之道”,这是两者最为重要的相似之处。1804年《民法典》颁布后,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逐渐固定,他们分别主导公共、私人空间,形成了二元互补的格局。在这种背景下,男性以工作为天职,应该具备审慎、勤奋等品质,同时外观装束必须弃绝鲜艳,保持朴素、低调。与此相对,女性关注家庭事务,她们被看成是“依赖、被动和弱小”[8]的,更乐意使用明亮的色彩凸显自己温柔、娇弱的一面,以此吸引异性。如萨特所说,“女人——资产阶级的女人——以深深依附他人的看法为其主要特征……她无所事事,受人供养,通过取悦他人迫使他人接受她,她为取悦而装扮自己,她的服装,她的脂粉把她部分交出去,部分隐藏起来;男子中若有谁意外地也在同样情况中生活,他就同样承担了女人的特性。”[9]法国丹蒂就处于这样的情况,他们以不事劳作、狂热修饰等女性化方式表现简雅的男子气概,这种矛盾的行为无疑冲击了业已确立的两性格局,因而在公众心中留下了超越男女的中性形象。事实上,一部分民众十分向往丹蒂雌雄莫辩的神秘气质。在他们眼中,不需要性別互补的丹蒂中立、超然,既有冷漠、高傲、自我控制的“男子气”,又有精致、敏感、耽于享受的“女子气”,已经“蕴涵了内在的均衡”。
二.冷酷无情
能否成为贵族需要由先天出身决定,但能否成为“贵族气”的丹蒂却取决于后天修行。十九世纪早期各位作家笔下的法国丹蒂在踏入上流社会前也多半是一些不谙世事的青年,然而当他们穿上华丽的衣着后,就会变得傲慢、寡淡,初涉巴黎社交界的吕西安·夏同、欧也纳·拉斯蒂涅、于连·索莱尔[10]莫不如此。不过,戴上冷漠面具的外省青年仍处于丹蒂自控的“学徒”状态,离真正的“大师”级别——如德·玛赛与德·脱拉伊——尚有距离。德·玛赛在《人间喜剧》初次登场时表情温和、谦逊,双目清澈如水,但内心 “既不相信男人,也不相信女人,不信上帝,也不信魔鬼”。[11]当时,这位年满二十二岁的自在青年爱慕着“金眼女郎”芭基塔·瓦勒戴斯,然而在知晓情人不忠后,他就毫不犹豫地想要杀害她,之后更是再未对任何一位女性付出真心。德·脱拉伊同样冷酷,而且毫无顾忌。“如果说德·玛赛已经是一个怪物,那他则更为暴力”,[12]“他喜欢挑拨人家侮辱他,然后先下手为强,一枪把敌人打死”。[13]另外,他总是无情地毁掉所爱,比如骗取高老头之女德·雷斯多伯爵夫人的财产。事实上,正常人很难像他们一样永久地抑制自身情感,小说中不少丹蒂的失败即在于此。《幻灭》中初到巴黎的吕西安才华横溢,但因为幼稚轻率、优柔寡断的个性在报业斗争中身败名裂,差点被迫自尽。之后,在苦役犯伏脱冷的引诱下,他转身变成了《交际花盛衰记》中的德·吕庞泼莱侯爵,一位看似冷眼逡巡的丹蒂。然而,吕西安始终无法割舍情义,在所爱埃丝黛含恨而亡后,他也因悔意自我了结。作为吕西安的同乡兼前辈,欧也纳也曾在无情、有情间彷徨、迟疑。开始,他不愿听从伏脱冷的建议,丧失神圣的心灵。但是,高老头的悲惨离世“埋葬了他青年人的最后一滴眼泪”[14],面对不胜向往的上流区域,他最终选择与自己曾讨厌的德·脱拉伊一样绝情寡义。
在文学想象中类似撒旦的德·玛赛等人彰显了与平庸相反的冷酷,在现实中,法国丹蒂追求相似的极致,却没有如此狠绝。大部分成员用傲慢一词更恰当,还有一些则连傲慢也谈不上,比如以开朗、随和著称的德·奥尔赛伯爵。这里,不再讨论现实、想象的差距,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民众能否包容这些古怪品质带来的不快。如巴贝·道勒维所说,“法国人天生具有多血质(nervo-sanguine)性格,热情、好交际”,[15]复辟王朝下初识丹蒂的民众曾容忍他们一如贵族的无用,但拒绝接受他们不接地气的冷漠。不过到了七月王朝时期,情况就有所改变。三十年代后,为了适应本土情势,绝大多数法国丹蒂都 “增添了些许笑意,变得更亲和、放松”,“他们开始考虑如何惊艳全场而非惹怒他人”[16]。渐渐地,民众便发现“只要这些阴阳怪气、傲慢冷漠的丹蒂乐意为之,也可变得迷人、优雅、彬彬有礼”[17]。其实,丹蒂只是用贵族优雅掩盖住了古怪无礼,不过人们不再介意。一个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司汤达,这位曾在二十年代嘲笑复辟丹蒂的作家却在几年后的《红与黑》中塑造了同样冷峻的于连,并称其为“当代丹蒂,十分了解巴黎的生活艺术”。总之,这一时期民众迥异于前的态度可以反映出丹蒂社会名誉的提升,而这点在下面提到的特质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三.无所不能
在十九世纪早期的法国文学想象中,具有第二项特质的丹蒂往往无所不能。他们妙语连珠,亦正亦邪,既能掌握自己的人生,也可影响甚至主宰别人的命运。巴尔扎克曾在《浪荡王孙》中作过如下描述:
那是一群二十多岁不超过三十岁的年轻人,个个自命不凡,而又都怀才不遇,但总有一天会崭露头角,成为赫赫要人……在这群浪荡公子中,有出色的外交家,只要有法国当局撑腰,他们就自信有斗垮俄罗斯谋略的能耐。在那里面还可以找到作家、行政人才、军事家、记者、艺术家。总之,可以从中发现各种各样有本领、有才气的人物。这是社会的缩影……而这些年轻人个个心胸豁达,多大的厄运都能处之泰然……他们坚强,坚强得足以对那些无能的统治者给他们造成的处境付之一笑;他们精明,精明得可以看出工作是没有用的,因而什么也不干;他们生气勃勃,能够寻欢作乐——这是他们唯一的,谁也剥夺不了的东西。[18]
德·玛赛依旧是其中的佼佼者,青年时期他在社交界尽得风流,以几句俏皮话就可彻底粉碎吕西安的自信心;中年时期他则在政坛中飞黄腾达,不仅自己当选首相还邀请已是同类的欧也纳出任内阁大臣。与其比肩的德·脱拉伊志不在此,他游戏人间,债台高筑,不过仍然风光无限,因为他总能骗取痴情贵妇的同情以解燃眉之急。即便没有事业、没有援助,那些成功控制情感的虚构丹蒂也屡屡急中生智,摆脱危机,比如以诈死逃避负债的圣雷米子爵、以雅谑应对布尔乔亚债主的德·拉巴菲林。
比之小说里一心为财、附庸风雅的“纽沁根”式暴发户,人们显然更推崇衣冠楚楚、淡然一笑的法国丹蒂。这些邪恶、优雅的“混世魔王”不曾经历现实同类的凄惨晚景——入狱、发疯、梅毒,他们构建了一种凌驾于社会秩序之上的神话。这一传奇不仅源于丹蒂征服上流的个人魅力,更得益于他们在某一方面和当时的民众同气相求——即反对七月王朝的平庸。1830年革命后,以基佐为首的奥尔良政府奉行“折中”观念,它试图依靠大资产阶级把君主主义(但并非“正统”)与自由宪政主义融为一体。在丹蒂和民众眼中,这种“寻求今、昔最佳平衡”的暧昧做法既没有旧制度的光荣,也没有大革命的激情,只剩死气沉沉。不过具体来说,普通百姓与痛恨工业主义、鄙视功利价值的法国丹蒂还是不同的,他们只是单纯拒绝新的不平等。路易·菲利普治下的七月王朝的确比查理十世的复辟王朝更具动力(比如推行教育改革等),但整个社会仍潜藏着断裂的危险。一方面,民主尚未完全达成,选举资格比例只是从七十五分之一略升至四十分之一;另一方面,掌权的大资产阶级却日渐奢侈,民众完全可以用摧毁贵族统治者的主张——反对特权、寄生——抵制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难免会对时常戏弄金融贵族的风雅青年抱有好感甚至希冀,于是拒绝民主、平等的法国丹蒂在文学想象里除了孤高冷酷,也偶尔会对底层人民展露温情:一无所有且婉拒皇家赈济的德·拉巴菲林在提到为其清扫烟囱的“小萨瓦人”时说:“他为我真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什么都明白,就是不明白我是什么也不能给他。”[19]最后,这位玩世不恭的浪荡王孙只好顺手牵羊了几串葡萄送给爱吃水果的童工。
那么,这种文学想象能否持久呢?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日益完善以及商品奇跡的初步浮现,在十九世纪中期,波德莱尔给出了否定的预示:“丹蒂主义是最后一道英雄主义的闪光……是落日余晖……它是辉煌的,没有灼人的炙热,只有淡淡的忧伤。”[20]追求文雅的丹蒂形同死尸,注定会为自己的教义而亡,因为“民主的潮流势不可挡,流溢八方,荡平一切,每日都在席卷人类骄傲的最后斗士,用遗忘之水淹没这些显眼的追随者”[21]。《拉·芳法萝》的萨缪尔是他理想中的末路英雄,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这位虚构的人物最后放弃了丹蒂身份,回归主流资产阶级。到了十九世纪后期,法国作家于斯曼在小说《逆天》中塑造了主人公德·泽森特公爵,这是一位更加纯粹但也更加颓废、病态的“贵族气”丹蒂。他比巴尔扎克笔下的德·玛赛更大胆,比波德莱尔笔下的萨缪尔更善思,可是他的结局没有传奇与温情,只剩崩溃与悲凉。至此,“冷漠纨绔”的神话彻底破灭。
总体而言,丹帝主要来自社会的中上层。他们追求简约的精致,摒弃了繁缛的假发、蕾丝花边以及华丽的珠宝。不过,他们依旧保持了昔日特权阶层的优越感:无所事事、自命不凡。在复杂的社会转型时期,丹蒂一方面拒绝平等、蔑视功利,延续了往昔的贵族文化;另一方面则崇尚独特、重视自我,昭示了全新的现代个性。然而,这一群体整体上缺乏经济、政治资本,不愿也无力介入社会事务,因此在资产阶级鼎盛的时代里,他们虽是心怀轻蔑的旁观者,却无法成为真正坚定的革命者。
在二十乃至二十一世纪,人们依旧可以在西方看见风度翩翩且毫无畏惧的熟悉身影,比如“衣不惊人誓不休”的克里斯汀·迪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米歇尔·福柯等等。这些后起之辈或许不会再系着过时的松垮领带,但他们会永远欣赏丹蒂自我升华的隽永:拒绝平庸,逃离束缚。
参考文献
[1]丹蒂(Dandy):词根源于Dandiprat(指十六世纪英国的一种小额货币,引申为无足轻重之人)。1632年,Dandy首次出现于英格兰、苏格兰边境流传的一首儿歌中,当时它指的是一个喜欢昂贵甜品的自大之人。到了十八世纪后半叶,该词又出现在北美战争时一首名为“Yankee Doodle Dandy”的歌谣中,英国士兵借此嘲笑吊儿郎当的美国士兵。1813年,诗人拜伦正式使用Dandy指代当时一批品味独特的英伦上流,该词得以广泛使用。在现代《牛津英语词典汇编》(1982年版)中,该词意为“过分关注衣着优雅、流行与否的人”。在法国,该词意思主要借鉴其英文原意。《利特雷法语词典》(1872-1877年版)称该词为“服饰讲究、时尚夸张之人”,在现代《罗贝尔法语词典》(1978年版)中则为“炫耀优雅服饰、行为,并且傲慢、自负的人”。我国学术界对Dandy的翻译有浪荡子(郭宏安译,详见其译作《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浮纨(毛尖译,详见其译作《上海摩登》)、纨绔子(周小仪译,详见其著作《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丹蒂(刘北成译,详见其译作《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等。正如李欧梵(《上海摩登》原作者)所说,Dandy在中文里并没有合适的译文,本研究选择刘北成的音译法,因为前三个词作为Dandy译名容易使人对Dandy的本意产生贬义的误解。Dandy虽是悠闲度日的“无用”之物,但绝不等同道德败坏之人.
[2]Deborah Houk, “Self Construction and Sexual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Dandyism”, French Forum, Vol.22, No.1 (January 1997), p.59.
[3]德·瑪赛出自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之《十三人故事》;吕西安·夏同出自同一系列的《幻灭》、《交际花盛衰记》;圣雷米子爵出自欧仁·苏《巴黎的秘密》。
[4][法]巴尔扎克:《十三人故事》,袁树仁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330页.
[5][法]巴尔扎克:《幻灭》,傅雷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2页.
[6][法]巴尔扎克:《高老头》,傅雷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46页.德·脱拉伊出自该书.
[7] Jessica R. Feldman, Gender on the divide: The dandy in modernist literature,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p.10.
[8][英]里斯特:《公民身份:女性主义视角》,夏宏译,吉林: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第110页.
[9][法]萨特:《波德莱尔》,施定强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
[10]欧也纳·拉斯蒂涅出自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之《高老头》、于连·索莱尔出自司汤达《红与黑》.
[11][法]巴尔扎克:《十三人故事》,袁树仁译,第330页.
[12] Karin Becker,Le Dandysme littéraire en France au XIX siècle,Orléans: Paradigme,2010,pp.92-93.
[13][法]巴尔扎克:《高老头》,傅雷译,第47页.
[14]同上,第223页.
[15]BarbeyDAurevilly, Du Dandysme et George Brummell,Paris:Les?魪ditions de Paris,2008,pp.26-27.
[16]?魪milien Carassus,Le Mythe du Dandy,p.33.
[17] Ellen Moers, The dandy:Brummell to Beerbohm, p.141.
[18][法]巴尔扎克:《浪荡王孙》,资中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34-235,244页.德·拉巴菲林伯爵即出自该书.
[19][法]巴尔扎克:《浪荡王孙》,资中筠译,第 245页.
[20] [德]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第255页.
[21] [德]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第255页.
(作者单位:上海书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