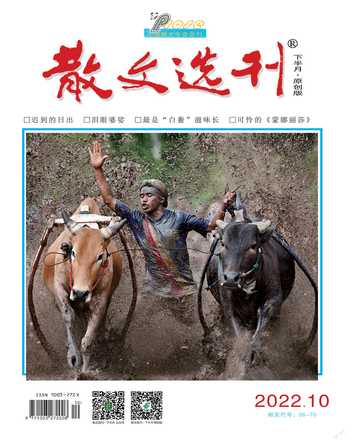剃头
蔡华建
那个炎热的夏天,爷爷去剃头,以一个听来就香到涎水直流的油炸豆巴子作诱饵,把我轻易地带去了桥头剃头店。
爷爷一坐上老式的剃头转椅,就要把拉扇放下来。这是一块用薄篾片编成的宽大的密不透风的竹席,上轴穿在两个竹节里,吊在转椅上方。我拉动着下轴,竹席扇过转椅,凉风阵阵。我拉得高,竹席荡过去也高。我的力气成了持续吹来的凉风,爷爷的白头发被竹扇吹了起来,前后飘转,闪过几丝银光。那是乡间最怡然、最悠闲的景象。
剃头师傅阿贵随爷爷第一次舒服地享受了这种待遇。他除了赞扬我是个乖孩子,还对爷爷买豆巴子奖励我进行督促,又让他的徒弟小云免费给我剃头,我对小云拿我的头做练习提出强烈的抗议。不知是我的头皮太软,还是小云紧张,他竟然在我的头上割出了血口子,留下了一道疤痕。
剃头师傅阿贵要赔我,同意免费给我剃一次头。两个月后,我来阿贵店里剃了头,刚剪完发,我就感觉有一股气从脑里冲出,我大叫一声:“头痛!”捂着头顶就几乎晕了过去,阿贵赶紧过来,用他厚实的手帮我紧紧地捂着头顶,两双手叠在头上,密不透风。
我在村学堂里第一次出现考试不及格这样重大的事件,村里人后来都说肯定是阿贵动了我头上的疤痕,出现裂缝,把我的灵魂放跑了。我对阿贵的谴责就如那天剃头时的碎发毛屑一般纷纷扬扬起来。
但我一直相信,我的灵魂没有离去,因为我后来仍学习成绩优秀,并无异常。
剃头这门手艺,只传男不传女。阿贵为这事发了愁,他只有三个女儿,都嫁了人,但女婿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学剃头,而阿贵已经老了。
就有人趁机而起!
阿喱不知从哪里学了剃头手艺,他在离阿贵剃头店不远处的桥洞里摆了个剃头摊,开始做起了剃头营生。生意起初自然是不好的,因为村里人都不知道他的剃头摊,也怀疑他的手艺没阿贵好。但他不管大人小孩,剃头都收一角钱,比阿贵便宜五分钱。他还在摊子上摆了一摞小人书,把孩子们都吸引了过去。我每次去剃头,阿喱会问我谁做了我的班主任,又跟我聊霍元甲的迷踪拳,争论坏人李元霸为什么是隋唐第一条好汉、程咬金和秦琼两人打不打得過宇文成都……他的手宽厚而温暖,也好像特别有灵性,只要稍微轻轻地一点,我就知道他要我转左转右,抬头低头,我们的默契让我能理解他的一个个细微的动作。他的最后一个动作,就是双手捧着我两边的太阳穴,左转看一眼,右转看一眼,然后用右手掌在我头顶贴着头发唰地划过,就给我剃完头了。
单从快这一点,阿喱肯定比阿贵好。他动作麻利,而且剃头的大多是小孩子,没有其他发型要求,统一平头,铲平剃短就好,也不用刮胡子,掏耳朵。所以,虽然排队的人多,但由于节奏快,也很快会轮到自己。阿喱师傅是往迅疾这个方向发展的,就像练短跑的,越跑越快,越快越短,直到他用手在最后一个人头上唰地划过,他就剃完了所有的头。他挪个凳子坐下来,吸一支烟,看着坐在摊子前的一大帮捧着小人书的孩子,他眯眯着眼,露出一丝笑容。
我知道,他那个手掌划过的动作是剃头的假动作,但我却非常喜欢,那是一个明确的信息,我再也不用忍受着不能随便动的僵硬身子了,也可以去挠一下那一根头发刺得我痒的肌肤了,还可以去看小人书了……
2017年,我在安化县扶贫,一个月后,剃头成了我要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最终选择了这个绿树掩映下的小剃头店,别的店有着高大上的店名,如一个个贵妇般让我难以靠近,而唯独它还是以剃头店自称,朴素直白,就像一个叫小芳或阿香的村姑一样,虽然使人觉得老土,但你想象得到她的简单和直接,这样的剃头店,不需要对价格及其他东西担心和提防。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这家剃头店稍偏僻,我也敢肯定,那个剃头的阿姨不会把电视上坐主席台的那个人与正走进她店里的我对应起来。
果然如我所料,当我进到剃头店用普通话跟她说“剃头”时,她只是站起身用安化话说“坐吧”,没有其他反应。她围好围布,拿出电推,还是用安化话问了我几句,这次我没有完全听懂,但我从听懂的几个词里知道,她是问我怎么剃,我用普通话告诉她剃短些,按原有发型剃。她又问了我一些话,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聊天的话,我都闭着眼没有回答她,她便不再与我说话。
我能近距离看到她粗壮的手腕与粗糙的手掌,自然也能感受到她粗放的剃头技术,她动作迅疾,大开大合,一铲到顶,只见头发一簇簇地跌落,快手过处,不再重复。我倒是正坐敛眉任她发挥。很快,我的头顶马上轻松起来,像是拨云睹日,一时疏朗清旷。她在那张古老的剃头转椅上重重地一拍,就开始解围布,我才知道,那是她告诉我剃完头了。
一直剃到2019年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