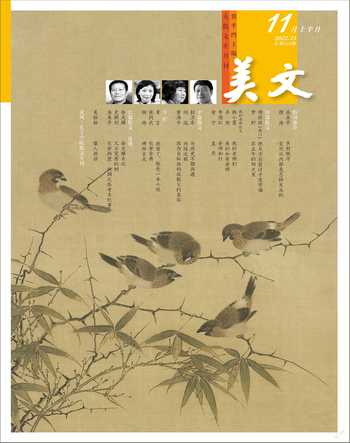亲历“巴铁”之后的思绪

张道建
在我从巴基斯坦回到祖国怀抱的第三周,伊斯兰堡孔子学院的“兄弟孔院”卡拉奇孔子学院遭遇恐怖袭击。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我的第一感受绝不是庆幸,而是极度的悲伤,还有很大程度的内疚:我平安回国了,我的“战友们”却牺牲在了前线。不过,今天我暂时不写这个,我想写一下亲历“巴铁”九年之后的一些感想。
一
1993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的第十五个年头,我幸运地通过高考进入到大学校园学习。当时中国的经济正在腾飞,全国上下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在中国内地的中小城市里,外国人的身影还难得一见,他们仿佛是稀有动物一样,所到之处都会遭到人们注目围观,甚至引起小小的骚动。好奇的人们边看边小声说:“看哪,有个外国人!”
我至今仍记得在大学校园第一次看到外國人时的激动心情。那天我见到的是两位美国外教,一对非常和善的中年夫妇,五十岁上下的年纪。男人有点发福,女人身材削瘦,但都精神饱满,满面红光。他们非常礼貌地叫住我,把一台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数码相机递给我,让我帮他们拍照。我有点不知所措,去接相机的手微微发抖,生怕把那个神奇的宝贝弄坏。这个场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后的某一天,当外国人在中国已经不再引人注目时,我却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当了“外国人”,我遭遇了当年外国人在中国的奇遇,同样被人围观,同样承受他们好奇的眼光,同样听到他们小声议论:“Chinese!Chinese!”
以上这个小小的例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几十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也反映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自我更新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文明既是古老的也是新兴的。
我所到的国家是巴基斯坦,中国人习惯称他为“巴铁”。巴基斯坦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我对那里的第一印象是路上行驶的中巴车,有的乘客把整个身体吊在车门外,甚至有人坐在车顶上,还有慢腾腾行走的牛群穿行在车流之中。这个情景让我联想到一些童年记忆,我也曾经在八十年代见过坐在行李架上的乘客,但那早已经成了被尘封的历史消失不见了。此外还有随处可见的荷枪实弹的军警、保安,被装饰得五光十色的大小车辆,这些都是我从未见过的。
我很快就对各种“异国情调”视而不见了。我习惯了每天五次从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中传出的唱经声,习惯了每天六次停电,习惯了那里的酷暑高温,也习惯了经常发出的安全警报和充斥着恐怖袭击的新闻……我融入了一个原本陌生的国度,不再感觉到自己是个异邦人。
在巴基斯坦工作生活九年,我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以孔子学院为平台,开展汉语教学和文化交流活动,和我打交道的人当中有巴方部队的将军、有国会的议员、有大中小学领导和教师,也有无数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他们对于中国人的友好、热情和真挚的感情让我非常感动,也铭记在心。
二
当然,我也经常会碰到各种有关中国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大致被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猎奇性的问题,例如听说中国人只喝开水,为什么?听说中国人下午四点以后就不吃东西了,为什么?听说中国人都不信宗教,为什么?听说中国人什么都吃,甚至吃油炸蟑螂……从这些充满了误解和好奇的问题里,我有时候会感到稍许的尴尬和压力。我心里时常感慨,即便是在信息化如此发达、全球化成为现实的时代,误解仍然是普遍存在的,在虚拟的数字化信息交互之外,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和交流也仍然是有必要的。因为,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文化交流的核心应该是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和人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孔子学院作为语言和文化交流的机构,承担了一部分这样的任务,但仅靠孔院是远远不够的,我个人也希望有更多的机构,包括大学和职能部门能够负担起更多的责任。中外国际文化交流不是仅仅靠几个机构就能完成的,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尤其是“Z时代”的年轻人。他们具有国际化的视野,思想开放、思维活跃,在文化传播与交流过程的作用不可估量。
当然,除了上述那些千奇百怪的猎奇性问题外,我也经常被问到第二类问题,是关于中国文化的问题。例如,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特性是什么?孔子是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思想?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也总是感到很为难。我们拥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灿烂辉煌,丰富多彩,我们的前辈大师们也试图简要地回答这些问题,对中国文化进行简短地总结,可是我总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层次丰富、思想多元,三言两语是无法准确概括的,甚至也无法描述任何一个历史横断面的文化。我只能另辟蹊径,告诉他们中国文化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它本身就是多元的、多层次的,也是动态的,并不存在一个“客观静止的”中国文化可供描述。中国文化包容世界主要文明所产生的重要成果。举例来说,在汉代,佛教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落地生根,在中国创造出了有中国特色的、辉煌的佛教文化;在隋唐时期,伊斯兰教随着商业活动来到中国,也落地生根,伊斯兰信众为中国的历史进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群星灿烂。同样在隋唐时期,基督教的一个教派“景教”到达中国,受到李唐政权的扶植,可惜后来由于政治运动没有扎下根来。到了明末清初,中外文化交流随着大批传教士来华而掀开了新的篇章,接受基督教的人士既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有贩夫走卒、引车卖浆的普通民众。传教士带来了新的宗教和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开始系统地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西方人通过传教士的著作发现了中国,为中国悠久的文明史和灿烂的文化成果而深感震惊。中国的经典文本也是从明清时期被大规模地翻译到西方去的。所以,我认为,不要片面地看待中国文化,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中国文化是开放的、包容的、多元的,这和我们改革开放所秉承的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没有开放和包容,再灿烂的文化也会在封闭和孤独中逐渐萎缩,直至死亡,这样的案例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并非没有先例。可以说,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也存在着“汉学西传”的路径,不同文明之间的互鉴和交流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也是各文明保持生命力的最主要动力。
第三类问题是具有实用性质的问题,我说的实用是国家和民族层面上的实用。例如,巴基斯坦的朋友经常会问道,中国为什么能够仅用四十年的时间就发展到了现在的地步?他们会把中国描述为超级大国,虽然我们一再解释,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人均GDP距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距离,但他们仍然惊奇于中国如此迅速的发展速度。不光他们惊奇,我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感到惊奇。我出生于河南贫困的农村,对于食物的渴望和贪婪至今还影响着我的生活,直到现在我吃饭仍然很快,还会被噎着,这都是童年生活给我打下的烙印。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多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孩童时期食物匮乏的记忆仿佛已经变得很遥远了。四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算什么呢?只能算是其中一个浪花吧!可是这个浪花如此璀璨辉煌、引人注目,一定会被记录为历史的奇迹。同样地,当外国人问我关于中国快速发展秘密的时候,我也感到很难回答。我可以说是因为中国执行了改革开放政策,这是主要的发展动力。但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的答案,作為一个文化工作者,我也想另辟蹊径,试图从文化层面寻求答案。我认为,中国传统中的“家国情怀”是让中国经济取得如此巨大成功的文化因素之一。中国人向来不把自己视为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注重个人修养,也注重家庭和家族的发展,再往外扩展就是关心国家的发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一种理想追求。而这种理想中的最高层面就是天下,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个道理。有人批判这是湮没了个体的集体主义,我对此持有异议。个体和集体在中国的传统中并不是一对矛盾关系。家国情怀让那些率先获得成功的人“兼济天下”,从而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全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不以发财为根本目的,我们要立德、立言、立功,我们要光宗耀祖,我们要在父老乡亲当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做好表率。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传统中独特的一面、积极的一面,也是改革开放取得如此丰功伟绩的文化因素之一。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没有像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那样经过详细周密地论证,分享出来供大家批评。
三
以上谈到的我作为“外国人”客居异乡经常遇到的三类问题对我而言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些问题促使我反思自身和自己所处的文化语境,让我意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既不可妄自尊大,也不可妄自菲薄。只有把中华文明所创造的灿烂文化成果放到人类文明的坐标体系中,才能对自己产生更加清晰的定位。总之,文化自信来自于正确的自我认知、表现为开放包容的态度,最终有利于我们自身文明的发展,创造出更多更丰富的文化。
最后,我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讨论一下国际文化传播的途径问题。我在一次会议中曾经将目前中国的文化交流分为四种情况。第一是“阵地型”的文化传播与交流机构,如孔子学院和中国文化中心等等。我认为这是保证面对面交流的主要支柱,从目前来看这些实体性机构的作用和功能仍是不可替代的。第二是“遭遇型”的传播形式,例如新闻媒体等机构。它们需要的是对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需要快速挖掘事件的意义阐释以及国际接受渠道和效果等等。这无异于一场“遭遇战”,所谓的遭遇,就是必须针对同一议题进行话语权的较量。第三是“游击型”的文化传播,我使用这个隐喻是要说它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也没有人能够预判到底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在何时何地能取得文化传播的效应。具有代表性的两个案例是李子柒和费玉清。李子柒的视频红遍全球大概是超出所有人预判的,早已退出歌坛的费玉清二十多年前的一首歌《一剪梅》风靡全球自媒体更是让人始料未及。文化产品本身的质量是一方面,无法捉摸的流行风向是另外一方面。我认为,认真做好自己的文化产品能让更多的“意外走红”发生。第四是“密集型”的文化传播方式,我主要指的是中华经典在海外传播。经典传播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我用“密集”一词作为隐喻,是因为经典作为载体信息量大且内容集中。何谓经典?经典就是经过了历史的选择机制而保留下来的那部分精神产品,它们可能存在于文本中,也可能存在于博物馆、存在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它们是关于美和价值的标准,是高度浓缩的集体记忆,是一个文明的文化基因。经典并非固定不变,学习经典、诵读经典更不是故步自封,我们应该看到经典所具有的持久价值和长久生命力,同时也应该看到经典的现代性和创造性,所以,经典既是古老的又是现代的。我们学习来自各大文明的经典,也向其他文明输送我们自己的经典。我相信,经典的多向传播是真正了解世界文化的必经之路,文明互鉴是创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我认为,上述几种国际文化交流的途径我们做得都还不够好。以后两种情况为例,我们的大众文化产品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有待提高,我们的经典译介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大众文化产品包括电子游戏、流行音乐、影视动漫、自媒体创作等等,它们的传播能力在当代社会是无与伦比的。一个李子柒能吸引世界的目光,一首《一剪梅》能把中国的文化意境通过流行歌曲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那如果能生产出成千上万的优秀作品被这样接受呢?那才是真正的文化繁荣。经典译介存在的问题在于没有和流行文化结合起来。中国的年轻人大概也无法在高节奏的生活中能静下心来阅读大量中华典籍,更何况外国人呢?只有通过创造性的工作,以更加生动、活泼的方式把经典译介和其他文化形式结合起来,才能创造更大的传播效应。否则,经典的翻译只能是少数专家学者的案头物品。因此,如何在这个时代将中国文化经典与现代大众传媒技术结合在一起,如何将我们的四书五经,我们的唐诗宋词,我们的传统戏曲小说,我们的现当代文学经典等等,通过交流与合作让其他国家的年轻人所理解,是我们肩上应该担负的重任。
(责任编辑:庞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