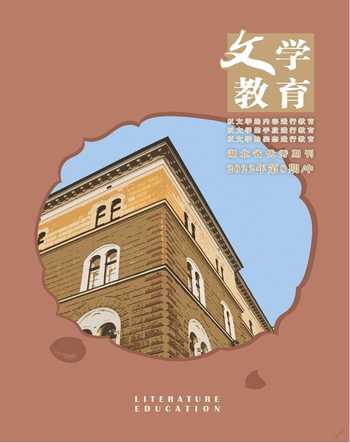论《热带癫狂症患者》中的东方形象
毛伊扬
内容摘要: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因其犹太人身份而遭受迫害,他的作品对20世纪西方社会现实进行深刻分析,宣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但是在他的《热带癫狂症患者》中,描写了一些东方男女,他们大多身份卑贱,愚钝、顺从、落后,与西方男女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类东方形象的塑造既是西方中心主义影响的结果,同时也加深了西方对东方人的刻板印象。这种情况反映出茨威格受到欧洲社会集体想象的制约和霸权主义与二元对立经验模式的影响,凸显了作家内心世界里“欧洲情结”与犹太人身份的尖锐矛盾。
关键词:茨威格 《热带癫狂症患者》 东方形象 社会集体想象
斯蒂芬·茨威格是二十世纪奥地利著名犹太裔作家,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富裕的犹太资产阶级家庭。《热带癫狂症患者》的故事发生在远洋客轮上,白人医生对“我”讲述其在马来西亚殖民地的经历:一位富商妻子与一位年轻军官有染怀孕后求助于自己,而医生与这位太太在交谈中产生矛盾,她选择在华人区进行堕胎手术却不幸死去。最后,医生和她的灵柩一同沉入海底,用自己的生命保守住了这个惊天秘密。
一.东方他者形象
茨威格作品中多次出现了东方他者形象,《热带癫狂症患者》中刻画了中国、印度与马来西亚的他者形象,多被描写成愚昧、落后、卑贱的负面形象。
1.中國地域
历史悠久的天朝上国以其富饶的物质文明与独特的东方魅力吸引着西方,如同一曲西方人魂牵梦绕的遥远歌谣。近代以来,西方资本的肆意扩张使得东方逐渐沦落为殖民地,西方人不再将中国捧于圣坛,而是将其视作低人一等的野蛮国度,茨威格对近代东方形象也充斥着负面评价。
在白人医生眼中,华人的居住地不堪入目:“小车离开了坐落在海滨的欧洲人聚居地区,进入下城,继续向前,一直进入中国人居住区的那些人声嘈杂、弯曲狭窄的街道。”[1]这与坐落于海滨的欧洲人聚居地区截然不同,华人区在医生看来破旧、落后、肮脏,所见之处尽是污秽,仿佛贼窝一般让人唯恐避之不及。
除此之外,作家对中国接生婆和黄种仆人的描写也毫不客气:“那可恶的中国女人两手哆哆嗦嗦地端来一盏直冒黑烟的煤油灯……我得压住满腔怒火,不然我会跳上去卡住那个黄皮肤无赖的脖子……”[2]中国接生婆在医生眼里不是迎接新生命的形象,而是长着獠牙的恶毒巫婆,看似是以手术拯救人的生命,实则在以非人的手段折磨着白人女士。
2.东南亚地域
医生曾于七年前到过印度,热带风景带来的新鲜感很快被消磨殆尽,那里的人们日渐颓废,只好用酒精来消磨望不到尽头的日子。马来西亚使医生的生活也充斥着空虚与寂寞,只能在烟酒慰藉中怀念在欧洲时的舒适生活,并宣称自己染上“热带病”:“不仅是癫狂……这是一种疯病,一种狂犬病……直到人家把他像条疯狗似的一枪打死,或者他自己口吐白沫倒地身亡。”[3]这是对马来西亚的一种鄙夷,将自己生活不适归咎于马来西亚的肮脏与落后,以“热带癫狂症”来命名,宣泄自己的不满情绪。他对马来西亚领地中的黄种人更是鄙夷至极,将黄种男仆拦住自己看作是十分放肆的行为,而自己可以在大庭广众下对他拳打脚踢,并用各种负面词汇:“狗一样的目光”、“迟钝的黄皮肤的动物”、“黄种混蛋”羞辱他。
二.社会集体想象
“异国形象应被作为一个广泛且复杂的总体——想象物的一部分来研究。更确切地说,它是社会集体想象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对他者的描述。”[4]这里的他者不是客观事实的再现,而带有凝视者的主观看法。西方确立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后,牢牢掌握着话语霸权,以排异性目光审视东方。茨威格的欧洲人身份也使他受到社会集体想象制约,对东方同样持有一定的偏见。在茨威格笔下,西方人以文明、高尚、智慧形象出现,东方人则被用野蛮、低贱、麻木等负面词汇描述。
1.霸权主义下的东方奴仆形象
《热带癫狂症患者》中的东方奴仆从未被视作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丧失话语权、被任意差遣与羞辱的沉默者。“欧洲的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这种观念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5]西方对东方的认知中便将这种霸权意识体现得淋漓尽致。
东方奴仆卑躬屈膝、怯懦卑贱,无论是唯唯诺诺的黄种听差,还是胆战心惊来送信的中国小男孩,以及被刻画成巫婆一般的中国接生老太婆,他们都没有为自身言说的机会。在女主人病危之时,听差一直尽心尽力协助白人医生,并且为女主人虔诚祈祷着。即使医生曾经当街羞辱过自己,他依旧对医生充满感激之情。而医生即便被听差的忠诚感动,也不过用些轻蔑的话语来“赞赏”,这实际上是欧洲人对东方殖民地人麻木愚钝的奴性感到不可思议。
小说中的东方是被看的他者,西方作为注视者以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心理审视他者时,“异国现实被视为是落后的”。[6]失去话语权的东方被西方以各种含有贬义性色彩的套话形容,这里的东方是欧洲人在霸权主义下对东方的集体想象物,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对东方的狭隘认知。
2.二元对立观念下的东方女性形象
当欧洲资本主义进行殖民扩张而迈向世界前列,东方逐渐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东西方势力的日渐悬殊使得欧洲文化形成了“东方/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欧洲将东方置于自己的对立面,东方形象也就沦落为异类或他者。
茨威格将英国太太塑造成美丽、高贵的形象,她与医生第一次见面时,医生便为她神魂颠倒。当医生提出以占有她作为条件时,她十分高傲地拒绝了他,而医生仍旧追随她至舞会,所见是“她薄薄的嘴唇四周漾起的讨人喜欢的、彬彬有礼的微笑。这笑靥又重新使我心醉神迷。”[7]此外,作家并没有谴责英国太太的婚外情有违道德标准,反而以丰富的情节将其塑造地合情合理,博得读者的同情。茨威格对“轻佻下作”的东方女人的描写与对“高贵体面”英国太太的刻画形成了讽刺性对比。小说中,医生对东方女人的描述无不渗透着歧视,用“顺从”、“奴性”之类的套话将其丑化,而东方女性的勤劳、温婉、智慧等正面形象却没有在小说中体现。
医生不但震惊于身份如此卑贱的中国接生婆竟然敢触碰贵族太太的身体,并且愤怒于她宁愿让这么一个“魔鬼似的老巫婆”对自己身体任意宰割却不愿意依赖自己。在医疗不发达的年代,中国确实有接生婆代替专业的医疗人员来为孕妇进行手术。茨威格在富裕的欧洲环境中长大,自然无法理解这种行医方式。这同时也是欧洲对注重传统的东方的轻视,欧洲将自己视为“权威”与“科学”,而东方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视作“歪理”与“邪术”。
茨威格在《热带癫狂患者》中对东方他者形象的描述始终离不开欧洲集体想象。他怀揣着身为欧洲人的优越感,以先入之见将东方他者描绘成愚钝、卑微的形象。
三.作家创作动机
茨威格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关于欧洲的情结深深植根于他的内心之中,在东方之旅中以偏概全地认为整个东方都充斥着原始与蒙昧。但是,两次世界大战迫使他流离失所,作家内心理想的欧洲大厦轰然坍塌,昔日美好的欧洲一去不复返,而犹太人的血统让处于身份困境中的作家民族意识觉醒,与犹太人的“流亡”苦难史产生遥远的共鸣,对殖民地人遭受奴役的生活更加感同身受。欧洲理想身份与犹太民族精神在其身上共存,这也使得茨威格创作中的东方形象更加复杂化。
1.幻想破灭的东方之旅
茨威格的创作动机直接体现在他的东方旅程。茨威格在自传里提到,他曾到过印度、美洲和非洲的一部分地区。作为旅行者,当踏上去往印度的游船,他没有被这座古老神秘的东方土地所折服,而是感慨:“印度给我的印象比我想象中的险恶的多。骨瘦如柴的身影,黑眼球流露出的没有丝毫欢愉的目光,及其单调的景色使我感到震惊。更使我吃惊的是其严格的种族和等级制度。”[8]作家在游船上邂逅了两位迷人的欧亚混血姑娘,她们没有被众星捧月般优待,反而被其他人刻意回避。因为这是一艘开往印度的船,种族偏见渗透进船上每一个人的毛孔之中,他甚至将其与可怕的瘟疫相提并论。作家头脑里“涂着一层粉红色彩”的瑰丽土地不见了,取之而代的是一座“充满警戒气味”的冷漠之城。经历这趟东方之旅,茨威格目睹到野蛮、贫困的丛莽之地,便以偏概全地认为整个东方都充斥着原始与蒙昧,断定现代文明从未踏足于这片土地。
小说中医生对东方的看法也就是作家头脑中的映射。初来东方,热带的异域风情深深吸引着他,想要将自己的全部热情挥洒于这片古老的土地。但很快他的热情便被消磨殆尽,逐渐在对欧洲的怀念中空虚度日。同时,医生还将殖民侵略美化成文明的传播。实际上,殖民扩张不可避免地让现代人成为物质的附庸,逐渐被社会边缘化,在精神上沦落为漂泊无依的流浪者。茨威格借医生的情感转变来诉诸自己对东方美好幻想破灭后的失望,以及对欧洲执着于殖民扩张却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痛惜。
西方的二元对立经验模式使西方将自己置于中心,而将东方置于边缘地带。“旅行者带着这种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上路,寻找并发现异域与本土的差异,并将这种差异极端化为对极或对跎想象,世界与他乡呈现在自我面前的样子,正如他虚妄的世界觀念秩序中期望的那样。”[9]作家在旅行中发现了欧洲与东方的差异,茨威格对东方即便有美好的想象,也始终难以挣脱西方二元对立经验模式的藩篱。
2.“欧洲情结”与犹太人身份
茨威格出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这是一座具有两千年悠久历史的艺术名城。在繁荣昌盛的氛围中,维也纳人每日醉心于文化生活的消遣,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和近乎苛刻的标准追寻着艺术,将艺术等同于维也纳的集体荣誉。维也纳璀璨夺目的艺术成就、“兼容并蓄”的艺术精神渗透在社会各阶层观念之中,也哺育了茨威格的童年与青年时光。维也纳既是茨威格的成长摇篮,也是他朝思暮想的精神乐园。
茨威格的自传《昨日的世界》副标题为“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不难看出他想以理想的欧洲人身份去回忆他的一生。维也纳独特的气质也使得欧洲意识很早就烙印在茨威格脑海中,他想从维也纳走向欧洲、迈向世界。文化之间的碰撞不仅坚定了茨威格以文字捍卫自己作家身份的目标,更培养了他作为世界公民的历史责任感,致力于追求全人类的精神自由。“即使欧洲,我心中选择的故乡,在同室操戈的战争中第二次自相残杀地将自己撕成碎片后,也从我心中消失了。”[10]茨威格内心理想的欧洲大厦轰然坍塌,战争使茨威格犹太民族意识觉醒,更加冷静地审视自己的世界主义理想价值。
犹太民族是一个优秀且苦难的民族,犹太人的“流亡”既是地理上的颠沛流离,更是心理上的居无定所。即便犹太教的选民观赋予了他们上帝选民的特殊身份,让流浪的犹太民族获得了一定的精神支柱,但在残酷的现实中,许多犹太人一生都在寻找精神家园却受尽排挤,临死前都无法采摘故土之花告慰自己的灵魂。漂泊使每一位犹太人都怀有忧患意识,并且格外重视自己的身份,犹太人想要通过对文化艺术的追求提升自己的精神层次,他们努力去认同欧洲文化,在与欧洲文化的融合中淡忘自身气质,试图获得欧洲的身份认同。犹太民族的苦难使茨威格对殖民地人怀有恻隐之心,同情他们遭受奴役的悲惨生活。
面对东方殖民地时,茨威格的内心也十分复杂。一方面,欧洲人的理想身份使他认同欧洲的主流文化,对东方投向轻蔑的一瞥。而两次世界大战使他心中理想的欧洲大厦轰然倒塌,身为作家的历史责任感促使他以文字宣泄自己的情感;另一方面,犹太民族颠沛流离的苦难史与无法解决的身份危机使茨威格对自己身份的认识产生了动摇,面对遭受奴役的殖民地人他心生怜悯却无可奈何。即便以最理想的方式追寻精神的慰藉,他仍然会因为找不到两全其美的方式而迷茫。归属感的缺失形成了茨威格矛盾的思维方式,他既存在于自我认定的身份中,又处于始终被抛弃的境遇中。欧洲理想身份与犹太苦难血脉在他体内共生,对欧洲主流文化的认同与对殖民地人的共情在他笔下并存。因此,《热带癫狂症患者》中对东方形象的负面描述也是作家掩饰自己复杂情绪的一种无奈方式。
茨威格在《热带癫狂症患者》中塑造了带有负面性色彩的东方形象,其笔下的中国不再是富饶美丽的天朝上国,而是肮脏蒙昧的国度。位于热带的东南亚也不再披上异域风情的面纱,而是由内而外都渗透着作家对殖民地的鄙夷,这显然离不开欧洲社会集体想象的制约、霸权主义与二元对立经验模式的影响。此外,茨威格对东方形象的偏见也与自身旅行经历、复杂的“欧洲情结”和犹太民族意识有关。茨威格的东方之旅使他想象中的瑰丽土地破灭了,身为维也纳人,茨威格想从维也纳走向欧洲、迈向世界,渴望以世界公民的身份追寻全人类的精神自由。作家痛惜于欧洲财富大肆扩张导致的现代人精神文明的衰落,而犹太民族的苦难历史又使得茨威格在面对东方殖民地时心生怜悯。他渴望获得欧洲身份的认同,在历史厚重的欧洲精神文明中扎根。但是,战争导致的犹太民族意识觉醒促使他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自我认同的怀疑使他的心灵失去庇护。作为知识分子,他笔下的偏见语言既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白描,也是对自己复杂情绪的无奈掩饰。
注 释
[1][2][3][7][奥]斯蒂芬·茨威格.斯·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选[M].张玉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194,195,196, 188.
[4][6]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21,175.
[5][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0.
[8][10][奥]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M].汀兰,译.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179,2.
[9]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07.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