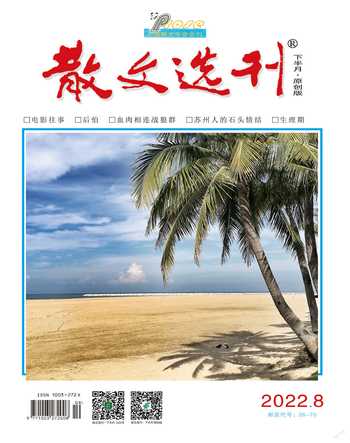钟声悠然
张学华

乡下学校,会规范敲钟的老师不多了。
年前下乡视导,正碰到学校停电。当今时代,停电是小概率事件。除了极端天气和线路检修,一般是不会停电的。电停了,下课上课的广播语音自动停摆。值班老师慌忙找来锤子,在教学楼拐角处挂的一段铁筒上猛敲一阵,学生才接二连三地走出教室。
这个铁筒,就是学校的钟。很多年前,就是这个小小铁筒,指挥着学校师生的一切。上课钟,下课钟,午饭钟,午休钟,晚饭钟,晚自习钟,熄灯钟,整天不时地敲着。有的敲得多,也有敲得少的,只有几响。在那铛铛声敲响的时候,许多老师、同学及工友都随着声响去做各自的事情。当然,有的学校是挂一段铁轨,两尺来长,锤子敲起来,铁轨的声音清亮,要好听些。条件更好的,是装有钟绳的挂钟。左右拉动钟绳,挂钟便会响起来。这种挂钟,只在电视剧里见过。
乡下学校的钟,一般挂的都是铁筒或铁轨,条件更差的,是在树下挂一铁片。当然,挂铁片的学校一般是村小。这些形式各异的钟,伴着一声声荡鸣,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记忆。
自己读小学和初中时,每天从朝霞到日暮,挂在树下的铁轨会按时被敲响。周末时,一些调皮的孩子也会偷偷地把钟敲响,引来老师的阵阵呵斥。随即,这些孩子会一溜烟地逃得无影无踪。
近些年,会敲钟的老师逐渐退休,新来的年轻老师对这些老物件有些不屑,甚至忽略了它们的存在。规模较大的初中和高中,这种老物件是必须存在的。毕竟每年中考、高考,实施的还是人工敲钟。
三十年前,自己刚入职时,学会的第一件事便是敲钟。那时候,學校基本不存在学生安全问题,老师值日的主要职责便是敲钟。开学刚几天,教务处殷主任找到我,“小张老师,明天是你值日,你会敲钟吗?”
“敲钟有什么不会的,不就是拿着锤子敲几下吗?”
“马上下课了,你敲几下试试。”
我拿起锤子,随意敲了几下。几分钟过去了,没有一个学生走出教室。
我正诧异,殷主任笑了,“你敲的是上课钟,谁敢出来?”
简单的敲钟也有技巧,原以为,只要敲几下,学生就会出来呢。
“预备钟:铛——铛——铛——一下一下敲,稳稳当当,提醒学生进教室,做好上课准备。上课钟:铛——铛铛——铛——铛铛——一短两长,提醒师生开始上课。下课钟声:铛铛——铛铛——两下并敲,提醒老师下课时间到了。集合钟声:铛铛铛——铛铛铛——三声连响,短促激越,提醒学生快速集合……”殷主任一边讲解,一边拿着锤子在菜刀上示范。
第二天,学校操场旁边那棵老槐树下,一个矮矮瘦瘦的年轻人拿着锤子敲响了上面吊着的那块铁片,据说是抗战时期日军丢下的炸弹皮。看着老师们拿着教学用具微笑着从我旁边走过,看到孩子们笑闹着跑进教室,第一次有了当老师的成就感。
值日的那一天,哪里都不能去,除了上课,就是敲钟。即便上课,也要时刻关注时间。钟声就是命令,不能提前敲响,也不能推迟敲响。那时候,自己没有手表,借来殷主任的手表,放在讲台上。看到下课时间快到了,就对下面的学生说:“马上要下课了,我去敲钟,钟声没响,任何人不得走出教室。”以后的日子,学生只要看到讲台上放着手表,便知道这天是我值日,没有一个学生调皮捣蛋。
这,也许便是钟声的魅力。
儿子开始上学的时候,学校的钟声变成了电铃。时间一到,一按电钮,室内外的电铃就会发出“丁零零——丁零零——”的响声,声音清脆悦耳,如同自行车的铃声,只是音量要大得多。值日老师不用再像过去那样,冬天戴着手套,拿着冰凉的锤子去室外敲钟了。
再后来,柔和的语音提示和美妙的音乐取代了电铃。电脑一次性设置好,再也不用担心钟声提前或推迟敲响了。
一天晚上,全家人一起在电视机前欣赏老电影《凤凰琴》,看到老师敲响树下的钟声,孩子们欢快地离开校园。儿子问我,“老爸,你工作时敲过这样的钟吗?”
“当然敲过。”
儿子沉默半天。我知道,他被故事情节感染了。
正月初四,一个人去了曾经工作过的故乡学校。校门口的保安师傅盘问了好一阵,又是扫码,又是测温,好不容易才让我进去。在这所学校工作多年,保安换了一茬又一茬,突然有了“儿童散学归来早,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感慨。除了校门没有改变,校内几乎彻底变样。校门左侧的鱼塘和花圃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幢现代化的四层教学楼。校门右侧建起了崭新的学生食堂,原来食堂处,建起了漂亮的学生公寓和教师周转房。校园大道已经刷黑,以往秋季开学半人高荒草的运动场,现在铺上了塑胶。
我亲手栽的竹子不见了,亲手栽的芭蕉不见了,亲手挖的鱼塘不见了……
校园里静悄悄的,外面一个人也没有。沿着刷黑的校园大道往前走,最前面那栋红色的综合楼还在。抬头望去,二楼拐角处,赫赫然挂着一段两尺来长的铁轨,那是自己曾经无数次敲过的钟啊!
门口保安师傅说,学校越建越漂亮了,老师和学生却越来越少了,语气中带着一丝惋惜。
我不知道怎么宽慰保安师傅。只知道,昔日雪天下鱼塘捉鱼已成为记忆;开学前,组织师生在运动场割草已成为记忆;课堂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已成为记忆。唯独那口老钟,那口锈迹斑斑的老钟,依然坚守原地,数十年如一日,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使命。斑斑锈迹中,似乎还在倾诉曾经的辉煌。
即便一年只敲几天,抑或数年只用一次,就这一次,它也做到了不可或缺。
“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白居易一首《长恨歌》,勾起了多少离人的苦痛和思念。我不会写诗,不会去歌颂已经没落甚至遗忘的校园钟声。只是,昔日敲钟的动作和记忆依在,心中的牵挂依在。
在保安的注视下,我握紧钟锤,稳稳地敲了几下。钟声依然那么清澈、那么悠扬,还是旧日模样。教师周转房里几个人探出头来,略显诧异。我笑了笑,轻步走出了校园。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