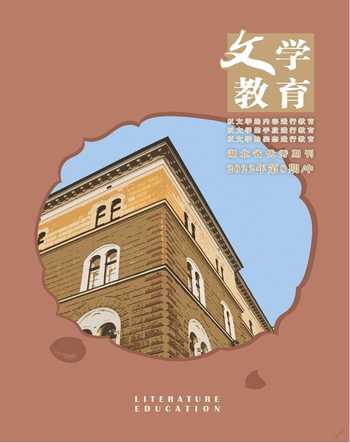葛亮《北鸢》中的民国书写
张雨纯
内容摘要:《北鸢》是葛亮历时七年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南北书”之“北”书。作品以作家的家族史为依托,展现了时代洪流下的人事浮沉,民国风云变化尽显其中。本文拟从政治、社会、文化三个方面直击《北鸢》民国现场,把握葛亮《北鸢》中民国书写的个人特色。
关键词:葛亮 《北鸢》 民国 写作特色
《中华民国史》中写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①关于民国,官方史书一般认为是1911年至1949年。自1949年以来,中国文坛上对民国题材的书写,出现过二三十年的空白,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历史小说的出现,作家们又重新将目光投向民国乃至更久远的历史空间。作为70后作家的葛亮,在长篇小说《北鸢》中,对民国发起挑战,这部小说将时间轴设为1926至1947年,横跨了大半个民国,这一次对民国的大胆想象与尝试,呈现着葛亮明晰的个人特色。
一.被淡化的政治色彩
动荡不安是民国的一层时代底色,政治是这一时期无法回避的关键话题,所以作家们在创作时往往不约而同地选择淡化作品中的政治色彩与政治事件,并且这种选择与作家本人处于什么时代无关。
叶兆言——与葛亮共同点颇多的一位文艺界前辈,同样拥有南京的成长背景,同样衷情于民国书写。在淡化作品中的政治色彩与政治事件这一问题上,叶兆言倾向于将重大政治事件背景板化,真实历史人物与政治事件更多的是为虚构人物的真实性而服务。如《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中,身处1937年的南京,新生活运动、禁娼运动、庐山谈话会、第一夫人主持追悼会等等政治活动丁问渔作为大学教授当然不会缺席。但是这些政治事件要么是被一笔带过,要么是成为人物行动的背景空间,总之绝不会成为小说描写的主角。角色身份设置上也是如此,丁问渔曾是法国留学生,自然而然地就会与同在法国的陈毅、邓小平等人产生交集,但这些交集对政治历史来说无关痛痒,虚构的人物与真实历史线上的知名人物相连的同时又尽可能的避免政治色彩,这些真实的名人只会提醒读者虚构人物的真实性,而不会想到政治。
葛亮也对《北鸢》中的政治色彩与政治事件进行淡化,但与前辈不同,葛亮不那么寻常的家族给他提供了便利,赋予了他独特的民国切入角度。历史上有名有姓的人物对他来说还有着家族长辈这一特殊身份,他在作品中也切实抓住了这得天独厚的切入点,将真实沉重的政治事件化入世俗、家常的家族故事中去,将政治人物放到了私人化的家庭生活中进行刻画,血缘亲情、伦理道德这些家族内部纲常冲淡了人与事的政治色彩。
以《北鸢》中的石玉璞为例,其原型为历史上直鲁联军统领之一的褚玉璞,是葛亮外公的姨夫。石玉璞在历史上是颇有争议的军阀将领,但在小说的主人公文笙这,就只是姨夫,尤其是孩提时代的文笙。孩童的视角更是给这位历史上的政治人物蒙上了一层家庭的柔和滤镜。文笙所见所闻的是姨夫和家中女人的复杂纠葛——和太太昭德、五姨太太小湘琴。石玉璞所面对的政治危机隐现于与太太的家常对话中,他和其他政治势力的纠纷对弈也是在五十岁寿辰上这种家常庆祝的场合显露峥嵘。文本并没有细致描摹石玉璞如何同柳珍年博弈,而是将他的颓势在家庭生活中展现,大势已去之时,连对家庭的掌控力都已不再,更何况政治话语权?五姨太太小湘琴对名伶徐汉臣的别样情愫触怒了石玉璞,一顶可有可无的绿帽子,了结了两条鲜活的生命和石玉璞的倥偬生涯。关于石玉璞的死亡,文本中写到,那只是一个很平常的早晨,他與家人闲话家常,还抱怨着早餐的不合胃口,谁都没能想到,这是见他的最后一面。民国时期一位军阀将领的死亡,其背后必定蕴藏着浓厚的政治色彩,而葛亮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举重若轻,政治斗争失败的一方身死后,家人甚至连尸身也无法为他收殓,只有一身喻示死亡的染血军装被送回。这一身军服是家庭生活的象征,石玉璞与昭德的最后一次互动就是昭德为丈夫捋平军装的领子,真实沉重的政治色彩被染血的军装展现,却又为军装所象征的家庭亲情消解。
写陈独秀也是,身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的政治色彩毋庸置疑,但他在《北鸢》中甚至未曾拥有名字,只是以毛克俞的叔叔——一个家庭叛道者的身份出现。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却也是葛亮祖父葛康俞的舅父,无论是现实中还是文本里,无论是陈独秀之于葛康俞,还是叔叔之于毛克俞,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本中陈独秀出场极少,几乎都是以毛克俞的回忆来进行描写,且最后一次出现时已时日无多,是毛克俞情伤出走之后偶遇。对于毛克俞来说,他得到的从来不是思想领袖陈独秀的政治思想引导,而是来自一个长辈言传身教的熏陶。陈独秀的政治影响主要是在1927年之前,文本中他出现已经是1942年,无情时光的流逝,家庭亲人的视角,使得文本里的陈独秀,政治色彩淡得几近于无。
民国局势变化莫测,文本中石家的败落背后是军阀混战,卢家的流离迁徙是日军的侵略所迫,冯家则在被日军掌控的襄城里艰难挣扎……石家、卢家、冯家等家族的沉浮转折都离不开政治,但葛亮将政治事件与世俗、家常的家族故事交织,把政治人物放入家庭环境,用家族纲常淡化了政治色彩。
二.“格物”的社会生活
“70后”作家对于历史书写,一直都处于“在路上”的状态。他们没有集体记忆,也谈不上什么想像共同体,对历史的再现都是“一种间接经验的移植和想像性再造”。②尤其《北鸢》还是搭建在虚构的城市舞台——襄城之上,这就使得写作难度再度升级,但葛亮显然成功把握住了诀窍,实现了对民国社会的精彩呈现。陈思和评价葛亮的《北鸢》以工笔穷形尽相地描绘了民国时期社会生活场景,而“格物”就是葛亮的成功秘诀。
“格物”本是宋明理学的概念。朱熹解释:“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③葛亮作品里的“格物”,其实是指深入细致地观察和研究社会生活,将对社会生活的呈现落实在具体事物及细节之处,使一时一事皆具精神。“格物”是葛亮的创作的必须。作为70后,葛亮缺乏对历史与时代的直接感知,与祖辈亲友的交流、访谈,是他进行感知的重要途径。他自陈写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祖辈亲友的陆续辞世,一手资料难以寻得。《北鸢》中的北方城市“襄城”同葛亮的故乡南京,南北之差,大相径庭,作者想要回到历史现场,实现对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工笔细描,就必须“格物”,从细节处落实、构造民国现场。
葛亮曾在外公家见到一张面目陈旧的纸币,他轻轻摩挲着这一坚硬厚实的旧币,通过“格物”打捞史实散落的碎片,丰富、延展,构成了一段由此而来的民国社会生活图景。当年的“羌帖”是沙皇发行,专门“祸害”中国人的钱,而持有这钱的是曾经的俄国公使库达谢夫子爵,而现在的“羌帖”是被子爵的儿子拉盖随意地放在口袋里,用来叠角子的玩具,现在的子爵也早已下野,被取消了公使待遇。沙皇倒台,“100”元面值的羌帖已经只剩下作为孩子玩具的价值,或者更糟一点,被用来糊墙,被昭德成为“沙俄的遗老遗少”的这两父子的生活境遇,借“羌帖”这小小的纸币展现得淋漓尽致。拉盖掏纸币时的漫不经心、叠羌帖角子时动作的娴熟,正隐含了别人对这对“遗老遗少”习以为常的不在意。
《北鸢》里,“格物”使得民国社会生活的趣味尽显。“汉升”戏院里,熟客一伸手,“便有一个热毛巾把旋转着飞过来”,堂倌抛得利落,客人接得也漂亮。这一处细节地处理,正是“格物”所致。民国的戏院里,堂倌招呼客人、客人唤堂倌,不需要开口,只是一个伸手的动作,各自便心领神会。毛巾这默契地一抛一接,腾腾热气中我们一下就进入了戏院,民国戏院里客人的那份怡然自得,乱世中藏着的那份气定神闲,就藏在了小小一方热毛巾里。
民国民间习俗也是葛亮细致刻画的重点。文本中昭如为继女秀娥操办的冥婚,一丝不苟、毫不含糊。男方送来的“鹅笼、酒海”龙凤喜饼、肘子喜果一件不落;女方陪嫁的金丝龙凤被、绸缎尺头、梳妆台一应俱全;迎亲、起灵、并骨等环节完整有序……这些细节使人物的塑造更加丰满深刻。昭如本身就是孔孟后人,虽是继母但她和善的天性使她怀抱着生母的心,秀娥的婚事更是家睦生前的一桩心事,对丈夫的忠贞、感激也推动着她,老夫少妻、丈夫逝世、继母的身份,这桩冥婚的大办对昭如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是她对他人、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交代,这种对人物塑造及其重要的事件,对作者的案头功夫提出了高要求,非得“格物”不可。作者将这民间习俗一件件、一桩桩、每处细节、每个流程仔仔细细、清清楚楚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办完这桩婚事后的昭如直接睡在了坟地,若是前面冥婚的细节含混了之,读者只会不明所以,怎么就忽然睡在了坟地,但通过作者的细致“格物”,读者可以清晰地感知到昭如的情感在这仪式的过程中的紧绷,这是最后骤然放松以至于睡在坟地就自然而然了。
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无不需要细节处的把握。回家省亲的仁涓,穿着“织锦缎的短袄,镶了紫貂的滚边,上面是金丝的游龙戏凤,下身着一条凡立丁的长裙”。④(p93)她是嫁给了旧式家庭的女子,又是与自己的妹妹有百般牵连的婚姻,回家省亲时自然会在衣着上多下功夫,这铺面的富贵之气就有了由头。圣保罗医院里,叶师娘与文笙母子围着炉火烤栗子闲谈,聊到了中国吃食,烤出来,瓤能如蜜汁般流出来的稀甜的红薯,外面烤到焦黑,里面是雪白糯香的老菱角。避难之时,寒冬围炉烤栗子的片刻闲暇,聊些吃食的闲话,是动荡民国一处温暖的角落。
在社会生活的呈现上,通过对具体细节的描摹刻画,铺陈开对社会生活的想象,一时一事皆具精神,是葛亮非常大的优点。《北鸢》里的风筝作为小说的主要线索,其制作流程自然是要仔细说明的。家睦与龙师傅皆是读书人出身,半路出家,一个投身陶朱,一个成了手艺人,家睦对龙师傅有“鱼渔俱授”之恩,赠铺、赠书册,两人之间的情谊,其中浓烈的东西,都在这一岁一只的风筝里了。所以这虎头风筝才会大毛竹做骨,劈出篾子,放到炉火上烤,边烤边用手指弯出形状,哪里都马虎不得。
三.坚守的文化传统
葛亮通过作品中人物的言行举止,向我们展现他向往的民国文化传统:坚守、诚信、执着、仁义……
《北鸢》中的女性身上,有一些隐而不发的精神。昭德、昭如两姐妹从身份的设置上,就有傳统的因素。“我们孟家人,可嫁作商人妇,自个儿却得有个诗礼的主心骨。”④(p54)亚圣的后代,可以说是女子忠贞的典范,一开始,昭如几乎是毫无犹豫地接下被卖的孩子,丈夫逝世后,照顾幼子,安排继女、丈夫后事,姐姐遭遇家变,接来家中细心照顾,即使是逃难路上,也要等一等落队的小蝶母女……昭如的淳厚善良、重情重义贯穿了她的一生。
作为姐姐的昭德,一开始就是强硬、坚韧的。她的疯癫与最后回光返照般的突然清醒,为很多人诟病,认为是葛亮作品中的一个缺陷。但这也是葛亮的一种坚持,昭德的坚韧,那是人的一种美德,疯癫绝不该是这样一个坚韧女子的最终结局,所以葛亮在一个破庙里使她清醒,她是需要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结局来收尾的。同样的还有名伶言秋凰,“望鹃啼血花落去,新凰清音换新天。”从一开始言秋凰的气节就有所展现,被迫与师父打擂台后半年不再登台,在师父死后守丧半年,从此离开京津伶界,这是尊师重师,为圆师徒情分。来到襄城,风闻日本人到场的前一天晚上,喝下了泡有雪茄碎末的茶水,不为敌人开唱。最后在她拜师三十周年的日子里,唱了最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戏。她销毁了关键名单,算是位抗日英雄,但她更多的是一位为女儿报仇的母亲。葛亮赋予这两位女性的一些超人的神力,不得不说,是他对她们身上精神的赞扬。
比较特殊的是民国时期的外国人。葛亮双城写作的经验,使得他的作品中一直都有他国者存在,《北鸢》中也塑造了一批生活在民国社会的外国人。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颇为青睐,言谈间也多有引经据典,雅各的姐姐叶小姐说:“我倒觉得,如今的中国人缺的不是雅量,却是任诞”④(p191)不止雅文化,说着蹩脚中文的罗宾逊医生还懂得中国人“吃辣萝卜喝热茶,气得大夫满街爬”的民间俗语。④(p39)这些生活在民国的外国人,言行举止上都受到了民国时期文化的影响,较为有特色。《北鸢》中的雅各可以说是接受中国文化最彻底的一个,甚至说过:“我不会离开中国,离开了,我就什么都不是了。”④(p432)中西碰撞下传统文化仍葆有活力,现代社会,我们又怎能让它们蒙上灰尘、不见天日呢?正如张莉评价《北鸢》“它提供了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进而引领读者一起,重新打量那些生长在传统内部的、被我们慢慢遗忘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能量。”⑤这些精神、文化传统被观置于整部作品之中,在时光更迭中代际相传。
注 释
①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第一卷[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
②张艳梅.“70后”作家的历史意识[J].上海文学,2017(05):106-112.
③朱熹.大学章句.经一张[M].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④葛亮.北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1.
⑤张莉.《北鸢》与想象文化中国的方法[J].文艺争鸣,2017(03):163-166.
项目:江苏师范大学2020校级创新项目课题2020XKT763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
——关于葛亮研究的总结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