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滨孙的精神史
康子兴

一
如果要评选世界文学史上最具生命力的小说人物,鲁滨孙·克鲁索(又译鲁滨逊)必定是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之一。直至今天,我们仍然乐此不疲地谈论他,思考这个形象的意义。许多人把《鲁滨孙漂流记》视为“现代性的寓言”,把鲁滨孙当成现代人的原型,致力于透过鲁滨孙洞悉现代社会、文化与道德的基本原则。也有許多人把鲁滨孙当成“我们”的一员,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身影,体会到强烈的现实感。在他们眼里,鲁滨孙是一位市井英雄。与我们一样,鲁滨孙拥有普通人的欲望、恐惧,乃至希望;他也有着普通人的弱点、才智与德性;他既如普通人一样脆弱,也如普通人一样坚韧。他的邪恶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堕入的罪恶处境,他的荣耀也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实现的成就。他只是社会中寻常的一员,他像一面镜子,既反射出人性的恶与善,也映照出社会的结构与根基。鲁滨孙不是超人,他无法超越历史,他生活在具体时空中,展现出时代的精神、危机与命运。
当然,还有人关注鲁滨孙代表的殖民史内涵。一九八六年,J. M.库切出版了《福》(Foe)。在这部小说里,他解构并改写了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他把场景设定为丹尼尔·笛福创作《鲁滨孙漂流记》的经过,借苏珊·巴顿之口重新讲述了“荒岛余生”的故事。苏珊的讲述显得笨拙而质朴,意在本真地刻画她与鲁滨孙、星期五在荒岛上的生活。然而,身处帝国中心的笛福先生却有更多考虑。他的读者是英国人,他必须让故事生动有趣,适合英国人的品位。笛福所处的时代无疑是西方的辉煌时刻:殖民势力向“新世界”大举扩张,大西洋上商船络绎于途,频繁往来。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苏珊·巴顿的女儿被人拐卖。为了寻找女儿,她前往巴伊亚,因此历经磨难,流落荒岛,遇到鲁滨孙和星期五。鲁滨孙在荒岛上的生活贫苦而乏味,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劳动却没有收获。星期五的命运最为悲惨,他是一个奴隶,还被人割去了舌头,丧失了诉说自身际遇乃至痛苦的能力。最终,在笛福笔下,这些小人物的悲惨人生像星期五的舌头一样遭到了切除。他们也都成了“没有历史的人”。
在写作《福》的时候,这位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预设,这本书的读者也一定是笛福的读者。倘若离开了妇孺皆知的《鲁滨孙漂流记》,他新写的故事就没了根系与土壤,变得不知所云。在《福》与笛福的互文对比中,他对写作与事实的追问就得以浮现。他希望读者走出笛福刻画的鲁滨孙形象,去思索真实的历史,并理解小说如何“以文学形式实现了对海外领土的美学控制”(王敬慧《〈福〉译后记》)。
二
库切将笛福的写作视为帝国权力的延伸。其批评固然重要,但谁又能否认,库切的写作不是另一种虚构?所以,在接受其解构与批判前,若不对笛福的作品与意图做一番分析,我们恐会误解笛福,也可能错失他想传递给读者的历史信息。
据说,库切在小时候十分迷恋笛福,深信鲁滨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也都是真实的历史。由于他在南非这一英国前殖民地的生活经验,随着年岁渐长,库切越发关注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联,开始反思文学在精神上具有的殖民力量。毫无疑问,在《福》这部小说中,库切想要表达这一洞见:欧洲的文学经典篡改、抹除了殖民地的本土文化与历史,使之在精神上沦落为西方文明的附庸,在现实生活形态上则沦落为一个低劣的西方版本。“真实的历史”构成了库切思索《鲁滨孙漂流记》的一个枢轴,他在年少时的阅读体验,以及成名之后的反思都围绕着这一枢轴旋转。

丹尼尔·笛福(1660-1731)
实际上,对于笛福的写作来说,“真实的历史”也是一大枢轴,是笛福意图借助小说来刻画、呈现的对象。为了让他的故事显得真实可信,笛福强调自己只是故事的记录者,他记录下来的事件正是“由事实构成的历史”(a just history of fact)。在笛福笔下,鲁滨孙是一个殖民者,他通过鲁滨孙的航海来呈现殖民帝国的结构、实质和危机,并指出帝国的可能未来。库切批判小说的真实性,剑指欧洲在精神上的殖民。笛福自陈,他在刻画历史,并剑指欧洲在政治经济中的殖民。就其对欧洲殖民的批判而言,两者实有共通之处,或者,笛福与库切实在一个统一阵营当中。“历史”将笛福与库切勾连起来。正是因为对真实历史的追问,库切才要重新写作鲁滨孙的故事。库切强调并批判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张力。然而,他的强调与批判也可以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也应该正视笛福对“历史”的强调。
在《福》中,星期五的舌头是一个重要隐喻,它象征着殖民地的本土文化,及其自我表达的能力。就此而论,星期五的沉默自然也是一种无声的控诉。库切笔下的星期五与笛福笔下的星期五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库切想要借此表明:笛福篡改并美化了西方殖民的历史,非但没有正视殖民地土著民族(及其文化)所受的摧残、奴役与伤害,反而将他们抹除了。星期五是一个奴隶,他虽然被奴隶贩子割掉了舌头,但他却成了库切的批判之舌。库切把他所遭受的无法言说的苦难从历史中打捞起来,用以展示西方扩张背后的野蛮与残忍。在《福》中,星期五虽然无法自我表达,只能在苏珊·巴顿的讲述中现身,但他是无可置疑的主角。他是库切用笔墨刻画的焦点,也是库切用心打造的一个窗口。借助这一形象,库切可以展现“身体本身就是符号”(J. C.坎尼米耶《J. M.库切传》,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土著文化的某种神圣性,以及殖民造成的压迫与罪恶。所以,星期五是他的堡垒,从这里,他可以向笛福喷射批判的烈焰。在某种意义上,星期五也是一个战场,围绕着殖民帝国中的主奴关系,他和笛福在此交战。然而,他对笛福的解构与批判是否公正呢?或者说,他的批判之火是否射向了正确的靶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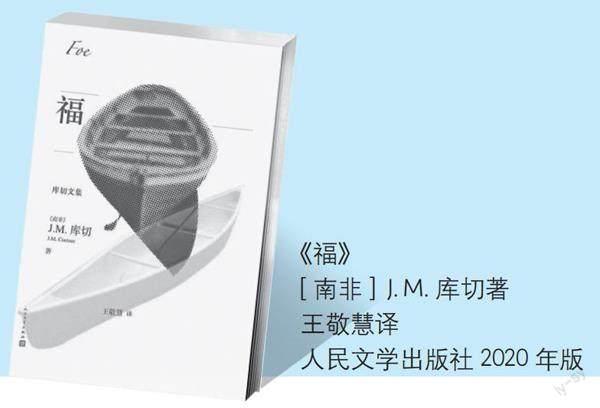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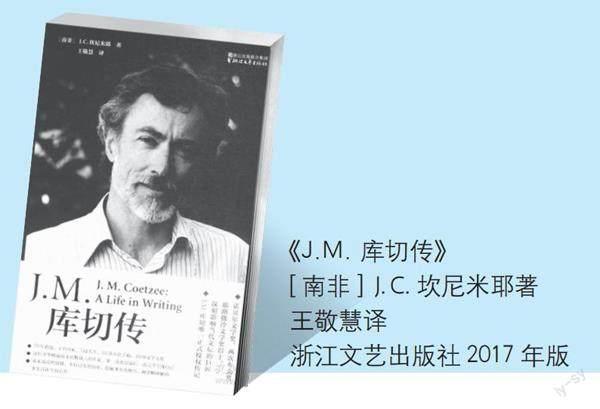
在《鲁滨孙漂流记》的序言中,笛福煞费苦心,试图告诉读者:他的小说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写作。笛福不会承认他有意忽视或篡改历史,不会接受库切的批判。他必然要否认他美化了殖民,或刻意切除了殖民带来的压迫与苦难。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笛福笔下鲁滨孙与星期五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星期五对鲁滨孙的感恩与自愿服从呢?如果我们把故事比作乐曲,那么,在《鲁滨孙漂流记》中,围绕主奴关系,笛福谱写了一首由多个乐章构成的变奏曲。鲁滨孙与星期五之间的交往只是这首变奏曲的一个片段罢了。鲁滨孙的精神史也在主奴关系的变奏中展开。在这部小说中,鲁滨孙经历了不同的生命阶段,他一直在成长、改变,甚至一度经历精神上的自我否定与“重生”。所以,我们切不可断章取义,认为星期五代表了笛福对奴隶的历史认知。相反,只有理解了整首乐曲以及每个乐章想要表达的主题,理解了鲁滨孙的完整的精神史,我们才能正确理解笛福对殖民帝国的态度。

J. M. 库切
对于笛福而言,奴隶问题至关重要。鲁滨孙是为了走私贩卖奴隶才遭遇海难、流落荒岛的。这次不成功的奴隶贩卖行动使之由一个殖民者沦落为荒岛的囚徒,成为其人生的转折点,也为他带来重生的契机。在此之前,他也曾遭遇海盗,被捕为奴。死里逃生,重获自由后,他又将给予他帮助、与他合力出逃的另一个奴隶苏里卖给拯救他的恩人。不仅如此,在成为种植园主之后,他也购买了黑奴,役使奴隶为其劳作。正是因为种植园规模扩大,劳动力不足,他和其他奴隶主才滋生了走私奴隶的念头。所以,怒海沉船,孤岛余生是鲁滨孙前半段人生的归宿,而其前半生的核心主题则是主奴间的战争。拯救和教化星期五已经是他后半生的际遇了,此时的鲁滨孙已因信仰而获得了新生。我们只有以前半生的经历为背景,在比较之中才能窥见笛福赋予星期五的意义。
三
在《鲁滨孙漂流记》的序言中,笛福不仅提醒读者留意他的历史笔法,还特意强调这部作品的道德和宗教意味。“故事的讲述谦逊而肃穆,且像智者诲人那般,常常以身说法,揭示遭遇之中的宗教寓意,在我们一切多变的境遇中斗争并荣耀上天的智慧,而不管事情的发生是顺心还是逆意。”笛福的意思很清楚。他要写作的历史是时代的精神史。他要通过鲁滨孙的出海游历来呈现时代精神,展示主宰政治经济秩序的基本原则,进而对之做出道德判断。
笛福为鲁滨孙设定了具体的时代背景。他于一六三二年出生,一六五一年第一次登船出海,一六五九年开启在海岛上的孤独生活,一六八六年离开海岛,次年乘船返回英国。鲁滨孙的一生都在与海洋和贸易打交道。在他所生活的这段历史时期,英国颁布《航海条例》,开始大举扩张海权。在这段时期,欧洲国家越发意识到海洋贸易的重要性,纷纷加入海外殖民的洪流。它们彼此竞胜,争相打造海洋与商业帝国。这是一个怒海争锋的时代,也是新旧海洋帝国更迭的时代—西班牙、葡萄牙帝国开始下行,荷兰与英国正在崛起。时代的喧嚣、欲念与冲突都融入民情,进而熏染并塑造个人的心灵。所以,在笛福笔下,个人心灵与时代精神高度同构,鲁滨孙的出海历程也与海洋帝国高度同构。
鲁滨孙是一个海洋人,打小开始,他就渴望出海远行。尽管老父苦心规劝,但他仍在十八岁那年离家出海,一脚踏入帝国旋涡。鲁滨孙在航海中获得成长,修习并锻炼了技艺,因此具有不同的身份。鲁滨孙几经历练,先后成长为水手、商人、种植园主和贩奴者。他的每项“技艺”都对应着帝国经济的一个环节。欧洲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美洲种植园生产、非洲的奴隶构成了帝国的基本框架。这是一个层级式的帝国架构。殖民地贸易是海洋帝国最外在的表象。实际上,输往欧洲的商品由种植园生产。种植园的土地是欧洲殖民者武力征服的结果,种植园的劳动力则主要由奴隶贸易提供。如果社会中的一切财富都由劳动创造,那么,奴隶贸易与种植园的奴隶劳动就构成了这两大海洋帝国的根基。亦即,一种彻底的压迫关系支撑起了帝国与贸易。
鲁滨孙的航行结构折射出帝国的结构。在被命运无情地抛上荒岛之前,鲁滨孙的出海经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每个阶段,他都会遇到灾难。第一阶段,他离开家乡,从赫尔乘船前往伦敦,途中遇到风暴和沉船。第二阶段,他离开英国,两次前往几内亚,历尽坎坷,最终来到巴西,成为一名种植园主。对鲁滨孙而言,这个阶段最为重要,他成长为一个水手、商人和种植园主,成为一个殖民者。正是在这一阶段,他遭遇海盗,变成一個“可悲的奴隶”。第三个阶段,他离开巴西,前往几内亚贩卖黑奴,却中途遇险。他的同伴全部葬身海底,他虽然活了下来,却不得不栖身在荒无人烟的海岛,开启长达二十八年的孤独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几次航行中,鲁滨孙逐渐深入地走进海洋帝国的腹心。与此同时,他遭遇的灾难也一次比一次严重。按照鲁滨孙在岛上的反思,这些灾难是上帝对其罪行的惩罚。借此,我们不难领会到笛福的言外之意:鲁滨孙一步步走进帝国深处时,他也一步步走进了罪恶的深渊,而这帝国就是由罪恶驱动并搭建起来的。究其实质,鲁滨孙对自身罪恶的反思乃是对帝国罪恶的批判。
笛福对奴隶与奴隶贸易的讲述扯掉了贸易帝国的伪装,揭示了海洋帝国奴役、不义,乃至荒谬的实质。奴隶是对人性的彻底否定,因为它只是一件工具、一件商品,是奴隶主所能拥有的物与财产。奴隶意味着最悲惨的非人生活。按照十八世纪的道德观念,对人身与道德自由的尊重是自然正义的基本前提。所以,奴隶与奴隶贸易也是彻头彻尾的不义。然而,令人讽刺的是,笛福告诉我们,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打造的海洋帝国中,奴隶贸易不仅是堂而皇之的合法贸易,甚至是需要国王特许令的垄断贸易。“那时买卖黑奴刚开始成为一门生意,还没怎么展开。贩卖黑奴需要定约,并有西班牙或葡萄牙国王的准许证的,在公共市场上市的一门垄断的生意,因此巴西买进的黑奴极少,而且价格奇高。”(《鲁滨逊漂流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虽然只是穿插在故事中间的一段评述,但这已经足够说明帝国的实质了。西班牙与葡萄牙王室不仅承认贩卖黑奴合法,还试图借此追求垄断利润,为垄断商人牺牲其他国民的利益。所以,就其意图而言,这一帝国既将另一个民族置于奴役地位,也极为粗暴地剥夺国民的利益,从而具有双重不义。
鲁滨孙只是帝国投下的黑影,他的罪恶反映、发源于帝国的不义。你看他,因为不愿意在巴西支付高价购买奴隶,就伙同其他种植园主一起,整饬装备,缔结契约,前往几内亚走私黑奴。这是何等贪婪、违背人道的行为!殊不知,在他逃难的旅程中,几内亚海岸的黑人一度向他伸出援手,为之提供食物和淡水。在一颗邪恶的心中,黑人的淳朴反倒成了遭受奴役的原因。我相信,在刻画鲁滨孙的心思时,笛福的笔一定吸饱了讥讽的墨水。
我们也不免惊讶,在筹划走私黑奴的时候,鲁滨孙难道已经忘记,当他被摩尔人俘虏,沦落为奴时,自己多么向往自由?他当然不会忘记,但那只是他自己的自由。对他而言,其他人都只具有工具性的意义;正如对摩尔人而言,他只具有工具性的意义。此时的鲁滨孙只受贪念主宰,并无推己及人的“同情心”与道德感。笛福想要告诉我们,奴隶鲁滨孙和奴隶主鲁滨孙是同一个人,他们信奉着相同的原则:正义只是“强者的利益”,他人只是牟利的工具,在这个世界人待人如豺狼。
所以,当他逃脱摩尔人的奴役,在海上获救后,他毫不感念小奴苏里与他共同经历的患难,转手就把他卖给了葡萄牙船长。对于鲁滨孙的无情之举,不少读者大感震惊,却认为笛福在此阐释了冰冷的“经济人”原则。如果我们注意到他在荒岛上的改变,再对比他与星期五之间的情谊,我们就会明白:此时此刻,这个无情无义的鲁滨孙是笛福的批判对象。我们切不可忘记笛福在序言中的提醒:《鲁滨孙漂流记》是一则反思历史的道德寓言。鲁滨孙的贪婪、冷酷、不义展示出海洋帝国在精神上的败坏。这样的鲁滨孙们驱动着帝国的征服与贸易。他们把彼此奴役视为通则与常理,对他人与其他民族的奴役与压迫正是帝国的基本精神。但是,彼此奴役的结果是无尽的战争与冲突。若不加节制,它也必将摧毁一切秩序与道德。君不见,西班牙、葡萄牙人奴役美洲人、非洲黑人,摩尔人奴役英国人,英国与西班牙为战,甚至国王还要借垄断奴隶贸易来剥削国民。这不都是笛福刻画的奴役、战争与剥削吗?这是一幅怎样的情景呢?种族之间、国家之间,乃至法律秩序下的国王与臣民之间还有一丝正义与公道可言吗?哪里没有赤裸裸的主奴战争与利益冲突呢?所以啊,这样的鲁滨孙如何能够承载作为商业社会基础的人性原则呢?

种植园主远赴非洲贩卖黑奴是这一帝国乐章的最高潮。然而,他们大部分人命丧黄泉,只留下鲁滨孙一人流落荒岛。承载帝国事业的航船不敌风浪,被“疯狂的大海”吞没。这喻示着,以奴役为基础的帝国必将被内在的战争逻辑吞噬,陷入危机,走向穷途末路。鲁滨孙则成为重塑帝国的唯一希望。
四
重塑帝国的前提是重塑自我。刚上岛时,鲁滨孙从沉船上搬运下来一些必要的物资。但是,面对岛上可能存在的危险,以及漫长的没有社会供应的生活,这些物资仍然相对匮乏。尽管那是一个人迹罕至的海岛,甚至在好几年中,鲁滨孙都没有见过其他人,但是,他无法摆脱既往的战争思维,仍保留着一个社会人的想象。他有着社会人的戒备、欲念与恐惧。他时刻担心自己受到攻击,担心财产受到侵犯。所以,一上岛,他就忙着修筑工事,把居所打造成一个堡垒。这座不断完善,变得日益坚固、隐蔽的堡垒正是其内心恐惧的写照。他在荒岛上劳作不休,克服种种困难,让自己生计无忧。然而,他始终不能让自己免除忧惧,也无法驱走孤独。他长久地处在这种矛盾与分裂之中:他既害怕他人又依赖他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认为自己是荒岛的囚徒。
很长时间以来,他都认为自己所历的劫难是出于偶然,也情愿受这种偶然性主宰。所以,尽管随行同伴皆葬身大海,自己也孤悬世外,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上帝的惩罚与恩典。终于,在登岛后的第二年,他遭遇地震,复而身染疟疾。他先是见证了自然重造山海的伟力,后又感受到自身的极度脆弱。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良心开始苏醒。他开始意识到,包括自己在内,整个自然都受到一个更高的理性支配。他开始努力去理解创造、管理万物的神意。他的身体逐渐康复,心灵大受震动。他幡然悔悟,认识到前半生的罪过。上岛之前,鲁滨孙是帝国的缩影,他也要依靠冒险与征服,依靠奴役他人来成就自己。对他而言,一切人与社会都只是工具。于是,他抛弃父母、离开祖国,舍弃苦心经营的种植园。甚至上帝也只是一种手段,他只在危险中祈求上帝。危险一过,他就将之抛到九霄云外。
现在他认识到,这座栖身的海岛是神的安排。他远离社会,接受自然的教育,理解文明的自然根基,滌除了他从帝国社会带来的虚荣和妄念。他开始游历并考察全岛,只为认知神意,理解自然的理性以及上帝对他的关爱。他开始观察并在劳作中认知自然法则,也掌握了当地气候变迁的规律,并以此指导谷物的耕种。他仍然在岛上劳作不休,但不再是为了修筑抵御危险的堡垒,而是为了经营自己的家园。他种植谷物、驯养山羊、制作面包、烧制陶器,他在岛上成长为农夫、牧人、工匠。他从一个志在驰骋怒海的征服者变成为勤劳的生产者,他用自己的双手在荒岛上打造出文明社会的各项技艺。通过劳动,他也洞晓并展示出财富与文明的奥秘。鲁滨孙驱逐了内心的孤独,海岛也由“监牢”变成他的家园与王国。
自此之后,神意智慧就成了思考财产权、社会关系,甚至国家与帝国秩序的依据。锻造了新的自我之后,他便在这个神圣的道德基础上锻造文明与帝国。在梦的启示下,鲁滨孙救下了星期五,并与之确立了主奴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就他们之间的臣属关系而言,服从的基础并非强迫,而是认同与感恩。或言之,笛福费尽苦心,为星期五的服从设计了一个道德基础。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之间的主奴关系也极为特殊,完全不似鲁滨孙亲身经历过的那种压迫关系—摩尔人对其人身与劳动的完全占有。鲁滨孙与星期五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立体的、复合的,融主仆、师生、伙伴、君臣于一体。鲁滨孙改造了星期五,使之厌弃野蛮的习俗,学习劳动和文明的生活方式。最后,无论在生活方式、劳动技艺,还是宗教和道德德性上,星期五都与文明人无异,甚至比文明人更为真诚卓越。
在星期五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鲁滨孙的感恩与忠诚,看到他对父亲的孝敬与爱,看到他嫉恶如仇,看到丰沛而敏锐的道德情感。在他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身手矫健、勤劳勇敢、刻苦好学,看到他对宗教与道德义理的深思,看到文明开化的能力。我们看到了卓越的天赋与高贵之德性。与凶残、野蛮的食人生番形象相比,这样的星期五具有云泥之别。当然,通过星期五的讲述,笛福也试图告诉我们食人部落野蛮风俗的根源:宗教祭司制度的欺骗遮蔽了他们的高贵天性。所以,星期五也是笛福为读者打开的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看到野蛮民族的社会结构、道德基础,更真切地观察他们的情感与理性。笛福要告诉读者,食人生番虽然具有野蛮的习俗,但我们不能粗暴地据此推测他们天性卑劣,因此是自然的奴隶。相反,笛福展示了野蛮人的高贵天性,也瓦解了奴隶制的基础。
鲁滨孙与星期五在海岛上共同劳作、深入交谈、彼此启发,建立起深情厚谊。对笛福而言,这一独特的主仆关系至少具有两大用意。首先,他批判了既有海洋帝国对土著民族的压迫与奴役。因为,尽管美洲或非洲的土著民族在商业技艺上较为落后,但与欧洲人相比,其道德与理性能力毫不逊色。无论是印第安人还是黑人,对他们的伤害与奴役缺乏道德基础,实乃极端的不义。其次,他也展现了一种“文明帝国”的可能性。在生产技艺和生活方式上,以鲁滨孙为代表的欧洲人具有某种“文明”优势,能够为土著民族带来好处,并因此获得权威。笛福也强调,星期五服从鲁滨孙,既因为他感恩,也因为他对文明生活的认同。
五
继星期五之后,鲁滨孙又救下了星期五的父亲和一个西班牙人。他也因此建立起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微缩版的帝国。“我的岛上现在有了人丁,我觉得自己部下不少了。每想到这我就喜不自禁,看上去多像一个国王。首先,整片土地都是我的财产,因此我有无可争议的主权。其次,我的臣民都极为顺服—我绝对是主人和立法者—他们都欠了我的救命之恩,如果有必要,都准备为我献出生命。还有一点值得一提,我虽然只有三个臣民,却分属三个不同的宗教—我的仆人星期五是一个新教徒,他的父亲是一个异教徒和食人族,西班牙人是一个天主教徒。”(《鲁滨逊漂流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这个帝国容纳了不同的宗教、种族与习俗,它也将土著文明与欧洲的商业文明融合进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中。
当然,与世隔绝的荒岛是一个隐喻,鲁滨孙在这里建立的帝国也只是一个隐喻。魯滨孙与星期五的主仆情谊是整首主奴变奏的终章。尽管它是一则寓言,是对未来秩序的勾勒,但是,它也足够有力地表达出对殖民帝国的批判,以及对土著民族与文化的同情。就此而言,笛福与库切并无二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