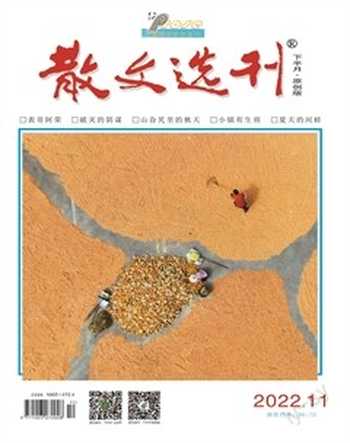弹花匠
赵延文
他的大名叫赵金泽,高大胖实,会弹棉花。他比我父亲大几岁,我们小辈都叫他大金伯。
大金伯弹棉花十里八乡出了名,谁家姑娘要出嫁,都要早早请他去,先把棉花弹好做成棉被,陪嫁的棉被一般都好几床,所以秋冬季是大金伯最忙的时候。大金伯手艺好,工钱也好说,但有一条,喜欢吃肥肉,红烧、清炖、米粉肉、腊肉,只吃肥的,要吃过瘾。有东家给几刀肉算作工钱的,大金伯就将肉挂在弹棉花弓柄上,晃悠悠地挑回家,有人见到他就说:“大金泽,你又胖了!”大金伯嘿嘿一笑说:“不假,有空来吃肉。”
我见过大金伯弹棉花。庄上一位姐姐要出嫁,家主请来大金伯,大金伯吃好了肉开始干活。弹棉花的工具也简单,一把抨弓,一把抨弓柄,一把抨锤,一个磨盘。在姐姐家院子里,姐姐家人搬来两条长凳,架上几个木棍,摊上柴箔子,再铺上凉席,然后将新收的棉花摊在席子上,大金伯就开始作业了。大金伯戴上老头帽,背上檀木抨弓,抨弓弯弯的,越过头顶,一根弦将抨弓柄吊着,左手操着抨弓柄,使弓弦靠近棉花,右手执抨锤敲打弓弦,弓弦发出“嘭、嘭、嘭”声,随着大金伯胖大的身躯前后移动,“嘭、嘭”声有轻有重,饶是好听。弹碎的棉花在弓弦上跳着舞,一会儿工夫就是一大堆雪白松软的云朵。我们几个小孩好奇得不得了,一会儿看看全神贯注弹棉花的大金伯,一会儿看看在弓弦上跳舞的棉花,一会儿看看大金伯那只粗腿大脚,跟前跟后,你推我搡,挤眉弄眼。大金伯也装作没看见,一把抨锤重复地敲打着弓弦,半日下来,帽子、眉毛、眼睫毛、身上都落满了棉绒,仿佛圣诞老人。
弹棉花一般都是在小黑屋里,外人平常难得见到。黑屋不开窗,没有风,棉絮不会飘,但那天天气好,又是家门喜事,喜事要敞亮,大金伯就安排在院子弹。棉絮弹好初具雏形后,女家主将一团白棉纱抛给大金伯,大金伯娴熟地走着纱线,纱线像精心设计一般将棉絮网住。接着间以红棉纱,大金伯牵着纱線,手走龙蛇,很快一个大大的红“囍”就落在被絮中间,煞是喜人,然后在被絮的一角落上日期,最后用磨盘将被絮反复压实,一床新人用的透着喜庆的棉被就成了。女家主也是我婶,她喊来女儿,小姐姐红着脸,母女俩一会儿用手轻轻摩挲着被絮,一会儿将脸轻轻贴在被絮上,开心地笑着,眼角都湿润了。
我老家赵大塘家家棉被都是大金伯弹的。那年我结婚时,我姑姑找大金伯给我弹了床新棉被,又厚实,又松软,那床被子用了多年,后来大金伯走了,旧被子翻不了新,就当垫被一直用到现在。大金伯最后得了肺病,又胖又喘走不动,算是职业病吧,也与他嗜吃肥肉有关。大金伯有两个儿子,大金伯死了,他俩也将那套弹具烧了。
大金婶瘦高个,早年也陪大金伯一起出去弹棉花,有一年两人经过一个石头塘时,石头塘正在开采,一阵轰天响声过后,一块石头飞来砸在大金婶头上,大金婶当时就血流如注,不省人事。我母亲的二姨夫,一个流落在民间的广西军医救了她,从此她再也不随大金伯出门了。
后来,大金婶认这军医为老干爷,老干爷死后,就埋在大金伯的地上,大金伯每年清明都带两个儿子去上坟,大金伯死后,就葬在老干爷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