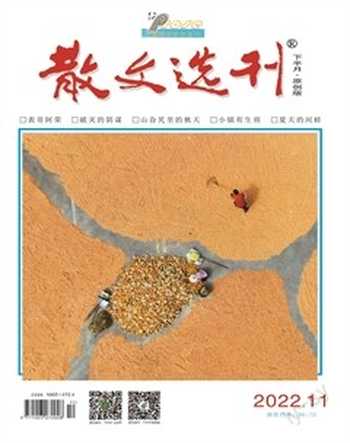六爷
郑曼

清明节前夕,恰逢小雨,一早父亲就打来电话说,今天两个姑姑和妹妹约好一起回老家给爷爷奶奶上坟。
驶入乡道,雨已经小多了,零星地飘散着。我跟爱人说:“今天我要多买一些,我六爷去年疫情期间走了,啥仪式也没有给举行,上次见我六婆,说埋我六爷就如同埋了一只猫,悄无声息的,他的一生太可怜了。你城里娃不懂得。”
那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整个农村文化贫瘠,村里面啥娱乐都没有,那时候我们村上的小孩都喜欢六爷,都喜欢围坐在他的周围,听他给我们讲古今中外的故事,讲仁义礼智信。每次讲到关键时刻,他就会停下来,端起他心爱的紫砂壶,咕噜噜地喝上一大口,我那时曾偷偷喝了一口,苦得我瞬间就吐了,再也不敢偷喝了,也不知道他为啥爱喝苦茶,而且端着那个茶壶,快乐了一辈子。记忆里,他始终微笑着,他喜欢村上所有的小孩,所有的小孩都爱去他门前的石礅子听故事,和他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六爷给所有上学的孩子讲知识的重要性,说改变命运就必须要好好努力学习,每次有谁考了好成绩,他都会奖励他一个水果糖。
我那时还小,也不知道大人们都经历了什么,只知道六爷肚子里咋能有那么多故事,他啥都知道似的,后来大一些追问父亲才知道,六爷毕业于凤翔师范学校,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教师……
六爷是我爷爷最小的一个弟弟,他们父亲不在时,他才三岁,从小衣食寒酸,在艰难的求学后走上了育人的讲台,一站就是 16 年。在“文革”中,他被批斗了整整一个月,在他身上留下了致命的刀痕,他依然不卑不亢,不申不辩,收拾好行李毅然回乡种田。此时爱人瞪大了眼睛:“一点也看不出来你六爷还有这样坎坷的经历,我每次和你回来见他,都是他坐在村口的大槐树下,一边听收音机,一边喝茶那微笑的样子。每次见面都问:‘雨雨娃乖得很。听你爸说,娃钢琴弹得好,好好培养娃,你爸那时也是对音乐非常有天赋的,但是咱家成分不好,一生也没走出去,我这侄子也命运坎坷,啥时把我雨雨娃的录像拿回来,让爷看看,听到娃们都出息,我就高兴。说着就端起茶壶,喝一口他那苦茶,笑着说:‘我娃心长的,每次见我都给我拿吃货,爷小时候没白爱我娃。完了就给我讲起村上以前几个小伙伴,说他们只要回村,都到他那去,给他汇报一下在城里的状况。”想到这,我心里泛起一阵难过,哽咽着说,六爷可怜地死在疫情期间,多爱热闹的一个人,却孤零零地走了。“好了,别难受了,一会儿去给六爷多烧点钱,让他在那边别受到委屈和排挤。”爱人小声地对我说……
车一进村子,老远就看见六婆在村口的槐树下张望,我赶紧下车,叫了一声,六婆,你认识我不?这瓜娃,六婆咋不认识呢,你是我曼曼嘛。然后拉起我的手,笑嘻嘻地说道,走进屋走,六婆给你做饭。“你等一下。”我快速从车上提下一箱牛奶,还有些水果,给爱人说让他把车先开到家去,我一会儿就回来了。我跟随六婆蹒跚的脚步,朝街道里面走,她不停地说,我啥都有,你还给婆买啥呢,可惜你六爷吃不上我娃的吃货了。她眼睛眯着,满脸笑意地说道。你放心六婆,我一會儿去坟上给我六爷多烧点钱,他想吃啥就自己买。“哦,看我娃乖的,还记得她六爷的呢!”她苦笑着说,“哎,不知道让谁把锁子给拿跑了。”(其实她已经患上严重的痴呆症了,经常把自己锁在门外,孩子把钥匙给收了起来)还是老旧的两扇木门,打开后,门道上还放着六爷以前坐的躺椅,那旧得都快成古董的收音机灰尘布满,放在门道的竹子床头;院子里六爷亲手栽种的杏树花开得正艳,正如他一生乐观的生活态度,只是院子里的青苔长满了院墙的两边。土屋陋室里,还摞了厚厚的报纸和书刊。就这一介布衣,粗茶淡饭,想起他八十多岁高龄还在为村上的老年文化事业做着贡献,心里就不由得一阵酸楚,看着六婆佝偻的后背,我急忙用手拭弄了一下眼角……
六婆现在孤零零一个人住在这两间土房子里,院墙有好大一截已经坍塌。她说,她要守着这两间土房子,哪里都不去,几十年已经习惯了,几个孩子要接她,她都不习惯,说不去给他们添麻烦,自己啥都能干,再说你六爷随时回来,家里还有人的。六婆也已经 86 岁了,院子虽然全是土路土墙,但被她打扫得干干净净,厨房里还放满了烧火的柴火,想起来就自己给自己做一顿饭,但是经常就忘记自己吃了没有,清醒时啥都知道,糊涂起来只说以前老早的旧事。这时六婆家的小姑也来了,她对我说,你六婆死活不和我去,就要守着她这破家,我隔几天来给洗洗衣服,收拾收拾。我笑着说,随她吧,年龄已经大了,她咋高兴就咋来。“关键是她现在啥也记不住了,钱都拿不住,一会儿就不知道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把人都能愁死。”小姑愁容满面地说着,随手抱起床上的床单被罩,装进一个大袋子,绑在一辆自行车上,“这些我要拿回家洗,你婆这儿没洗衣机。”随后又开始要脱六婆身上的衣服,六婆说不脏,不让脱,娘俩在屋里开始争执了起来。
看着被搁置在窗台上的茶壶和那些旧书旧报,我脑海中就浮现出六爷给我们讲故事时的笑脸,不用说,他当年教书的样子一定也很好看。我给小姑和六婆告了别,说要赶紧回去,今天大姑他们都回来了,一会儿一起去上坟。小姑说她来时顺便去坟地了,叫我走慢点儿。
我从土房子里走了出来,看着对门和隔壁的红砖大瓦房,还有更好看的一家二层小楼,和六爷的家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住了四五十年的土房子,是那么熟悉又那么的扎眼,六爷临死也没住过一天的砖瓦新房子,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