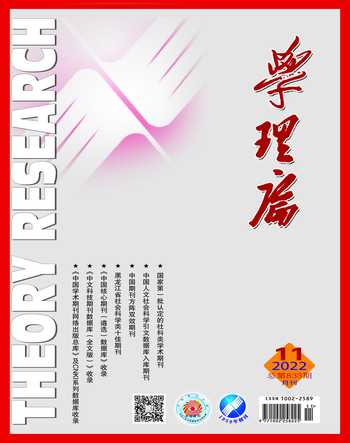论中国共产党赢得意识形态革命话语权的叙事策略
胡伟光 牟方君
摘 要:意识形态革命话语权的争夺为中国共产党赢得政权、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锻造的革命话语体系运用革命话语的叙事策略,凭借政治宣传话语塑造共产党的良好形象,通过道义话语凝聚民众认同共产党的共识,构筑红色叙事感染民众参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行动。话语策略遵循了一条从宣传塑造到心理认同再到采取行动的阶级话语贯穿始终的逻辑链。这对长期执政的政党如何继续掌控意识形态话语权具有一定的经验价值。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国民党;话语权;争夺;话语叙事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2)11-0053-03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革命话语权斗争中,经过长期较量最终取得胜利,赢得了意识形态革命话语权。原因之一在于中国共产党精于话语主题制造,善用话语主体询唤,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协同一致,形成了一整套凝聚民心的意识形态革命话语体系。这套革命话语体系从各不同话语层面瓦解对手,建构自身,在革命的不同阶段适应不同形势的话语变化。话语主体、话语对象、话语表述遵循话语规则的同时结合灵活的话语叙事策略形成话语效果,建构了共产党的话语权威。在话语实践中能够与话语保持一致,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一、政治宣传话语塑造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形象
中国共产党最重视并善于政治宣传。为共产党最终夺得意识形态革命话语权起到重要作用。在政治宣传中,报刊宣传为首,辅之以标语、墙报、通告等。在宣传共产党政策主张的同时,宣传阵地又是与对手展开话语权争夺的主战场。
共产党的领导人大多是理论宣传高手。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王明、博古、张闻天、毛泽东等同志都是理论宣传家,经常发表政论文章。共产党即使在最艰苦的岁月也不忘记出版刊物以统一全党思想,对外宣传自己的主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所到之处都会书写宣传标语宣传自己的主张。在长征途中仍然坚持出版《红星》报、《战士》报。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是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1]445林之达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史》统计了共产党政治宣传的形式和途径“多达60种以上”[2]。利用政治口号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最具代表性。
共产党最了解民众的心理和需求,善于抓住某个阶段的热点事件影响民众心理,用简洁而摄人心魄的政治口号或打击或联合或鼓动或揭露。政治口号灵活多变,不拘一格,随革命形势变化的需要而变化。共产党早期动员工人参加革命运动的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北伐时期口号:“打倒军阀,打倒(除)列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口号:“打土豪、分田地”;鼓动群众参加红军口号:“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实现抗日统一战线口号:“停止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处理群众关系口号:“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争夺革命领导权口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全面进攻口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等。
宣传标语作为政治口号的书面形式,红军在长征途中曾大量书写。如“不当白军当红军去!”“不当无钱的白军,拖枪过来当红军!”“白军兄弟不打红军,北上抗日去!”[3]1935年2月,红军总政治部下达“各部队立即动员编写标语”的命令后,红军战士不管走到哪里,第一件事就是由宣传队员,在墙上书写红军的宣传标语。沿途的红色宣传成了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另一个战场[4]。利用政治口号进行话语宣传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充分吸收借鉴,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许多革命者追忆自己参加革命的原因,称自己并非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受中国共产党政治宣传尤其是政治口号的鼓舞而参加革命的。
在学校教育工作中贯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思想工作,也是共产党政治宣传的特色。抗战时边区的各级各类学校都必须灌输共产党的政治思想,服务于共产党的政权建设。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中国的各级各类各层次的学校教育当中。抗战时期,延安许多重要高校党校军校的校长都是由党内领导人担任。如毛泽东同志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林彪担任红军大学校长,张闻天担任马列学院院长,王明担任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等。毛泽东、王明等同志还经常到中央党校、红军大学、陕北公学等学校讲课。通过学校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埃德加·斯诺到延安访问时看到延安山区的“社会教育站”在教农民识字的同时也没忘进行政治宣传。《西行漫记》记载:在延安山区的“社会教育站”,经常有这样的高声问答:“这是什么?”“这是红旗。”“这是谁?”“这是一个穷人。”“什么是红旗?”“红旗是红军的旗。”“什么是红军?”“红军是穷人的军队!”[5]
除了自我宣传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借用第三方话语进行宣传。当然这种宣传是共产党被动的被宣传,共产党自己并不能完全掌控,因而话语更容易让人相信。1937年10月,埃德加·斯诺在伦敦出版了纪实新闻报道《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为《西行漫记》)。1936年8月,范长江将采访中国西北部的旅行通讯结集出版《中国的西北角》。1936年,传教士勃沙特在伦敦出版《神灵之手:一个在中国被俘的基督教徒的自述》等。这些通讯报道对共产党进行了正面宣传,对塑造共产党的良好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第三方局外人的话语阐述比共产党自己的宣传话语更让人相信,话语效果更令人深信不疑。正因为如此,国民党人坦言:国民党不是败于枪杆子,而是败于笔杆子。
二、道义话语凝聚民众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共識
道义话语是道义文化的主要载体,它对稳固政权、建构社会秩序极其重要,成为国家之间、党派之间价值评判标准。因此,一个政党能否赢得民心,利用道义话语取得民众同情是话语权争夺的关键一环。中国共产党在话语权争夺中就充分采用了道义话语的叙述策略,即使在革命低潮也仍然拥有不少同情者,有些同情者甚至是自己的对手。如肯尼斯·米诺格所说:古“罗马的声誉主要建立在它的道德力量上,所有与罗马打交道的人们都深有感受”[6]。
用话语揭穿国民党北伐胜利后反共清党,违背道义。《评〈中国之命运〉》文中指出:“1924年后国民党所有的革命事业,和中国共产党的名字完全是分不开的。”[7]可是国民党对共产党却以怨报德。制造“中山舰事件”嫁祸共产党,限制、打击共产党,北伐胜利后背信弃义地突然袭击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致使“无数忠勇为国的共产党人”“都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流血在大资产阶级刽子手的刀下。”“这就是昨日同盟者的道义!”[7]国民党利用共产党,达到自己的目的后,“就拿了朋友去屠杀”。“这批自称代表‘仁义道德‘固有德性的人们是怎样一种刽子手大王。”[7]
共产党作为一个恪守道义的政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赢得国人尊敬,与国民党蒋介石在事变后违背承诺、背信弃义、丧失道义形成鲜明对比。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毅然决然主张释放蒋介石”。可是蒋介石被释放以后就背叛了他自己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话所说的不计较个人恩怨,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余向来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语”[8]的承诺。事后不久,张学良被圈禁;杨虎城被关押,后全家被杀害。
皖南事变发生后共产党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真诚与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虚伪形成强烈对照。1941年1月19日,共产党发表社论《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反共真面目,并从道义上痛斥国民党“有悖于中国人为人的道德!”“言行不符,损人利己,本是此等人所代表的阶级之天性,对根本没有仁义道德之人,本不应责备他们不仁不义不道德。”[9]
1945年11月,国民党撕毁国共两党达成的和平建国《双十协定》,进攻解放区,发动内战,背信弃义。1946年初,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后形成《政协决议》。6月,国民党又撕毁决议进攻共产党,内战全面爆发。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几次庄严的停战协定被蒋介石撕毁得干干净净之后,”“什么人也不会相信蒋介石的所谓和谈了。”[10]1227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总结指出:“早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蒋介石就忘恩负义地背叛了国共两党的革命联盟,”“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西安事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德报怨,协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释放蒋介石,希望蒋介石悔过自新,共同抗日。但是蒋介石又一次忘恩负义,”“前年(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人民又一次宽恕蒋介石,”“但是毫无信义的蒋介石,在签订停战协定、通过政协决议、宣布四项诺言以后,随即将其全部推翻。”[10]1236这些总结性的话语把蒋介石国民党缺乏道义的无耻行径完全公之于世,为共产党顺理成章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做了最合理的注脚。
总之,一个政权的存亡与是否符合道义密切相关。当大多数民众通过中国最传统的也是最朴素的道义标准来决定自己的政治立场时,道义话语为共产党赢得了更多的同情和支持。无论是大革命中帮助国民党反遭屠杀,十年内战遭到围剿,还是抗战时期遭到“暗算”,抗战胜利后被再次围剿,在道义话语的叙述中,中国共产党都以坚守“道义”而受害的弱者形象出现。而国民党则被斥为“过河拆桥”“以怨报德”“出尔反尔”“不守承诺”“没有道义”的“无道”政党,其政权合法性基础经常受到严重侵蚀。道义为构筑一种政权的合法性具有重要作用。“道义论”中蕴含的人道主义可能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最核心部分[11]。
三、红色叙事感染民众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行动
利用红色叙事从情感上感染打动民众,影响民众的情感和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赢得革命话语权的又一法宝。红色叙事营造的语境使民众潜移默化地受到红色故事的感染,在情感上接近、认同、进而接受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加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当中。红色叙事话语并不深奥,往往用简单的话语述说一个浅显的道理,以此唤醒感染民众。
红色叙事着重于情感动员,周期短,见效快,容易发动。能在情感上引起群众共鸣,因其戳中群众“泪点”,揭露了群众所受的经济压迫,振奋了群众做人的尊严,为民众从理论上即阶级斗争的高度认识到受压迫根源。红色叙事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故事和话语唤醒群众。红色叙事的话语召唤功能起作用的机制是先从情感动员开始进而触发利益动员的开关,由利益动员深入引向阶级意识,由阶级意识最终成为反抗意识和行动。如红色故事中人物经常说“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这句话语最能打动底层弱势群体的心。首先是振奋做人的尊严,这种人性中必备的情绪已经被日常生活折磨得麻木了;其次是明明白白的利益诉求,穷人吃亏的利益计较一直就存在心底;最后才经过深入的理性思考上升到阶级剥削和阶级反抗理论。这个理论定义工农大众目前的处境“非人是牛马”。原先工农并无此意识,现在接受此意识,共产党的理论表述为“有了阶级觉悟”。这样,“牛马”们就被动员到“做人”的斗争中来。
长征叙事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红色叙事中最成功,最能吸引世人关注的叙事。它“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解释体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犹如“英雄创世纪”。如果共产党没有“长征”这一段具有传奇色彩的话语叙述,有关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叙述就会褪色许多。
1937年10月,《西行漫记》在英国出版,引起西方世界巨大轰动。埃德加·斯诺运用话语叙述为中国共产党在欧美世界赢得好感和同情。斯诺通过对红军将领及普通战士的访谈,叙述了他们不同的成长经历。在这些故事的叙述中,斯诺明显表达了对他们受压迫的同情,以及对他们立志改造中国、笃信共产主义表达了钦佩。斯诺认为红军“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5]他说“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5]
范長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客观地向读者介绍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他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话语叙述抛弃了国民党官话“剿匪”“赤匪”“流寇”等的叙述模式,公开称“红军”“北上抗日”。这完全颠覆了国民政府官方话语体系中的红军形象,让国人看到了与国民党报刊宣传中不一样的红军。他回忆说,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在国统区的合法出版物中,他是第一个公开称“红军”,透露红军“北上抗日”,对“剿匪”加引号的人[12]1181。
利奥塔尔说,叙事确定能力的标准,通过叙述语用学使自己合法化[13]。文学作品为共产党的话语传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红色叙事打破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文化围剿,不仅向外界传播了共产党的声音,而且红色叙事中的红军形象,共产党领导下的西北一角与国民党国统区形成的鲜明对比更为人们认同共产党奠定了基础。
总之,中国共产党向外界宣传自己,借助文学艺术等形式的话语表达,在革命话语权的争夺中,讲述了一个个共产党人是有信仰的“信徒”,红军是正义的队伍,“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等富含隐喻的故事,建构了以“红军”“长征”等为叙事中心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革命话语体系。
四、结语
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权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不断调整话语策略。与国民党或团结合作或对抗斗争,共产党竭力谋取革命话语的主导权。即使在革命力量最微弱的时刻,也能充分利用變化的形势格局,主动求变的话语体系,顺应历史趋势,谋求自身力量的壮大。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话语权功能的重视和较高的话语技巧。通过适应变化的形势而内化的思想观念外化为灵活的话语体系,赢得越来越多的同情者、拥护者。一步步在民众心中建立起话语权威,铺就了一条通往政治权力的成功之路。
中国共产党赢得意识形态革命话语权的叙事策略对于长期执政的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续保持执政党的话语权威,使广大民众主动接受话语权力主体的“询唤”,自觉服从话语权力的“规训”,以实现政权的长久稳固,是一个值得长期深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林之达.中国共产党宣传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3.
[3]闵廷均,颜永强.红军长征在遵义时的标语探析[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0(6):74.
[4]师永刚,等.红军:1934—1936[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75.
[5][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212,7,180.
[6][美]肯尼斯·米诺格.当代学术入门:政治学[M].龚人,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3.
[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24,526,528.
[8]存萃学社.为第二次国共合作铺平道路的——西安事变与张学良[M].上海:大东图书公司,1977:227.
[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82-483.
[10]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吴根友.道义论——简论孔子的政治哲学及其对治权合法性问题的论证[J].孔子研究,2007(2):23.
[12]范长江.范长江新闻文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13][法]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车槿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