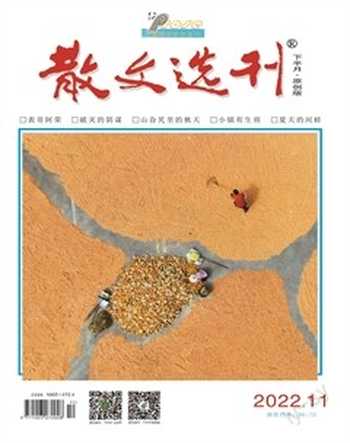三姑
海拉提别克

上世纪 60 年代末期,我和三姑住在二哥家过日子。其实,二哥是我的亲爸,亲爸怎么会叫哥哥呢?
这个问题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坦白的“历史性秘密”。
哈萨克族历来就有着这样的传统:长子的或其他任何孩子的第一个孩子一生下来,就被他(她)的爷爷奶奶抱走。从此,这孩子就成了爷爷奶奶的老小,生父的弟弟或妹妹,爷爷奶奶把他(她)养到成人、立业成家为止。这样的孩子不允许认自己的生身父母(他哪知道自己身世,知情的人也严格保守秘密,绝不会透露半点儿风声),而在爷爷奶奶、叔叔和姑姑们嫉妒思想的灌输下,这样的孩子从小就对自己的生身父母产生厌恶感和敌视态度,虽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也死活不认;若爷爷奶奶过世了,被逼认了生身父母,也不会有亲近感,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
我就是这样的孩子,不是光我一个,过去哈萨克族八成的孩子都有着同样的经历。这种习俗叫法上很别扭的:生父叫“哥哥”,生母叫“嫂子”,爷爷叫“爸爸”,姑姑叫“姐姐”,弟弟叫“侄儿”……奶奶呢?我不说您可能已经感觉到答案了。还有,说法上也很难表达:说“收养”或“领养”吧,人家是你的爷爷奶奶;说“送养”吧,也不太对口;说“抢养”吧,更不是滋味。
我的三姑呢?她也是我爷爷的堂兄弟送养的,还有大姑也是,只有二姑才是我爷爷奶奶亲生的。
当然,我到了二十多岁才得知我们三个人的身世来历。
三姑比我大六岁,父母(爷爷奶奶)死了之后,我们在“二哥”(我父亲)的家里长大。三姑从小就特别疼爱我、护着我,可以说,是她把我一手拉扯长大的。吃的她总是把自己的一份分给我一半;睡觉时,那羊皮大衣最暖和的一块盖在我的身上;干活时一人承担分给我的任务。
有一次,我下乡查看牧业棚圈建设的具体开展情况,那时,我在喀尔交乡当乡长,就顺路在三姑家吃了个饭。肉熟准备下锅时,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哈兰从窗外大声喊:“大头啊大头(小时候,我的头比他们头都大,所以他们叫我大头),三姑不让我们进房,说你脑子里进水了,正在清理着……你给我滚出来!”原来三姑把他们挡在门外,说:“我弟是一乡之长,他工作很忙又很累,如果你们有什么事,就到他办公室说去,非说不可那就一个一个进,最好不要打扰他,他正要休息片刻清清脑子呢……”
三姑啊三姑,乡长是个多大官儿呀!
有一年夏季,那时我大概五岁左右。一天早上,三姑带上我、牵着黑犍牛到森林里拉柴。那山面一片松树,满地都是枯掉的树枝,我们不费力就捡到了很多枯枝并捆成两捆,绳系两头打在牛背的小木鞍上,然后准备往回走。那天是阴天,一直下着细雨,时强时弱。我们快要走出森林时,雨水下大了并开始打雷,天隆隆大响,声音特别大,森林里瞬间更加暗淡起来,不停地闪着淡黄色的雷光。
三姑用恐惧的眼神看看我说:“我们赶快找个雪松避雷吧!听人家说,雷不打雪松,快跟我来。”
她还没说完话,天地就地震山摇般轰隆一声,整个森林被淡绿色的强光扫了过去,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三姑尖叫了一声抱着我趴下,我在下她在上,我的右脸蹭着地趴下的,觉得有点疼。惊吓的黑牛纵身一跳,背上驮的柴火脱落在地。紧接着倾盆大雨,但雷声减弱起来,好像在远方响起。我们起身时才发现,离我们大概五十米远的一棵大松树被雷电劈成两半,倒在两边的地上噼里啪啦燃烧着。
三姑牵着我的手,她在前我在后,顺着草丛里的崎岖小路往家的方向拼命地跑了起来。可没跑多远,三姑猛地刹住脚步停下来,我也越过她一步停下。她双眼盯着前方的小路,我也望了一下前方,就看到一米多长、大人大拇指粗的一条黑斑蛇沿着小路蠕动身子也在爬着跑。三姑说:“看你这副被吓的模样,和那些胆小的娘儿们有什么区别(说得好像自己不是女人),不怕,不怕,我们走草丛里,路就让给它。”
我们跑到毡房前时,就看到二哥二嫂(我爸妈)愣着神儿站在房外,目光呆滞,犹如鱼类一样眼睛往外凸出。
据说,奶奶在我刚满四岁时病故,参加葬礼的人极少,除了我家附近的亲戚外,就没人参加葬礼。更糟糕的是,二哥和二嫂偏向于他们的孩子,本来有限的食物让他们先吃,我和三姑毕竟是爷爷的孩子,因而受到严重的歧视,他们经常挑剔批评我们,甚至责罚。
后来,我们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办法:偷。他们另眼看待我俩,偷吃他们的也是应该的。
我们开始实施行动,时间在夜晚。因为他们白天参加集体劳动很晚才回家,一进被窝就睡,睡得死死的,二哥还发出唱歌般的呼噜声,我们以这个呼噜声为信号,光着脚鬼鬼祟祟地进厢房,摸着黑找到那个放食物的旧木箱,开始偷吃。我们越偷越有经验了:肉不能分块吃,用指甲一点一点地抠上吃,馕也是,但不能多吃,差不多了,就溜回到当被子盖的皮大衣里。
我们的偷吃办法很奏效,一直没有被他们察觉。
他们以为都是老鼠啃吃了。
过了很多年,三姑出嫁了,我也长大成人了。其间,大姑去世了,她老人家去世的那天,我号啕大哭,在她的尸体一旁边磕着头,边哭个不停(一般哈萨克人会给死者磕头),满脸泪水地啜泣着,在场的人被我的啜泣声感动得都流下了眼泪。大姑的十二个儿女走过来扶我起来并安慰说:“舅啊!节哀吧,你大姐她老人家已经八十四岁了,没有留下有任何后顾之忧的事,请您起来!您这样伤心我们的心都碎了……”三姑满脸淚水也走了过来,用手掌擦擦我的眼泪鼻涕,说:“大姐这一辈子对我们不薄,你哭哭也是应该的,可不能这样伤心啊,让她老人家安心入土吧,快起来,我的好弟弟!”
二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用手绢一直捂着脸装着哭泣的样子,可我心里清楚她没哭。以前她和大姑老是说不到一块儿,还为一些琐碎小事翻脸,但她也从来没提过大姑的身世。
三姑的丈夫是个老实巴交的人,而且怕她,可他唯一的缺点就是酒量差得很,喝两杯就会耍酒疯,或和旁边的人吵架甚至打架,但从来不碰三姑的一根毫毛。可有一次,他在邻居家喝酒,没喝几杯就出手打人家。三姑可能想要拉架站在两人中间,结果被他踢了一脚屁股,可能踢得狠了一点。大晚上,三姑给我打电话,只说有人打她了,也没说是谁动的手(那时,牧区已有了程控座机电话)。这还了得,我立马坐上吉普车,连夜往高山区跑。那晚没刮风,但特别寒冷。我们照着车灯,沿着沟底里硬雪上牛羊蹄子踩出来的崎岖小路缓慢行车。车到不了三姑冬牧场的家,我们只能把车停在几公里远的山口,再步行上去,因为那时深山里的好多冬窝子通不了车。
我和司机到她家一看,油灯亮着,三姑夫穿着衣服,面朝墙侧身躺在床上,三姑背靠火墙坐着。我一进门就大声喊:“三姐,你还好吗?哪个吃了豹子胆的家伙委屈你了?那人呢?弟为你出气来了。”
三姑夫立马起身坐在床边,吞吞吐吐地说:“是我嘛,都是酒惹的祸,可不是故意的,本来要踢那个家伙,可就在这时,她突然站到我们中间了,结果我就踢到她了。”三姑说:“你那猫崽一样的酒量还喝,还无缘无故地打人家,我能不拉架嘛,真是窝囊废一个。”
我明白了真相后,一时半会儿不知说啥,就垂着头一动不动地站着,且事情也没那么严重嘛。三姑一眼就看破我的心思,因她一手带我长大的,看不破才怪呢。可她不吱声,这下我就左右为难了。可没过一会儿,我也琢磨到她的意图了,就说:“啊,原来是这样,三姐夫你明明知道自己不是个喝酒的料还喝它干啥?以后啊,你想喝酒就到我家喝去,想打人就打我好了,如我还手就不是个人,但你找任何借口,动我三姐的一根汗毛绝对不行的,如她遇到什么难事,我会把自己的命都搭上去的。三姐,你也是,我本以为你受委屈了,就这么鸡毛蒜皮的事大喊大叫,还大半夜的惊动我,家丑不可外扬啊,人家听说连乡长的姐姐都被人打了,我这个脸往哪儿搁呀,值得吗?老两口了,还好意思……”
三姑夫立马站起来恭恭敬敬地说:“是的,这事不能怪你姐,都是我的错,我给你姐赔个不是,下不为例,下不为例……”三姑这时才站起身,摸摸我的头发说:“冷吗?把帽子给我,快,坐到火墙旁边暖暖身子。”
三姑从来没有难为过我。这一次,在深更半夜,她为什么为了这么个鸡毛蒜皮的事麻烦我?不管咋说,这就是我大半辈子为她办的一件事。
令我高兴的是,三个姑姑儿孙满堂,子女对她们特别孝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