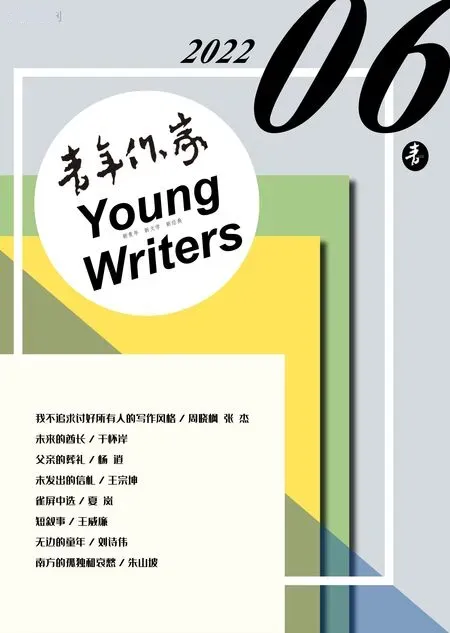“新南方文学”的文明转型面向与区域现代性特征
刘起林
一、“新南方写作”的文化感知与逻辑自洽
“新南方写作”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命题确实具有相当的敏锐度与前瞻性,触及了某些正在逐渐彰显的问题。但就现有讨论看,其中又存在着可以进一步深化和提升之处。
我们首先对相关讨论的大致轮廓和基本内容略做梳理。
按照命题主要倡导者的思路,“新南方写作”包括三方面的要义。从外延看,“新南方写作”既是针对“北方”的南方,又是针对“江南”的“南方以南”,具体是指海南、广西、福建、粤港澳大湾区和东南亚华文文化圈;从内涵看,“新南方写作”之“新”有四点:文化遗存和文化族群丰富多元的“地理性”,相对于传统中国“土地文学”的“海洋性”,陆与海、方言之间和美学风格的“临界性”,有待召唤和塑形的“经典性”;从实践意义层面看,“新南方写作”“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单一性民族国家的限制,……政治(主权)无法抵达的地方,汉语的主权却可以预先书写和确认”,因而可以成为走向“世界文学共和国”的方向和路径(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其他讨论主要从命题内涵充实和文学史视野拓展两个方面展开。在命题内涵充实方面,既有学者从理性层面的意义维度强化,如“地域性与时代同行”(贺仲明)、“地方性与世界眼光”(刘小波)等;又有作家从艺术感觉层面的内在特质真切化,如“蓬勃的陌生”(林森)、“蛮荒及其消隐”(李壮)、“异样的景观”(朱山坡)、“新寻根、异风景与高科技神话”(王威廉)等。在文学史视野拓展方面,讨论者或者从“成长性和提示性”的角度,将韩少功、刘斯奋、林白、东西、鬼子、凡一平等作家和王十月、郑小琼的“打工文学”,分别作为“新南方写作”的源头和支流(张菁);或者从具体文本出发,将黎紫书的《流俗地》、陈继明的《平安批》、林白的《北流》等近期有影响的作品,都作为“新南方写作”经典出现的可能性来看待(见林培源、曾攀、蒋述卓等人的相关论文)。
这些论述与言说各有其切实的领悟和针对性明显的思考。但在认同之余,笔者又发现其中存在某些未能逻辑自洽之处。首先,“新南方”针对北方和江南而言的深层次基础和依据是什么?在“异质性”背后,南北之间的关联和矛盾统一性又是否存在、基于怎样的背景而存在?其次,“新南方”侧重于揭示其本土性的内在特质,但在估量由外来力量所构成的文化丰富性方面则有所欠缺。具体说来,“新南方”常年生活着数以百万计的湖南、湖北、江西、四川等地的打工农民,他们分属楚文化圈、赣文化圈和巴蜀文化圈,对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至大至深,这些形象的审美意味却既不是“地理性”“海洋性”所能涵盖的,也不是“临界性”所能充分阐释的。再次,“新南方写作”的主要关注视野是一些新南方地域中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写作”一词内含着“在新南方”和“写新南方”双重界定。但实际上,表现“新南方”的作家类型众多,本土作家中既有年轻的也有年长的,还有邓一光、陈继明这样的“新移民作家”,又有韩少功等“两栖”作家,甚至地道的四川内地作家罗伟章也创作出了表现“新南方”的精品力作。所以从逻辑层面看,反而是将“在新南方”的界定去掉,修正为从题材和内涵层面着眼的“新南方文学”更为妥帖。
总体看来,在已有探讨的基础上,我们尚可从“新南方”之“南”、“新南方”之“新”和“新南方文学”的背景与线索几个方面,对相关讨论略做深化、拓展与提升。
二、中华文明差序格局与“新南方”之“南”
“南方”“北方”的区分在中国历史上古已有之,而且存在着不同的层面,其内涵也是不断变化的。
从历史文化层面看,“南”“北”的区分起源于西周分封制。先秦时期,中原王朝称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带为“华夏”,而将周边四方称为“北夷、南蛮、西戎、东狄”。战国策士们沿“秦岭—淮河”一线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的各诸侯国活动,“合纵连横”“远交近攻”,逐渐形成了中华文明内在的差序格局,中原正统文化和南北蛮夷文化的观念也随之确立。随着某些王朝的定都与南迁,长江三角洲又发展起来,形成了“六朝古都”“东南形胜”,加之沿海资本主义发展较早,所以直到近现代,长江三角洲始终是生活优裕的“江南”富庶之地。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实际上也称南方,在历史上统属于“中南”地区,这些地区长期作为瘴疠、蛮荒之地而存在,“永州之野产异蛇”就是最好的注脚。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中南”地区曾一度领时代风气之先,具体从事的却是政治、军事之类需要“霸蛮”才能成功的行为。中国革命史上存在着“南方根据地”“南方游击队”“中共中央南方局”之类的称谓,这些称谓基本上是将“东南”和“中南”统称为“南方”的结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六大区行政区划中,长江三角洲并不以“南”相称,而叫做“华东区”,广东、广西与湖南、湖北、江西同属于“中南区”,现在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和西藏则属于“西南区”。所以,长江三角洲的“江南”不过是一个古代历史地理的文化遗存。
在中国文学史上,艺术趣味、审美风格的南北差异也相当明显。关于北方“内陆文学”的趣味与风格在这里暂且存而不论。在南方文脉方面,从《离骚》化政治冤屈为情爱幽怨的凄艳悱恻,到南朝民歌“郎歌妙意曲,侬亦吐芳词”的旖旎缠绵,再到宋代婉约词好作“妮子态”、稼轩词也不时“男子作闺阁音”(毛晋《稼轩词跋》语),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相当明显的侧重“阴柔之美”的线索。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南方审美话语内部,也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具体形态,其一是“东南”长江三角洲地区传承江南士人文化趣味的典雅整饬、精致伤感的审美形态,其二是“中南”地区远接“楚辞”浪漫神奇传统的神秘诡异、民间巫风气息浓郁的审美形态,其三是以周立波《山乡巨变》、陈残云《香飘四季》、陆地《美丽的南方》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牧歌风格的审美形态。在新时期文学中,也存在着苏童、叶兆言式新历史文学和韩少功寻根文学的不同南方审美话语。
从这样的历史文化与文学背景来看,“新南方写作”的地域范围既是区别于长江三角洲的“东南以南”,更是关联着“中南”“西南”地区的“岭南”“华南”。只是由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地域差异,广东、海南走在了经济变革前列,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变成了有待崛起的“中部”,广西则与四川一道被归入了“西部地区”,相互之间的关联未能表面化而已。在“新南方写作”所列举的作家中,陈崇正的小说“潮汕巫风”(杨庆祥语)气息浓烈的魔幻想象,林森的小说对海南岛奇风异俗和地域文化的审美热情,朱山坡小说的反讽、诙谐与荒诞感,我们均可从韩少功的《爸爸爸》等作品中发现审美意象、艺术趣味的端倪。事实上,韩少功曾经“寻根”的湘西本就属于与广西、云南接壤的“大西南”地区。所以,“新南方写作”者的艺术风范虽然不同于长江三角洲的“东南美学”,却颇近似于浪漫神奇、巫风诡异、气息浓郁的“中南”文学。在湘南地区中,永州与广西的文化共同性,永州、衡阳、郴州与广东的经济关系之密切,均不亚于广西与广东的关系。如此看来,“新南方”之“南”并不是真正自成一体的存在,既可以从内部将广东与广西相区分,又可以从文化角度将广西与湖南、从经济互动角度将“华南”与“中南”相关联。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的发展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差序格局,文学创作因为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层面的差序格局,也表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和南方内部差异。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环境中,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仍然存在,由此构成了与“江南”相区分,却与“中南”紧密关联的“新南方”。这才是“新南方”之“南”的确切方位。
三、“全球南方”现代化与“新南方”之“新”
“新南方”之“新”,则存在着时代和世界两个维度。
其一是时代维度的中国“新南方”经济开发潮。从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福建的经济特区建设,到八十年代末开始的海南大开发,再到新时代的“粤港澳大湾区”及“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南方各省或先或后地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行先试”地区。而且,这种“先行先试”不是如长江三角洲那种历史积累深厚的顺势而为,而是虽有广州这样的传统商业繁华之地,更多的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差序格局中的边地,是一种边地跨越式发展。深圳从小渔村起步、海南大开发都是如此。在那些潮湿蛮荒之地、“鸟语”方言之区、浓厚的宗族文化氛围之中,转眼间就流行起从拆迁面积、开发方案,到GPS定位、互联网,再到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文明的气息,而且成为标志性的现象。在这从传统边地文明到现代科技文明“陡转”的历史进程中,不仅“新南方”的本土文化产生了令人目瞪口呆的巨变,内地文化、西方文化也强势加入其中。于是一时之间,文化的演变如同一锅各种原料都有的“杂合饭”“八宝饭”,杂糅性、兼容性、临界性就成为显著的特征。
其二是世界维度的“全球南方”现代化背景。“新南方写作”的倡导者敏感到港澳台、东南亚华文文化圈均可纳入“新南方”的范围,根源在于它们与大陆的南方沿海各省同属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全球南方”。从海南自由贸易港、“粤港澳大湾区”到“新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东盟合作,又高调强化着相互之间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联系。在这“南南合作”的过程中,“新南方”内部的各方共同享受着全球化红利,也共同存在着反西方霸权的诉求,于是因立场、利益的一致性自然地形成了价值的共识。在这中国沿海的“新南方”之中,东南亚和港澳台有着诸如“解殖”抗争、种族矛盾、身份认同之类的历史背景,中国沿海则存在着从明清时期“下南洋”到改革开放初期港台文化流行的地域渊源,相互之间的联系本就源远流长,如今则由于这“南南合作”而更为生动鲜明起来。尤其应予注意的是,中国大陆的岭南已经由现代化“实验区”成功转型为国内的现代化“示范区”,而且秉持非资本主义、非西方路径的发展模式,充分体现出主体意识高扬的精神文化特征,从而更滋生出一种精神与文化的向心力和“虹吸效应”。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南方”就显示出一种混杂性与聚合性一体两面的总体特征。其中既有传统南方的地域文化与经济大开发的科技文化、技术理性的相互碰撞、融合与消解,也有岭南社会内部之客家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海洋文化、下南洋文化的并呈,还有随内地打工潮而来的湘楚文化、赣文化、巴蜀文化的涌动,港澳台文化和东南亚华文文化的“内迁”同样是引人瞩目的大趋势。正是在“全球南方”经济共同体的基础上,这多重文化关系的格局和文学共同体建构的可能性才得以存在,“新南方”之“新”系由此而得以充分体现。
四、文明转型与区域现代性:“新南方文学”的基础和线索
“新南方”文化圈的形成和文化新意的凸显,根本原因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区域不平衡状态。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为追求独立富强走过了一条极为艰辛的道路,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但当今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种“不平衡”也表现为转型形态的多样性和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具体说来,当下中国存在着京津冀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东北经济圈、中部经济圈、西部经济圈等,相应地形成了京津冀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东北振兴”“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发展战略。社会文化层面也逐渐显现出各自的独特性。东北文学的“铁西三剑客”近年来引起极大关注,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东北工业区的社会、文化独特性进行了颇具个人才情的艺术定型。“新南方文学”命题的思想实质,则是对又一种文明转型形态、又一种区域现代性的审美塑形期待。换言之,中华文明转型的地方路径和区域性特征,才是“新南方文学”审美形态与意义建构的基础和背景。
文明转型面向的也是阐释“新南方文学”的意义线索和观念轴心。已有讨论的诸多感悟与论断,均可围绕这个线索和轴心得到有效解释。“新南方文学”相对于北方文化和江南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这“异质性”并不是因为早已存在的地域环境和民间风俗文化特性,而是因为这种特性与区域性新发展相碰撞、相融合而呈现的新形态。“新南方文学”之所以能够将内地本土文学与港澳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纳入共同的意义格局而无重大违和之感,则因为“新南方”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本身就出现了跨国族、大同盟的格局,正是置身这样的格局之中,中国本土的文学创作才获得了跨国族的精神视野和叙事元素,出现了与海洋文明对话的可能性,东南亚文学也才在长久的“离散”叙事之后,逐渐表现出基于中华传统“家国天下”伦理的文化和文明向心重生趋势。“新南方文学”边地蛮荒感与都市焦虑、迷茫感兼而有之的生命体验境界,则源于在改革开放初期那种“工业文明拓荒”阶段之后,“新南方”呈现出了边地文明原初形态、工业文明产业大发展形态和后工业文明高科技形态杂糅的新特征。总之,“新南方文学”所列举的诸多特征,均可由文明转型和区域现代性特征提供较为思路清晰而逻辑根基坚实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