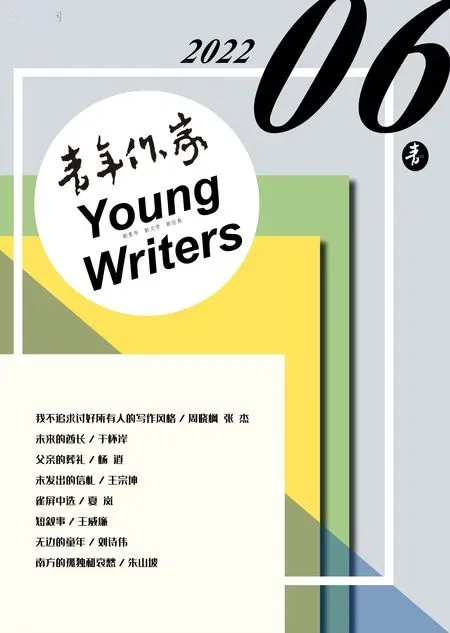孽 胎
夏岚
上篇
“李耳在娘胎里八十一年,一出生便是老头儿,所以他成了道家始祖。”姚申一边说一边用柏树枝蘸水往窦果儿所在房屋的门楣上洒。他是村里的算命先生。村里人干大事都要问问姚先生,盖房修坟,婚丧嫁娶,一律得问。
十七岁的窦果儿大着肚子一年七个月了,稳婆说娃还在胸口没入盆。
“几十年来头一遭见着,肚脐以上大如鼓,小腹始终扁平,不是怀个孽种还能是什么?”稳婆这样告诉姚申,让他施法的时候千万要断了窦禄的命根子,不然亲妹妹肚子里的娃永远生不下来。
“八十一年?果儿要是死得早了,岂不是一尸两命?”窦上仁使劲瞪起浑浊的双眼问姚申。
“啊呸!老子是太上老君!果儿怀得出这么个老神仙?你还真是寡妇老婆梦见毬 ——尽想好事!”姚申唾沫星子喷了窦上仁一脸,虔诚念叨“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又一碗水泼在门槛下。
窦果儿在床上虚弱地喊:
“老爹,给生盆火,冷。”
窦上仁应:“三伏天生哪门子火,你这肚子一大怎么脑子都不好使了?”他正一头懵,没搞清“老子”是老子还是姚申。
果儿没有接话。帐内,只听得牙巴骨错得格格直响,床板隔一阵就乒乒乓乓擂鼓一般按捺不住。室内灯光昏暗,帐幕厚重,谁也没有关注她身下有紫黑的液体浸湿破旧的棉絮。
半月前,她坐在木门前拣选豆子,感觉腹部有被钳子拧了一把的疼痛,随后一股热流喷涌而出,浑浊而黏稠,带着恶臭。窦上仁遣儿子窦禄去请稳婆,窦禄磨磨唧唧难得出门,瞎眼妈妈扬起扫帚朝着他一顿乱舞,吼道:
“作孽的,你不去该谁去?一人作孽好些人替你担当,你到底还是人不是?”
稳婆到窦家住了三天,吃下去二十来个鸡蛋三四斤腊肉,走了。她说此生没有见过这么奇怪的胎位,这要生下来,不是个死娃娃就是个孽障,安全起见,建议窦家找半仙姚申。姚申要价九十九,窦上仁卖掉一半的存谷子,凑了五十三,连续三日求着,人家总算勉强来了。杀鸡烧香贴符咒,阎王观音土地公,东南西北各路牛鬼蛇神,个个仔仔细细上座伺候,好话说尽,这又是两天一夜。
姚申施法的第三天清晨,窦果儿感觉自己五脏六腑被撕裂,身体里无数个小气泡在爆炸,四肢已然失去知觉,整个人完全不能动弹。到了中午,依然没有生产的迹象,姚申收了钱,带上两斤砂糖和三米三的上好红布,走了。他将七片桃树叶子塞在果儿枕头下,说:鬼神已经不会再祸害孕妇,现在只等着她肚子里的孩儿问娘亲要完上辈子的债,自会出来。
王灯挑着火腿和糯米与姚申在小山梁子上相遇,他是村子里排得上号的二流子。姚申保持惯有的姿态昂首阔步,王灯扁担一横,端端撞上姚申的胸口。
“青天白日还有拦路鬼,老子也真是头回见!”姚申疼得弓着背呻吟稍许,直起身来见王灯已经挑着担子晃晃悠悠走出去十几二十米,他怒气难平,追上去破口大骂。
王灯不回头,兴致勃勃地迈着步子,哼起轻松的小调儿。姚申当然受不得这种气,捞起一把泥沙灌进他的小筐,又骂:
“你个狗杂碎,撞了老子不说请吃茶,歇下道个歉总该有吧?你他妈的没人教?”
本来还有好多句盛怒之下的经典词句,可惜还没来得及一一道出口就被王灯摁住了,他把他摁进了干涸的堰沟,拳头捣大蒜一样地落在他面颊上。
王灯的嘴不动手不停。他一个二十来岁的精干小伙子,姚申花甲老头儿,当然没有招架之力,只顾得叽叽哇哇大叫。打得累了,看姚申连喊的力气都没有了,他站起身来转转手腕,拍拍泥土,走了。
姚申蜷曲着身体,好半天才稍稍回过气,挣扎着爬起来,坐在石板上小心擦拭嘴角的血渍,愤愤道:“狗杂碎,明儿就给你户口迁去阴曹地府。”王灯没有听见,他已经到了窦家,可惜筐子里的糯米有大半喂了鸡,泥沙浸染得利害,完全没法吃了。
“果儿嫁我,这火腿归你,糯米我重新送一筐。另外加一块手表和现金三百块,逢年过节,该给老丈人过的礼节,我王家绝不怠慢。”王灯这天中气似乎比平日足了好几倍,语气昂扬。
“嫁你?你什么来路?你的火腿糯米手表现金什么来路?你亲哥哥王布还在牢里吧?那可是个抢劫犯!”窦上仁侧身对着王灯,一手背在背后,一手指天指地配合自己的调子。
“嘿,窦老爹,你别问我钱财什么来路,我也不问您闺女这肚子揣着谁的种,欢欢喜喜结个亲,谁都自在。”王灯双手一摊,表达自己的风度和诚意。
“全天下都知道,我闺女是被城里来的那个大知识分子祸害的,他敢做不敢当,搞大我闺女肚子跑路了!大队干部都说了,我闺女是受害者,值得同情。”窦上仁脖子上的青筋和眼珠子都在往外鼓。
“哟!您这说的是教书的周老师?嘿,周老师什么人品大伙儿心里都清楚,然后啊——窦家都出过一些什么蹊跷事,大伙儿心里也清楚。那周渊宁愿丢了铁饭碗也不要您这女儿,凭着敢做不敢当就解释得通?再说说同情,村干部逼走周渊,恁是没收上一万块罚款,还来同情过您?同情过果儿?姚骗子作法的钱吃茶的砂糖和孝敬红布,村里给出的?”王灯凑近窦上仁逼问。
窦果儿肚子隆起五六个月的时候,老村主任领着一大波人拦住周渊,为她主持公道,威逼利诱苦口婆心。但周渊抵死不从,百口莫辩之下,走了。村主任说:周渊不想缴罚款,穷文人舍不得掏大笔钱,等着娃娃大了,他铁定会回来相认。
“那她肚子里的娃跟谁姓?要是个通了天的神仙娃娃,我窦家可得算顶大的功劳!你别想好处都捞尽!”窦上仁歪着脖子问王灯,他记着老村长的话,思来想去,不能让周渊得逞。
“既然嫁我,生了个屁,咱就放到空气里;生了个神仙,那自是他升他的天,我种我的田;生了喘气儿的娃娃,跟我姓,王侯将相的王,您家不吃亏。”王灯涎皮赖脸。
窦上仁拉上儿子去墙角嘀嘀咕咕个把小时,然后回王灯:
“果儿许你了,你先把那些东西样样置办齐全给我送来,再寻个好日子办喜事。不过喃,果儿要是这两天生产,满月你再来接人,月子里的口粮算你的。”
“哎哟,我的亲爹爹,好日子哪还需要寻,今儿就是个好日子!这样,我现在去取东西,转回来就带果儿过门。”王灯麻利地扛上扁担,拎着空筐子,十分急切。
“今儿?今儿咋行?这啥也没准备,请帖来不及下,好几家欠着我的人情,不操办个席面,咋收得回来?”窦上仁明显不乐意了。
“啧啧啧,我的亲爹爹,结婚是我跟果儿的事情,我们俩准备好了,那就万事俱备。等咱哥结婚,好好儿操办操办,几辈子的人情都给收回来!”王灯往窦禄肩膀一拍,又说,“哥也是这个意思对吧?看在哥的份儿上,我再加一担货的彩礼。”还没等窦家父子俩反应过来,他已经一溜烟跑出好远,还喊着:
“等着哈,我去去就回。”
窦上仁看着那方火腿,又看看窦禄,再围着屋子踱了一圈儿后,跟自己的瞎眼婆子说:
“你说这王灯是不是想等果儿生下孩子后,大小分开卖价钱?要不然干嘛下这么大本钱娶个大肚婆?这家伙可不是什么好角色,两兄弟同进同出那么多年,吃香喝辣怕是没少过他,偏偏坐牢王布一个人去了,他却在外面逍遥自在,蹊跷。”
瞎眼婆子正在摸索着摘臭草叶,擂碎取汁,然后蘸着汁液给果儿揉肚子,缓解疼痛。她停住手沉默片刻,说:
“嫁他吧,别琢磨了。烂摊子让人收去,比捂自己兜里生蛆虫的好。”
“哎,老婆子,我可听说眼瞎的人天灵盖上有第三只眼,大事儿比睁眼的人还看得真切。果儿怀胎十七个月,天下奇闻,你没看到来的是哪路神仙?”他死死盯着瞎眼婆子的眼睛,要确认她说真话。
“狗屁个三只眼,狗屁个神仙!也亏得我眼瞎摊上你这么个糊涂蛋,生一个儿子祸害了两个女儿,孽障!你但凡勤快一丁点儿,哪怕墙边搭个茅草棚子,也不至于让儿子女儿挤一个被窝里睡吧?出这么大乱子,果儿受这么大罪,你脑门上还糊着屎?死糊涂!”瞎眼婆子眼眶红了,气得整个身体都在颤抖。她不只一次埋怨过窦上仁懒惰和贪婪,两个女儿三五岁的时候她就反复提及要给女儿们准备睡觉的地方,不能跟哥哥窦禄挤在一张床上。窦上仁嘴上答应,头年砍回来的树第二年也没修理成木材,一年堆积一年,直到大女儿窦英儿在家怀了娃,姐妹俩的卧室依然没有着落。英儿出嫁了,果儿又大了肚子……
窦上仁灰溜溜地走了,看见窦禄倚在门框上啃指甲,他故意直冲过去撞了他一个趔趄,骂:
“一天就知道杵着当拴马桩,几十岁的人了,不长进!”
窦禄莫名其妙瞅了他一眼,继续靠着门框啃指甲。
窦上仁准备到房间里看看果儿,刚跨进门又退了出来,他把姚申贴在墙上的黄符一把扯掉,揉成团儿给吞了,噎得翻着白眼儿说:
“果儿嫁出去可以,符咒保佑我无病无灾,福寿绵长。”
他背着手在大门口来回走动,时而呵斥乱窜的鸡群,时而盯着山脚下的炊烟发呆,总之就是坐卧不安,心事重重。看见那只大白母鸡终于完成了当天的下蛋任务,在草垛边昂着脖子高声叫唤,向着全世界邀功的架势,窦上仁跑过去捡出那颗热乎蛋握在手心摩挲,突现出灵光一闪的咋呼神态喊:
“窦禄,你去找镇上潘春阳要些东西来,果儿给他家做了三年保姆,他可答应了果儿出嫁要向亲哥哥一样置办嫁妆。啊呸,亲哥哥不行!你这个亲哥哥啥也置办不上,你一定要让他比亲哥哥还亲。喊他不用客气,就铺子里有的,随随便便选个三五件就成。对,大红喜字的搪瓷盆子要一对,哎,办喜事儿有讲究,得成双成对。啊,还要一对暖水瓶,鸳鸯印花的那个。记住,这两样是最要紧的,剩下的嘛,你让他看着给吧。这样好了,单的双的你也别计较,都拿上,大喜日子,别驳了人家情面。”
窦禄闻声收拾了几条破旧蛇皮袋子,准备出发。脚还没跨出门儿,窦上仁又说:
“你顺道儿给苏耕家、刘木匠家和你姐夫胡晏带个口信儿,就说果儿出嫁,请他们来吃晚饭。”
“灶都没烧热,哪来的晚饭招待人?”窦禄说。
“这个你别管,我自有主意。还有王百岁也要通知到,之前帮忙抬棺材他没给力钱。哼,今儿要是不来,我就把他老娘的死法儿抖出去。千万别漏了唐芝敏,这婆娘比她那个走江湖的草药贩子男人讨喜,谁家红白喜事她都舍得掏份子。”
“哦,晓得了。”窦禄找了根木棒子,挑着蛇皮袋出了门。
“爹呀,你,给找个——郎中行不行?我,快要死了——”果儿在屋里喊。她牙齿打战,明显咬字不清。
“哪有什么郎中,也不嫌丢人?谁个女人生孩子能见郎中?你说说你,怎么就这么不自重?那妇道人家生孩子,郎中进屋瞧得?郎中他就不是个男人?光腚生崽儿的日子,你要见郎中?你就这么不要脸?哼,你不要我还得要喃。”窦上仁听见果儿呼喊便气不打一处来,絮絮叨叨骂开了。
果儿的瞎眼妈妈端着绞好的臭草叶汁,扶着墙壁踩着深深浅浅的步子去到她跟前,轻声唤她,缓缓揉搓她的腹部。果儿痉挛的频率越来越高,牙巴错的声响越来越大,盖过她的呻吟。许久,她已经没有力气呻吟。
窦上仁骂得累了,坐在石磨上眯缝着眼睛休息。其实他的大脑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王灯还没有来,让他有些焦躁。糯米、手表和三百块现金,还有一担,他自己说好要多加一担,别想抵赖!不来?他小子敢不来,不来也得把糯米给我补上,火腿也别想拿回去,哼!
日头西斜,刚好照在脸上,火腿也在,他真的有点儿困了。涎从嘴角滑落,眉梢上挑,不知不觉间左手抓住自己的右手手腕。他感觉老村长正盯着自己手腕上亮光闪闪的手表,感觉村里最丰腴的婆娘唐芝敏看自己的眼神格外热烈,真真儿是直直射进心窝的眼神;家里摆着红盆子,挂着崭新的长绒毛巾,茶缸也是崭新的,暖水瓶里滚烫的水倒进去,热气直往上腾;好几路媒婆领着俊俏的大姑娘排在自家门口,窦禄正挑着呢!资历最老的陈媒婆说:
“咱禄小子挑剩的,让窦老爹也瞧瞧。殷实人家,瞎眼婆子当家不合适,来来来,窦老爹看一看……”
窦上仁似乎看到一个身形儿饱满的独辫子姑娘,奋力睁开眼睛,眼前是渣滓遍地的土坝子,还有随风轻轻晃动的树影。他不甘心,将眼睛睁得更大更圆,有干透的或者没干透的鸡粪,一块脱落的桉树皮掉进干涸的池塘,阳光已经退到脚边。站起来走到土坝边缘,那里视线更好,目之所及,是连绵不断的群山,看了几十年,熟悉的脉络和陌生的细节。伸展伸展胳膊,跺跺脚,梦醒了,心里空落落的。
女婿胡晏急喘吁吁地跑来:
“爹,听说果儿要嫁给王灯?”
“啊,是。”
“就今天?”
“对,今天。”
“怎么说得这么急?不等等?”
“娶媳妇儿都不急那啥才急?急你爹死了小舅子?”窦上仁忽地觉得胡晏很差劲,女儿窦英儿嫁给他白瞎了,啥也没捞着。不如王灯阔气。
说曹操曹操就到,王灯“哐当”一下放了一大堆东西在窦家堂屋中间。
糯米、板油、砂糖、梨膏、橘子罐头、枕巾、布匹,还有两只洁白的瓷罐和一副十只装的碗筷,满满当当摆满簸箕。窦上仁一样一样仔仔细细瞧着,打开梨膏盒子的盖,深深吸气,感叹:
“值钱的东西真喜人儿啊!”
胡晏伸出小拇指准备蘸一点尝尝,窦上仁啪一巴掌打开他的手,骂道:
“啧啧啧,你要脸不要?甜水水都不曾给我端过一碗就得了我大闺女,还想蹭我的梨膏?呸!”
胡晏悻悻地转回手,假装伸出来抠鼻孔,尴尬地笑了一下。王灯忙活着卸掉一块门板,把三百块钱和一块新手表交到窦上仁手上,指着门板说:
“快,搭把手,把我媳妇儿抬上来,我们该走了。”
“走?哎,杂种,母猪配种也没这么急的吧?”胡晏把肚子里的怨气出给他。
“姐夫,你不懂,这种娶娘子送孩子的婚事,很讲究个风水时辰,我都是找外边的高人看好了的,耽搁不得。千万耽搁不得!”王灯已经冲进果儿床边,把帐子高高撩起,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
窦上仁喜不自胜地将手表戴上,蘸口水反复搓着几张大钞,对着亮光举起放下,放下又举起,反反复复确认,确认真假,确认在自己手中。他无暇顾及恶臭而垂危的果儿,胡晏问:
“大兄弟,你花这么大本钱娶个僵蚕一样的媳妇,为何?”
“别废话,搭把手帮我抬起来。”王灯已经将果儿从床上搬上垫了破褥子的门板,他需要再将果儿和木门一起架上背篓。
瞎眼妈妈拽住王灯的手说:
“儿啊,难为你了,果儿活过来,你给口饭吃,要是去了,也给点棺材板子吧!我果儿啊,可怜的果儿……”
王灯应诺。小心地用薄毯子为果儿盖上,再用宽布带子固定,面上罩了红纱巾,看上去像是一场喜事,又像是在演一幕悲情剧,他是个活跃的滑稽演员,背景声为果儿虚弱的呻吟。
纵然果儿隆起的腹部在门板上堆得像座小山,王灯还是轻轻松松背了起来。她实在太瘦了。
“新娘子出门喽!”王灯喊。
胡晏满脸疑惑地看着他们,窦上仁还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瞎眼妈妈跟着走到土坝边上,脸上挂着泪水。
山间的路枝枝蔓蔓,王灯踩着高低不平的步子,不停地侧身转身或者下蹲躲避路边茂盛的荆棘或者横生的树枝。在与姚申打过一架的山梁子上,跟窦禄相逢,他两手空空,一脸疲惫,王灯问:
“我舅子这是去哪儿了?”
“你背着啥?”窦禄反问。
“背媳妇儿。”王灯已经和他错身而过,没有要耽搁的意思。
窦禄茫然,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持续交流,呆呆地望着骆驼一样的王灯顺着小路隐入公家的芦竹林子。红纱巾显得格外刺眼,果儿在笑吗?他不由自主地抠着自己的手背,其实应该掀开看看。她今天当新娘子,会不会挺美?他不停地想着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感到沮丧落寞,甚至抓狂。
“房里没个女人怎么行?”他喃喃道。坐在地上卷了一根旱烟,吧嗒吧嗒抽了几大口,随手抓起一块石子扔出老远,吼一句,“滚你妈的蛋,畜生。”果儿经常这样骂他。
王灯一路上都在向好奇的乡亲们解释,我背的我媳妇儿,我今天娶媳妇儿,对,是窦果儿。王百岁接了窦禄的口信,提着五斤挂面和一斤白酒,准备给窦上仁贺喜去,半路遇见王灯背着媳妇儿下山,他也折返了。既然错过了吉时,省下礼物自己消受,挺好。
苏耕、刘木匠、唐芝敏天快黑的时候赶到,看见瞎眼妈妈沉默地坐在厨屋小木凳上,灶膛没火,锅里无烟。窦禄用水瓢兑了糖水咕咚咕咚喝着,窦上仁红光满面地走到他们面前,手腕高高抬起,说:
“看看,看看,进口货。芝敏,你说说,是不是比你家草药贩子的更亮?”他说着,刻意往唐芝敏面前蹬了几步,口水滴答。
唐芝敏只好往后退了退,敷衍道:
“是呢是呢,亮。”
“你这是不是戴反了?”苏耕扒拉了一下窦上仁的手臂说。他是个汉子,声线却有点像女人,尖细,特爱骂老婆,经常一边骂一边哭。
“哼,你懂个屁。”窦上仁举起手画个大大的弧线,插进裤兜。钱在,不能给他们看到。
刘木匠出于职业习惯,自然是好奇窦家门板少了一块,看尺寸,一根二十来年的松木足够。窦上仁却以为他专心打量的是簸箕里的好东西,走过去刻意挡在他身前说:
“你们带了啥,给我就行,乡里乡亲的,不用太客气,是多是少我不都计较。果儿已经被男方家接走,你们的心意我都替她收下,等我窦禄娶媳妇,都过来多吃一顿席面。”稍稍停顿一下,他又说,“还有很多讲究的货色,潘春阳得给。”
窦禄什么也没拿到,因为潘春阳去县城进货,百货铺子没有营业。
下篇
王灯带着窦果儿出了村子,没人知道他是怎样冲破夜色到达县城的。
主刀的老医生脱下血渍斑斑的大褂,摘掉口罩,认真洗了个手,疲惫地对王灯说:
“水云村的?我知道那个大山里的村子,是咱们县最偏远最穷的地方。幸好,你们来得比阎王快了半步。”
“那她现在如何?”王灯问。
“手术很成功,住院半月,回去好好休养一段时间就没事了。”老医生显得比较轻松愉快。
“孩儿喃?是不是可以自己走路?”王灯又问。
“孩儿?”老医生一脸疑惑。
“对,孩儿,她肚子里的孩儿。”王灯的表情热烈而急切。
“你不知道她长的卵巢肿瘤?”老医生惊讶地问。
“不是孩儿?那是什么?能换钱吗?”王灯依然急切。
“肿瘤,是长在身体里要人命的坏东西。”老医生已经换上干净的白大褂,还有另一台手术在等着他。
王灯被允许隔着玻璃门看一看果儿。她静静地躺在那里,身上插着各种管子。白得晃眼睛的被单铺在她平直的娇小身体上,她紧闭着双眼,胸口不见起伏。
“她是不是死了?肚子里的东西哪儿去了?”王灯问身边穿白大褂的年轻姑娘。
“没有,她只是暂时昏迷。”年轻姑娘说。“那她肚子里的东西呢?”王灯又问。
“处理了。”
“处理是什么意思?”
“就是扔了烧了又或者冲进下水道了。”年轻姑娘将手中的本子挂在墙上,没好气地答道。
“那么一大肚子货,你说扔了?冲进下水道了?费钱费力翻山越岭地来,你们用这么一句话打发我?你陪老子睡一辈子都抵不上老子花在窦家的钱。”王灯不依不饶地跟在年轻姑娘后面,穿过长长的走廊,进了医生办公室。一个胖乎乎的中年妇女将一大叠红色单子放到桌面上,喊:
“你是窦果儿家属吧?来得正好,这些都是你的,拿去一楼交钱。”
“交钱?今天不把她肚子里的货交出来,老子炸平了这里。”王灯将桌子拍得啪啪响,指着几位医生说狠话。
这事儿源于王灯之前在几百公里外嘈杂的码头认识的那个矮个子男人,那人与一只戴秀才帽、穿着长衫的猴子形影不离,他似乎无所不知,挣钱很厉害。
王灯有意跟他套个近乎。一天,他对矮个子说:
“老乡,今晚我请你喝酒,给你讲个奇事。”
猴儿不喜欢王灯,它故意绕圈,将绳子缠在他腿上。不过它喜欢喝酒,咕咚咕咚一壶喝完,倒地酣睡去了。矮个子酒量好,花生米上了三碟,他依然清醒伶俐。王灯说家乡一位女子因为乱伦,怀胎一年半了依然没有生产。矮个子盯着王灯看了半晌,他眼神终于在又一杯酒的催化下有点儿飘忽了,他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然后压低声音说:
“你知道我这猴儿为什么有这样的神通吗?它爹——宙斯,它妈——赫拉,同胞姐弟。这是写进书里的,全世界都知道。”
“你是说她也能生个通灵的猴儿?”王灯问。
“那可不一定,个个儿都能生神猴儿,孙悟空犯得着从石头缝里蹦出来?所以啊,这种事需要缘分。”矮个子鄙夷王灯眼中那一丝欣喜的光芒。
“不生猴子生啥?”王灯又问。
“不好说。牛黄、狗宝、猪辰砂,听说过吗?名贵,稀缺。这些都需要长在活物肚子里一年以上。我看哪,你说的女子很有可能肚子里是这类货。”矮个子已经醉得有些神情恍惚了,说话大舌头。
“女人得怀多久才能生出这些东西?”王灯问。
“生不了。你,要去找大医院的大夫,操刀的那种,让他给你割出来。畜生的是杀死了就割出来,人不行,杀人犯法。”矮个子说完就趴在桌上,人事不省。
那一刻王灯眼前恍若有光,他迫不及待回到村子找窦果儿。小饭馆还有稀稀落落的客人在吃饭,猴儿睡在矮个子脚边,脸和屁股一样红。他抬脚走了几步,又折回带走了矮个子的包,猴儿作揖挣的钱,都在里面。
他深信果儿肚子里的一定不是凡物。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欺负老子不懂?她怀孕十七个月,能是什么都没有?啊,对,不止十七个月,她肚子这么大就已经十七个月。叫你们当官的来,必须给我交代清楚。”王灯怒不可遏,撸起袖子在医生办公室横冲直撞。
几个医生带着自己的病历本和诊疗工具出去了,面对这个一副公鸭嗓的男子莫名其妙的怒气,他们不屑搭理。王灯盯着穿白大褂的满楼道跑,吵吵嚷嚷没完没了,几个年轻力壮的安保工作人员追上来把他架到街边,扔了。路过的街坊说:
“哟,又一个给不起医药费的。”
王灯不依不饶地拽住人家的裤腿说:
“是他们坑我,大了十七个月的肚子,割开啥也没有?啥也不给说得过去?”
“瘤子吧?”“给你干啥?回家熬汤毒死家里的母狗?”“肚子大得像怀孕?那得是肿瘤晚期吧?”“好些个割肿瘤的手术台都没下得来。”“也不好说,我见着好些个前几年剖开肚子取掉肿瘤的,眼下活得好好儿的呢!”
他拉过一个又一个路人的裤腿,歇斯底里地喊着自己被骗,大家压根儿没听懂他冤在哪里。最后,他似乎总算明白过来,自己可能是被耍猴儿的人耍了。幸好,顺走了他的钱包,这样一想,倒也觉得平衡了不少。在还没有想得十分明白,到底要不要去拿回送到窦家的东西时,身体已经替他做了决定:离开医院,远离县城,跑掉。
窦果儿则因为欠费被扣留在医院数月之久。
这个消息传到水云村后,老村长安排窦上仁将家里所有值当的物件儿一一卖掉,包括手表和剩下的半筐糯米。村子里所有人家也都力所能及地凑了份子,百货铺老板潘春阳拿出了半个月的营业额。
就这样,在大家善意的目光中,果儿回家了,住在哥哥窦禄的屋子里。
然而,又三个月,她蜷缩在屋后的槐树下,永远地离开了。去时,她孱弱的身体怀孕了,那是一颗致命的胎芽。
一件轰轰烈烈的奇闻,至此画上一个惨惨淡淡的句号。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讳莫如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