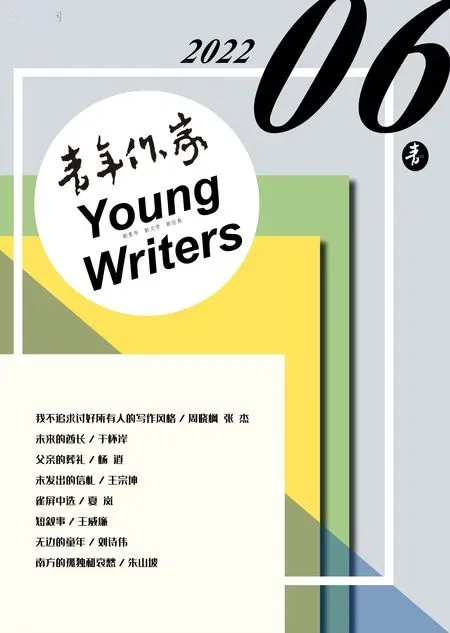活成另一个人
米布
我要讲的是名叫度府的这个人。论名字,我更喜欢同桌杨伟的名字。听着普通,细品起来,却暗含阳刚伟岸的意思。不像度府,太招眼,还惹是非。
我那时就叫度府。那是我少年时光里起床最早的一次,凌晨4点多,天完全是暗的,星光全无,是真正的黎明前的那种黑暗。我偷偷起床,摸黑赶到小学同桌杨伟家,用学猫叫的暗号把他叫起来。我们一起来到小镇的主干道东方红大街。这条熟悉的街道因为黎明前的黑暗而显得陌生。在黑暗的巨大的门框内,沉睡的街区被寂静包裹,白天喧闹的马路宽阔而空旷,仿佛整个小镇只属于我俩。空气明显比平时冷,吹在脸上的冷风让寻常的跑步有种圣洁的仪式感。我的双脚交替拍打着马路,内心有些膨胀,我能清晰地听见黑暗中的心跳,响亮而有力。我第一次有种做上小镇主人的感觉。
偶尔,还能听到夜宿街边的醉汉的鼾声,或是某种小动物突然窜动又消失的声音。
其实早起的还有做小生意的人。
经过街边的一个烤红薯炉子,杨伟神秘地扯了一下我的衣袖,示意停下。他朝四周看了看,确认没人后,用右手搭着我的肩膀,故作轻松地走到街边。他伸手揭开烤炉上的铁皮盖子,炉火立刻映红了他闪着惊喜光芒的侧脸。杨伟踮着脚,从炉肚子里取出一只烤红薯。红薯很烫,杨伟咝咝地倒吸着气,左右手替换往空中抛着刚取出的红薯。看着接连发生的一切,我忍着惊讶,在黑暗里表现出一种见惯不惊的平静。心里却在发问,杨伟这厮怎么敢这么放心大胆地偷东西。
带着疑问,那天我俩一直往北,跑到沙河边,又沿着沙河往西跑到很远的新桥。
杨伟家是回流户,就是在自然灾害时期城里没吃的,城镇居民为了活命回到农村。在过上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之后,又发现还是城里人好,能吃商品粮,能招工,后悔了,又举家回到了城里,却失去了商品粮户口。他爸在东市街的小学旁摆摊做烧饼,他妈白天在家做活,晚上在大十字街卖水鸡(青蛙)、变蛋(皮蛋)、五香花生仁。他家的收入不低,却最怕城管,在居民眼里低人一头。
但孩子和大人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对尊卑的认知并不相同。杨伟在班级里,丝毫没有回流户的卑微。
杨伟总是带着烧饼上学。烧饼放在书包里,杨伟的胸口就涌出那种特别的香味。我和他一张桌子并排坐着,无论是语文还是数学课,所有的知识也都满是烧饼的气息。我虽胃口不好,在食品上缺少饥饿感,在学习上,却有超常的吸收能力。我能用比别人更少的时间,学到比别人更多的知识。我无法忍受老师对一个简单的问题,在课堂上翻来覆去地讲,那感觉就是你已经饱了,还要往嘴里不停地塞肥肉,能把人腻死。
可惜那时还没有恢复高考,学习好不好不重要。学霸这个词还没有在生活中出现。学习好的孩子只是招个别老派的老师们喜欢,学生之间,价值体现在物资上,威望体现在拳头上。而学习成绩好,还抵不上手里拿一个烧饼有价值。
除了喜欢杨伟的名字,我还欣赏杨伟的领袖气质。他天生左腿比右腿细,也比右腿短一点,走起路来身体会左右晃动。也就是说,他是个瘸子。可是这种缺陷,并没有影响到他的霸气。那是一种内在的气质,他总是比同龄人更懂社会上的事、小学里的事和男女同学间的事。他虽然成绩不好,却能像说书人那样,大段大段讲述历史上的传奇故事,比如《说唐》《七侠五义》等等。常常是一下课,便有几个同学自动围着他,央求他来上一段。他心情好的时候,就会开讲。他比金庸更早地让我们迷上了充满传奇的江湖与武侠。一段讲完,往往是停在一个巨大的悬念上,这时就会有人把从家里偷来的两支香烟,塞进他的上衣口袋里,既有巴结的成分,也有讨要他“且听下回分解”的含意。
杨伟抽烟,不是有些同学那样仅仅把烟吸进嘴里,而是像个老烟鬼那样,把烟深深地吸进肺里,再缓缓地吐出来。除了说书和抽烟,他最帅的还是具有做大哥的能力和实力。他练过摔跤,曾把一个高出他半个头的同学摔得无法近身,最终以一个出色的过背摔让对手彻底认输。他还练过散手,都是一招制胜的狠招,他说师傅虽然教了他,却不让他用,因为这些招式出手就会伤人,非死即残。他最帅的一次,是因为班上一个女生被欺负,冲到隔壁班,把门反闩上,一对三地教育了学校名气很大的三人帮,从此一战成名。
我之前说了我叫度府,没错,这个名字注定会让人产生遐想。比较直接的如豆腐、夺夫、杜甫、湿人、食人、尸人等等。度府是河南人,似乎这又是一个标签,河南人做过农业文明的先驱,又在工业文明的后期遭受地域黑。度府出生在上世纪的物资匮乏时期,那时吃的用的,基本上都是凭票供应。有粮票、布票,肉、蛋、茶叶、白糖、好烟、名酒也是限量购买,自行车、缝纫机更是又少又贵还要托人找关系排队开条子才能买到的稀罕物。度府的老家是一个中原小镇,但又不是一般的小镇,而是全国都少有的地级镇,地委、地政府都在镇子上,所以小镇就是地区中心。一条沙河把小镇隔成南北两半。沙河由上游的易水和弱水组成。易水寒冷而清,水流呈黑色,弱水温暖而浊,水流显白色。在交汇处,便有一种奇观,就是在水面可以同时看到黑白分明冷暖交织的图案,那景象如同同时看到白天和黑夜,而这在现实中原本是不可能同时出现的。
镇子又被沙河分作河南与河北。镇政府在南边,小镇的河南又比河北繁荣些。行政管辖上这里还管理着周边的县城,而那些县的名字,有的还活跃在中国古典名著《封神演义》里。镇上还有一个光环,就是离人祖坟,也就是离女娲娘娘的墓地很近。虽然女娲只是一个神话传说,但她的坟却是一个真实巨大的土丘。逢年过节,这里又成为热闹的集市,香火混合着凡尘里的祥和欢乐。镇子不仅繁荣,还位高权重地管辖着周边的县域,以至于度府在懂事后的很长时间里,都以为镇比县大。在全国别的地方,这种认知无疑就是一个笑话。
小镇作为一个人的故乡,如同一处建构在神话里的真实之地,抽象而现实,矛盾且平和。
因为出生在困难时期,度府虽然有亲妈,却没能吃上奶。无论是人奶,还是牛奶、羊奶,一滴都没吃过。他是个真正的“没奶吃的孩子”,不知母乳为何物,更不知母汁是何滋味。奇怪的是,与其他有奶吃的小孩相比,他反而没有那个时代特有的饥饿感。这很奇怪,也很难有合理的解释。比如杨伟,就巨能吃。背着大人,杨伟有次把家里仅有的十个鸡蛋一个一个打进一个土陶大海碗里,自己生好火,自己掌勺下厨炒鸡蛋,并且一气呵成地把一海碗炒蛋吃个干净,然后还意犹未尽地把碗上沾的油也舔了一遍。他吃之前还问过度府,要不要也来几口。那是下午四五点钟的样子,我说还不到吃饭时间,我不饿。听度府这么说,杨伟像是听到一块石头落地那样,踏实地松了口气。杨伟说,吃十个鸡蛋根本就不算事,如果吃面包,他一直吃都不会饱。他说这就像他爸说的,一个人骑在自行车上,一直都不会累一样。他还说,他爸爸有一次蹲在马路边悄悄吃烧鸡,正好被他撞上。他问爸你吃的是什么呀,他爸机智地说你回头看看就知道了。就在杨伟回头之后又转身的一瞬间,他爸爸就像变魔术一样,手里的半只烧鸡就只剩下骨头了。杨伟说做大事者不拘小节,这是人生智慧。度府听杨伟讲这些,并不觉得奇怪。吃惊的是,他们父子怎么都有那么好的胃口,而且不会被腻着。
度府因为缺少饥饿感,从未对食物有太大的渴望,他吃东西像只猫一样挑,总是几口就饱了。而且,他忌嘴的东西太多,比如不吃肥肉、不吃豆腐、不吃葱、不吃菠菜、不吃韭菜、不吃胡萝卜。总之,他极不懈于把精力花在吃上,平时能吃又想吃的东西也不多。反映在度府的审美上,也有些与众不同。上小学时度府暗恋着班上的两个女同学,但都是清水挂面那一类的。一个是典型的黄毛丫头,发丝细软、皮肤白得像贫血。另一个是长着“鱼盆是我的”那种脸形的班长。度府自己都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同时暗恋着班上的两个女同学。有一次,度府以家访为名,把班长拐骗到家里,看望奶奶。等班长走后,度府问奶奶班长长得如何。奶奶说除了嘴瘪瘪的,还是怪好看的。度府很失望,觉得和奶奶在审美上有代沟。在他眼里,瘪瘪的嘴才是班长身上的亮点。
一起偷吃一只烤红薯的经历,让我和杨伟亲近了不少。
那之后,我们经常交换吃的——杨伟用他书包里的烧饼换我家的馒头,或是用他妈做的五香花生换我妈去北京看大姨带回来的大白兔奶糖。除了吃的,我们还互换过很多可以互换的东西,比如说笔盒、书包、玩具、帽子、手套、外罩、书本,还有各自肚子里秘不示人的家事、幻想等等。
交换让我单调的生活有了新奇的内容。通过交换,我身体中的另一个灵魂开始苏醒,我感受到陌生人的体温,身体也有了别人家孩子的气味,我还能体会到交换物品带给我的不同手感,这些气味、体温、手感混合起来,形成一个有趣的道具,通过这个道具,我会进入一个与现实不同次元的空间,拥有一个区别于日常的角色,在短暂的体验中做一次“别的人”,做一个互换身份的白日梦。正是这种想做另一个人的吸引力,让我在交换物品的路上越走越远。有一次,我甚至与杨伟互换了双方的鞋。当我穿着杨伟厚重、潮湿的老棉鞋回到家里,让妈妈惊得不轻。
“你穿的这是谁的鞋?”
“同学的。”我故意大大咧咧。
“哪个同学?”妈妈皱着眉追问。
“杨伟。”
“杨伟?你为什么跟他换鞋?”
“好玩。”
这个理由妈妈显然不相信,“杨伟欺负你了吗?”
“没有。”我坚定地说。
“这双鞋太丑了。”妈妈满脸厌恶。
交换给杨伟的那双皮靴是大姨夫过年时特意从北京寄来的,漂亮而昂贵,要不是过生日,我妈都不太舍得让我穿。小镇上孩子穿的皮靴很少见,故此杨伟才会看上,并提出换着穿一天。所以妈妈才觉得这种交换不可思议。
“从来没听说过换鞋穿好玩的,明天赶紧把你的皮靴换回来。”
很难向大人解释,我和杨伟之间的友谊。我只好立马答应了妈妈的要求。 但妈妈不会知道,我对于友谊的特殊认知,开始于记忆中的那只烤红薯。那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吃到偷来的东西,而且烤得半生不熟。红薯并不好吃,外软里硬,还烫嘴。整个过程,我的心一直在狂跳,担心烤红薯的主人会突然站出来,把我俩抓个现行,然后告诉我们家长、学校、派出所,然后人生被一只半生不熟的烤红薯搞砸搞臭。我甚至想到了妈妈用冰冷声调追问我:“我们家就差这半块烤红薯吗?你的人生连这半块红薯都不如吗?”但人就是这么奇怪,一旦危险过去了,反而会对冒险的经历念念不忘,甚至还会美化和放大那些并不光彩的过程和细节。
小镇的时间过得很慢,每一天都漫长得无边无际。
度府打记事起,就觉得自己的身体里住着另外一个人。那个人让度府知道,一个人的身体并不是他的全部。度府的心,常常在身体之外的某个地方,甚至是家乡之外的某个地方,一个他的身体从未到达过的地方。
度府一度认为,他眼前的一切,都不算是真正的生活。这些日复一日地上课、下课、吃饭、睡觉,只是过日子。在小镇上,爸爸、妈妈、同学、老师、百货商店、警亭、邮政所、马路、阴沟,所有的东西他都烂熟于心。这熟悉的味道,如同一只鸟笼,把度府困在里面。打开笼子的唯一方式,就是去远方。
远方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它的样子是模糊的,因为没去过。但同时,远方也是清晰的,因为远方肯定是和家乡不一样的地方。度府不清楚自己的远方是什么,在哪里。但他知道,他生下来,不是为了只在小镇上待着,做一个小镇学生,然后是小镇青年,然后是结婚生子,生老病死。他不允许自己这样像上一辈人的复印件一般苟活着。
死水一潭的小学校园里,能让度府心动的,是暗恋着的两个女生。
排在第一的是坐在他前排的黄毛丫头,叫米雪。她是外地转学过来的,说的是洋气的普通话,还会唱歌、画画和跳舞,这些都是小镇女孩身上缺少的特质。外地本就是度府心中的远方,而女孩米雪仿佛是由远方派来引领度府的特使。每天看着米雪背后那营养不良的黄色发辫,度府就很满足,如果再听见米雪说几句普通话,就会又满足又快活。
这一切并不持久。
因为喜欢米雪的,除了度府,还有杨伟。
那天正上着音乐课,杨伟就当着度府的面,用手捏了米雪的发辫。米雪肯定感受到了身后那只手,但她既没有反抗,也没有表达任何的厌恶和反感,平静得就像这事从来没有发生一样。
而我像被雷击了一样难受和震惊。
我这一生第一个喜欢的女生,被一个人当着我的面玷污了,而这个人,正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同桌杨伟。这是为什么?怎么会这样?!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这么可恶,有些事情这么无耻,有些时刻会这么无助。
此时,音乐老师正在讲台上领着全班齐唱“一条大河波浪宽”。
我大张着发不出任何声音的嘴,眼里的泪在往心里流,而我心里,不仅有眼泪,还在流血。
这件事我没对杨伟说过,也没对任何人说过。
这件事过后,我和杨伟,杨伟和米雪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
而我觉得,自己突然就长大了。
这些年,改名似乎成为一种时髦,不知是不满意自己的名字,还是想与曾经的过去做个彻底告别,很多成功人士,都干了这件事。
再见到杨伟时,杨伟已改名为杨比尔。事隔多年,他已是家乡人口中的传奇人物,是早已实现财富自由的成功投资人。
我给杨比尔递烟,他却摆手称早戒了。
杨伟的更名,让我多少有点不适。毕竟,杨伟这个名字,是我少年时期重要的回忆,也是曾让我眼馋的一个名字。
“怎么会想起改名?”在杨比尔如同一间巨型茶房的办公室里,我问道。
多年未见,这话有点无话找话说的成分,但我也确实想知道答案。
“其实也没太复杂的原因,你知道,杨伟的谐音让男人不太舒服,尤其是对一个又在做投资的男人,更别扭。既然要改,还不如改一个跟牛人有关的、好记的名字,也是取法其上嘛。”杨伟谐音上还有那一层令杨伟不悦的意思,是我从没想到过的事。被他一说破,我才意识到人生真是时时有意外、处处有隔阂。你看到的和想到的,远不是事情真相的全部。
也是风水轮流转。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大发展,城区快速扩张。杨比尔郊区的户口反而比城里更值钱。他们家先是利用宅基地扩建了一个农家乐,后又因城市扩容拆迁,得到了一大笔政府赔偿金。于是杨比尔带着分得的第一桶金到省城,看准时机低价买进了一排棚户区的老破房,因压对拆迁又赚到数百万。后来随着资产的不断增值,又不断融资抵押,进行了一轮轮滚雪球般的再投资,短短十多年工夫,就迈入了亿万富翁行列。
“别人都说我运气好,其实那都是扯淡。你还记得当年我们一起偷烤红薯的事吗?你肯定以为我特胆大,做了你从不敢想也不敢去做的事。其实你完全想错了。第一,那个烤红薯的炉子就在我们家隔壁,我听我爸说过,干烤红薯这活很辛苦,因起得太早,第一炉红薯烤上后,会回去睡个回笼觉。我们跑步那会儿,主人家正在睡回笼觉,所以安全得很。第二,那个红薯炉子是我二伯的,即便运气太差给他撞上,也是亲戚,不至于翻脸。第三,万一都不行,我兜里也预备了一只烤红薯的钱。还有,上小学时你们爱听我说书,都以为我天生能说会道,可是那只是表面。首先我酷爱听书,在别人买冰棍吃的时候,我把仅有的零花钱,都花在了听书上,我是那个时代罕见的对知识付费的小学生。其次,因为酷爱,我花在听书上的时间也比别人多得多,这让我记得住听书的内容。第三,我不只是死记内容,还要把听到的故事揉碎了、掰烂了再吸收、消化,变成自己的故事和语言。第四,我每天睡到床上,都会闭上眼进入想象的说书世界,自己给自己说上一段。我在学校说的每一段,之前起码都练习过五次以上。所以,你们看到的平常,背后都有着我的反常。像老话说的,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个‘妖’,既是我比别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也是老天赏我的那份才能。”
水开了。杨比尔往工夫茶杯里续些热茶,接着说:“你应该也听说了我投资上的一些事。其实投资买拆迁房和偷烤红薯、能说书看似不同,背后都是一个道理。在别人眼里,我赌的是运气,是胆大,说白了,还是那些人认知不够,不明白背后的因果。我也许只是比别人更早地看到人生是有风口的,而房子买对就是某个时候人一辈子最大的风口。买房也不等同于炒房。买房是你买完房子后,就完了。你什么也不用去想、什么也不用去做,更不用再卖出。你会发现,你最好的投资就是买定离手,最好的操作就是什么都不做。最安全的活动是躺着别动。在买房这件事上,往往是反人性的。勤奋的人是最悲惨的,也是最败家的。”
告别时,杨比尔对我说,现在钱对他来说只是一些数字,越来越让他感到乏味。他写了一部小说,想讲一讲过去的经历,讲一讲这个时代,也讲一讲他曾经希望的人生。他说我当年就是学霸,又在书堆里待了大半辈子,他说把小说发在我微信里了,想听听我的意见。
小说的开头是这样的:
在接触度府之前,我已经被度府控制了。
在我看来,人生的意义在于精神的价值,而物质只是形而下的东西。一切形而下的东西,都不值得努力、付出和追求,也不值得铭记和流连。比如工作,工人、职员等一切正常安稳的工作,我都视为粪土,因为他们机械、重复,没有新鲜感和创造性可言,更没有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感。而工程师、科学家,虽然高大上,但也只是在物质文明的层面上忙碌,这些具象的研究,单调、枯燥,也谈不上太快乐;而诗人、作家、音乐家、哲学家这些创造精神产品的职业,才是有光环的职业,从事这职业的人才是有价值的人。当然,像鸟一样在天空自由翱翔的飞行员的职业是个例外。
但这只是我过去的想法。
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在不知不觉中改变太多。
我仍然叫度府,还生活在出生的那个小镇上。非但没能成为像杜甫那样的大诗人,连远走他乡的愿望也落了空。
和原先相比,小镇早已升级为市,沙河上游的易水和弱水的颜色、温度也越来越相近,不像几十年前的上世纪那样,黑白相间,泾渭分明。曾经热闹的女娲坟也被同为人祖的太昊伏羲庙取代,而每年盛大的祭典却像舞台剧那样,有种程式化的空洞感。
我在高中毕业后接了母亲的班,当了市图书馆的一名图书管理员,娶妻生子,后来又读了在职本科和研究生,现在已有副高级职称。
我的胃口不知何时开始,变得越来越好。那些过去坚决不吃的东西,在漫长的生活中,一样样地开戒。我发觉每一种过去不被接受的食材,都有不可取代的诱人眼神,看着他们,我就有一种恋爱的冲动。我不断试探着我对滋味的认知,开拓着我对美食的新领地,我从一个深度精神至上者一步一步演变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地道吃货。我的美食微博渐渐积聚了上百万的粉丝,我新开的美食抖音号也观者如云。我还出版了一本研究家乡美食的书,并因此成为本市美食协会理事。
我只是不太确定,我是少年时的度府,还是少年时的杨伟,就像我有点疑惑,是现在的度府像我,还是现在的杨比尔更像我。毕竟,小学时我们交换过太多的东西,吃的、穿的、用的,还有头脑里冒出来的许多奇奇怪怪的想法。后来的我,天天在图书馆里上班,却不再想看书,现在干的也是少年时瞧不上的职业,却过得体面安稳。我曾经暗恋的两个女生,一个出了国,还有一个做了我的同事,她们都已长成了不同流派的大妈,只是还没有混入广场舞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