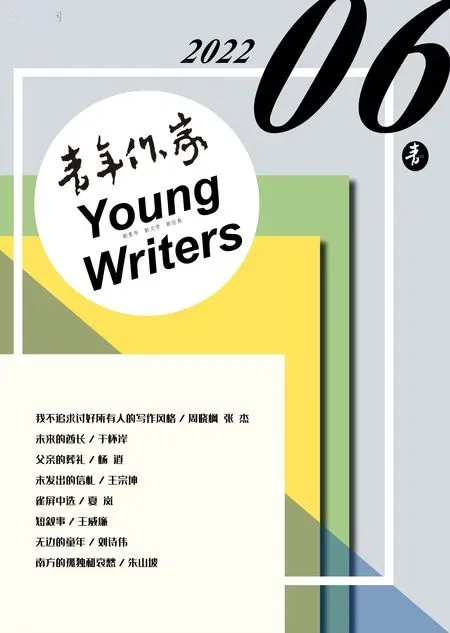未发出的信札
王宗坤
实话说,你的电话确实让我意外,你在电话里让我猜,我真没想到会是你。这几年我接触过几个年轻的女孩子,她们都是奔婚姻而来,我坚持认为以这种有明确指向方式结识的女孩子是有固定程序的,无论有着何等浪漫情怀,都逃不掉相识相熟相爱这些步骤,所谓一见钟情也应该存在某些必然因素。所以,目前在我生活中很少出现陌生女孩子的声音。做这样一番解释是希望你不要失望,按当时的情形,你猛然把电话打过来我确实有些措手不及,等到你把自己的名字说出来,我所有记忆就都复活了。我怎么会忘记你呢!黑山联中是我迈入真正人生的第一站,很多经历都是刻骨铭心的,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你和你的妈妈况建华。
站在现在的角度反观那时的我,我觉得自己当时太脆弱太矫情了。
我师范毕业那年十九岁,正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年龄,但面对自己即将从事的那份职业却没有丝毫兴奋与新鲜。之前我也做过挣扎,先是想留在城里教书没有成功,在学校谈了两年的女朋友也随着学业结束离我而去。后来就退而求其次,想去镇上的中学,为此找到了教育组长。我跟教育组长是认识的,在初中的时候我是尖子生,教育组长每次到我们学校开会都会点名表扬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次我参加数学竞赛在全县取得了较好名次,回到镇上,教育组长亲自给我颁发了奖状。记得教育组长当时把奖状交到我手上,还顺便拍了拍我的肩膀。
在家里老人的指点下,我带着两条大前门香烟和两瓶好酒找到教育组长的家,报上了自己的名字,并结结巴巴地说出了自己的诉求。教育组长用浑浊的眼球在我窘迫的脸上轮了几轮,又用目光扫了扫我带去的礼物,然后就痛快地答应了,说像我这么优秀的师范毕业生理应得到重用。我听了,心里有了些安慰。我理解的重用当然是要去镇上最好的学校。谁知,等报到证发下来我却被发配到了偏僻的黑山联中。我有些不甘心,拿着报到证来找教育组长。他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说,下一步马上要合校定点,黑山联中很快就会跟中心中学合并,现在去黑山联中也就是去中心中学。说完就闷着头摇桌子上那台黑色的老式电话,不再搭理我。看着前后判若两人的教育组长我知道自己已经别无选择了,只好拿着报到证默默地转身离开。
从以上述说就可以看出来,我是在经过接二连三打击之后,才不得不走进了黑山联中,这种失败者的心境是没有激情的,等见到了黑山联中那些栖栖惶惶的新同事,心里就更凉了,无论如何我都不想自己将来变成他们那种样子。安排课的时候,校长问我有什么专长。我说自己想教语文。校长说不缺语文教师,缺的是教英语的。我的英语程度怎么说呢?二十六个字母没有问题,再往下就难说了。上初中的时候我们那个学校也缺英语老师,一直到了初三才从外地招聘来一位,一学年就把初中的六册英语全部吐噜完了,庆幸的是,我们考中专的那年没考英语,进了师范自然也就没英语这个课程了。从这份受教履历就可以看出我当时的英语水平,但那时我年轻自负也很虚荣,没有把自己真实的英语水平说出来。校长执意让我教英语,并说当时学校跟教育组打的报告就是要英语教师,谁都知道师范毕业生是全才,到了工作岗位都能绕着八仙桌子转上一圈,是我们这些土八路不能比的。直到校长说自己是土八路我才知道他也是民办教师,在这所联办中学里,连校长都不是正式教师,全校的教学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我的心在下沉,潜藏在心底的想法越来越强烈,我一定要离开这里!既然这样我还争什么,让教什么就教什么呗。
住宿条件比我想象的要差很多,房间内的墙壁已分不清什么颜色;地面是普通的泥土地,到处坑坑洼洼的,像拔光了树木的河滩。一个用砖头支起来的三抽屉桌,外加一张大木床就是全部家当。木床是最简单的那种,四根锯开的木条撑起云梯般狭长的骨架,由于地面不平,床腿下面同样垫着不规则的砖块,床身那原本白色的木茬子发出一种被时光淘旧了的暗绿色,木床上面铺着一张破破烂烂的苇席,苇席下面有几块黑乎乎的东西揉在一起,仔细一看原来是女人例假期间用过的卫生纸,内心不禁一阵恶心。刚才给我安排宿舍的时候,校长说这个房间之前由一位叫李兰的女老师住着,校长还说女同志总比男同志在行一些,房间不用很打扫就行,没想到这位李兰老师就是这样在行的。
更让人难以忍耐的是,房间里遍布着一阵阵恶臭,我找遍整个房间的角角落落也没寻到源头,后来才发现这恶臭是从离门口不远处的鸡窝传出来的。我的房间在最东边,鸡窝借东墙而建,正对着我敞开的房门。我把房门虚掩了一下,那股污浊之气果然就弱化了不少。虽然立了秋,但天气依然是热,我总不能天天关着门窗吧。一开始我断定鸡窝是你们家的,因为它离你们的房间也很近,就想找合适的机会跟你妈妈说一下,我已经见过况老师了,第一印象她是个很豪爽的女人,长相也很周正,在这群土得掉渣的乡村教师中还是很显特别的。校长也专门说到了她,话题是由邻居这个字眼引出来的,校长说况老师单身带一位十多岁的孩子,就住在你西边,你们是邻居了,下一步要互相照应。校长说这话的时候笑了笑,我不知道很平常的一句话校长为什么会笑,而且笑得还有些暧昧。
下午的时候我看那位干瘦的于大娘颠着小脚去鸡窝摸鸡蛋,才知道鸡窝是她们家的。我心里更加气愤了,之前的李兰老师怎么会容忍这样一个污浊的东西存在?想必她也一定是个懒惰邋遢的女人。我返身到办公室找校长,校长听了我的陈述笑了,一迭声地说一个鸡窝……一个鸡窝,居家过日子还能没有个鸡窝?校长的话让我吃惊,没想到校长会这么搪塞我。我失望地从办公室回来,见于大娘揣着手正站在她家房门口,刚见面的时候她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不错的,笑眯眯的,挺和善的一位老人,可现在这种感觉荡然无存了。
“下课了,李老师。”她是想跟我随便打个招呼,我听着却非常刺耳,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我初来乍到怎么会有课可上?我想黑着脸不回应,她脸上那硬挤出来的笑纹让我产生了更大反感。
“你们怎么能把鸡窝建在别人的家门口?”我口气很硬地说,“难道就没有其他地方了?”
于大娘脸上的笑容僵住了,那堆积起来的皱纹如重叠的云层一样滞留在了空中。稍后,云开雾散,她叹了口气,说,“搬,我们这就搬。”
第二天早上,我去办公室早了一些,第一次跟学生见面总得有所准备吧。现在忘了当时的心境,应该还是有些激动的,毕竟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很大逆转,由在讲台下听课的学生变成了站在讲台上的教师。当然,脑海中不缺乏跟学生初次见面的方式,十多年的读书生涯已经留下了太多范本,尽管这些范本的创立者并没有几个留在我心中。过了一会儿,况老师来了,我们的办公桌错对着。况老师看了我一眼,笑了笑说:“李老师,早啊!”我回应了一下就埋头在书本里了,书本是英语课本的教学参考书,它交给你怎么讲授英语。我感觉况老师昂着头一直朝向我,似乎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我抬头装作无意识地朝她瞭了一眼。她开口了,说:“李老师,于大娘一家最近刚遭遇了不幸,唯一的女儿刚嫁出去不久就喝农药自杀了,她现在还经常去后面的黑山子上痛哭,以后对她说话能不能客气一点儿?”这话分明与那个臭不可闻的鸡窝有关,我那时还体会不到况老师那种善意的提醒,感受到的只是不友好的指责,内心也就升起了一股不平之气,鸡窝堵在人家门口本来就不对,而且也与她没关系,她凭什么操这份闲心?况且还以这种教训人的口气。幸亏当时我是初来乍到,还知道收敛一些,才忍下了这口气。
鸡窝是在一周之后拆除的,在这一周里我黑着脸几乎不跟两个邻居说话。那个下午,看着于大爷和于大娘两位老态龙钟的老人在费劲地搬砖,忽然又有些不忍,想上前帮忙又拉不下脸来,心里就祈盼着有人能够尽快出手。到鸡窝拆除得快接近尾声的时候况老师下课了,她走出教室,连教材都没往办公室放,就赶紧过来了。来到近前,一边捡拾于大爷拆下来的砖头一边说:“这鸡窝这么多年了,砖都粉得不成样子了,也该换换新鲜了。”我听了这话,心里的内疚减缓了不少,对况老师也有了一些好感。鸡窝最后被改建在了校园最南头,于大娘要再去鸡窝摸鸡蛋就要走得远一些。
这一周我对校园环境也逐渐熟悉起来,班里四十多个学生的名字也已经记得差不多了。当然也注意到了你,黑黑瘦瘦的一个小女孩,整天一副很害羞的样子,见到我老是躲得远远的。此时,我已经对你和你妈妈的情况也有了一些更多了解,知道你父亲早就离你妈妈而去了;知道况老师跟教育组长有扯不清的关系。这些信息基本上跟我印象中的况老师是相吻合的,在我们办公室,况老师是唯一的女性,可没人把她当成一个真正的女人。乡村教师是乡村文化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乎男女之事的,男教师们发布这些荤故事时一般都会无所顾忌,甚至越是当着况老师的面渲染得越过分,久而久之,况老师不但变得百毒不侵,反击起来还能做到游刃有余、左右逢源。跟我对桌的仇老师有次就撞在了枪口上,仇老师的笑话很简单,说一个老头儿为儿媳妇看孩子,孙子老是不听话,后来儿媳妇回来了要给孙子吃奶,孙子不肯就范,老头儿就哄孙子说,孩子快吃,你再不吃我就吃了。这个笑话本身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仇老师故意把那位儿媳妇的姓氏改为了比较少见的况,这下老师们笑得就很有指向性了,都咧着嘴巴撇着眼珠子朝向况老师,况老师也笑,一开始是朝着大家无目的地笑,后来是看着仇老师笑,笑着笑着却猛然刹住了,满脸郑重其事地走上前来,撩起自己的衣襟对正一脸得意的仇老师说:“正巧我也想奶孩子了。来,孩子,吃奶。”说着就开始往上掀身上那紧绷绷的白色胸衣,办公室的所有人都愣住了,没想到况老师会以这种方式回击。仇老师更是吃惊,一开始还以为况老师只是做做样子,看况老师已露出一截白白的肚皮立刻慌了,赶紧起身躲避,在众人的哄笑声中,况老师敞着胸脯袒露着半截奶子在后面追,仇老师逃得慌不择路,在教室里转了几圈,最后逃到了墙角。仇老师见没了退路,也就只好向况老师缴械投了降,承认那位儿媳妇不姓况而姓章(事后我得知仇老师的妻子姓章)。
这样的场景让我目瞪口呆,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况老师会这么泼辣。之后,我又听到了况老师的很多故事,都是与性和男女之间的隐私有关。譬如说有次镇上一位分管教育的副镇长来学校视察,中午酒喝多了,去方便的时候没看清标记去了女厕所,巧合的是,况老师此时正蹲在里面如厕。镇长进来找了个边角的位置就开始拉裤子拉链,况老师这时徐徐站了起来,问镇长这是男厕所还是女厕所?镇长猛然看到里面蹲着个女的吓了一跳,又见厕所里没有尿池立马就明白了,一边把拉链往回拉,一边仓皇地往外逃。见把镇长吓成这样,况老师反而不好意思了,在后面追着镇长的屁股说,镇长,你不用这么慌,咱们这个年纪无所谓了,你就凑合着解决了吧。还有个故事是说况老师有次去赶集,从口袋里往外掏钱的时候,把月经带附带着扯了出来却浑然不觉,以致让那红色的月经带挂在口袋外面飘扬了整个集市,况老师的小红旗也就成了人们的又一笑谈。
这些故事是我的新同事们作为笑话讲给我听的,自然也有了些再创造的成分。事后,我想假如况老师不是学校里目前唯一的女性,这些笑话的传播恐怕也就没有这么畅通无阻了,一个女人在男人窝里生存总是会被格外关注,这种关注有多种形式,创作出很多被人津津乐道的笑柄自然是其中之一,作为当事人的况老师如果对这些笑柄一味排斥显然不利于自己;而一味迎合似乎也显得低贱了些,其中的分寸很难拿捏,况老师以这种自嘲方式来处理显然是最为明智的。我发现男老师们只是跟况老师玩玩嘴上的功夫,没有真正的非分之想,应该是况老师没有为苍蝇们留出可叮咬的缝隙来。
我来黑山联中不久,况老师就问我是否有女朋友了,当时我犹豫了一下选择了肯定。之所以犹豫是因为虽然跟女朋友在毕业时候分手了,但我总感觉我们之间不会就这样完结,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虚荣,都知道师范毕业生分回农村是不好找女朋友的,因为当时在农村吃国库粮的女孩子太少了,再加上那年头教师这个职业颇不吃香,这就更增加了难度。我当时是自命不凡的,不肯让自己落入这样的俗套,就硬说自己有女朋友了,说完当然也感到了心虚,就说自己的女朋友分到了城里,她们家的人不愿意让她找一位乡村教师,为此我们正在积极努力。应该说对这个回答我还是动过一番脑筋的,既挣足了面子,也为自己留足了后路,同时还表述出了自己的梦想,这梦想就是,希望她能真像我说的那样冲破家庭的阻力,不顾世俗观念,勇敢地回到我身边。
大概爱人之间的心灵有时真是相通的,在秋天的假期里,她果然来找我了。那天我回家了,早上刚起床,况老师班里的一位学生就骑着车子来我家找我,说是一个女孩子正在学校等着我,我当时有点懵,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这又怎么假得了呢?待真正见到她我反而平静了很多。本来我是打算先去找她的,没想到她居然先来了,要知道我分配的时候只是领到了去郊区教育局的报到证,她并不知道我具体来到哪所学校,她要找到我,得先去郊区教育局政工科,然后再找镇教育组打听。当然其他的途径也是有的,遗憾的是,我来到黑山联中就把自己封闭起来,我想彻底与过去告别,让一切重新开始。这也就是我迟迟没有去寻找她的原因所在。那段日子,我每天几乎都在跟自己这个脆弱的决心做着斗争,所以应该没有任何同学知道我现在工作的这所学校。
女朋友的意外降临给我传递了一个错误信号,我以为我们之间又可以重新开始了,很快我就发现我错了。在这之前,我们已经有过肌肤之亲了。我们原本应该更为保守一些,从第一次单独接触到初吻历经了大概一年的时间,有了初吻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明朗了,但未来依然很模糊,没有关于婚姻的梦想,有的只是爱情的指向,基于这种认识,她一直没让我突破最后的那道关口。分配方案公布了,她留在了城里,这一夜我们约定分手却谁也不肯离去,在远离学校的一个小河边我们厮守了好久,到了后半夜,我们来到了附近一家小旅馆,说好不要的,但最后我还是进入了,是那种浅尝辄止的尝试,却也感到了天旋地转,瞬间就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她感到了疼痛,我们都懵懵懂懂的,以为这样的蜻蜓点水不会有什么大碍,她还是完整的,有足够的信心和资本面对将来的另一个他。没有准备卫生纸,她临时就急,随手用枕巾擦了一下,黑暗中,那原本以白色为底色的枕巾有了一片黑色的晕染,她默默地流泪了。我把她揽进怀中安慰着,这时她仍然残存着一丝希望,抬手捋了一把眼泪说:“但愿是来例假了。”
她跟着我走进位于你们东边的房间,外面的世界随之消失在身后。那间破破烂烂的宿舍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这个世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她扑进我怀里,我默默抚摸着她柔软的秀发,然后嘴唇往下找寻着,我很快就感到了那灼热的湿润,我终于又再次拥有了她,上次那痛彻的感觉似乎已远离了一个世纪,这么长久的渴望是足以让我们疯癫的。我浑身的血液暴涨着,猛烈地把她掀翻在床上。应该是弄出了很大的动静,当时只沉浸在彼此的激情里浑然不觉,事后我才发现本来垫在床腿下的砖头都偏离了原有的位置。
平息下来之后,我希望我们能进行一次有针对性的交流,但她似乎什么也不想说,只是默默地流泪。我有些明白了,她这次费尽周折来找我并没有带来什么承诺,那泪水又是什么呢?应该是既有相见的喜悦又带着离别的酸楚,既然这样,至少我的内心应该明朗起来,我们之间跟过去的很多次纠结一样,还是没有结果的。那我还能说什么呢?让她去找寻属于她的幸福,她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爱她就得让她快乐……类似这样冠冕堂皇的话语正是送人情的大好时机,是展现自己男子汉风度的大好时机,而此时此刻,我却什么也不想说。我此时的幸福绝对与她有关,她的幸福里如果没有我,我绝对是不会幸福的。
下午的时候她走了,我没有出去送。我们没有吵架却彼此明白这比吵架的结果更恶劣,这种最后的结局是没有必要拿出来展示的,我想让两个人的行为恢复到一种最自然的状态。她走她的阳光道我睡我的破烂床,心跟心之间是有距离的;男女是有距离的;乡村和城市是有距离的。既然有这么多的距离,我们还有必要强捏着走在一起吗?我不是在为自己辩解,这种行为应该不关乎人情冷暖,只关乎自己的感觉,为了世故人情或者看起来体面,委屈自己是当时的我所不能接受的。
她消失了,至少是从我的眼前,房间里还残留着我们做爱时的热烈气息,应该告别了,跟她、跟自己的过去,那就把这最后的留恋当做拜祭离别圣坛的贡品吧!我几乎睁着眼睛躺了一夜。
难熬的一夜终于结束了,透亮的阳光如约而至。我从床上爬起来,推开房门,太阳还没有升高,房屋、树木、腐朽的篮球架……一切都拖着一条长长的影子,校园里到处都留有发人深思的阴凉角落。门下有张纸条,我有些意外,俯身捡起来展开,只见上面写着:该来的总会来,不要为失去的而悲伤。一开始我以为是况老师留下的,再看这稚拙的字体就否定了,况老师的字我是见过的,很饱满也很苍劲,几乎不带女性特征。会是谁呢?遗憾的是,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你,因为你在我眼里只是个小孩子,尽管我没有看到过你在况老师怀里撒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是一个学生的口气,一个成熟的成年人是不会这么坚定的,他不会坚定地认为该来的必定会来,现实中有很多东西该来却没有来;很多东西不该走却走了,就如我跟她的爱情,我们相爱却不能在一起,这怎能让人不悲伤?我当时猜这有可能是八年级那位姓裴的女生写的,她家就是这个村的,我不是他们班任课老师,她却总用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来找我讨教。
太阳升高了,金色的光芒驱赶了东方的曙光。校园空荡荡的,于大娘一家的房门紧紧闭着,正是农忙季节,于大娘老两口这几天一直在帮儿子们忙秋。隔壁你们家的门也上着锁,况老师应该是带着你继续去学校旁边的那块菜地摘豆荚了。我在校园里转了好多圈,我已想不到还有比这更值得去做的事情了。教室后面是简陋的操场,操场是用土硬垫出来的,比周围要高好几个台阶,我站在上面可以远眺那条通往城市的道路,这是黑山水库的一道长堤,水面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粼粼波光,那长堤被这波光所缠绕,也幻化出无数个彩色的斑点。她就是沿着这条多彩的道路离我而去的。这个事实在脑海中再次炸响,我窒息般把眼睛紧闭起来,想竭力从那强烈的感觉中剥离出来。
跑出校园才感到我几乎无处可逃,在这陌生的村庄里我只有我自己。我已走上了那长堤,右面就是波光浩渺的水面,夏天的时候我经常过来游泳,有时是在晚上,有时是在学生们都上课的时候。现在我站在这一泓平静的秋水前,心里却鼓胀着一股莫名的情绪,跳下去会怎样?既然不知道那就跳吧!因为我本身就是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牵引着走到今天的,所有莫名的东西混搅在一起也许就能找到明确出路了。我纵身跳了进去,瞬间就感到了阵阵沁凉,这种沁凉让我复苏了许多,很快就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惬意。我睁开眼睛,眼前是一片淡黄色的模糊。为什么这水下的世界依然这么混沌!忽然身后响起炸雷般的声音,我把脑袋从水里浮出来,刚一冒头立刻就感到了一股凌厉的风,随即就有一记老拳飞了过来。
我昏昏沉沉地被况老师拖上岸,况老师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年纪轻轻的干嘛这么想不开!”她竟然以为我在自杀,怪不得先要把我打懵,落水的人遇到施救对象的时候很容易胡乱抓挠以致拖累对方,所以挥拳把落水者打懵是施救的第一步。我该怎么解释呢?说只想下水找一条出路,那不跟自杀一样吗?说想游泳了,那也不能穿着衣裳直接就跳入水中!更何况现在是秋天,水开始变凉也不适宜游泳了。但辩解还是要的,我说我没有什么想不开的。况老师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那目光中没有同情,而是有一种让人酸楚的哀怨。
回学校的时候,况老师默默走在前面,湿透的衣服紧贴着她那有些变形的身体,屁股的轮廓愈加浑圆,连接大腿的地方出现的折痕有了明显的缓冲,再往下就是两排渐进式的湿脚印。我回到自己房间刚开始换衣服况老师就进来了,浑身上下依然湿淋淋的,手里还拿着一床厚厚的毛毯,说天凉了让我先用这个取取暖。其时我正把粘湿的衬衣扒下来光着肌肉饱满的上身。况老师朝我看了一下,我有些不好意思了,赶紧接过毛毯披在身上。况老师似乎没有在意,摇着手说:“不要这样披,要把湿衣服全脱下来盖在床上才能暖过来。”我一边躲闪着她伸过来的手掌,一边一迭声地说:“我知道,我知道……”我这种仓皇的状态显然提醒了她,她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神情中流露出难得的羞涩,又叮嘱了几句,接着就转身离开了。
我很快暖过来了,换上干净衣服去给况老师送毛毯。房门虚掩着,我敲了几下才听到低低的回应,推门进屋发现房间里没人,电视机前的小凳子上摞着况老师刚才穿着的湿衣服,最上面是一条红色的内裤,抻着肢体窝在湿重的黑色长裤上就像正在开裂的伤口。我正在迟疑,听得靠窗的布帘子后面有窸窸窣窣的声音传来,知道况老师可能在换衣服,就想放下毛毯离开,还没转身,帘子后面突然传来一阵呻吟声,声音突兀而凄凉,似乎怀有极大的痛苦。我吃了一惊,往帘子前移了几步,犹豫着想拉开帘子,但最终又把手缩了回来,急遽地问:“况老师,你怎么了?”呻吟声停止了,我放松下来想接着抽身离开,那呻吟声再次响了起来,而且比上次更加凄凉,我不再犹豫,猛然掀开帘子走了进去。
里面的空间极为逼仄,靠东墙的地方竖着一个大樟木箱子,箱子上摞着不少杂物;西边是一张大大的木床,木床上正斜躺着一个一丝不挂的女人。我怎么也不能把这个女人跟我脑海中的况老师相联系,两只光光的脚板肆无忌惮地伸展开来,往上是饱满的小腿肚,浑圆的大腿以及微微隆起的小腹,小腹之下是黑色的毛发,两只乳房随着身体侧卧着,像两只沉静的大白兔带着随时跃出的凌厉。皮肤不是那种雕塑般的洁白,而是略带着一种淡淡的灰黄,是一种错落有致的纯色。那目光没有任何的病态,眉毛往上斜挑着,带有一种轻微的嘲讽与傲慢。如果不是有明确的指向,很难把眼前的裸体女人跟况老师联系在一起。我一直认为她老了,至少已是半老徐娘,可眼前呈现的却是一种风光无限的景致,她的身体充满着热情,还有一种历尽沧桑之后的曼妙。
不知为什么,那一瞬间我有些麻木,也没有想逃走的欲望,似乎这是脑海中早就有所预设的场景。她笃定地看着我,把披散下来的头发往上捋了一下,嘴角往下撇了撇,低声说:“我比你女朋友怎样?”
我想抽身而退,却动弹不得,内心连续涌动着,脑海中不停地浮现出况老师的形象,一会儿是她以探寻的口吻说:“以后说话能不能客气一点儿?”一会儿是她袒露着半截雪白的奶子往墙角里追仇老师。这些画面竖立在眼前,混淆成一个令人恐惧的场面,这种恐惧一定流露在了我的脸上,但她却似乎没有在意,仍然重复地问我:“我比你女朋友怎样?嗯?”说着她变化了一下姿势,把斜躺着的身子往上扬了起来,两个白腻的乳房也随之左右摇摆着。
“她快没有了。”我突然盯着她的乳房恶狠狠地说。
“她快没有了是什么意思?”她问。
“这里。”我指了指她的胸部,“她的乳房快没有了。”
“怎么回事?她这么年轻!”
“乳腺癌。晚期。”这是我知道的女性所能得的最严重的病症。
“啊!”她似乎被吓着了,“这怎么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的!病魔有时候就像人的命运,是不长眼睛的。这次她就是来向我作最后告别的,医生说她只有半年的时间了。”我坚定地说。
她遽然坐了起来,散落在身前的头发往后垂落着,眼泪渐渐从她眼窝深处溢了出来,我的心里滑过一丝快意。但我们仍然这样僵持着,不知道怎么来安放自己。
门口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她昂起头认真听了一下,然后对我做了一个闭嘴的手势。是于大娘回来了,于大娘在门外喊了好几声老况。门是虚掩着的,这就给了于大娘某种确证,应该是你在菜地里摘豆荚累了,恰巧看到了要回学校的于大娘,顺便让于大娘来给况老师送信。
于大娘在门外继续喊道:“老况,你不是回来给晓彤带水了吗?晓彤在菜地里可渴得受不了了。”
况老师这才警觉起来,一边答应着,一边开始起身找衣服。
我继续有些茫然地站着,知道这时候出去会正巧碰到于大娘,快嘴的于大娘是藏不住事情的,我可不愿意用她的舌尖制造出我跟况老师的故事来。而况老师此时却表现出一副无暇顾及我的态度,自顾自地穿着自己的衣服,仿佛这个房间里从来也没有出现过第二个人。穿戴完了拿出挂在墙上的水壶,倒满了开水就走了,我呆呆地站着,意识到房间里的门没有锁,这正是她留给我的机会。
那天我很快逃离了你们的房间也很快逃离了学校,有些伤口需要医者来治疗,有些伤口却需要独自舔舐,我想要忘记一切;我想要一切重新开始,哪怕就这样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教师,我的愿望已变得如此微小,而沉重的现实却不能给它生存的空间。
秋假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是你所不知道的,镇教育组安排检查教师们的备课情况,由组长亲自带队,当时上面的教育部门正在大力推广布鲁姆目标教学法,发下的备课本都是表格式的,此时距离我任教才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备课本也就用了十来页,而其他老师的备课本都是厚厚的一大摞,这些都是他们多年积攒起来的,我的备课本跟他们的放在一起就显得太简单了。原本以为教育组长应该清楚我刚任教不久,遗憾的是,那天中午他喝了很多的酒,一看到我那单薄的备课本就指着鼻子开始指责我,如果单纯地指责我也就忍下了,酒精把他那低劣的人性暴露出来,说着说着他居然对我开骂了,而且骂得还极为难听。我再也忍不了了,一股无名火从心底冒出来,岔开手指猛地给了他一巴掌。这就是我后来被再次发配到空杏寺小学的诱因,至于来调查我跟况老师的男女关系那不过是借口而已,那个时候对男女关系已经有了足够的宽容,只要两个人你情我愿外人是不会过分干涉的。
还是说说那个雨夜的事情吧。那个雨夜你看到了什么?是一对男女在床上苟合吗?我现在告诉你,事情不是那样的,至少不仅仅是你看到的那样。那天晚上你过来说况老师去了城里,到现在还没回来,整个学校只有我们三户人家,于大爷年龄大了,我只好别无选择地去接况老师。
我冒雨出来,当时雨下得很大,是秋天里少见的大雨。黑暗中我看不清那细密的雨线,只感到它如急促鼓点般敲打着身上的雨衣,眼前的视线一片模糊,手电筒的微弱光芒被不断飞溅起来的雾气所遮蔽。我沿着长堤一路往前,走到尽头也没有发现况老师,再往前就是一马平川的柏油路,沿着这条道路就能一直走到城里。况老师在这么宽阔的道路上不可能遇到什么阻碍;家有独自在家的女儿,她也不可能不回来。这两个原因让我决定回头再重新找寻。这次我比来的时候看得更加仔细,差不多走到长堤中心的时候,我在堤坝沿上发现了一个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自行车斜躺着,一只轮子搭在坝沿的矮石墙上,另一只轮子淹没在了堤坝边沿之下。这是况老师的车子,我拎着手电伸头往下,模糊的光柱下,我朦朦胧胧地看到况老师正在下面挣扎着往上爬。况老师看到了光亮,猛地就把头昂了起来,白亮亮的雨点利剑般射下去,那张半明半暗的脸顿时变得更加浑浊。可能是没有了力气,或者是堤坝上的石板太滑,况老师的身子虽然努力着往上攀附,但却一直在往下沉,眼看都要沉到堤坝底部了。幸亏况老师车子后座上留有预备带东西的绳索,我把绳索解下来伸到下面,况老师攀着绳索才慢慢地爬上来。
回到宿舍,况老师给我送来一身新的秋衣,跟上次送毛毯不同,这次她没有接着离去。实际上,刚才我就发现了况老师情绪上的异样,她的神情有着不同于一般的悲怆。她从大坝上来,一句话都没有对我说,包括最基本的谢谢,一开始我以为她是身体受了创伤,还想着要搀她回去,但看她推自行车的样子又不像。她把衣服放在我的床上仍然没有说话,只是把湿湿的头发往上甩了甩,眼睛似乎朝我瞭了一眼又赶紧躲开。这种躲闪不是羞怯,而是对某种状态的回避,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似乎历经了什么样的大难,滑下水库堤坝应该不会使她有如此悲伤的情绪。我很快就发现了她眼中的泪水,这种压抑着的悲痛更加让人哀怜。我问怎么了?她吸了一下鼻子说:“你上次的故事是假的吧?”
我问:“哪个故事?”
她说:“就是你女朋友患乳腺癌那个。人生哪里会有这么多生死离别!?”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无言以对。
她接着说:“彤彤爸爸马上就要走了,是肝癌晚期。”
我惊呆了,没有想到在她的身后居然藏着这样让人意想不到的故事,但我又能干什么呢!我那时候太年轻,还没体会过生死离别,尤其是身边的亲人。
她哭着说:“我爱过这男人,也恨过他。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已经不爱他了,原本以为他只是我女儿的父亲,这也是我们仅有的纽带,没想到,现在知道他要走了,我心里还是很难受。”说着,她脱下了上衣,撩起乳房,指着下面那一排类似牙痕的伤疤说:“这就是他留给我的,我去城里找他完全是为了彤彤,他答应给彤彤安排工作的,这话我信了,毕竟他是彤彤爸爸……”
她就这样站着诉说着。过了一会儿她停住了,房间里出现了可怕的静寂。“我冷。”她说着抱起了肩膀,我上前搂住了她,我们随即仰卧在床上,她乖乖地倚在我胸膛上,两个裸露的乳房挤压过来。奇怪的是,此时我身体里没有任何欲望,怀里这个温软滑腻的躯体似乎不是来自另一个性别,而是我羽翼下一只小小的雏鸡,我需要的就是把自己的翅膀伸张得更加宽阔与厚重。
你就是在这时进来的,以一个正常的目光来看,对于一对在床上裸着的男女自然不会产生其他的想象,但我们却是例外,因为当时我们的内心确实非常单纯。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你妈妈,按理说我们是有机会见面的,我们的教学单位都属于一个乡镇管理,尽管空杏寺小学偏僻一些,但还是有对外交流的,起码每年的两次统考是要跟外校轮番检考和阅卷的。但我们恰恰就没有照过面,这样也好,这就为我们预留出了更大的空间,我想这个空间里也应该包含着思念吧,而这种思念又很难用普通的男女之情来界定。
你问我后来的生活?怎么说呢!这么多年我跌跌撞撞地走过来,有起伏有波折也有收获,说起来真是一言难尽。有时候你觉得自己走对了,但过后很可能就会否定自己,也许这就是生活,有对也有错,有失也有得。我常常会忆起在黑山联中的那段日子,想到与况老师那次意外的温柔相拥,每次心里都会感到暖融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