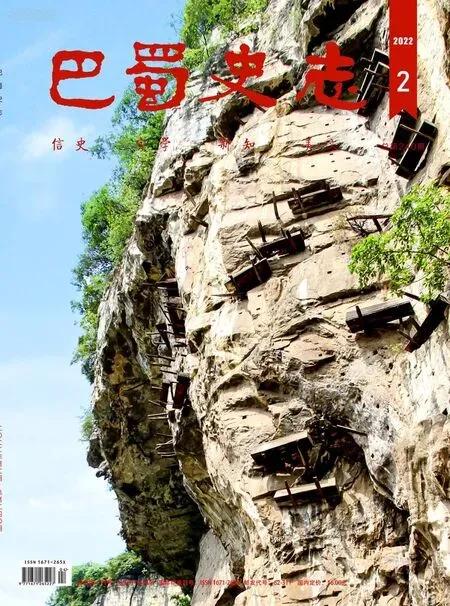民国初年成都的近代化转型进程
——以《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为中心的考察
杨向飞
(作者单位: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所谓近代化,从西方的概念来说,以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为主要标志。近代化是综合性的概念,包含各个方面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以及各种近代新兴事物的出现。清末民初,是四川近代化转型的肇始时期,在这一时期,东亚同文书院组织学生对四川进行多次详细考察,并形成一大批考察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保留了大量清末、民国时期珍贵历史资料。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编译《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内页
一、东亚同文书院与其“大旅行”概述
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头号强国。而与此同时,清王朝正处于国势衰微、内忧外患的困境中。日本方面看到中国的落后,开始起觊觎之心。因此,从19 世纪70 年代开始,日本开始公开或秘密地派出大量情报人员,对中国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并形成一批考察成果。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而与此同时,中日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战争原因而破裂,反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军事方面都展开了广泛的合作,“日清战争后到日俄战争之间的年份,是无比的日、中两国的亲和时代”①(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页。。而且两国几乎同时兴起一股研究对方的热潮,东亚同文书院就是在这种所谓“亲和”背景条件下的产物。
东亚同文书院由东亚同文会主持创立。1900 年5 月,南京同文书院正式成立。同年8月,受义和团运动影响,书院迁至上海。1901年8 月,改称上海东亚同文书院。1939 年,东亚同文书院由专科学校升格为大学,更名为“东亚同文书院大学”。1945 年,日本投降,东亚同文书院大学随之关闭。东亚同文书院一共存在40 多年,在中国有较大的影响力,很多著名人物如孙中山、鲁迅、康有为、梁启超等,都与该校关系密切。
“大旅行”是东亚同文书院的一项传统活动,从建校起一直到学校关闭,该项活动贯穿始终,参与者多达5000 余人,考察线路700 余条,基本走遍中国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这些学生考察期间,都撰写考察日志;考察结束后,向校方提交考察报告。校方对学生的报告加以整理,并对相关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形成《中国经济全书》《中国省别全志》《新修中国省别全志》等书籍。
二、《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视野下的成都近代化进程
成都作为四川省会,是“大旅行”考察队在四川的重点考察对象。在对四川的18 次考察活动中②18次考察活动分别是:(一)1908 年,第六期“长江班”(调查日志收入《禹域鸿爪》)。(二)1909 年,第七期“西鄂巴蜀班”(调查日志收入《一日一信》)。(三)1910 年,第八期“云南四川班”(调查日志收入《旅行纪念志》)。(四)1911年,第九期“湖南四川班”和“四川班”(调查日志收入《孤帆双蹄》)。(五)1913 年,第十一期“甘肃四川班”和“秦蜀班”(调查日志收入《沐雨栉风》)。(六)1914 年,第十二期“云南四川班”(调查日志收入《同舟渡江》。(七)1916 年,第十四期“湖北四川班”(调查日志收入《风餐露宿》)。(八)1920 年,第十八期“云南矿业班”(调查日志收入《粤射陇游》)。(九)1921年,第十九期“四川省盐业调查班”(调查日志收入《虎穴龙颔》)。(十)1921年,第十九期“资江、北江经济调查班”(调查日志收入《虎穴龙颔》)。(十一)1922 年,第二十期“秦蜀产业调查班”(调查日志收入《金声玉振》)。(十二)1923 年,第二十一期“云南贵州班”(调查日志收入《彩云光霞》)。(十三)1923 年,第二十一期“贵州四川班”(调查日志收入《彩云光霞》)。(十四)1925年,第二十二期“滇蜀经济调查班”(调查日志收入《乘云骑月》)。(十五)1926 年,第二十三期“滇蜀经济调查班”(调查日志收入《黄尘行》)。(十六)1926 年,第二十三期“蜀秦政治经济调查班”(调查日志收入《黄尘行》)。(十七)1929 年,第二十六期(调查日志收入《足迹》)。(十八)1930 年,第二十七期“岷江、涪江流域调查班”(调查日志收入《东南西北》)。,很多次都到过成都。在他们笔下,记载了大量关于清末民国时期成都的第一手资料,从中可以一窥成都近代化初期曲折、缓慢的进程。
(一)新式工业的艰难发展。工业是近代化的基础和第一推动力。成都的近代工业,最早可以追溯到丁宝桢于清光绪三年(1877)创办的四川机器局,在全国也是创办较早、规模较大的近代工业企业。到清末民初,虽然经过30 余年发展,但受环境闭塞、经济落后等因素制约,成都并没有形成完善的工业体系,不仅与沿海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甚至也远远落后于重庆。比如,1895—1927 年间,成都新增工厂数仅相当于上海的3.3%;新增资本只有上海的1%,重庆的50%。1890—1919年间,四川全省兴办的民营工矿企业共计115 家,其中,重庆有52家,占总数的45%;而成都仅有7家,占总数的6%①隗瀛涛:《重庆城市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69页。。因此,时人说成都工业“尚在幼稚时代”②(清)傅崇矩:《成都通览》,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年,第38页。。
在《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中,记载了成都的7个具有代表性的工业企业,分别是模范制丝工场、四川制革官厂、同仁教养工场、惠昌火柴厂、裕德肥皂厂、制粉工场和乐利造纸公司。从《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的记载可以清晰看出当时的成都工业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以轻工业为主,这些引起日本人关注的有代表性的工业企业,无一例外都是轻工业企业。重工业企业当时成都也有,但主要集中在官办的军工和铸造领域,数量也寥寥无几,而与民生相关的重工业企业几乎没有,而同时期的重庆则形成较为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二是数量少、生产规模小,以火柴工业为例,当时成都仅有惠昌火柴厂一家③还有一家“星牌火柴厂”,但仅仅停留在试验阶段,并未批量生产。,年产火柴3150 箱④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编译:《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年,第415页。;而重庆则早在1906年就有6家火柴厂,并且形成了行业,仅森昌泰、森昌正二厂,每年各生产火柴4500 箱以上①唐春生:《晚清重庆民族火柴工业的兴起、发展及其没落》,《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三是技术落后,机械化程度较低,很多工业还停留在手工业阶段,比如乐利造纸公司,虽然“资本额为当地民营工业公司中最多”,但设备落后,“有两个原料蒸热筒(非回转式),6 个原料混合槽,虽有送原料至抄纸器械为止之全部设备,然此仅为前半工序之设备。现其设有数个方形木槽以从事手抄纸之制造,仅有压榨机以机械动力驱动”②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编译:《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年,第416页、413页、277页。;又如模范制丝工场,“女工之座席有90 台缫车(小缫车)及60 台再缫式缫车(大缫车),皆以人力运作”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编译:《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年,第416页、413页、277页。,其他绢织物、竹器、藤器、木器、金属器等传统工业品,则几乎全靠手工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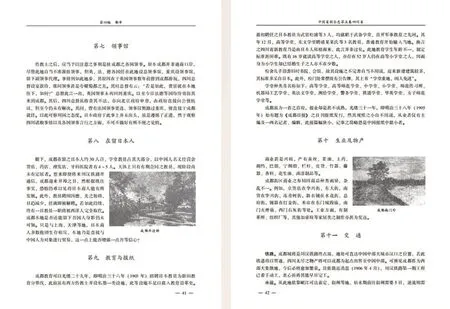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编译《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内页
可以说,成都的近代工业化“先天不足”,疲软的工业无法提供稳定的动力源,导致成都近代化进程艰难而缓慢。
(二)近代邮政事业的兴起。四川邮政事业发端于重庆,清光绪十七年(1891),重庆设立邮政司。光绪二十三年(1897),重庆大清邮政局成立。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成都才成立大清成都邮政分局,隶属于重庆总局管理,且规模极小,“全局仅有3 人,现银百两和一百块钱的邮票,业务清淡,每周只发重庆邮件两次”④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都市志·邮政志》,成都出版社,1993年,第16页。。到清宣统二年(1910),全国重新划分邮界,由于成都是四川省城,且邮政业务发展较快,因此将成都改为邮界,而重庆降为副邮界。民国三年(1914),在成都设立四川邮政管理局,统管全省邮政事务,成都正式成为全省邮政的中心。
邮政事业意义极为重大,时人称:“四川文明之进步,邮局实促助之……成都风气实赖以渐开。”⑤(清)傅崇矩:《成都通览》,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年,第43页、45页。成都邮政有三个显著的近代化特点:一是邮送范围广,不仅全国绝大部分省份可以直接通邮,甚至还能直邮到日本、法国、英国等国家。二是速度快,“重庆五天到,雅州三天到,叙府四天到,嘉定二天到,石泉四天到,灌县一天到,资州二天到,上海不过二十天到”⑥(清)傅崇矩:《成都通览》,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年,第43页、45页。。三是邮费便宜,同文书院大旅行队来到成都后,就惊叹于寄信费用之低廉,从成都寄到日本,“只要花三钱的邮资”⑦(日)沪友会编:《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37页。。同文书院对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邮务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在《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中不仅记载了一等局、二等局、三等局,还记载了近500 个基层代办所,对于学者研究民国初期成都乃至全川邮政业的发展有极大的资料价值。
(三)电报业务的出现。成都有线电报业务始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到清宣统二年(1910),成都电报已经可以通到全国除内蒙古、青海、西藏外的各个省份,甚至可以通过上海,传至国外。民国元年(1911),成都电报局有电报线路1500 公里,接下来的几年,发展速度极快,到民国六年(1917),成都电报局“铺设电线之长度为官设2700华里(900英里),民设2874华里(958 英里)”⑧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编译:《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年,第416页、413页、277页。。在《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中,对成都的电报业务给予高度关注,对其进行详细记载。比如对外线路:“四川铺设电线通过地为:一线自湖北起,沿长江经梁山、垫江,至重庆。二线自重庆起,经永川、泸州南下,过叙永,至贵州毕节。三线自泸州北上,经资州,至成都。四线自成都起,经雅安,至打箭炉”①这些记载并不全面,漏载一些重要线路,比如成都—西安、成都—昭通的线路。。此外,《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还记载了成都电信局所辖的40个基层电信局所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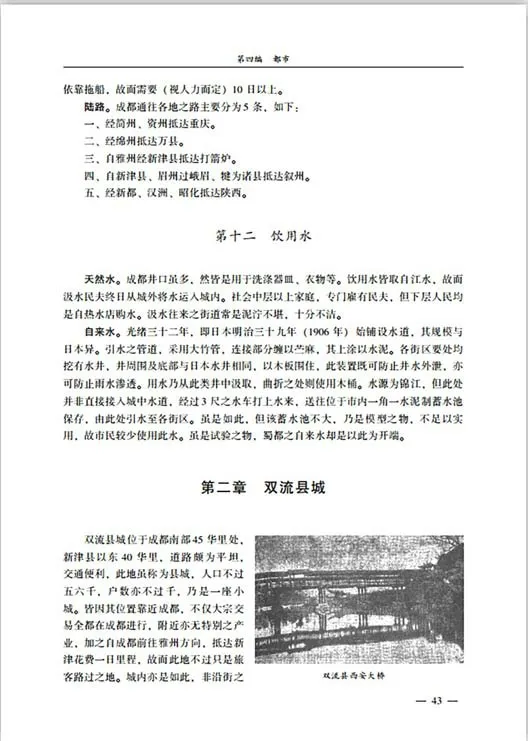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编译《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内页
但客观来说,民国初期成都电信局的电报业务发展较为落后,与浙江、福建、江苏等地差距很大,甚至在西部地区也不算突出,线路长度“较广西之6045 华里尚少471 华里”②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编译:《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年,第277页、42页。。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成都的近代化进程偏慢。
(四)近代报业的缓慢发展。成都近代最早的报纸是宋育仁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蜀学报》,但该报仅存3 个月即告停刊。此后,成都报业生存环境一直不甚理想,到清宣统二年(1910),仅有《四川官报》《成都日报》《成都商报》《教育官报》《通俗日报》《通俗画报》6 种报刊,而且大多发行量很少,与当时重庆报业的繁荣程度相去甚远。《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也认为“成都虽为一省之首府,报业却是甚不成熟,光绪三十一年,即明治三十八年(1905)始有题为《成都日报》之日刊报纸发行,然其规模之小自不用说,从业者仅有主编及一两名记者、编辑,此报篇幅狭小,记事之简略恐是中国报纸中最小者。”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编译:《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年,第277页、42页。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当时成都城市人口总量偏少,市民所受教育程度不高,很难理解报纸“启迪民智”的重要作用,“阅报者不及百分之一”,报纸对城市近代化所起作用十分有限。虽然如此,这些报刊还是为成都带来一股新气象,缓慢地推动着成都向近代化方向迈进,也为辛亥革命后成都报业的繁荣打下基础。
(五)供水方式的变革。自来水事业作为城市公用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城市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当时,成都市民生活用水一般是河水和井水两种,而井水大多水质极差,“城中之井水,味咸而恶……如以井水烧茶,水面必有油垢一层”④(清)傅崇矩:《成都通览》,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年,第4页。,因此最主要的饮用水是锦江的河水。但锦江位于城外,城内生活的居民取水不便,因此,“自来水”就应运而生。在《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中,详细记载了成都最早的自来水情况:“光绪三十二年,即日本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始铺设水道,其规模与日本异。引水之管道,采用大竹管,连接部分缠以苎麻,其上涂以水泥。各街区要处均挖有水井,井周围及底部与日本水井相同,以木板围住,此装置既可防止井水外泄,亦可防止雨水渗透。用水乃从此类井中汲取,曲折之处则使用木桶。水源为锦江,但此处并非直接接入城中水道,经过3 尺之水车打上水来,送往位于市内一角一水泥制蓄水池保存,由此处引水至各街区。”但由于蓄水池太小,供水能力极为有限,市民很少用,只是供给蓄水池周边商户使用。但《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中,仍对其意义给与较高评价:“虽是试验之物,蜀都之自来水却是以此为开端。”①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编译:《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年,第43页。
这里记载的是以马正泰、尹德钧为首的成都商人创办的“利民自来水公司”。该公司创办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成都南门外万里桥附近选择一水深处为起点,架起水筒车把河水提升起来,引水通过管道越过城墙,并在盐道街、学道街、总府街、劝业场等6处设立蓄水池,河水通过管道输送到这6 个水池,再通过人力担挑、车运出售给消费者。虽然这种自来水输送方式较为简单,也没有经过任何过滤、消毒处理,与当时上海先进的自来水系统不可同日而语,但这是四川乃至整个西部第一家自来水厂,代表着成都市政供水从传统向近代化的转变,其意义十分重大。
三、结语
总体而言,清末民初成都的近代化虽取得一定成效,但与同等城市相比,进程相对滞后、迟缓,从《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的记载中也可以直观地看到这种情况。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原因:一是成都深居内陆,对外交通不便,自然条件的封闭性强,与沿海、沿江地区城市相比,区位优势受到严重制约,导致成都近代化发展不充分、不均衡。正如有学者所言“在农业时代经济相对封闭的情况下,成都依靠自身的优越自然地理条件可以得到较好的发展。但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封闭的自然地理条件成为发展现代经济的重要障碍。”②何一民:《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3页。同时,封闭的地理条件导致成都受到外国的直接影响较小。沿海、沿江城市开埠后,迅速融入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而成都“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洋货进入都存在极大困难,外国资本主义对这一地区的冲击也大大减弱。”③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2001年,第8页。长期主导成都发展的仍然是传统经济,现代化的工业、商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等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成都封建经济基础的解体作用相当微弱。二是成都文化条件的封闭性强,传统的力量(也就是“盆地意识”)过于强大,导致近代化转型明显偏晚、偏慢,一直到“清末新政”时期,才开始“被动”逐渐转型。冯天瑜先生说:“与西欧‘原生型’或‘自生型’近代化相较,中国的近代化可称之‘次生型’或曰‘后发型’。”④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与近代化》,《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成都就是这种“次生型、后发型”近代化的典型代表。
通过以上两个原因可知,封闭的自然条件限制了成都的对外交通,而“盆地意识”则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其中“盆地意识”是发展最大的阻碍。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四川省就进行了多次关于“盆地意识”的大讨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指出,“新时代治蜀兴川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盆地意识’,为推进四川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深入的进程中,成都必须矢志不移地继续破除“盆地意识”,坚持全面开放发展,持续优化对外交通条件,高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