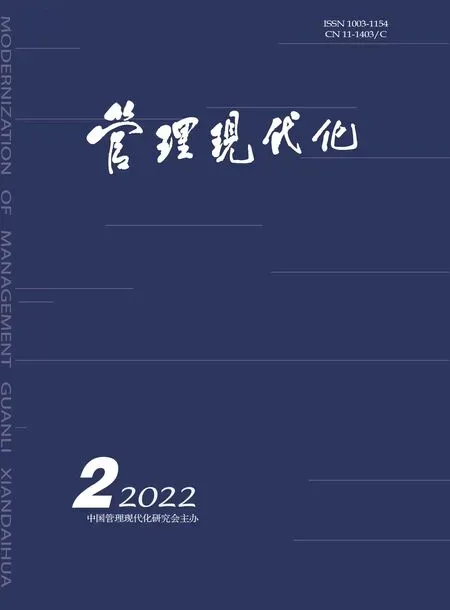“恢复体验”为何重要:文献述评与未来展望
□ 胡君辰 李荣华
(复旦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200433)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24922)。
一、引 言
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全球竞争的到来,长时间、快节奏、高强度的工作已经成为诸多行业的常态。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逐步打破传统的工作与非工作的边界,使员工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压力。已有研究表明,工作情境中不同的压力源会对员工的行为和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1]。为了能够适应新时期下的工作挑战,员工除了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知识、技能与视野之外,还需要在身心上保持良好状态,始终以充足的精力和饱满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中[2],但这势必会造成员工体力、脑力、情绪智力等的过量资源损耗,导致高度工作投入和积极情绪的不可持续性。为此,企业就不得不直面这样一个“困境”:一方面需要保持长时间、快节奏、高强度的工作来创造高水平的产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由此产生的压力过载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恢复体验”应运而生,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焦点。
恢复体验作为管理学领域方兴未艾的研究概念,全面梳理其研究现状,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其研究脉络是开展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对恢复体验的现有文献开展全面检索,进而系统回顾与总结是十分必要的。为此,本文首先以“recovery experiences”、“recovery activity”等作为主关键词,在Web of Science和EBSCO英文期刊数据库中进行SSCI期刊文献检索,经过严格筛选和反复比对,共检索到170篇与恢复体验有关的SSCI期刊论文(2007年恢复体验量表文章正式发表2021年6月);其次,本文分别将索引关键词设定为“恢复体验”、“工作恢复”、“恢复感知”等相关概念,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使用相同时间段进行检索,最终共获得16篇CSSCI期刊论文。从研究趋势图(见图1)可以看出,国外关于恢复体验的研究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同时已有不少研究对恢复体验的现有成果进行了元分析或述评。相较而言,国内对恢复体验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学者们尚未对该构念给予足够的重视,且还未形成系统的研究脉络。
鉴于此,本文评述恢复体验国内外的既有研究,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从而及时推动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
二、恢复体验概念和测量
本文首先对恢复体验的概念与内涵进行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研究中关于恢复体验的维度划分与测量方法进行阐述。

图1 恢复体验研究趋势图
(一)恢复体验的概念与内涵
“恢复”的概念最初来自于生理学领域,被认为是有机体在应激后的休息过程,反映出有机体在身体和心理反应参数上的持续提升程度[3]。2001年,Sonnentag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开创性地探索了工作情境中恢复的作用,指出为了降低或避免在工作应激过程中的损耗,员工需要对损耗掉的资源进行修复[4]。目前恢复领域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互补但又各有侧重的视角展开的,一种是将恢复视作一个过程,主要探索个体的恢复活动以及个体在恢复过程中的潜在心理体验[5];另一种则将其归纳为一个过程的结果[6],当前学者们比较倾向于开展第一个视角的研究。研究指出,个体可以通过在非工作时间里参与睡眠、放松、休闲、运动等活动形式进行恢复[4][7-12]。然而,近年来学者们发现如果仅仅关注恢复活动的研究,那么还只是停留在研究的浅层,无法全面深入地洞悉恢复的心理过程,而心理层面的恢复往往会对个体的认知与行为产生更直接的作用,只有深入到心理层面,才会更好地理解恢复体验产生的原因并能对其深层次的作用机理作出解释[6][13-14],由此也拉开了“恢复体验”深入研究的序幕。“恢复体验”的概念最早是由Sonnentag和Fritz[15]提出的,认为恢复体验是指个体通过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恢复,最终达到的一种潜在心理恢复的过程。这一构念随后引起了学术界的持续关注与讨论,主要的概念界定见表1。
综上,本文将恢复体验定义为个体通过实施适当的策略和方式使之能从工作压力和应激状态中及时恢复身心资源的心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前期在工作中损耗的身心资源会得到相应的修补并同时产生新的有效资源。
(二)恢复体验的维度与测量
由于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情境对恢复体验进行了定义与探索,这也引发了关于恢复体验构念维度和测量量表的学术争论。本文通过梳理发现,当前关于恢复体验的维度划分包括了单维度[11]、双维度[24]、三维度[9]、四维度[15]、五维度[25-26]等多种方法,其中Sonnentag和Fritz提出的“四维度”结构模型是当前使用最广泛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方法[17-19][27]。该模型指出,恢复体验应包括心理脱离、放松体验、控制体验和掌握体验四个维度[15],心理脱离是指个体从工作中脱离出来的一种心理体验;放松体验是指一种低应激水平(低交感神经兴奋),能产生积极情绪感知的体验;掌握体验是指个体通过学习与工作不相关的新知识与新技能,从而获得应对困难与挑战经验和能力的体验;控制体验是指在非工作时间中员工感知到自主性的一种心理体验,即员工在非工作时间里可以完全自主选择和决定做某件事情或某项活动以及做的时间与方式[14-15]。

表1 恢复体验的定义
现有关于恢复体验测量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部分学者将恢复体验视为一个“过程”概念,认为其是一个具有稳定特质的变量,主要通过采取“横截面法”来对恢复体验进行测量;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恢复体验是一个心理恢复过程的“状态”,是会受到外部情境和时间的动态影响而发生改变,主张通过经验取样法来捕捉和分析员工恢复体验动态变化的状态信息。国外研究有不少学者已经尝试了用“经验取样法”对恢复体验进行测量,然而国内研究中普遍采取了“横截面法”,采用“经验取样法”对恢复体验进行测量的研究非常鲜见。
三、恢复体验的前因变量
通过对恢复体验现有研究的梳理,本文将恢复体验前因变量归纳为三个方面,分别是工作情境特征、恢复活动和个体特征因素。
(一)工作情境特征
工作要求资源模型(JD-R模型)是工作特征研究领域使用最广泛、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模型,该模型的主要观点是工作情境中存在着影响个体生理与心理健康状态的特殊因子,这些因子可归集于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两大集合。
工作要求。工作要求(Job Demands)是指在工作中要求员工保持身心努力的因素,这些因素容易引起员工的工作负荷、角色冲突等资源消耗[28]。已有研究指出工作要求与恢复体验之间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15]。
工作资源。工作资源(Job Resource)是指为工作者提供支持与帮助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帮助员工实现工作目标,激发员工潜在的动力[28]。拥有较多工作资源的员工拥有更多的能力保护自己不受资源进一步消耗的负面影响与压力。Bennett等[13]通过元分析发现工作资源与放松体验、掌握体验和控制体验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Siltaloppi等[29]研究发现工作资源与掌握体验和控制体验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二)恢复活动
恢复活动和恢复体验并不是相互独立的,某些具体的恢复活动会对恢复体验产生影响[6]。
利于恢复的活动。有关恢复活动的研究指出,在非工作时间里的身体活动可以积极预测心理脱离[8]、放松体验以及掌握体验。非工作时间里的社交活动,特别是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联活动,对心理脱离、放松体验和掌握体验都有积极的影响。低努力活动(如睡眠、散步、阅读等)则可以预测高水平的放松体验。此外,一些学者也注意到工作期间的“微休息”和午餐休息等工作时间段内发生的恢复活动[30-31]。
阻碍恢复的活动。已有研究指出,非工作时间里从事与工作有关的活动会阻碍员工的恢复[32],导致低水平的放松体验,控制体验也相对较低。而在非工作时间内使用与工作相关的智能手机也会降低个体的心理脱离水平[33]。此外,从事家庭家务与育儿活动也可能会对个体的恢复体验产生负面的影响[4]。
(三)个体特征因素
除了工作情境特征与恢复活动之外,还有一些个体特征也会对恢复体验产生影响[6,15]。
人口统计特征。个体的性别、年龄等基本特征会影响恢复体验,例如,相对未婚员工来说,已婚的员工普遍存在较差的放松体验感[34]。个体的人力资本也会影响恢复体验,例如,受教育程度会导致员工在心理脱离这一维度上产生差异,而职位等级会影响员工在工作中投入程度的不同进而影响恢复体验。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会导致员工在心理脱离这一维度上产生差异[35]。
人格特征。现有研究已指出,大五人格与恢复体验之间也存在某种联系[15],其中外向型和开放型人格会正向影响个体的掌握体验。员工消极的情绪特质与过度承诺的职业个性则会对员工的恢复体验产生负面的影响[36]。此外,员工关注当下的时间观、接纳正念、高工作中心性等人格特征因素也会对其恢复体验产生一定的作用和影响。
四、恢复体验的影响结果
通过对恢复体验结果变量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梳理,本文认为分别从近端、中端、远端三个视角对其进行归纳总结,能够较好地呈现出恢复体验结果变量的研究面貌。
(一)近端结果变量——心理与生理变量
身心健康。研究指出,员工恢复体验能够改善其身心与情绪问题,提高他们的睡眠质量。Sonnentang & Fritz[15]在研究中发现,员工恢复体验能够改善其身心与情绪问题,提高他们的睡眠质量。类似的,Ganster & Rosen[37]也指出,恢复体验能够提高个体的身心健康,缓解健康抱怨、睡眠等问题。此外,Sonnentang等[6]还发现,当员工具有较高的恢复体验时,他们的身心健康会得到较好的修复,病毒菌株等生物标志物对他们身心的影响也会相对较低,从而防止慢性健康问题的发展。
职业幸福感。职业幸福感主要反映的是员工在工作中对于情绪与认知方面的体验与评价,体现出高积极情感和低负面情感[14]。已有研究表明,恢复体验及其子维度显著正向影响员工职业幸福感的多个维度,包括积极情绪、职业幸福感、生活满意度。例如,Fritz等[16]指出,员工在周末期间内的恢复体验会正向影响他们的积极情绪。Hahn等则在其研究中发现,夫妻共同活动可以通过放松体验的中介作用进而影响员工个体的积极情绪。Newman等指出,非工作时间里员工可以通过放松、低努力活动等进行恢复体验,并由此提升主观的幸福感。Siltaloppi等[29]研究发现心理脱离和掌握体验能够积极地预测员工的职业幸福感。Chen等[38]研究发现,恢复体验会正向影响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即当个体的恢复体验较高时会激发其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不过,也有研究持有不同观点。例如,Kinnunen & Feldt[34]在其研究中指出,若从长期的视角,员工恢复体验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显著的。
恢复状态。研究指出,员工恢复体验能够降低个体的身心压力水平,增加其内心的平静,心理脱离、放松体验、掌握体验和控制体验以及快乐都能积极预测员工的疲劳减轻、活力增强[32]等恢复状态。Kinnunen等[34]检验了恢复体验对减轻工作倦怠、增强工作活力等恢复状态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恢复体验中的心理脱离维度有助于降低恢复要求和倦怠感,掌握体验能够促进工作活力的提升。Siltaloppi等[29]通过纵向研究法发现放松体验有助于缓解员工的疲劳问题,掌握体验和控制体验则能积极促进员工的工作投入度。Brummelhuis & Bakker采用日志研究法探索了心理脱离和放松对员工次日上午的活力状态和工作投入感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心理脱离和放松体验有助于员工次日上午活力的增强。Schimazu等[39]发现心理脱离与工作投入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即适当的心理脱离状态最有利于增强员工的工作投入。Bosch等发现员工午间恢复体验可以负向影响个体的午后倦怠水平。
(二)中端结果变量——行为变量
主动行为。Binnewies等[40]研究发现,在双休日和假期中的放松体验和心理脱离都可以通过员工恢复水平的中介作用影响员工工作的主动性。Fritz等[16]研究发现心理脱离与员工的前瞻行为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即适度的心理脱离更有利于员工产生前瞻性行为。de Jong等[41]研究发现,不同层次的心理脱离对员工主动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其中认知脱离会负向影响员工的主动行为,而身体或情感脱离则会对员工主动行为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组织公民行为。Eschleman等[18]采用自评和主管打分的方式对恢复体验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控制体验对自评的组织公民行为以及掌握体验对他评的组织公民行为都具有积极的影响,心理脱离对自评的组织公民行为具有负向作用。不过,这一结论也并不稳健,Binnewies等[40]使用经验取样法发现员工在周末的恢复体验与其在下一周的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关联。
(三)远端结果变量——绩效变量
创造力。有研究分析了员工恢复体验在创造力与主动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发现心理脱离会负向影响员工的创造力表现,而其他三个方面(放松、掌握与控制)并不显著影响和作用于员工的创造力[18]。恢复体验或许可以通过创造力效能感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员工的创造力[20]。
任务绩效。恢复体验与任务绩效关系尚不明晰[6]。虽然理论分析指出恢复体验对员工绩效有着积极的预测作用,但实证分析却表明两者之间具有某种模糊性:有的研究认为恢复体验可以积极的预测员工任务绩效水平,但也有研究指出恢复体验对任务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7,40]或是存在非线性关系[16],也有研究指出二者之间的关系取决具体的某种体验类型[18,25]。
五、恢复体验的边界研究
通过对现有研究的回顾发现,目前有关恢复体验边界变量的讨论还比较少,本文尝试着从三方面因素进行划分。
个体因素。个体间的差异不仅仅直接影响恢复体验,同时也会作为边界变量对恢复体验起到交互影响。有关性别方面的研究就曾指出,在某些情境中两性性格特征会存在较大差异[42],这些差异会造成员工在感知与应对压力以及在理解恢复上的不同,从而会动态调节某一变量对恢复体验的作用过程。Ragsdale等研究发现情绪特质(积极特质、消极特质)会动态调节周末活动与恢复体验之间的关系。
工作因素。Oliver & Christine[43]探讨了任务进展的边界作用,他们发现在工作日结束时,任务进展的情况有助于缓解工作要求对恢复体验的负面影响。曲怡颖和任浩[20]指出,工作复杂性在恢复体验影响员工创造力自我效能的过程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石冠峰和刘朝辉[44]在研究科研人员的恢复体验对其工作绩效影响时发现,工作意义负向调节恢复体验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
情境因素。员工是高度嵌入在组织情境中的,员工在工作中不仅仅会受到工作本身特点的影响,同时更容易受到组织情境因素的限制。谢雅萍等[22]在研究休闲参与通过恢复体验的中介作用影响员工工作激情时指出,非安全型组织依恋会负向调节休闲参与通过恢复体验中介作用影响员工工作激情的过程。
六、研究评述与展望
本文首先对恢复、恢复活动以及恢复体验的定义与内涵进行了界定,随后对恢复体验构念维度与测量的有关研究进行了回顾,并进一步梳理了恢复体验的前因变量、结果变量和边界变量。基于以上讨论,本文提出了恢复体验现有的研究框架(见图2所示)。

图2 恢复体验的现有研究框架
虽然有关恢复体验的研究不断涌现,但是现有研究对恢复体验的过程探究和机制解释仍显乏力[6],特别是国内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截止到2021年6月,以“恢复体验”等为关键词共检索到文献16篇CSSCI期刊论文,相较国外的研究发展,国内研究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与国外研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随着人社部明确提出近年来盛行的“996”、“007”工作制违反法律规定,互联网大厂纷纷取消“大小周”,以及职场“反内卷”风暴的来袭,在中国情境下加快开展恢复体验的探索与实践变得尤为迫切。
由于恢复体验是在西方情境中提出来的构念,中西方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西方文化更强调个人主义,追求独立自我,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具有明确的划分,为恢复体验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和制度情境。而东方文化以集体主义为导向,强调个体在群体事业中的责任意识与奉献精神,即使在非工作时间,完全的“心理脱离”也不被认可与鼓励。在即时通讯工具日益发达的今天,工作与非工作不再存在明确边界,不管是工作日夜晚还是周末时间都很难做到完全的休息与放松。因此,中国情境下恢复体验的研究需要首先检验东方文化情境中恢复体验的概念、结构及量表的有效性,为大规模研究提供坚实的概念与测量基础。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发现国内研究当前仍主要采用横截面问卷研究的方式,这一方法存在严重的社会称许性偏差,也无法对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作出推论。本文鼓励国内恢复体验的学者参考国际相关研究采用的方法,以经验取样法的方式展开一定时间区间内的追踪问卷测量,并结合手环、手表等智能穿戴设备同时测量被试的睡眠、运动状态,在数据的质量和测量手段上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为国内恢复体验研究的理论进展奠定数据基础。
再次,从现有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来看,恢复体验的研究多探索其与前因变量、结果变量之间的简单关系与边界条件,但是,对于其中的机制“黑箱”尚缺乏深度理论探索。从前因变量来看,恢复体验的前因变量主要集中在恢复活动[9]、工作特征[29,32]和个体特征因素等方面,一方面缺乏不同前因变量之间交互作用对恢复体验影响的深入探索,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借鉴压力评估理论、工作资源要求模型、自我调节理论等解释恢复体验的形成路径,加深对恢复体验前因变量的全面理解。从结果变量来看,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心理与生理变量的探讨,对行为变量和绩效变量影响的研究还比较缺乏,未来研究应聚焦讨论恢复体验对个人主动性、创新性、建言行为、组织公民行为等主动行为的影响,以及对员工创新绩效和任务绩效的探究,响应当前对全民创新和企业主人翁精神的号召。从边界条件来看,目前关于恢复体验边界条件的研究更多地还是聚焦在工作意义[44]等工作本身的特点与性质,未来更应考虑组织制度与文化等情境因素,探讨组织、团队或领导塑造的容错文化、创新氛围、支持氛围等如何助力员工更好地从压力中恢复,以最佳的精神面貌投入工作。
在VUCA时代,不确定性带来的工作压力已经不可避免,恢复体验也随之成为时代“必需品”。了解科学的恢复手段、学会高效的恢复方式、获取极致的恢复体验,应该列入每位职场工作者的“技能清单”,也需要组织积极响应,通过给员工提供休息空间、锻炼场所等方式,“让子弹(思维)飞一会儿”,激发员工创造精神,也更好地维护员工身心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