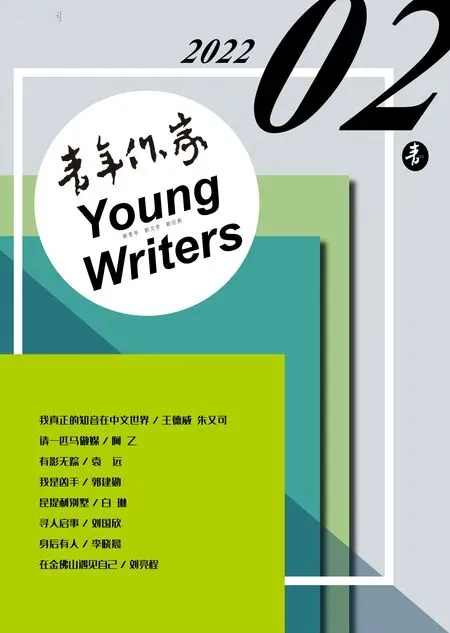隐山
智啊威
山野静默,没有一丝风,晚霞把山顶映成橘红,仿佛大火一直在那里烧,视线里有几只鸟,一动不动,像僵硬的松果。他坐在朝山崖凸出的一块石头上,长发因疏于打理而纠缠到一块儿,胡须杂乱,树根样爬满了整张脸。
他不知道这是哪里,也不知道今夕何夕,只隐约记得群山黄了又绿,来来回回折腾了大概有六七次,也可能是八九次,他没有刻意记,自从进山后,时间于他而言已经完全丧失了意义。
刚到这里那会儿,他常去山坡或山涧里采一些野果充饥。有一次,他爬上一棵柿子树,打算摘上面红彤彤的果实,结果“咔嚓”一声,从树上摔了下来。
在身体的下坠中,他不由得感叹,为了活命,这一路吃尽苦头,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隐蔽的藏身之所,可眼下,就要死在这片陌生的山野之中了吗?如果早知道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又何必没日没夜像野狗一样不断奔逃?
他不知道自己在树下那堆干草上昏睡了多久,只记得醒来时身边围着几只硕大的老鼠,每一只看上去都有四五斤重,有的爬到了他身上,有的在嗅他的手和脚,他庆幸自己早醒了一会儿,不然那几只老鼠恐怕就要开始啃他的肉了。
月光下,他缓慢地朝山上爬,手臂撑地,每一次用力,都像有刀片在割他的骨节。与此同时,耳边充斥着鸟雀的鼾声和低语。有时从月光朦胧的林子里,突然传来野兽的嚎叫,声音嘹亮,山野也跟着震颤起来。
他回到山洞时,朝回望去,看到月光下的山林雾霭氤氲,像贴了一层透明的薄膜。他想脱下衣服察看一下伤势,却发现连抬起手臂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在山洞里接连躺了两天,直到饥饿掐着他的脖子,把他从睡梦中拽醒,迷迷糊糊之间,他听到蛇在耳边吐信子,发出嘶嘶声。老鼠叽叽叫着,争抢他辛苦晾晒的鱼干。
他抓起一块石头,使尽浑身力气,抛出去的距离还不足一米远,老鼠和蛇停下来,瞅他一眼,又继续在山洞里哄抢和“嘶嘶”。
第三天,他依靠石壁,缓慢从地上站起来,打算出去寻一点吃的,可右腿虚软得厉害,几次站起又瞬间瘫下去。不得已,只得爬出山洞。
外面阳光普照,门前的溪流上闪着粼粼波光,群山起伏的线条在碧蓝的天空下清晰可见。他爬到溪边,把脸埋下去,喝了一肚子冷水,抬头时,看到自己的倒影,人鬼难辨,他苦笑起来,笑着笑着,眼泪涌出,砸在水面,像鬼魅一样的倒影顷刻间破碎成了一片虚幻的光斑。
喝过水后,肚子很快又叫了起来,他斜依在石头上,揪起身边的荒草往嘴里塞,干硬的草茎划破他的口腔,血渗出来,像草里撒了盐,他已经很久没吃到盐了。
他努力把干草嚼碎,可下咽的时候分明感到自己是在吞咽铁钉。这种糟糕的饥饿感又把他拽回了痛苦的往昔,那时他正走在逃亡的路上,四周荒芜,风沙翻卷。他没日没夜走了两天,不仅找不到水源,连能充饥的东西都没有,有几次他跪在地上,抓起沙土准备往嘴里塞,又在即将碰到嘴唇的时候松了手。他从沙土滑落的过程中起身,拖着沉重的双腿继续往前走。他不知道路还有多远,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往何处,唯一清晰的就是要走,只有走,不停地走,才有可能保住这条命。然而,他并不珍视自己的这条命,自从他从小超市老板手里接过刀子的那一刻便意识到,自己往后的命将像洪水中的一叶孤舟。可即便如此,他还是揣着那把尖利的刀子,走向了那个男人的家。一路上,他感到怀里的刀子一直在跳动、怒吼,他知道,它饿了,急需那个男人的血来喂饱它。他抚摸着它,他安慰着它,他告诉它,就在今晚,他会让它敞开肚子喝干那个男人的血!
他来到他家对面不远处的那片树林,用她的手机给他发了一个短信,临末,还特意提醒他带一个套子来。
打完最后一个字,他把牙咬得咯吱响,与此同时,他右手里的刀子再次躁动起来,在流水的呜咽声中,他摁下发送键,然后躲在树林入口处的干草中,等待着那个令他恨之入骨的男人走来受死。
他本不想这样,当他想到自己七岁的孩子和年迈的母亲,却又不得不如此,没有人能体会他早晨看到她手机短信时的复杂感受,像被巨雷暴击了一般。那一刻,他意识到,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婚姻成了自己的耻辱,平静的生活在巨雷的轰鸣中碎成了一地粉末。那时候的她刚从卫生间出来,还完全没有意识到,今晚过后,她的生活将由无尽的悔恨和余悸来填充。
这天傍晚,他把儿子送到母亲家回来后,她为他炒了两个菜,烫了一壶黄酒。她告诉他,吃完后把碗筷放在桌子上即可,她洗完澡后再来收拾。自从她感受过那个男人坚实的胸膛,对他宽容和温存了很多。遥想刚和他结婚那会儿,她还很喜欢他的。那时候他在广州工作,三十一岁就当上了一家电子厂的车间组长,一个月工资扣除五险一金还能到手五千块钱。逢年过节,在几个姐妹面前,她觉着脸上有光。可孩子出生后,他竟突然辞职,回到了他们眼下生活的这座北方县城找了一份新工作,一个月工资两千五百块钱,中午还不管饭。她骂他脑子有病,但他不这样认为,并为自己申辩,说不想让孩子一出生就当留守儿童,加之母亲年龄大了,就他一个儿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他不在身边,会后悔终身。
她气不顺,就一直用冷硬的话去刺他的心。他坐在客厅,垂着脑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那时候的他和今天的他坐的是同一个位置,只是心境已完全不同。那时候,他满怀隐忍,而今天,他怒火中烧。
他坐在餐桌前,毫无食欲,直到她裹着浴巾从浴室里走出来,丰满的臀部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他承认她是一个性感的女人,如今这份性感却在加重他的恶心。尤其是当他想到那个给她发信息的男人,像一头发情的公猪伏在她身上气喘吁吁……他再也忍不住胸中的怒火,对着她的背影吼道,你还能再贱一点吗?她满脸诧异回过头,看到他已经朝自己扑了上来,像一头力大无穷的猛兽。
他呲着牙,胸口起伏,怒视着她的脸。如果不是在他根深蒂固的观念中,只有无能的男人才会对女人下手,他今晚会顺带一起了结了她的命。
他用胶带封住她的嘴,把她绑在冰箱上,拿起她的手机,临出门时,她看到他顺手把一把刀子揣入怀中,目光阴冷,撞入北方的夜色中。
她身上的浴巾在挣扎中脱落,堆积在腰间,粗糙的绳子几乎要勒出她的血来。
这时,她感到从脚底涌来一股虚脱之感,如果不是紧绷的绳子束缚着身体,她会一头栽下去。她的后背紧贴着冰箱,裸露的乳房唤起了她隐隐的羞耻,即便这间屋子空荡荡的,除了她再没有任何人,可那种难言的羞耻感却愈加强烈,几乎要从她的胸口爆炸开来。
她努力调整呼吸,想到刚生完孩子那会儿,每天下班,常因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跟他吵架,那一刻,两个人像疯子一样相互谩骂和指责,把孩子吓得躲在门后哇哇大哭。然后她抱着孩子一起哭,声音里塞满委屈,故意让楼上楼下的邻居都听得着……从那以后,他们的婚姻就出现了裂痕,且随着时间的流逝逐年扩增,在他习焉不察之间,早已到了不可修复的地步。即便如此,老实讲,她也从未想过要离开这个家。即便在遇到那个令她倾心的男人之后,她也从未想过要离开这个家。
和那个男人共度的第一个下午,他们去了县城北街的一家咖啡馆,她看着他柔和的目光,不禁感叹,这世上怎么会有和自己如此契合的灵魂?一整个下午,她始终面带微笑,用手臂撑着下巴,仰视着他的脸。她很少说话,一直在听他讲。她喜欢他的声音,像春日的溪水,慰藉着她多年来苦涩而压抑的婚姻生活。她说不清楚喜欢他哪一点,仿佛他哪一点都令她着迷、沉溺。
傍晚,分别时,她望着他的眼,很认真地说,我觉得我们上辈子就认识,你信吗?他微微一笑,很礼貌地帮她拉开车门。她的头依靠在玻璃上,从后视镜看到他的身影在霓虹闪烁的细雨中越来越小,她突然笑了,摇着头。她想不明白,自己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怎么还会对别的男人起心动念?正当这时,手机响了一下,她看到他发来的信息,两个字:我信。
她的心一颤,赶紧去捂,又恍然想到,自己坐在出租车后排,压根儿没有人会窥见她的手机。她侧过头,望着雨中的街景,在嘴角上扬的时刻,怎么也不会想到,两年后,她将为今天的相遇痛哭失声。
她尝试了几次,发现自己压根儿不可能从勒紧的绳子里挣脱。她歪着头,绝望的脑袋里映现的是那个男人浑身是血,惨叫着奔逃,而他满脸狰狞,举着刀在后面追他的彪悍场景。有好几次,她吓得甩着脑袋尖叫起来,但因嘴吧被胶带封住了,发出的声音呜呜啦啦,微弱到连自己都听不清。
她闭上眼,感到人生中的很多事,并不会按照自己设想的轨迹发展。她原本想着,和他成为朋友,抑或知己,一个可以敞开心扉说话的人,可不曾料到的是,和那个男人频繁见面后的某个晚上,他突然握住了她的手,而令她诧异的是在那一刻,她非但没有把手抽出来的念头,反而希望他能握得久一点,再久一点。天黑透了,他们沿着雀河一直往前走,她的手开始出汗,而他握得更紧了,没有丝毫要松开的迹象。也就是在这一天,在雀河的拐弯处,在那片枝叶繁茂的树林中,他不由分说地抱住她,用嘴封住了她的唇。
她闭上眼,感到自己的身体正沉入一片温暖而潮湿的湖。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仿佛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了。
那个晚上,她看着那个男人,像一只敏捷的猴子,翻越她身体的山岭后进入一块狭窄的沼泽地,那里漆黑,而他并不慌乱,手指沿着她敏感的神经游走,拨动身体的琴弦。她含着浅浅的羞涩,期盼和担心,任凭那双充满魔力的手在自己身体上肆意弹奏……必须承认,那是她这辈子听到过的最美乐曲,很长一段时间她都这么认为。可直到今天,当她被自己的丈夫用愤怒的双手绑在冰箱上回忆往昔的时候,才愕然发现,那首曾令她心潮翻涌的曲子竟然回荡着一股死亡气味。
夜已经深了,她听到房门响动,看到他走了进来,把那把用她情人的鲜血喂饱的刀子猛然刺入她脚下的木质地板,刀子颤动,带动刀柄,在她惊恐的视线中,他笑了,表情怪异,像一个吸血鬼。
他一句话也不说,蹲下身,一直注视着她。咸腥的血味扑鼻而来,他拍了拍她惨白的脸,起身消失在那扇铁门之后。
他戴着口罩和一顶黑色皮帽,出了县城,沿田间小路走在北方的寒夜中,有好几次,他停下脚,想回去再看母亲和孩子一眼,因为这一走,不知道这辈子是否还有机会再见到他们。他犹豫片刻,转过身,双手合十,朝母亲家的方向跪下去,磕了三个头,然后起身,脚步匆忙,继续走向生死未卜的远方。
一路上,他像惊弓之鸟,从未睡过一个囫囵觉,走累了,就钻到柴垛里,或依在土岗上睡一会儿。他的嗅觉和听觉变得极为灵敏,任何风吹草动都能把他从睡梦中惊醒,然后迅速观察左右前后,即便四下无人,也不敢再睡,匆忙起身,迈着踉跄的步子继续走。
逃亡中,他不走大路,也刻意避开村镇和人群,在茫茫田野或荒僻的大地上跋涉,远远望见人影,就立刻躲起来,待那人彻底消失,才敢从藏身的草丛或沟渠里起身,弓着腰,继续往前走。一路上,他忍受着恐惧、饥饿、疲惫和寒冷,不分昼夜地走,直到在那耀眼的晨光中,远山的轮廓映入眼帘,像静止在大地上的绿色波涛。
他满怀激动地走进大山,循着一条溪流往上走。时值盛夏,山林苍翠,鸟鸣此起彼伏,像在欢迎他来到这个新世界。他走累了,洗了脸,坐在溪边的一块石头上,突然想到六祖惠能得到五祖弘忍的衣钵后,为了活命,一路南逃至大庚岭时,也曾坐在一块孤独的石头上。想到这,他不禁苦笑,心想,虽然都是逃亡,但自己岂能跟六祖相比?人家逃命是为了能弘扬佛法以普度众生,而自己,一个杀人犯,逃亡不过是为了苟且偷生!
他叹了口气,起身沿溪流继续往上走。这里怪石丛生,他走走停停,到半山腰处,见前方有一石洞,洞口被野藤遮掩,甚是隐蔽。洞前是一块空地,溪流途经于此,发出细碎的叮咚声。石洞内部平整、阴凉,密布着蛛网。他在山洞里反复打量了半天,然后走出洞穴,满怀感激地在炙热的阳光下站了很久。
他把山洞收拾一番,决定在这里住下来。
秋冬天的时候,他在山洞里铺上一层干草,躺上去柔软很多,只是山中的冬天太过寒冷,他没有棉被,经常半夜被冻醒,瑟缩成一团。直到两三年后,才勉强适应这里的冬天。
山里野果很多,只是吃多了胃酸得厉害,所以,他经常拿着自制的工具,去山中狩猎,打一些山鸡或野兔回来,有时运气好,也能逮到野猪,他一个人吃不完,会给山洞里的老鼠和蛇分一点。毕竟这孔山洞,是他们共同的居所,有吃的,相互分食一点,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直到后来他从树上摔下来,没办法出去觅食,老鼠吃光了他储备的食物后,趁他睡着时,还咬掉了他的一个脚趾头盖,他捂着流血的脚,倒吸冷气时,才恍然意识到,老鼠和蛇,都他妈不是好东西,像一群喂不熟的狗。
由于没有火,他打来猎物,在溪边用石斧开膛部肚后,直接生吃,一口生肉咬下去,伴着腥咸的血水,忍不住呕吐了好几回,后来渐渐就吃出了生肉的鲜美,几天不吃倒还有点嘴馋。
多年的山居生活,令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回归到了一个人最原始的生命状态,而刚进山那会儿,则完全不是这样。那时候,虽然他藏身的山洞足够隐蔽,却依旧每天都活在担惊受怕中,感觉警察随时都会追过来,用枪抵住他的脑袋。他经常梦到自己被反绑着双手,跪在地上,看到子弹从漆黑的枪管中飞出,击中他的脑袋:残渣四溅,像稀烂的番茄。
他从噩梦中惊醒后冷汗淋淋,睁着红肿的双眼,直到晨曦从洞口的枝叶间射进来,才敢再眯上一会儿。
随着时光的流逝,这样的梦越来越少,他的胆子也渐渐变大,偶尔在山中遇到猎人也不再躲避。别人看他衣衫褴褛,长发挽成发髻盘在脑后,以为是隐居此地修道的大师,颇为尊敬,有时他向他们讨一只山鸡或野兔果腹,也不会遭到拒绝。
在山中的日子很静,长年累月,很难遇见一个人,他经常躺在山洞里,感觉自己像一个死人。有时候他想,倘若自己真死在这里,除了蛇和老鼠,大概也不会有别的人知晓。只是,还不能死,为了母亲和儿子,还不能死。逃亡的滋味并不好受,无时无刻不在煎熬着他的心,尤其是当想到和母亲以及儿子相伴的欢乐往昔,眼泪总会不由自主地掉下来。
然而最近,他已经很少再想到儿子和母亲,也几乎没有再梦到警察和子弹,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从山洞搬到万佛寺的缘故。
万佛寺始建于北宋淳化年间,说是寺,其实就是一间房子,建在山顶的巨石上,用大小不一的石块砌垒而成,室内刻满了佛像,神态各异,形象生动。
通往万佛寺的山路崎岖难行,因此来这里上香的信众并不多,但千百年来,香火从未间断。他那天在山中游荡,感觉这间石屋很别致,就走了进来,看到石桌上堆满了贡品,还以为自己看花了眼。
他喊了几声,见无人应,就站在供桌前狼吞虎咽起来。
山居多年,他吃的都是些生肉野果,哪曾想过,这辈子还能再吃到沙琪玛小饼干和夹心面包......他拼命往嘴里塞,没嚼碎就往肚里咽,噎得满脸通红,翻着白眼,差一点没死过去。
从那以后,他每隔三天就来一趟万佛寺,把佛前的贡品洗劫一番,说是洗劫,也不准确,因为每一次,他都不会全部拿走,而是每一样都给诸佛留一个。
从他居住的山洞到万佛寺有三四公里,山路难行,来一趟并不容易。起初他以为寺里有人住,每一次来都偷偷摸摸,后来发现,除了前来上香的零星信众,压根没人会走进那间石头屋。
有一次他正坐在万佛寺吃贡品,外面忽然下起大雨,直到傍晚还没有停的迹象。眼看天要黑了,他正准备冒雨走时,忽然一拍脑袋,心想,既然这里没人住,石头房又不漏雨,视线也好,吃食不断,何必再回到自己居住的那孔潮湿的山洞中?当天晚上,他便在万佛寺住了下来。白天有信众来上香,他就躲出去,趴在不远处的灌木中盯着,待信众下山后再出来。有时他刚走回万佛寺,忽然瞥见又有人来了,吓得赶紧往外跑,几天下来,累得眼冒金星。
他觉得长此下去不是办法,回曾经的山洞去住又有点舍不得这里。正当焦头烂额时,他低头看到水中自己的倒影:整张脸被杂乱的胡须覆盖着,头顶发髻高耸,几绺头发垂挂下来,颇有仙风道骨之气。他嘿嘿笑了,嘴里喃喃道,还躲个鬼啊,就我这样子,估计我亲娘见了都认不出!
他晚上睡在万佛寺,醒来后就盘腿坐在屋子中间那尊独立的主佛旁边闭目养神。两个女信众进来后,见他衣衫破烂不堪,发须雪白,闭着眼一动不动,一时间有点搞不清是何方神圣。她俩在屋子里拜完佛准备走时,又突然回身,扑通跪在地上,对着他磕了三个头,嘴里念叨着“保佑,保佑”,说着,各点了三根香,插在他身前的石头缝中,退出石屋,朝山下走去。她们走后不久,来了一位愁眉苦脸的老汉,拜完佛后,围着他转了五六圈,然后问道:
“你坐这干啥哩?”
“别问,对你不好。”
“我已经够惨了。”
“想好不想?”
“想!”
“磕吧。”
那老汉挠着脑袋,半信半疑,但看他这身装扮,透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仙气儿,于是就跪了下去,咚咚咚磕了三个头。然后恭维道:
“大师,我一进来就看你不像个凡人!”
“走吧,转运后记得来还愿。”
那老汉还想再问,但看他已经闭上了眼,就知趣地退了出去。
老汉走后他嘿嘿笑了,回味着刚才那声“大师”,觉得挺好玩。久居山中,生活单调至极,他已经很久没跟人开过玩笑了。
第二天,他把那尊主佛身上的披风取下来,披在自己身上,继续盘腿而坐。面对信众好奇的目光,他纹丝不动,也不多言。有人围着他看了一圈准备走时,他忽然高声道:
“还不磕?”声音浑厚、突兀,吓得那人一哆嗦,转过身来,也不敢多问,咚咚磕了几个头,然后双手合十,还没开口,他又炸声道:
“你最近有事!”
那人的脸色一变,头点得像小鸡啄米:
“大师神算啊!”
其实他哪里会算卦,不过是抓住了大众的心理而已,再说了,来这里烧香磕头的哪个人心里没有点“事儿”?
从那以后,他便开始给信众算命消灾,看似云里雾里,又满是细节,比如:
“第三天早上五点,绕房子三圈,灾消了记得来还愿。”
“在后山看着眼熟的那棵松树上滴一滴自己的血。”
“拔一根公鸡脖子上的毛,晚上睡觉含在嘴里,连含七七四十九天。”
他说话时一脸严肃,眼睛深藏在雪白杂乱的胡须后面,像两口深井。他睁开眼时,目光落在你脸上,但你分明感到,他在盯你的后脑勺。
他算得很准,算得准并不是因为他会算,而是他说出的话总能自圆其说。比如面对那些说他算得不准的信众时,他会反问:
“绕房子三圈你先迈的左脚还是右脚?”
“你滴血时,割的是第几个手指?”
“你把公鸡的毛含在了舌头下还是舌头上?”
最先来还愿的是那个老汉,他请了一个打鼓的和一个敲锣的,一路走来,鼓声和锣声交织着,在幽静的山野里回荡。老汉走在最前面,双手托着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有求必应。旁边是一排小字:赠万佛寺白发大师。
万佛寺外锣鼓震得他脑袋嗡嗡响,他睁开眼,看到那个老汉提着锦旗,满脸喜色地走了进来,不由分说就把锦旗往他怀里推。别的前来烧香的信众围上来,看到大师接过锦旗时便一起鼓掌。其中,那个老汉鼓得最起劲儿,把手拍得通红了还在拍。
那个老汉对围观的信众说,大师真是菩萨下凡,有求必应!我种了几亩地苹果,摘下来装箱后,采购商突然说不来收了,气得我跺着脚骂。正当我发愁的时候,上山拜了大师,结果第二天村子里就来了两个年轻人,说要帮我搞一场助农直播卖苹果。两个人对着个手机像拉家常,结果不到一个小时,那个胖小伙告诉我,几千斤苹果已经全部卖出去了。刚开始我有点不信,直到第二天接过钱,看到苹果被装车拉走后,我才意识到,是大师显了灵!
老汉对围观的信众滔滔不绝,临走时还往他兜里塞了一卷东西。他掏出来一看,是几张百元大钞。他手里的锦旗滑落在地,把那几张钱数了两遍,整整五百元。虽然他在山里用不着钱,但那五百块钱在手里还是让他脑袋发懵,第一次觉得挣钱竟这么容易。
由于口耳相传,来找他祈福和还愿的人越来越多,每个人见了他都毕恭毕敬,张口必称大师,这些人除了给他带吃的、衣服棉被之类的东西,临走时大多都会给他塞点钱。后来,他怕影响不好,就用木板钉了一个小木箱,遇到有人再给他塞钱时,就紧捂住口袋说:
“我从不碰钱,我对钱不感兴趣。”
对方满脸羞愧,觉得冒犯了大师,赶紧道歉。这时,他的目光落在自己做的那个木箱子上,道:
“施主若真有布施的心,就给万佛寺捐个香火钱吧。”
每当夜幕降临,他蹲在摇曳的烛光下,把功德箱里的钱倒出来,一张张地数。这时候,钱于他而言就像一张张废纸片,直到某天深夜,他从梦中醒来,想到久未谋面的儿子和母亲,又止不住突然难过起来。多年不见,也不知道他们生活得怎么样,想必儿子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小伙,母亲大概也被时间压成了一个脊背佝偻的老人。他突然扬手,朝自己脸上狠扇了两下,一下替母亲,另一下替儿子。眼泪滚落,无声,他睁开眼,看到地上大小不一的钞票,突然觉得应该为他们攒点钱,也不需太多,十万块钱。儿子结婚,母亲养老,估计也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