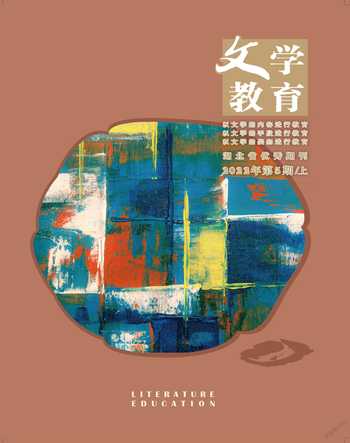安德森电影中的戏剧性研究
李梦驿
内容摘要:此篇论文主要选取瑞典导演罗伊·安德森2000年后的三部故事長片作为分析对象,分别为《二楼传来的歌声》(2000年)、《你还活着》(2007年)、《寒枝雀静》(2014年)。之所以选择安德森导演的作品是因为笔者从其作品中体认出了极强的“戏剧性”特点,如极强的程式化表演、陌生化的情境、格式化的人物等不断将他的电影推入似戏剧的电影行列中。除此之外,还将对比电影中的“戏剧性”和戏剧中的“戏剧性”之间的区别接联系,这种对比的目的不在于将两者中分出高下,而在于分析电影艺术通过何种途径达到戏剧性、产生了何种后果、电影如何产生戏剧性以及如何打消一提到戏剧性就只能联想到惊悚悬疑类电影的思维定式。
关键词:陌生化情境 格式化人物 戏剧化电影 罗伊·安德森
为什么称安德森电影为似戏剧的电影,首先以《二楼传来的歌声》为例,来举例何为似戏剧的电影。其一,固定镜头似戏剧视点,其二,演员将全身涂白似戏剧脸谱,给剧中人都套上一副苍白的面孔,暗示着在交通堵塞、漠视生命、交流不畅的现代人如何活在这样无血色的一张脸下,这种无血色表现为孤独麻木、刻薄无情。其三,非生活化场景,如电影七分三十秒所表现的,一群人推着汽车走,另一群人站在路边无动于衷看着,以及,看到有人被群殴,观看者也同样采取漠视的态度;非同寻常的交通堵塞,被火车车厢门卡住的人;医生在面对鲜血淋漓的病人时所表现的疏离与麻木;切人魔术表演时将参与者真实切中;在满是人群的地铁车厢中,大家和轰隆的铁轨声一起唱起歌剧,镜头下一秒,切到一名手持电话的女士这里,她也和车厢里的人一样,唱着歌剧。
那么,似戏剧就有“戏剧性”吗?
在关于“戏剧性”是不是戏剧独有的问题上,我们已经得出“戏剧性”非戏剧艺术独有的结论,在日常言语中,我们常常会用“这真是戏剧性的一刻”来形容某件事情的出乎意料和反转性质。生活中所表带的这种“戏剧性”可以在戏剧艺术中得以极端呈现,戏剧以凝聚的、极致的、集中的戏剧情节来实践着“戏剧性”。回到安德森的三部电影作品,笔者认为这三部电影是似戏剧的电影,但是否似戏剧就可拥有戏剧性呢?这要回到电影的本质属性上来,法国电影理论家巴赞认为“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就把电影这种物质复原的艺术打下真实的烙印,电影始终处于走向无限接近真实的世界,从演员表演、台词,分辨率,故事原型等方面均无险贴近真实,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李安导演在2016年的作品《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分辨率和摄影技术的极致追求令演员脸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清晰可见,平衡的摄影技术使用使得就算是在拍摄摇晃的车厢,观影者也还是不会感到眩晕。这种技术理性的表现代表人类想要将影像世界和人眼世界的界限尽可能地缩小,通过3D、4K、120帧高帧频拍摄&放映技术将观众带入一个无限接近“真实”的世界,正如学者李勇对新技术的评价,“李安新片的技术手段,使观众更加直观于‘现象’,缩小了电影与现实的间离感,无限接近地利用人的感知去体悟人眼前的诸多‘现象’”i。电影这种造梦艺术为的是给观众在黑暗的影院中做一场白日梦,尽量脱离戏剧所带有的程式化、夸张式表演。但安德森电影所带有的非日常化、非电影化的特征中包含着的戏剧性体现在一个接一个的反日常情境中。
一.陌生化情境
1.异化、陌生、非交流——“我们被困住了”
《二楼传来的歌声》全片陷入一种凝滞不动的氛围,连续不动的交通堵塞,摔倒在地无法爬起来的女人,被火车车厢卡住的男人,被堆砌的行李拖住的人们艰难向着检票口迸发,这一系列行径的无解和与观众的非交流性全然将观影者带入一个与日常生活隔绝开的异化的、经过精妙处理的陌生化情境中。扔掉耶稣,上帝已死,汽车从堆满耶稣像的的废墟中走过,远处突然站起一群黑衣人,向男主角这边逼近,领头一位是被蒙住眼睛的女孩。这女孩,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向跳板,坠入悬崖。《你还活着》开篇便已一个老人推着轮椅,轮椅后面拖着一只狗作为风格基调,还有吹大号的人被楼下住户用扫把攻击,“明天将是新的一天”这是这部电影里的人物常说的一句话,临上课前突然崩溃的小学老师,互相谩骂的夫妻,在迷雾中行走的人,连续不断的交通堵塞,对着空气诉说忧愁的男人,把一桌子有着两百年历史的瓷器无缘无故摔碎的男人被法庭判处电椅死刑,而观看死刑执行的人就像观看电影一样往嘴里不住地递着爆米花,在礼堂吃饭时的突然合唱,面对紧急事件的过于不慌不忙,电影总处于电闪雷鸣的极端环境里,他们整天饮酒,奏乐、漫游,合唱,好像不需要正常的生活来支撑自己一样。
2.极净、极灰、极木纳——"安坐者是可爱的"
《二楼传来的歌声》的场景设计讲求极净,无多余装饰物填充,极简的电影装饰空间将影像世界与现实世界区隔开来,好似活在电影中的人物无需正常进食、交往和生活。剧中人物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宽容者是可爱的”,陌生化的层层累积把电影空间构建成一个不在场的空间,一个置身事外的空间,一个间离的空间。影像风格的呈现方面,在装饰、人物着装、情境设置上总体呈灰调,以灰白为主,电影总是在阴天雨天的情境中展开剧情,为剧中人营造一种极端的生存环境。电影的每一秒仿佛都处于"极地"当中,随时都有下坠的危机。这种危机总是隐匿在剧中人一张张麻木的脸上和极端的情境中,观众时刻悬着一颗心,关注这种极端情境下的极端情绪何时决堤,在极端情绪的聚集中,戏剧张力犹如火山喷发。
二.程式化人物
《二楼传来的歌声》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通身涂满似日本艺妓的白粉,统一灰棕色着装,成群结队但彼此不交流,活眼神麻木独坐,喃喃自语,采取非交流性单项式交流方式,似宗教祭祀的凝重神情,在这样的人物形象塑造与包裹之中,人物的个性化被扼杀在集体的程式化面前,带着这幅面孔,好似所有的人都行动受阻,这种受阻表现为所有外化的动作都迟缓,具体在电影中,一个人乃至一群人常常静坐在某处,眼神呆滞而不知目的为何物,例如拉大提琴的人只是说自己的弦弓要换而不去换、一个人要去大楼里面找一个人而不去找、面对大楼要倒塌了女人也坐在座位上无动于衷。这种行动受阻并非哈姆雷特式——延宕而优柔寡断导致行动受阻,而是不知为何而不采取行动的受阻,但我们在每个角色那通身发白的外衣下看到这种受阻的原因,似脸谱似的白色将人物心情外化为停滞不前的。《你还活着》情绪的疏离与克制,“看”与“被看”模式中医生与患者、观众与死刑患者的两级对立关系。
三.凝固的空间
1.固定镜头:似戲剧空间
《二楼传来的歌声》安德森的电影均采取片段式的固定镜头拍摄,影片从来不采取任何推拉摇移等电影一贯使用的拍摄手法。因此这种固定的观影感受带给观众似剧院的固定视点的观剧感受,剧场在整体上保持空间位置的恒定,更不会同电影一样有景别的变更。而安德森刻意放弃了摄影机这种可以随意变更景别的能力,有意将自己的电影空间“退化”一个似戏剧空间的电影空间,演员在摄影机所限定的四边形方框里面表演,正如克拉考尔的电影“画框论”所说,演员在画框之外穿梭,便意味着电影并非是封闭的艺术,而是除却画框之外还存在万千生活的艺术。但安德森又克制了这种画框外的无限可能性,他将人物限定在四边形的摄影机、荧幕之上,人物只可在限定的空间表演,且这种表演大都是缓慢的,观众好似坐在一个不会移动的剧院椅子上,看到演员们从不跨出画框之外的表演。就连戏剧演员也开始走向观众席的时候,安德森电影里的人物却一直停在画框里。“在电影中,我们一般将由摄影机定点摄影造成的‘固定空间’和‘持续时间’,称之为‘舞台化倾向’。事实上,电影正是在不断克服这种‘舞台化’倾向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成熟的”ii。
2.戏剧空间营造
安德森的空间排列表现为极其洁净——人物缩在一角,和极拥挤——人物塞满屏幕,前者表现出个人在空间中的压抑,后者虽然人潮拥挤,占据空间,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畅和单向度式交流模式让空间充满嘈杂的压抑感。再者,人物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两极分化态势——聚集人群的一方往往是“观看”空间占有稀少的实施者,人多一方与人少一方的"看"与“被看”人物都被封锁在压抑的空间里,失去行动欲望。这种戏剧空间的制造,来源于一种朴素的回归电影本质的欲望,导演甚至想要回到绘画、回到戏剧。“他认为电影作为艺术最难实现的不是顺服电影媒介的材料特性,无休止地展现繁复华丽的视听内容,恰恰相反,导演需要驾驭和征服电影语言的滥情与无度,压制、捆绑和削弱视听材料带来的挥霍式的解放”iii。
四.结论及反思
有意味的形式决定有意味的内容,安德森通过固定镜头、程式化人物塑造和表演表现出瑞典人民从瑞典电影大师伯格曼那里继承的的某种国族性特征——质疑上帝、后现代精神危机和对人性荒芜的叩问。在电影似“戏剧”是否就等同于具有“戏剧性”这个问题上,笔者有过很大的思想挣扎,首先必须指明,电影艺术和戏剧艺术都是独一无二不可互相取代的;其二,不可认为电影隶属于戏剧;其三,电影中的戏剧性到底是戏剧性如何产生,以及研究这种戏剧性的必要性,以及电影中的戏剧性如何区别于戏剧中的戏剧性;其四,抛开电影中的戏剧性,一提到戏剧性三个字,我们就只能想到冲突和矛盾吗?戏剧性这种能指到底可以指向几种所指,如果狭隘,便会陷入思维定式,不利于理论的活跃于发展,如果过于宽泛,又存在“戏剧性”元素泛化的危机,泛化就有非专业危机,而笔者,只能讲自己感受到的对于"戏剧性"是什么的理解大致罗列出来。重点谈一下关于电影中的“戏剧性”与戏剧中的戏剧性的区别问题。这种区别来源于两种艺术截然不同的载体和传播方式,电影播放的重复性于戏剧表演的非重复性、变更性决定了电影是时间的滞后者,观看产生于拍摄与剪辑之后,观众不参与表演过程;而戏剧是共时的,观众参与表演,与舞台上的演员共享时空。所以,电影中的戏剧性必定是以观众的不在场作为前提的,这种前提在大量的排练和场面调度之下来确保任何行动的万无一失,加之电影本身就拥有强大的技术支撑作为载体,除却让画面更为清晰、更为宽广、声音更为立体,全画幅、立体声等为了更大程度提升观影真实感的技术,在后期处理上,电影可以让演员飞檐走壁,可以让火星撞向地球、可以通过特殊手段让成群的丧失逼近孤独无依的男女主角,可以让演员从高空突然坠落等,这种开掘人体极限的特技已经与格罗托夫斯基式的身体开掘完全区别开来,前者是超越生理的过分开掘而表现出某种极限性,后者表现为在在身体可控范围内的开掘而表现出某种日常性。2016年李安导演的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就将电影如何通过技术达到真实效果完成到极致。电影通过种种特殊拍摄手段、特技和剪辑将千钧一发的最具有戏剧性的时刻变现出大胆、反日常与多样性而戏剧就算借助于来自舞台上方或下方的力量,也很难将某种戏剧性场面表现出极限,例如,在一个戏剧性时刻,杜十娘要怒沉百宝箱,戏剧不可能似电影一般有真实的河流和真实的船在场,而杜十娘沉百宝箱这个动作也不会似电影拍摄一样通过全景、近景、特写大特写以及正反打来表现沉箱的水花之大、杜十娘的内心之煎熬。我们在戏剧表演中所观赏到的很有可能是杜十娘在没有水的地方沉了一个空箱子。这就表明,电影的戏剧性主要通过“合力”而形成,而戏剧的戏剧性则通过演员的一连串表演和行动来获得,前者明显带有后天的合成性,而戏剧带有天然的自发性。“动作在固定空间和延续时间中的持续发展。戏剧动作的本性之一就是它必须是持续发展的,而任何动作的持续发展都必须在具体的空间和时间中进行”iv,这就是否意味着同样的表演素材和表演情节,电影中的戏剧性强度高于戏剧中的戏剧性呢?电影所带来的真实的箱子,箱子里面可能会有真实的首饰衣服,演员还站在真实的船上,船行驶在真实的河流上,蒙太奇递进、场景变更加强杜十娘这一动作的戏剧张力,而在戏剧表演中,所有这一切的发生不带有拼凑和断层,是一系列的连贯性动作。“电影剧作家的才华恰恰表现在,对镜头的特性及其组合方式具有很高的铭感,在选取素材、剪裁、加工的过程中,善于把握银幕时空的特性,善于把众多人物的松祚、冲突、清洁,纳入到各种镜头及其组合之中,使它们在流动空间、构成空间和各种‘时间蒙太奇’之中发展下去”v。但戏剧性是否在这种种差异中产生高低之分了呢?笔者认为没有,电影的观赏者对于荧幕上发生的一切都有安全的一面屏幕作为安全保障,这种安全保障在于,就算电影里面的丧尸正在向"我"走来,也有那层屏障保护着我不受威胁。而戏剧表演的现场性在于,演员与你之间没有了那层屏幕的区隔,所有的情绪、威胁和颤栗都在共时中产生,笔者以《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的电影版和戏剧版作为比较就可得出两者在优劣方面的互相抵消。德国表现主义电影《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以其夸张的造型、诡异的影像风格、超现实的布景为观影者营造出一种彻骨的恐怖观影体验,但这种恐怖的体验往往是滞后式的,卡里加里博士不曾真的存在于你的身体周围,他只是幻化成一个影像,从脑海中时常闪现而造成回忆惊悚,这种惊悚体验完全是图画、影像时代才具有的虚假性惊悚——你对一个陌生的、不存在的人产生了恐惧。反观剧场版《卡里佳里博士的小屋》,笔者借鉴来自友人在乌镇戏剧节上的观剧体验作为分析素材,她告诉我,“卡里加里博士穿着黑色的袍子,隐现在观众席中,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从观众席中站起来,这已经就引起了不少尖叫,然后,卡里加里博士对我们说‘谁是下一个?’我真的要吓死了,他(演员)真的太像卡里加里博士了”,在剧场表演中,观众见到了“真实”的卡里加里博士,他走路时飞舞的的袍子可能还打在了观众的身上,他说话时所喷出的热气可能在某个观众的背后发颤,他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卡里加里博士。经过对比,剧场版的卡里加里显然带给了观众即时的、可触的、可视的、活灵活现的颤栗和惊悚,而电影虽然通过景别变换的所带来的强度是抵销不了剧场所带来的这种生命力和鲜活程度的。综上,电影所带来的有强度的戏剧性可与戏剧剧场所带有的现场性所产生的戏剧性相抵消。
注 释
i李勇,《电影技术的维度——由李安新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说开去》,《当代电影》2017年第1期)
ii谭霈生,《‘舞台化’与‘戏剧性’——探讨电影与戏剧的同异性》,《电影艺术》1983年年第7期
iii肖熹,《嘲讽在静默中冷却——罗伊·安德森的荒诞美学》,《电影艺术》2016年第4期》
iv同2
v同2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