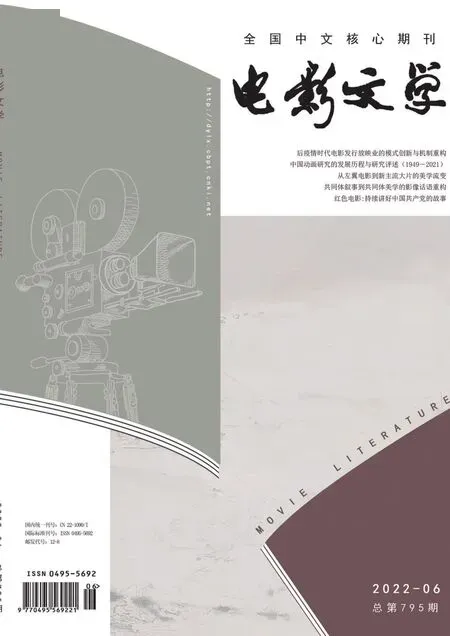共同体叙事到共同体美学的影像话语重构
赵书豪 卢兆旭
(喀什大学人文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0)
一、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共同体叙事的赓续
《奔腾的托什干河》(以下简称《奔》)根据全国人大代表、道德模范库尔班·尼亚孜的先进事迹为创作原型,影片叙事时间长达四十载,叙事空间横跨中国版图的东西两端。主人公阿里普用四十载时间参与见证了南疆小村镇的文明化进程,描绘出广袤南疆地区在千禧年前后所经历的前所未有的时代与文化变迁。电影语言叙事展示了民族地区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体现国家脱贫政策改变了新疆最偏远区域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双重渐变历程,是国家意志与民族命运交互作用的共同体叙述。
新疆电影创作生态与其国家地缘政治环境之间相互连缀使得弘扬主旋律命题成为新疆题材电影的底色。自较早期体现边疆反特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到新世纪的大历史题材《和平将军陶峙岳》《整编岁月》《翻身》、援疆题材《大漠青春》《塔克拉玛干的鼓声》《漂着金子的河》《远去的牧歌》《昆仑兄弟》等类型片均不乏主旋律电影“独有的特征和不可或缺的界定: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具有浓厚思想教育意义的故事片”。《奔》的题材构成延续了这种现实主义共同体叙事特征。按照以往影片划分标准,《奔》以白描式电影拍摄手法表达出一个少数民族青年精神反哺的故事,当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主旋律类型片。值得注意的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与“主旋律电影”两个述语虽本质仍是国家意识的体现,但现实语境的更变已然转化了最初的“主旋律”指称,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是“主旋律电影”在向“主流电影”靠拢,融主流市场与主流价值于一体,如“战狼”系列、“我和我的……”系列的家国情怀与奋斗精神焕发出强有力的情感投射与价值感召;《湄公河行动》《长津湖》等将政治奉献主体“人情化”,力求思想性与艺术性、文化产业与商业机制的弥合,从而剔除原有主旋律电影的修辞显在性,这是“主旋律电影”的一种新变。此外,关于少数民族影片命名,“从‘少数民族电影’‘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再到‘民族电影’等,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悄然经历了一系列的知识转型”。可以看到的是,少数民族影片始终在这种概念交叉中寻找本区域电影自身的指称,其背后的价值关联是此类题材电影如何展现国家意识在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有效呈现。新疆题材电影也不例外,尽管新疆电影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局限,但并不妨碍新疆电影在时代发展的“新”与“变’中寻求一种共同体意识的阐释。
回到《奔》,与其说它是一部主旋律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不如说它是一部共同体叙事的边疆电影显得更为贴切。“边疆电影”立于全球视野及互联网传播的当下,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电影”“少数民族电影”在面对“外国电影”时所面临的“民族”指称模糊的问题。回到本土电影划分体系中,“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与“边疆电影”概念界定与衍生还须更进一步地厘清。在此将《奔》归于“边疆电影”除去一种形式平等的表述外,还缘于影片所展现出来的“跨域”“跨民族”及“跨文化”的叙事表达以及其小众性传播现状。不同于一般少数民族电影无跨域镜像构成的将叙事地定格在少数民族同胞生活区域之内,彰显少数民族人文精神及文化特质的主体性叙述特征,《奔》中的男主人公阿力普的成长故事穿梭在两个异地空间里,一个叙事空间为南疆地区,另一个叙事空间是上海;一边是奔腾的托什干河,一边是风云自如的黄浦江岸。同时,阿里普与童玲的情感交织本身便隐喻着汉维两种文化的吸引、碰撞与融合,两个非同族的青年为新疆的现代化建设奉献出青春,对“共同命运”的合力担负以及朝向文明的生命自觉将主旋律修辞话语衍生为共同体叙事的温情表述。严格地按照以往的少数民族电影划分标准,这种“跨域”“跨民族”“跨文化”的共同体叙事已无法寻求到合理的界定表述,鉴于“边疆电影”的话语表述尚未成形,有很大的待补充空间,将《奔》归于“边疆电影”保留了对该影片继续阐释的可能性。从“边疆电影”的共同体叙事中可以看到《奔》在赓续以往新疆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创作方法时有所变通,青年求新求变的成长史到反哺家乡的“根文化”无不是一种“共情化”的情节构建。这种共同体叙事方式的转变是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糅合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一种尝试,在当下意识形态空间里,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无疑要彰显中国立场、中国价值与中国精神。更进一步,无论是放置于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电影”或是本土视野下渴求“走出去”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求得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互证实为其持续摸索的路向。
二、共同体意识下多元性电影创作语言尝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围绕民族团结与边疆建设的社会功用是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艺所必须担负的使命,也鉴于早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基础较为薄弱,本民族创作人员极为匮乏等现实局限,大部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由汉族导演执导、汉族演员主创、汉语表达并借由少数民族地区自然人文景观反映一定国家叙事与价值导向。随着新世纪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蓬勃发展,尤其是2005年之后“母语电影”成为民族题材电影一种新的呈现方式,如《碧罗雪山》《鲜花》《塔洛》等优秀母语电影的出现使得多民族文化视角与多民族语言融入表现为一种“原生态”艺术特征,抓住了观众审美需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一直以来被冠以“小众电影”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与商业市场之间紧张关系所致的拉裂感。
较传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而言,“母语电影”最突出的特点是将民族创作演员与民族语言对白进行黏合。传统译制机构为保证通用语言传播政策的落地,将民族语言译配为普通话后出现“视”“听”不同步的观影感,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不得不在艺术表现上留有遗憾。当下,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及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显得尤为紧迫,少数民族区域包括五个自治区及云南省,其多地处祖国边缘接壤众邻国,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途经区,特殊的地缘位置使得“母语电影”或“成为呈现国家形象的重要文化资源,其所表达的文化诉求以及在表现少数民族精神气质、民族文化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并且在市场化、国际化的历史大背景下有可能在中国电影对外传播战略中充当领头羊,发挥积极的作用”。由此,当下“母语电影”的输出势必以民族融合与民族文化多元化发展为基调的中国影像带给世界以中国印象。从少数民族视角出发,电影创作语言的多样性是一种文化兼容、文化认同的共同体审美表现,民族语言的合语境表达“使少数民族母语凸显出来,在电影中成为少数民族族群向内凝聚的绝佳黏质……对于少数民族观影者来说,更是一次身份认同的镜化演绎”。此外,艺术创作语言须考虑合语境的创作生态,电影尤其如此,作为一种电媒信息传播艺术,不同于纸媒较线性的呈现特点,其本身具有一种直观性,几乎不需要阐释,双通道的感官体验直接沟通影片与观众。弗雷格的“语境原则”认为“一个词只有在句子中才有意义”,同样,一种语言若脱离原有的语境是否能够保证其信息传达的完整性?语言之外的非言语语境在判断意义中又充当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或许“母语电影”给出了一些探索,像外国电影的输入在跨语言的观影环境中仍然得到观众的热烈追捧,如《沙漠之花》《何以为家》《摔跤吧!爸爸》等均收获了很高的上座率。这是民族题材电影在文化叙事的同时如何兼顾文化语境所需要考虑的问题。由此,民族题材电影创作中的合语境化语言译配显得尤为重要。
于新疆电影而言,“母语电影”的发展仍需一段过渡时间。前文提到几部新疆影片中,反映哈萨克民族“阿依特斯”文化特质的《鲜花》是一部母语制作片,其余的如《远去的牧歌》《昆仑兄弟》等仍保持着原有普通话译制风格。而《奔》的创作语言融合了母语与普通话,在共同体意识建构下兼顾母语语境真实性。影片中对母语的自然呈现以及维汉因缺乏统一的语言导致交流受阻的画面真实深刻,我们可以看到语言障碍成为南疆闭塞落后、发展缓慢不可推脱的一个因素,语言影响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而教育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地区的发展,代际之间无法生发出新的变革力量与中国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征程呈现出不协调。影片用慢镜头方式突出一块普通的香皂,童玲拿给阿力普的不仅是可以清洁皮肤的生活用品,更是一种代表着“文明”的象征物,在童年阿力普心中留下深深印记。深切感受语言所带来环境闭塞及发展落后的阿力普在上海高校毕业之后重返家园,成为一名推广国语的教师,身体力行普及国语,推广文化,更明白国语教育对下一代、对这片故土的意义。可以理解影片中的多元性创作语言尝试有突出国语普及主题的客观性需求,但也不乏影响力与观赏性双结合,它表现出了原汁原味的南疆村落,记录了这些村落的发展变化。“我们看新疆题材的电影,不仅要看大美新疆的景色、新疆景色的风情万种,更要看新疆的人文,新疆各民族人民对共同的精神家园、情感家园的建设和追求”,南疆地区尤其如此。走出“母语电影”的纯民族主体性叙事、传统“民族题材电影”的强意识形态宣传,《奔》在共同体意识构建下对创作语言进行多元糅合,其镜像语言合思想性选择及合语境化表述是在共同体叙事中探寻共同体美学的一种尝试。
三、少数民族艺术形象的共同体审美表征
少数民族艺术形象似乎是讨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区域电影”时始终无法绕过的命题。在界定什么是“少数民族电影”时,有研究者参照地缘学概念界定,将少数民族艺术形象与其他艺术形象做了二元划分。当然,这种关系的阐明语境是研究者基于十七年电影创作实践给出的定位,在当时确实反映出了所谓的“少数民族电影”表现特征与表达困境。相形之下,当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多元丰富的少数民族艺术形象展现出了少数民族地区新镜像面貌与共同体表征。
谈论少数民族艺术形象,还要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之初面貌说起。新中国早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无母语呈现,鲜有民族演员参演,主创组多汉族同胞的创作生态无法从内视角给予少数民族文化以切实的关照,这是无可厚非的历史局限,限于我们电影业发展不够成熟。随着电影进入市场,开始自我调整以适应商业生存机制;同时,“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班底展现出新面貌,有了经过专业化训练的本民族导演及演员。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创作团队制作的影片中确实对本民族文化有着潜意识表露,使少数民族影片艺术性更为突出,丰富了多元文化的镜像呈现。也正是民族导演执导,民族演员参演表达本民族文化精神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出现,使以往的汉族导演执导民族演员参演的影片抑或汉族导演执导汉族演员参演的民族影片其“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身份的合理性受到质疑,质疑声之一就是所谓的非少数民族制作身份塑造出的少数民族艺术形象不足以代表或难以真实展现少数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特质。所谓的非少数民族制作身份,首先从形式上将地域与地域、人与人做了主客体之分,再将主客体视角对立,从而形成了所谓的非原生态少数民族艺术形象,这种质疑声本身便是一种质疑,其逻辑原点缺乏一定的可推理性。任何一种少数民族文化都具有流变性与更替性,它不是一种形式固化的物态品,尤其在中国这片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大杂居、小聚居的土地上,在共同体建构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形态下,所谓的“原生态”少数民族艺术形象,其能指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难以找到恰如其分的所指。少数民族艺术形象中的共同体表征或许使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国家想象、精神依赖及文化选择更具可能性,同时亦避免了出现部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为了迎合观众的猎奇心理而陷入“异托邦”叙事的旋涡里。影片所呈现的“少数民族”桃源乡土抑或“香格里拉秘境”均是“在一个真实的空间里被文化创造出来,但同时又是虚幻的东西,即它并不是你所认为它是的东西”,这种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偏离了其创作初衷。
少数民族艺术形象成为共同体表征是《奔》很突出的一个特点,虽然影片是汉族导演执导民族演员参演的创作模式,但整个故事叙事方式及合语境内容表述均是以内视角的方式展开,不再重复以往如汉族人帮扶少数民族进行社会转型等模式化叙事。它反映维族青年的自省、自觉,以教师身份、革新思想兴教育、兴家园的生命价值追寻。南疆与上海两个空间带给阿力普的生命体验使他深刻体味到故土文化守旧所致的愚昧,他目睹了玛伊莎毫无选择权地嫁给吐尔逊,将孙女传染病视为咒语并拒绝就医的维族老奶奶,一群有形无形之中被剥夺接受现代化教育的“国之少年”。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封闭的文化圈势必会导致落后,文化交流互通促使文化不断进步。阿力普意识到了这种规律,先觉醒的人成了改革的先锋,在沉睡的村庄中跨过重重阻拦,试图通过国语普及与现代化教育为族人打开通往世界的通道。“在新疆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亦即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过程中,阿力普这一艺术形象不再是个单一化的带着韧劲与冲劲的新疆巴郎子,而是在“文化共同体”的现实交流中透露着多元文化视角的新时代边疆建设者,其本身是共同体文化的表征。少数民族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不论是自发的觉醒抑或非自发的觉醒都会经历一段艰难的变革期,自发的觉醒通过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融合对本族文化自省、自查、自建,以达到一种新的文化态势,也只有自发觉醒才能对自身发展的方法与路向有更为切身的考量。阿力普建立国语小学的实践证明国语的普及确实有益于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及南疆的现代化建设。“国语”及拥有多元文化视角的阿力普均呈现为共同体审美表征,南疆镜像里的人民生存面貌也不再是所谓的汉族导演无意识中的非原生态少数民族艺术影像,童玲也不是单以启蒙者的身份出现在阿力普的生命里,而是与阿力普共同担负南疆社会转型使命的青年,南疆的“命运”成为中华儿女的“共同命运”。
四、集体理想与个体意义的共同体审美互证
集体概念是大历史叙事题材核心要素,个体置于群体中保卫其所共生同存的国族山河以完成承递历史的使命。随着意识形态变迁、社会生存语境变更以及现代性所带来的较为强烈的个体生存意义唤询,主旋律电影题材中的大历史叙事与小个人叙事紧密结合,“大我”与“小我”合体,集体意义与个体意义相互依托、相互胶着表现为集体理想与个体意义的共同体审美互证。早在20世纪末电影转型期,尹鸿的“泛情化”叙事策略便对主旋律电影这一悄然转向做了翔实的论述。他赋予“泛情化”两个阐释特征:一个是“对国家意识形态的伦理化处理”,另一个是“使影片主人公平凡化”。可以看到,“泛情化”的叙事处理方式是电影进入市场后对观众审美心理转变的直接回应,远行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观众也远行在个体价值意义探寻中,将集体理想与个体意义结合是大历史叙事的现代化演变,契合大众的时代心理。当然,我们并不能将这种艺术形式转变单纯归结于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双峰对立,其更多的是一种文化自觉,“作为民族文化进步准则的,也只能是对人的价值的认识”。
距离尹鸿提出“泛情化”叙事策略已20年有余,不难发现,当下主旋律电影或多或少仍体现着这种叙事手法。同文学转型一样,康梁时代觉醒的“民族—国家”意识及“五四”觉醒的“人—个体”意识在文学文本中是未完成的书写,当代文学一直走在接续书写的路上。主旋律电影亦是一部未完成的影像,集体叙事向个体叙事的兼容是其叙事革新中的一部分,顺接中国社会发展持续转型的特点也顺应观众审美心理的适时转变。回到《奔》的审美转向上,它不再是一个单纯集体叙事、英雄叙事或模范叙事,尽管影片原型确实是一个可以被称作“英雄”的模范式人物,但影像表达一直有意无意地剥离神圣化的、人格神的“英雄”语境,甚至在影片宣传片上都印有“每个人都可能是平凡中的英雄”。少年阿力普受红色电影影响立志长大后做一个英雄;青年阿力普面朝闭塞落后的土黄色村庄,望着一群眼神空洞的人间精灵,发出“我找到了比做英雄更值得做的事情”的呐喊,这是影片中两个极具震撼力的镜头对比。从红色电影中的保家卫国到世纪末的现代化建设,各自时代有着各自时代的英雄。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与长期性决定了一个当代“英雄”所面临的可能不是轰轰烈烈的生死,而是在纷繁复杂的变化中以持之以恒的韧劲推进现代化建设,这种时代特质也从某种程度上表明21世纪“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主旋律美学风格势必会从单纯的集体理想审美转变为集体理想与个体意义的共同体审美。
从本质上说,集体意义到个体意义的审美转向并未否定集体意义社会功用。集体理想、集体叙事在强化国族意识方面有着先天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具有不可替代性。讨论《奔》的去单纯化集体意义的审美表达及对集体意义与个体意义回环式衔接的艺术融合是基于共同体美学的一种考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加大中国文化传播的当下,新疆电影不只是拍给新疆人看,中国电影也不只是拍给中国人看。中国电影“走出去”,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走出去”无可避免地要考虑影片所承载的形式或内容的共同体美学意义,但什么是“共同体美学”或怎样体现“共同体美学”是当下学界的一个重大课题。以《奔》言,我们似乎可以窥见星点要义。就影片叙事情节,一个普通南疆年轻人自醒后困于家园落后闭塞的现实环境而进行的精神反哺,有两个燃点扣住了观众心理。第一个是故土情怀,第二个是困顿青年的理想与抱负。中国人的心中始终埋藏着浓厚的故土情结,这是血脉里的文化因子,生于斯长于斯的情感使无数国人愿为家园建设奉献自己的力量。其二,对个体意义的追寻是青年人日常困顿,影片中童玲将生命留在了义诊路上仿佛打开了阿力普的情感闸门,他放弃了沿海地区优渥的生活重返家园,将个体生命嵌入那片土黄色村落里,嵌入故土现代化建设中。合大众审美心理的故土情怀及合时代心理的个体意义追寻使得《奔》的呈现效果与众不同。就影片的叙事审美而言,阿力普个体意识的觉醒缘于集体意识、共同体意识的潜存。影片中阿力普童年时“为人民服务”的理想转换为青年的扎根文化脱贫的现实抉择,以个体的行动推动南疆村落的国语普及,将个体命运嵌入家园命运是个体意义对集体意义的原子化,亦是个体担负集体使命可视化、可实施的现实指称。集体是关乎人群的,个体是关乎人的,实际上,从集体叙事向个体叙事的兼容是个体叙事的主动回归,是集体叙事的丰富延展。从《奔》中家国理想与个体意义的互为、互卫中,不难发现,当下主旋律电影创作生态与生存生态中,集体理想与个体意义的胶着呈现与镜像共生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二者于主旋律电影中的共同体审美互证。
《奔》在模式化的新疆电影中表现出一种新面貌:“跨域”“跨民族”“跨文化”的共同体叙事、共同体意识下的多语言制作尝试、少数民族艺术形象的共同体表征以及集体理想与个体意义互为、互卫所形成的共同体审美互证。从《奔》看新疆电影,地缘上新疆处于祖国边境,亦是丝路重要途经地;文化上新疆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交织的地方,其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当下意识形态里,中国话语体系构建及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尤为紧迫;同时,边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任务艰巨。故新疆电影毋庸置疑要赓续共同体叙事,“‘共同体’所带来的稳定性、安全感、归属感,它所强调的人的整全性和‘共同的关怀’,具有先天的伦理优先性”,然实现共同体叙事到共同体美学的影像话语转变或是一条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