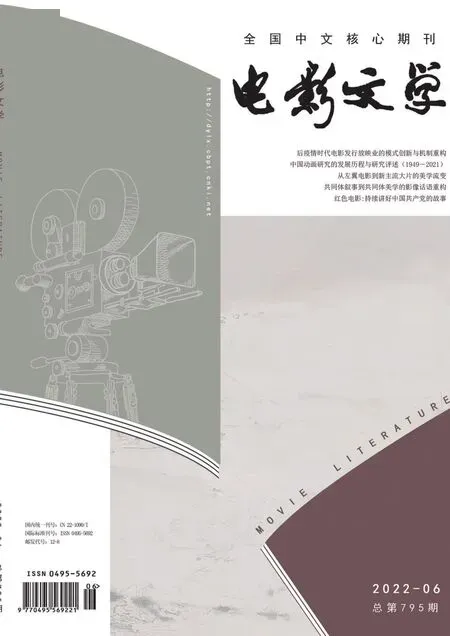生态美学视野下数字奇观电影之场所美学
方 丽
(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儿童IP中心,北京 100080)
一、相关概念
(一)数字奇观电影
数字奇观电影因其更为奇幻的叙事、宏大的场面、逼真的动作、独特的造型、多元的声音而吸引了观众的眼球,刺激着观众的感官,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观影体验。由此,奇观电影的概念应运而生,特指“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美国好莱坞形成的、以营造‘奇观性’为核心,利用数字技术创造出具有强烈视觉吸引力的奇观影像来呈现富有想象力的奇幻故事,从而形成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大范围传播的电影”。数字奇观电影指利用数字技术创造出来的电影,从而与非数字化的奇观电影做出区分。数字化媒体技术为电影创作和美学探索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成为近年来主流的电影制作方式。数字技术所带来的影像美学变革主要表现为三方面。首先,数字技术将电影中虚拟世界赋予了强烈的真实性,例如以《阿凡达》为代表的沉浸式数字技术更是为人类感受虚拟真实带来革命性的感官体验。其次,数字技术拓宽了电影创作视野,题材更多元,视听元素更丰富。最后,数字技术缔造的奇观化影像既能满足观众的视听快感,又能参与叙事表达,对于表达本文所侧重研究的生态议题电影具有天然的优势,成为观众最喜爱的电影形式。数字奇观电影按照其主题和风格可以分为科幻电影、魔幻电影、动画电影、灾难电影等。本文选取了具有鲜明生态审美内涵的数字奇观电影来深入分析数字技术所营造的场所意识和美学特征。
(二)生态审美之场所美学
20世纪80年代生态学迅猛发展并渗透到其他学科中,它与美学相结合形成了生态美学。生态美学的产生是一种现实的需要。现代工业革命发展的负面因素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思想造成了人类对自然环境及生态的严重破坏,因此,生态美学是以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作为研究和考察的对象。本文重点在于在生态美学范式指导下揭示具有生态整体主义观念的数字奇观电影中所蕴含的场所美学。
场所意识最早由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是一种和个体感受、生活与环境具有密切联系的生态审美意识形态。场所意识也是关于人之存在的重要理论。海德格尔这样界定场所意识:“我们把这个使用具各属其所的‘何所往’称为场所,依场所确定上手东西的形形色色的位置,这就构成了周围性质,构成了周围世界切近照面的存在者环绕我们周围的情况”“这种场所的先行揭示是由因缘整体性参与规定的,而上手事物之来照面就是向着这个因缘整体性开放出来。”场所可以理解为人生存于其中并产生紧密关系的物品的位置与状况。海德格尔认为人在生活中总要接触到很多物品,而这些物品与人会产生一种因缘性的关系,统称为“上手的东西”,分为“称手的东西”和“不称手的东西”,分别指向了良好的因缘和不好的因缘。那么人所处环境遭到损坏,“属于极端‘不称手’的情况”,是不利于人生存的、不好的因缘之所。对于这类“不称手的事物”、不利场所的展现成为数字奇观电影创作展现其批判性的一面。
二、场所破坏与人类迷失
对于极端“不称手”情况的批判是诸多灾难奇观电影的刻画重点,从负面典型入手强化生态破坏之丑陋,从而使人们对习以为常的空间场所产生认知,其深层隐喻在于揭示人类精神的迷失。
在灾难奇观电影《后天》中,人类赖以生存的场所被悉数毁坏,极端气候所造成的自然破坏对人类造成了极度的危害,就连图书馆这种承载着人类文明传承的场所也遭遇被淹没的危险,最终成为电影中拯救幸存者的避难所。最终在营救人员到来之前,图书馆彻底被冰冻起来,除了点燃书本获取温暖的壁炉闪动着一些火的微光,整个图书馆成为一片死寂的冰冻场所。冰冷的画面、黑暗的场景、拥挤落魄的人群、绝望恐怖的神情,这幅末日图景传递出具有强烈批判与警醒意味的景观。人在恶劣天气肆虐之下,蜷缩在炉火前生死未卜,体验着本能性的互相取暖,将人的存在带回到一种原始状态。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破坏的不仅是场所,更有可能导致人类整体文明的毁灭。图书馆最大的价值在于其文化承载所彰显的精神价值,导演在此想要警示人们只有不断提高人类的学习能力和生命觉知,才能提升生态理念和环保意识,从而实现真正的自我救赎。
中国数字奇观电影《美人鱼》中虚拟出的场所奇观“青罗湾”,是鱼人族在世界上最后的栖息地。在刘轩为代表的房地产开发商的破坏下,人鱼族不堪声呐的强大干扰性和破坏力,不得不躲避到这个狭小的场所——人类遗弃的一艘破船中谋求生存机会。在这艘具有工业化和消费社会双重意味的废弃船只上,布满了种种人类丢弃的物品,诸如蹦床、轮滑轨道,甚至还有一个“海鲜酒家”的霓虹灯牌,充满了讽刺的意味,一派废土与蒸汽朋克糅杂的美学气质。对于人鱼族来说,选择在这样充满“不称手事物”的场所居住,实属无奈之举。青罗湾这个破败的角落,揭示出的是人类社会在谋求高速发展的时代,对生态环境和非人类生命的漠视与懈怠。青罗湾的场所破坏景观与人类尊享的现代都市景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通过一系列情节细节展现得淋漓尽致。
当珊珊第一次引领观众到达人鱼的栖息地时,一个人鱼族孩子泡在充满药水的人类遗弃的澡盆中,浑身都是鲜血淋漓的伤口,人类对于海洋的破坏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其他生命种群的健康。导演采用直观形象的方式,将血淋淋的事实暴露给观众,揭示出生态恶化导致的悲剧。船只——这个临时的避难场所,也曾经是人类征服自然的航海工具。在电影中人鱼族长老幻化出一对水流组成的特效船队,她控诉着每一次人类发现人鱼族的踪迹,均开始大肆捕杀,他们只有远离人类,但后者却总是变得更加狂躁凶狠,对于人鱼族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赶尽杀绝行动。鱿鱼精也泣血控诉道:“现在他们把声呐放入海里,我们避也没法避!”电影特效用水流、晶莹剔透的奇幻动画美学方式展现出人类船队、原子弹爆炸等场景,将人鱼族对工业化和核武器滥用所构成的威胁精准地表现出来。
然而,船舶这个临时避难场所也并不安全,随时面临着被人类发现并彻底驱逐的危险。逼仄的空间、拥挤的人鱼、四处充斥着废弃物,这个场所蕴含的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不好的因缘关系”。最终这个临时避难所被人类发现并遭到了残酷的武力袭击,多条人鱼在纷乱的枪击中丧生,废弃船只成了一片血的海洋。导演通过展现人类对场所的破坏和对人鱼族的残酷屠杀指引观众进行更为深入的生态反思。在影片中,科学家代表只关注研究人鱼族所能带来的科学价值,漠视珍贵的生命,忽视人鱼族的种族延续,是导演对彻头彻尾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典型讽刺。人类膨胀的欲望吞噬了人类自己,也毁灭了人鱼族的诗意生活,而对场所的破坏正是人类自我迷失的揭示。
在《百变狸猫》中,人类对于狸猫生存场所不断侵扰和开发,迫使狸猫们做出种种反击。在一项政府颁布的城镇开发计划下,一座座青山的植被全部被挖空,取而代之的是密密麻麻的人类建筑。接下来,导演采用非常具有动画创作思维的镜头设计,深化了这种过度开发的艺术表现。一片绿色的树叶,上面布满了如蚂蚁般密密麻麻的挖掘机、拖拉机等工地用车,它们不断蚕食绿色的叶片,留下一个个触目惊心的大洞,仿佛是害虫在破坏绿植一般,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的不断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幅画面设计,形象而深刻地体现出了导演独具匠心的表达和生态美学内涵。下一个镜头更具深意,一尊大大的卧佛占据了画面的上半部空间,几个小和尚在摆弄着人类市镇所占据的生活场所。人类打着发展和善念的幌子,忘记了曾经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和原初生命的万物有灵观念,以神的姿态自居,毫无节制地破坏着非人类生命的生存场所,这无疑会遭到自然更激烈的反抗。人类在商业和发展面前迷失了自我,导演用这种“神明”视角提醒着人们,人不是万物的主宰,应该在发展自我的同时以更高远的眼光看待人与自然场所的关系。整部电影的叙事,都因为这种场所被破坏的外在力量而持续推动着,狸猫们最终不得不采取一次又一次对人类行为的反击,且不说反击的效果如何,这些有组织的行为本身就代表着自然在无节制的破坏面前并不是一直忍气吞声、任由宰割,迟早有一天,会用某种形式来警醒人类。较为极端的案例可以参考生态灾难电影中自然对人类的反噬,如《完美风暴》《天崩地裂》《后天》《2012》等经典作品。
在我国的一些数字奇观电影中也通过东方美学的构建表现场所的破坏和人类迷失,中国的电影创作者也进行了宝贵的尝试。如《大鱼海棠》中下沉到大海中的异世界,是椿所生活的重要场所。当椿违背自然规律偷偷养了鲲的灵魂之鱼后,场所中发生了种种奇怪的事件——夏日降雪、海水倒灌、暴雨骤降。过去万般温馨美好的场所均被破坏,象征着祖先精神的牌楼牌匾被洪水冲走,人们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对场所的破坏推动着故事情节向前发展。主人公需要更高的使命感、更强烈的牺牲精神去改变这样极端的局面。在和谐—和谐被打破—重归和谐的故事结构模式下,场所的破坏推动着叙事进展,激发观众产生对重归和谐的向往和期待,这也是对东方传统生态美学观念“天人合一”的美好憧憬。“天人合一”是东方式的人和自然和谐与共融之美,“是‘道法自然’思想所指向的生态全美之境,体现出了道家的生态审美智慧。在天人合一境界中的‘与物无际’‘万物与我为一’,这种道境中的美是超越了对物的美丑判别的全生态的无言之大美”。“天人合一”中蕴含着整体联系、动态和谐生态整体论审美内涵。
三、场所美学的情感关联
空间就是场所,是“此在”在世之“世界”。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理想的空间化或场所意识即为真理广泛传播和栖息不受到干扰——“空间化为人安家和栖居带来自由和敞开之境”。数字奇观电影对于表现理想的场所之美有着天然的优势。对场所意境之美的追求成为数字奇观电影的审美特征之一。例如在《飞屋环游记》中,创作者选用了明亮艳丽的色彩来勾勒整体电影气氛。卡尔和艾莉所居住的小房子被导演设计成清新自然的淡绿、淡黄等颜色,屋子里摆满富有生活气息的小装饰,桌子上摆放着两人的照片、玩具小鸟,艾莉还亲自手绘了一面彩绘墙——美丽的天堂瀑布边上有一座跟他们的房子很相似的小屋。这个家宅空间就是卡尔和艾莉爱情的最好证明。这体现出一种场所美学中的情感性,交织着体验、记忆和想象。著名的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在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和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的基础上,研究人与场所之间的主体性关系,主张一种空间研究的“场所论”——空间是与人的存在直接关联的世界。场所作为人类精神意识的栖息地,具有体现人之想象、记忆和感知的价值。
在《飞屋环游记》中,承载卡尔记忆的记忆之场所,将过去引入当下,在爱的空间中被保存,记忆被唤起又被重新构建为一种情感流动。当小屋面临被拆迁的命运时,卡尔甚至突发奇想用五颜六色的气球将这个精神场所带着飞向高空,他为了延续对艾莉的爱,为了实现妻子生前的梦想而出发。屋顶的小鸟是飞屋的风向标,颜色明丽的窗帘做风帆。飞屋体现出作为一种理想化场所之美,它与高空蓝天、郊野绿地融为一体。坐在自己的家宅之中,卡尔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他归属于这个熟悉的场所,感到理想实现的自在和惬意,家宅的腾飞与对妻子的爱将电影的情绪推到一种新的高度。
当飞屋遭遇雷电袭击时,尽管屋内陈设被损坏,但是卡尔仍然不离不弃,积极抢救。人和飞屋实现了物我一体,飞屋具有了女性主义的母性色彩,是对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 1884—1962)在《空间的诗学》中所描述的涉及风暴中心住所的视觉表现:
“家宅英勇地斗争着。起先它发出呻吟:最猛烈的风从四面八方一齐向它袭来,并夹杂着强烈的仇恨和狂怒的吼叫,我害怕得一阵阵战栗。然而家宅坚持着……而家宅早已成为人性的存在,我的躯体躲避其中,家宅丝毫不向风暴屈服。家宅把我紧紧搂在中间,像一匹母狼,有时候我感到她的体味如母亲的爱抚直达我的心房。”
飞屋和卡尔互相保护,每当飞屋遇险即将飞走时,卡尔总是用尽生命的全力拖曳着这座爱的家园,并深情地说:“艾莉,放心,我会抓住的。”孤独的家宅赋予了卡尔坚强的形象,也是他抵挡一切艰险的后援。在寻找梦想的过程中,诞生于家宅的场所意识从一种单纯的感官体验进入精神世界,与情感紧紧地关联在一起。影片最后,卡尔逐渐敞开心扉,他和艾莉的爱情随着飞屋一起永恒地停靠在天堂瀑布的顶端,成为最诗意的风景。他对大自然的热爱、对曼茨无限掠夺自然的欲望之批判都是基于场所意识所体现出的更深入的生态美学内涵。
与此相反的是,《百变狸猫》采用反面对比的方式刻画出都市场所对于狸猫们无法产生归属依恋的矛盾。化身为人类身份进入城市生活的狸猫们并不能适应新的场所,他们找不到安全感和归属感。这些情节安排可以看作一种对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合理反思,人与生存场所根深蒂固的情感关系与紧密连接在快节奏、高压力的发展进程中变得愈加脆弱。虽然狸猫们也可以适应人的身份去工作,但城市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个谋求生存的地点,远远不能产生一种基于情感角度的依恋。他们只是找到了一种临时栖身之所,却无法在城市中获取归属感。因此,他们在夜晚仍回到大自然原本的家宅中休息,他们与田园有着天然的亲近,是一种场所美学下的生态审美生存的追求。
在重点呈现人类精神生态的动画奇观电影《寻梦环游记》中,导演通过两种世界——现实世界和亡灵世界中多样场所形态构建的叙事美学,勾勒出一条寻求梦想与回归家庭矛盾冲突的解决之道。两种世界中所呈现的典型场所,打造出独具墨西哥风情的承载家园情感的视觉空间,主要包括梦想与亲情冲突上演的家宅场所、现实与亡灵世界的穿越场所以及寻求梦想与亲情回归的亡灵场所。空间场所对于情感的建构和情节叙事起到了唤起、激活、嵌入和生成的作用,借助主人公的知觉体验、小镇居民的集体记忆和亡灵幻想世界的情感信息,场所空间关联时空耦合,以奇幻、温馨、充满美感的视觉设计塑造出人物对于场所的依恋关系——一种紧密的场所归属感和认同感。
首先,现实世界中米格的家宅场所,是亲情的汇聚之地。错落有致的小院子里有大人们眼中维持常态生活的制鞋工坊、有祭祀先祖的祠堂,还有个人化的生活空间如太奶奶的卧室、米格内心梦想世界外化的物质空间——隐蔽的小仓库。从视觉设计的角度来看,祠堂的布置温馨而充满神性,装饰着各种亡灵节传统饰物,有万寿菊、蜡烛、水果、先人相框等,融合在一片橘红色的氛围中。在这个场所里,奶奶跟米格强调着家庭和亲情的重要性。毫无疑问,祠堂是家族集体记忆与情感的寄托之所。也正是在此,故事埋下了悬念——祖母Coco爸爸的照片被撕掉了一角。此外,仓库中昏暗而温暖的小屋,是米格内心世界的外化,这里摆放着歌神德拉库斯的雕像和海报、墨西哥传统剪纸拉花、代表音乐之梦的胶片和一台电视机。这个场所起到的是梦想唤起的功能,米格一再地观看歌神的表演,并确认着自己追求音乐的梦想。他意外中发现自己的吉他和电视中歌神的吉他是一样的,因此内在的梦想与外力推动因素达成完美的统一,从而进一步激发他向着梦想采取更坚定的行动。
其次,歌神的纪念馆——现实与亡灵世界的穿越之所。这里是米格逐梦道路上意外发现的异世界的入口。导演将穿越场所设定在代表至高梦想追求的歌神纪念馆中,并且通过米格弹奏歌神的吉他开启了穿越的通道。向着第二世界的转向充满了奇幻性色彩,场所中的重要生态元素万寿菊开始闪现出金橘色的灵光。穿越入口的构建体现出创作者丰富的想象力,而且这个场所是实现第一世界(现实)和第二世界(亡灵)并置的神奇通道,它承担着神秘之“门”的媒介作用。这样的场所在很多奇观电影中都有体现,比如《哈利·波特》中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就是穿越第二世界的神秘之所,由此空间开启了角色情感的转折,进一步激活了情感推动下故事的发展。
最后,寻求梦想与亲情回归的亡灵场所。亡灵世界中多种场所的美术设计凸显了墨西哥文化和艺术元素,将独特的想象力与现实世界的建筑逻辑相结合起来,成功地塑造出奇幻的虚拟世界,虽然这是一幅体现生命逝去后灵魂存在的灵界图景,但它也是基于现实世界的幻想升华,因此营造出类似现实场所带有的亲和性。其中一些场所的设定别出心裁,对于推进情感和叙事起到积极的作用。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水下洞穴和舞台场所。当歌神生前的恶行败露后,米格被他推向一个水下洞穴,陷入一种极端绝望的处境中,并且再次与埃克托重逢。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场所中,他们被困于四面环水的小岛之上,在深层的沟通交流中实现了亲人的相认和情感的升华。米格在思想上完成一次观念转变——从一味地追求梦想到开始憧憬回归家庭的亲情。这个水下洞穴成为激发个人、家庭情感历史和回忆的宝库。场所中的水元素作为一种生态意象意味深长,水代表着生命之源,是人类最为熟悉的自然事物,并常常让人想到家的包容和温柔。在亡灵世界的很多场所中,水代表着一种爱。例如猪皮哥居住的亡灵世界贫民窟也是一处临水的场所,他在水边去世,在向往着亲人之爱的遗憾中完成了生命的终极死亡。很多导演都非常痴迷水元素在电影中的使用,他们喜欢将电影里的角色视作缺水的绿植,由于干渴快要走向灭亡。正如蔡明亮曾说:“水对我来说就是爱。”爱恰好是人们所匮乏的,水的元素具有象征意义,即追求爱、渴望爱。一旦水作为一种对生命存在有积极意义的源泉时,才能体现为电影中一种爱的象征。另一处别具特色的场所设定是歌剧院的舞台,这里是电影中亡灵世界精神生态的艺术化呈现。当米格一行人来到舞台追赶歌神找寻埃克托照片时,埃克托太太和他上演了一出戏剧性的舞台表演,真实的追杀变成歌剧,舞台成为突破真实和歌剧虚构世界的场所。最终,米格使用舞台上的道具元素如麦克风、屏幕将双方对峙中的话语播放给全体观众,德拉库斯人性的残暴和贪婪在众人面前暴露无遗。导演对这种精神生态的扭曲和异化给予了严厉的批判,舞台上灯光昏暗预示着一种压力和悬念。最终德拉库斯的亡灵被具有象征意味的大钟压死,这也是给世人敲响的警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性之恶迟早会遭到应得的报应。与此同时,歌舞剧院中的观众感情也达到了顶点,米格一家人在舞台上因担忧埃克托灵魂的终极死亡而将紧张情绪推向高潮;米格背负起浓厚的亲情穿越回家中,他急切需要唤起太奶奶对父亲的情感与记忆。
在电影的大结局中,米格一家人在家宅院落中迎来新一轮的亡灵节,亲人们故去的亡灵包括埃克托悉数顺利返回人间,在充满爱与祥和的院子里共同起舞。电影采用了两个长镜头来呈现这个欢乐的场面,并最终在一家人载歌载舞中将情感推向高潮,以天空中的礼花作为视觉爆发点。这个承载着祭祀祈祷、节庆仪式、日常生活、谋生安身等多种功能的场所与神圣灵界交融渗透,完成了具有抒情意味的空间叙事。这也恰恰体现出场所依恋的概念——起源于1974年段义孚所提出的“恋地情结”,表示人对场所的爱恋之情。在这部电影中,人们对场所的依恋,是一种超越生死观的情感记忆与生命延续。
结 语
在深刻洞察了数字奇观电影中的场所表达与情感深层关联后,生态美学理论以一种特别的观念视角进入电影的创作当中,为数字奇观电影中人与自然场所、人与社会场所的关系指明了价值方向,从而进一步提升场所美学之于塑造人类精神的力量。与此同时,对于目前经典作品中场所美学的提炼和总结,将有助于指导未来的电影理论家、创作者在刻画场所时保持对于生态审美的自觉,营造数字奇观中的生态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