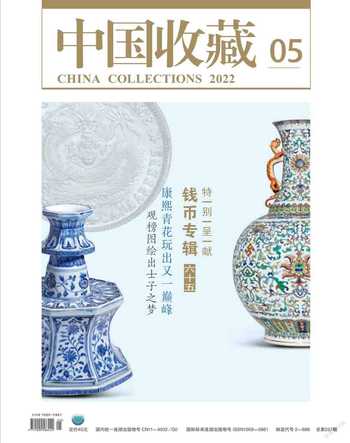“观榜”绘出士子之梦
徐文宁
明代画家仇英出身贫寒,幼年移居苏州吴县,与著名画家周臣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仇英在16世纪30年代声名鹊起后,很少独立生活,一直与一些有名望的收藏家生活在一起,如苏州富商陈德相、嘉兴收藏家项元汴、昆山收藏家周于舜等。查阅有关资料可以发现,仇英一生基本没有离开过吴越之地。
而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幅挂在仇英名下的《观榜图》,未出过江南地区、一生未参加过科举考试的仇英,是如何完成画中的皇城景象,又为何画出一幅“观榜”之作呢?
仇英《觀榜图》纵34厘米、长638厘米,以河流、建筑斜向为构图分区,大致分五段画面,绘出一幅明代士子乡试发榜、殿试入场、皇帝亲临殿试策问的通景叙事画面。

《观榜图》开始部分的城外垂柳及热闹的观榜景象

灵星门围墙边有一条河流,河上有三座石桥,其后为一座五道卷拱门城楼。这些建筑是根据什么记载绘就的呢?

这是天子临殿策问的情景,宫殿里里外外有大批文武百官、侍卫,烘托出殿试、传胪的盛世景况。
其开卷画面隐荫垂柳间,苍古的树荫里隐着不少乡野民居。画面上下有日月云纹华表,两柱界定了皇城与城外的区域。接下来是人员最为集中的观榜盛况,场景中有数百个人物,簇拥在高院大墙的张榜棚下争相观榜。一座琉璃瓦饰檐脊城楼,高高的单卷拱门,由12名全副甲胄的武士把守,刀枪剑戟寒光逼人、拦路木栅横挡在士子面前。观榜人物着装单线平涂,表情刻绘细微,把心理活动描写得十分深入。穿过单卷拱门又见一组华表界隔,不远的灵星门形成一堵围墙,围墙边一条河流分界,河上有三座石桥横跨。一座五道卷拱门城楼与庑廊形成城门与桥之间的广场,一头象和两名象奴在城门前与侍卫把关,几名锦衣卫持杖看着庑廊内的人群。
再往后展开画卷,是天子临殿策问的情景。金碧辉煌的大殿内丹楹饰金,色彩绚丽,墨绘蟠龙窗布于四面,中设七宝云龙御榻,皇帝站其中受百官朝拜。宫殿的里里外外,丹陛丹墀上有大批文武百官、侍卫,烘托出殿试、传胪的盛世景况。
最后一段画面为一群宫女太监站在御后苑门前,园内一对漫步的孔雀悠闲自得。大片的绿柳成荫,假山与亭阁淹没在其中。卷后段有“仇英实父制”落款和朱文葫芦印“十洲”钤记。从绘画风格看,御后苑门楼围墙和绿柳成荫,假山与亭阁的淹没,以及漫步的孔雀,都与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仇英《汉宫春晓图》相似。对比《观榜图》与《汉宫春晓图》的雕栏画柱、地面石板上的绘图,都以铅白打底,这种手法与藏于故宫的仇英《人物故事图册·吹萧引凤图》中石栏构件绘法几乎一致。且《观榜图》与《汉宫春晓图》中宫殿墙壁上都有墨龙模样。
从全画构思上,《汉宫春晓图》由宫墙始至宫墙止,与《观榜图》由绿柳始至绿柳止,风格上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尤其《汉宫春晓图》中有一位画师正在为宫女画像,有人推测仇英似在引用汉宫画师毛延寿为王昭君画像的典故在为作品点题。这与《观榜图》上以观榜作为主题,为诸如仇英一般一生没有参加过科举的人实现一场精彩的殿试梦景有异曲同工之妙。

《观榜图》(左图)与《汉宫春晓图》(右图)中的两只孔雀几乎就是颠倒了一下位置。

《观榜图》(左图)与《汉宫春晓图》(右图)的御后苑也是极为相似的。

《观榜图》的画者如果是对《汉宫春晓图》进行临摹的话,就不会出现“十洲”葫芦印章出入很大的问题。这枚印章似乎很值得深入研究。
《汉宫春晓图》当时被项元汴收藏,《观榜图》的画者要想画出与其孔雀如此雷同的形象,一定要在一段时间内与《汉宫春晓图》有过亲密接触。但如果那样,就不应该出现“十洲”葫芦印章出入很大的现象。另外,项元汴有个癖好,一旦有人要看他的藏画,便会要人先看他的题诗,并且只有当人家夸他的诗句写得好时才肯拿出画给对方看。所以,《观榜图》的画者要想看到《汉宫春晓图》并进行临摹的话,应不会与项元汴陌生。如此一来,也有可能其与项元汴合谋创作了《观榜图》,但那就更不会出现“十洲”葫芦印章的问题。因此,该枚印章的出入问题尚待考证。
如果以《汉宫春晓图》做母本来绘制《观榜图》,画者没有其他宋元皇宫古建筑数据在手,想画出图上的皇宫建筑列序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妨结合史料就《观榜图》上的建筑布局和建筑风格进行分析,看看要想获得这些古画中的元素在当时会有多难。
纵观故宫现存建筑,并未发现一座与《观榜图》中大殿建筑风格相一致的。而翻阅明清两朝的故宫平面图,也无法找到金水桥旁的灵星门,更找不到与灵星门相隔不远的单卷拱门城楼建筑。不过明代萧洵对元大都记载大明殿的《故宫遗录》云:“殿右连为主廊十二楹……连建后宫,广可三十步,深入半之,不显楹架,四壁立,至为高旷,通用绢素冒之,画以龙风。中设金屏障。障后即寝宫,深止十尺,俗呼为拿头殿。”这与《观榜图》中大殿“工”字形顶部结构较为吻合。《故宫遗录》在刊刻之前300多年间,以传抄形式流传于江南吴兴、苏州、南京、武进、常熟、绍兴、余姚等地,并在北京有传。项元汴在收集古画的同时也收藏许多古籍善本,仇英长期客居他家,是否得见《故宫遗录》也未尝可知。
《故宫遗录》介绍宫城南墙有三门,中央是崇天门,约在今故宫太和殿位置,从皇城的灵星门进来数十步就是金水河,“河上建白石桥三座,名周桥,皆琢龙凤翔云,明莹如玉。桥下有四石龙,擎载水中,甚壮。绕桥尽高柳,郁郁万株”。元陶宗仪《辍耕录》载:“正南曰崇天,十一间,五门……崇天门,有白玉石桥三虹,上分三道,中分御道,镌百花蟠龙……大明门在崇天门内,大明殿之正门也,七间,三门。”由此可见,《观榜图》中那三座玉石桥内,有五个拱门的城楼便是崇天门,图中大殿应是以元代大明殿为母本的。

看这几位似是落榜后有些沮丧的考生神情,说明这份榜单应不是殿试发榜。

《观榜图》里站在三座石桥附近庑廊内的这群人,穿着圆领青袍,戴唐巾,有人提着卷袋,应该是具有举人以上身份的人,他们是来参加殿试的会试中第贡生。
据史料记载,元朝中期实行科举考试,进士及第者作二榜,用敕黄纸书,揭于内前红门之左右。“内前红门”就是皇城灵星门左右的墙上。到了明代,则将黄榜张挂在故宫中轴线外的长安门外临时搭起的“龙棚”上。因此,《观榜图》开卷观榜场景的第一道城门,按上述建筑逻辑排列,既不是元代的“内前红门”,也不是明代的长安门。那么,《观榜图》观的是什么榜呢?
明清两朝的殿试是对参加过科举会试后的举人进行三甲排名的考试,故而不会存在落榜的可能性,所以也就不会出现《观榜图》中观榜人名落孙山后极为沮丧的样子。《观榜图》中的观榜人几乎都是穿着右衽襕衫戴着儒巾。襕衫是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太祖亲定士子巾服样式。《三才图会》中说:“古者士衣逄(逢)掖之衣,冠章甫之冠,此之士冠也,凡举人、未第者皆服之。”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观榜图》中观榜人是举人或秀才,相对应的考试发榜应该是乡试榜或会试榜。
而在《观榜图》里还有一群人,站在三座石桥附近的庑廊内。他们穿着基本是圆领青袍,戴唐巾,其中有人提着马扎、有人提着卷袋。
《七修类稿》卷八载:“洪熙中,上问着蓝衣者何人?左右以监生对,上曰:教着青衣好看,乃易青圆领也。”因此,明代举人、贡士、监生等穿的当是青圆领,戴大帽或儒巾、唐巾。所以,这群人应该是具有举人以上身份的人,他们是来参加殿试的会试中第贡生。
明代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认为,仇英的画为“习者之流,非以画为寄,以画为乐也”,致使后人对仇英的绘画认识稍显偏颇。其实我们从《汉宫春晓图》中引用汉宫画师毛延寿画明妃王昭君画像的典故,以及《观榜图》以科举观榜为寄的主题亮点上,不难发现仇英的作品并非如董其昌所说。相反,恰好这些作品显露出画家内在情感表达,即有樂有寄的意境构思方法,具有一定的相似处。
由此可以推断,仇英《观榜图》是在参考了当时收藏家们收藏的宋元宫阙界画建筑结构的基础上,又汲取了一定的民间素材,描绘出的一幅乡试发榜、贡生殿试、皇帝亲临策问等带有明代士子之梦的通景叙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