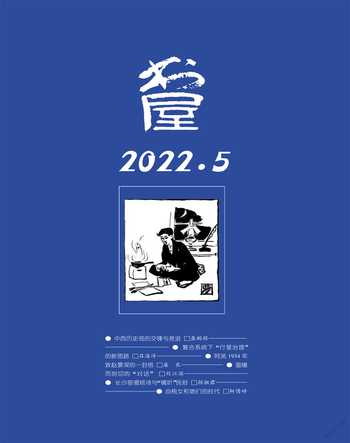阅读的年轮
周朝晖
午后在阳台曝书,边整理归类,目光边落在一本包封的旧书上,顺手拿起摩挲翻阅,心里涌起如见故人般的亲切与感动。牛皮纸包的书皮上“书林秋草”四个中楷墨书,点画稚嫩拘谨,是我学生时代的笔迹;书皮的边角已磨破,书页间多有茶水、油汗晕染过的斑点和蠹虫蛀过的痕迹。这本旧书引发我的感触,不仅因为它是我最早购读的藏书,而且书本身自带故事与传奇,承载着我与《书林秋草》这本书的作者孙犁之间一段难忘的因缘。如果说,个人阅读史也有年轮的话,那么与此书有关的记忆是其中最深的轮线,密圈勾勒,阅读的年轮也与生命的年轮重叠,回头重读,算得上一个心灵史片段。
此书购于1984年夏天。当时我还是初中生,稚气未脱,却已是一个老“书虫”,喜好阅读并热衷于买书藏书,且有了自己专属的书架。这一嗜好,或许得益于家庭环境的潜移默化,也与当时整个时代氛围的影响有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可以说是一个全民崇尚知识学问的年代,也是中国纸质阅读史上的黄金时代,身在“南方之强”的厦大学府,更能感受到书香氛围。先父在大学学报从事文字工作,兼在哲学系执教,交游往来的对象也以教研读写为本业的师生居多,读书、谈书、编书、写书、出书,既是职业生计,也是嗜好,书成了生活的一大中心。从小置身于这样的环境里,耳濡目染,很容易培养出对书的亲近感情。那时我已上了中学,对书的兴趣取代了以往的养花、集邮和船模制作,也不满足于先父指定或购买的书籍,积攒下的零钱几乎都用来买自己喜欢的书,用过期的挂历或用过的牛皮纸书稿袋精心包装,再一本一本充实书柜,怡然自得。大概也是从那时起,我对教辅书籍占主流的高校校园小书店失去了兴趣,转而向市区的大书店探秘寻宝。
那年剛放暑假,参加完闭学式时间尚早,我就去中山路新华书店选购课外读物。在我的记忆中,这个书店曾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厦门一大图书流通中心,也是几代人心目中的文化圣堂。每当节假日,中山路的新华书店里总是人流如潮,遇到某种影响力巨大的新书刊上市,从书店玻璃柜台前排起的长龙一直延伸到局口街的老字号中梅理发店大榕树下。这天书店里显得异常清静,售货员们难得清闲,隔着玻璃展示柜闲聊,我得以在四处从容巡回浏览。在文史书籍专柜前,我的目光一下子被一本《书林秋草》吸引了,只因书的“颜值”实在诱人:素净的封面画了两片荷叶,孙犁题写的书名墨色秀润,与草绿色原稿纸相映成趣,给人一种坐拥书房的充实富足之感,一元三角五分的书价对我来说实属不菲,但我不假思索就买下了。
那时,我已从语文教材里的《荷花淀》和父亲收藏的《孙犁小说选》初步涉猎了孙犁的作品,实话说,谈不上有特别的共鸣和喜欢,也许是因为年龄、阅历的差异限制了我对小说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吧。但这本《书林秋草》却给了我另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我读到了另一个孙犁。书中所写几乎全是与“书”有关的文字,但立意与情怀完全有别于通常的“书话”与“书评”:有阅读经验的分享,如《野味读书》《与友人论学习古文》;有写作的“秘辛”,如《文学与生活的路》《谈散文写作》等;其中最具个人色彩的还有围绕着买书、读书、藏书的故事与传奇,如《书的梦》《报纸的故事》等,将个人阅读这一日常琐事与时代风云、民族大义和人生百味交织在一起,融汇在凝练的文字中娓娓道来,真知灼见流露其间,令人想起风雨之夕与智者在火炉前的促膝谈心。这本书让我懂得了读书的门道,开拓了阅读的眼界,最富启迪意义的还有它独特的写作范式:在阅读中融入自己的情感和生命体验,并用一种收放有度的方式来讲述。顺便提及,半年后我的第一篇习作《契诃夫“札记本”的启示》,就直接来自阅读此书的感悟。
《书林秋草》也让我接近了孙犁的情感世界。孙犁早年喜爱文学阅读,受到鲁迅文学精神的熏陶,同情支持革命,青春时代即投身全民族反抗日寇侵略的革命行伍之中,是出身延安“鲁艺”的资深作家,早在抗战时期的就以独特的文学风格而享有盛誉。随着革命的成功,他随大部队进入大城市,成了一名党报副刊的文艺工作领导者。以他的资历和学识,一步步进入上层并非难事,但他淡泊名利,始终保持一个读书人本色,“一生嗜书如命”,视官位、财物和虚名如浮云,终生与功名利禄保持必要的警惕和距离。他读书有道,每读一本则作一记一录,《书林秋草》里就记录了很多有关“读书”的故事,个中有孙犁本人的阅读史的年轮,也构成了他精神史的一个重要截面。从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来看,正是从这类“读书记”中,我看到了被笼罩在“荷花淀派鼻祖”光环之外的另一个作家孙犁,情感上也由景行行止的敬仰转向息息相通的“理解之同情”,再转而亲近起来。当我从阅读《我的子部书》一文中得知,孙老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家,大半生节衣缩食,甚至在战争年代冒着枪林弹雨保护下来的书籍也被洗劫一空。拨乱反正后,虽然退还了被抄走的书籍,但已残缺不全,特别是早年按照鲁迅购书目录搜集的子部书,如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子部丛书》刻本,都已七零八落,这使他格外伤心、痛惜,好像散失的不是书籍,而是亲人,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这段文字令人动容,透过字里行间,我仿佛看到老作家的落寞无奈,听到他沉重的叹息,只恨自己不能为老人做点什么。冥冥中如有神助似的,机会很快就降临了。
也是暑假的一天,我在某旧书门市部淘书,意外发现了几本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国学丛书》的散册,加上“编著者王云五”的字样,让我确信它就是孙犁丧失的版本,随之心生一念:买下寄给孙老吧,也许可以补他的残缺,于是挑选其中品相稍好的《王守仁》《论衡》打算给他寄去。想到给一个大作家寄书,我不禁怦然心动,不敢声张,一人关在房间悄悄写信说明缘由。我想,既然只是寄书就不必留名,但没有名字地址的邮件如何寄出呢?刚好当晚,有位名叫徐梦秋的哲学系年轻讲师来访,我略加思索想了一个名字作为寄件人投递,不久后开学,也就把这事淡忘了。
一次课间休息,传达室的校工林阿姨走进教室,手里举着一个牛皮纸包喊道:“七班周梦秋,谁叫周梦秋?谁叫周梦秋?有天津的包裹!”一连几遍无人回应,林阿姨转身离去。这时我才猛然醒悟过来,急忙上前迫不及待和林阿姨确认。我第一眼就看到似曾相识的“周梦秋”几个大字写在《天津日报》编辑部专用纸袋上,惊喜之余犹难以置信;再看寄信人处写着“天津市多伦道二十二号孙犁寄”,悬念才落地:孙犁给我回信了!我在蜂拥而来的同学和“啧啧”的惊叹声中哆哆嗦嗦地打开纸包,一本精装版《孙犁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赫然眼前,眼光落在扉页上“周梦秋同志指正,孙犁,1984年8月24日”那一刻,感觉自己仿佛立于世界之巅。对于一个少年幼稚而冒昧的举动,孙犁竟会给予这么真诚而慷慨的回应,让我在幸福荣耀之外又夹杂着感动和感激。唯一让我不自在的是那个让孙老信以为真的假名字,好像做错事却得到赏赐似的,连同私自冒用徐老师大名一事也让我于心不安但又不知如何是好,总之颇为纠结,就先给孙老写信致谢,特别为伪造名字的失礼道歉。
不久后我就收到孙老的回应,是一本精装版《孙犁文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签赠写着:“朝晖同志指正。”显然老作家宽宥了我的冒失,并赠书给予勉励,我也为名正言顺成了孙犁的赠书对象而高兴。我将这一奇遇向父母和盘托出,两本珍贵的赠书也交父亲保管。那时候,我在学业各方面的表现乏善可陈,与父母的殷切期待相距甚远,与孙犁的这段书缘竟然一度成了他们向亲友津津乐道的“殊荣”,好像犬子会因此而变豹似的。这些往事背后,也连带着对父母周边亲故的温情记忆。那位曾被我冒用名字的厦大哲学系年轻讲师徐梦秋老师,早已跻身国内硕学名流之列,如今偶尔相見,还会拿我当年“名字侵权”的行径打趣。
这是初中时代的往事,但由这本《书林秋草》引出与孙犁的故事还有后续。
此后经年,我奔命于中考、高考的升学应试,无暇他顾,后来又随波逐流远渡日本游学,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少年时代的陈年往事在忙碌奔波的异国漂流中渐渐淡忘。想象不到的是,即便远在万水千山之外,即便相隔十年的岁月,我在日本又与孙犁再续书缘。
说来奇巧,在日期间我认识了一个来自天津中医学院(现天津中医药大学)的留学生,得知她曾是孙犁的邻居,也住在多伦道的大杂院里,后来孙老搬离了多伦道旧居,但距离也不太远。话题开启,沉睡的少年记忆一下子苏醒过来。从她的描述中,我在脑海里拼凑出一幅孙老的影像:高大的身材,孤独的背影……尽管女同学提供的信息琐碎,却一下子拉近了我与孙老的时空距离,也在不知不觉让我对那个与孙犁有比邻之缘的女同学产生某种微妙的亲近之情。相识后的第一个春假,女同学回国探亲,我委托她带一盒银座文明堂茶点去看望孙老。
落樱时节,回到日本的女同学给我带来一连串意想不到的惊喜——一本孙犁签赠的《孙犁新诗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同样难得的还有她拍摄的孙老照片:老作家坐在带扶手的藤椅上,很配合地对着镜头,消瘦的长脸,儒雅、温厚,带着洞察世事的睿智。根据女同学的追忆,见面情形大致如下。
老人在书房热情接待了远道归来的小街坊,静静听了说明,不知是否记得当年与他结下书缘的厦门少年,微笑着点点头,起身到书柜取出两本书,分别签赠给我们,女同学还与孙老合影留念。“书房一尘不染,老人个子很高大,中式对袄,衣帽干净利索,慈祥得像我姥爷。话不多,专注听你说话,微笑着点头。辞别时,一直站在门口目送我下楼梯……”
十多年后,我在日本与天津女同学重逢,她还清晰记着与老作家近距离接触的每一个细节。不过那时,孙老已辞世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