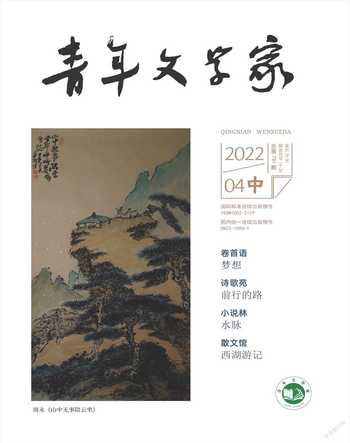从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的角度浅谈毛姆作品中的女性侧写
范家瑜 娄晏如 刘芊寻


《面纱》是英国作家毛姆根据自己于1919至1920年游历中国的亲身经历,以中国为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总体来说,《面纱》讲述了女主人公凯蒂在一段无爱婚姻中经历各种变故最终走向自我救赎的过程。
小说中面容姣好、内在空虚的女主人公凯蒂为了在妹妹之前出嫁,匆忙嫁给了孤僻寡言的细菌学家瓦尔特,并随其来到香港。对凯蒂而言,新婚生活并不美好,她与丈夫之间时有摩擦。最终瓦尔特决定离开,前往疫区救助苦难中的人们,凯蒂除了依附于婚姻别无他选。经当地副海关长的引荐,凯蒂来到当地唯一的修道院从事琐碎的工作。受到众多善良的法国女子与院长的感染,凯蒂对丈夫的人格有了新的认识,其灵魂也受到了洗涤。然而,好景不长,二人关系刚刚缓和时,变故横生,紧接着便是瓦尔特的死讯。回到香港后,凯蒂无比鄙视屈身于欲望的自己,最终不堪心灵重负离开香港。母亲逝世后,凯蒂彻底与过去一刀两断,陪父亲开始了崭新的人生。
本文将从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的角度剖析《面纱》中的女性角色,探究毛姆的女性观。存在主义女性主义是女权主义运动第一次高潮中的重要流派,波伏娃的《第二性》作为该流派的重要理论支撑,对女性“内在性”的束缚与“他者”的身份进行解构,思考性别身份的差异所带来的社会文化问题,探究女性实现自我觉醒的可行性路径。
波伏娃的《第二性》堪称创造性地将存在主义哲学充分应用到女性理论的研究中,并在书中较为全面地分析与介绍了她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的思想观念。“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波伏娃的“他者”理念追根溯源可以至萨特,同时又在女性主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她认为女性作为“他者”最大的特性是依附性。“他者”,顾名思义,是相对于主体的概念。这种依附性体现在女性身上就是一种被动性。女性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和人生,其一生在多数情况下都受人安排。与此同时,女性的这种依附性实质上产生于其内在性。波伏娃在此所指的内在性,指的是女性那种封闭的、缺乏创造性和超越性的生存状态。她认为:所有的生存者都应同时兼具内在性和超越性,两者同时并存,相互关联。如若社会制度没有给生存者提供任何目标,或者阻止他达到任何目标时,超越性就会重新陷入内在性。由此可得,女性并非天生只具有内在性,而是在所处的男权社会制度的压迫下,被困于内在性之中,只能作为客体存在。
《面纱》中的女性形象具有反映时代特征的特殊意义。从女性视角而言,《面纱》堪称一部人生教科书,特别是通过分析女主人公凯蒂的自我蜕变之路,可以让读者体会到“婚姻自由”的意义,感受到“自我意识”的重量。母亲的精明势利、原生家庭爱的缺乏促成了凯蒂扭曲的爱情观。虽然瓦尔特是她自己选擇的丈夫,但这种选择掺杂了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却唯独缺失了爱,这并不是真正的婚姻自由。在疫区的经历,促使凯蒂自省,当她开始希望自己的女儿成为一名自由自主的女性时,可以确信她的重生已然完成了。
通过《面纱》一书中形象各异的女性,我们捕捉到当时社会背景下的女性在经济、文化、情感精神等各方面对男性依赖的每一个瞬间,深刻感受到二十世纪的时代特征与中英两国的文化差异,切实体会到女性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实现意识觉醒与自我蜕变的难度。多名女性角色突破经济、文化、情感精神方面的枷锁,通过自救式的行为,为我们展现了在经历过真实的生活后,女性发自内心想要获得独立人格的决心。这也很好地说明了我们为何要聚焦本书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
透过《面纱》中的女性形象,我们对毛姆的女性观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毛姆有着较为严重的厌女情结,这也深刻影响着他的创作。在他的作品中女性大多贪婪自私、虚伪庸俗、精神缺失且无独立人格。而达到毛姆心中理想的中国女性则是贤惠温顺,对丈夫言听计从,她们牺牲自我以实现对家庭的无私奉献。这也充分迎合了当时普罗大众的女性观,即女性是客体,是依附于男性的。与此同时,毛姆也肯定了具有缺陷的女性能够在外部环境的熏陶下蜕变,从而成为其心目中的理想女性。《面纱》中凯蒂的自我救赎之路以及要把女儿培养成自由自主女孩的愿望说明毛姆深知精神重生需要一场自我拆解,才能获得觉醒。
一、《面纱》中的女性形象及对比
本文将以存在主义女性主义为纲,从经济、文化、情感精神三个方面分析《面纱》中女性角色对男性角色的依赖,思考其中女性角色尚未实现自我觉醒的原因,主体意识觉醒的契机,主体意识觉醒的表现和对女性的影响。
贾斯汀太太即凯蒂母亲的所作所为从极大程度上反映出了女性在经济、文化层面对男性的依赖。如书中所写,贾斯汀太太是名八面玲珑、善于操持、野心勃勃的女性,然而在书中她却只有一种称谓:贾斯汀太太。她的身份永远只能建立在自己丈夫的存在之上,她的经济来源也毋庸置疑来源于丈夫。正如她从一开始所承认的那样,自己只能通过丈夫来出人头地。为了使自己获得看上去体面且受人尊敬的地位,她想方设法地操控丈夫,逼迫他去竞选皇家法律顾问,以便自己认识更多所谓的上等人士。在当时的英国社会,父权制文化对女性产生的束缚根深蒂固,男权思维模式在法律和伦理层面均被合理化,即便贾斯汀太太极尽可能地操控自己的丈夫,她所作所为的出发点仍是默认自己应当作为男性的附属而存在,这从一开始便是父权制社会文化下产生的悲剧。在这种社会文化的影响下,女性只能具有“他者”的身份,而非作为完整的人而存在。
女性在情感精神方面对男性的依赖则在凯蒂身上更为明显地体现出来。她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现在与未来寄托于瓦尔特也就是她的丈夫身上,甚至认为只能通过与其结婚来实现自己存在的价值。她无理由地相信着社会以及家庭对女性的定位,自发地从男性视角出发,恶意评判其他女性的外貌、性格等。这也是她在文化层面上依赖着男性的体现—自愿将自己处于“他者”的地位,习惯性从男性的角度进行考虑,运用男性的处事规则,而未意识到自己本应是一个具备思考能力的主体。
从女性角色在经济、文化、情感精神方面对男性的依赖,我们可以窥得女性迟迟没能实现自我觉醒的原因。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男性把控着对女性标准的绝对话语权。而女性也习惯于在男性主体意识的领导下生活,默认处于附属地位。由于自身主体意识未能觉醒,在长期的父权制文化浸润下,大部分女性反而成了父权制的助推者。为了不在妹妹婚礼上显得难堪而嫁人的凯蒂和深谙只有迎合男性喜好才能实现自己价值的贾斯汀太太……每个人看似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奔走,实则只是按照父权制文化的发展轨迹忙碌着。
若论觉醒,凯蒂就是《面纱》一书中自我意识觉醒的典型代表,唤醒其主体意识的契机有二,其一是对人性的了解,其二则是在疫区的见闻。所爱之人的背叛使凯蒂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她一方面为唐生的自私钻营而心碎,一方面又对自己受欲望指使的所作所为感到悔恨,对自己迫于苟且只能依附于瓦尔特的行为感到不齿。心境的变化使凯蒂对人性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这可以被看作是她自我意识觉醒的契机之一。
而真正唤醒凯蒂主体意识的则是第二个契机,即她来到疫区之后的所见所闻。这里的一切都与香港纸醉金迷的安逸生活完全不同。整个城市尸殍遍野,饥荒,动乱。巨大的冲击不仅给她带来了对疾病的恐惧,也让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和爱情。与修道院修女们的接触也让她得以审视自己。她们虽然都深爱着自己的祖国法兰西,却出于人道主义背井离乡来到了充满疾病、困苦的异国,救助照料苦难中艰难生存的人们。这些都激发了凯蒂极大的同理心,她蔑视一心投身于爱情的自己,于是向修道院院长自告奋勇,希望为照料患者贡献一份力。凯蒂终于意识到人的价值在于奉献,原先烦扰自己的琐事并不值得牵挂,甚至有些可笑。
再次回到英国之际,凯蒂的主体意识已然觉醒,疫区的见闻、瓦尔特的死亡、怀有身孕、母亲病逝……所有的经历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凯蒂,她不再是父权统治下没有个人意识的洋娃娃,而是成了一个拥有人性与信仰的理智的人。毛姆虽看轻女性,却仍然描写女性自我觉醒的过程,根本原因在于他始终认为由他所塑造的觉醒后的理想女性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他希望现实中的女性在看到这些文字后可以逐渐成长为他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这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男性凝视。
若论主体意识觉醒的表现和对女性的影响,沃丁顿的满族妻子和主体意识觉醒后的凯蒂均能提供一个很好的说明。沃丁顿的满族妻子来自名门望族,在革命屠杀满人时期,她被沃丁顿好心救下,从此深陷爱河,并在他要离开的时候逃出家门誓死跟随。此时她跟随沃丁顿既不是出于经济依赖,也不是出于精神依赖,只是受自己的爱驱动而希望与沃丁顿长相厮守。为了追逐自己所爱,满族女子不再受家族桎梏捆绑,在自我意识的影响下,打破了生活习惯和思维的不同。在书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凯蒂一直都对这名满族格格心怀崇敬—她总是安宁地坐着,对自己所想清晰明了,并坚定追寻着—仿佛她身上呈现的就是凯蒂自己一直以来所苦苦追寻的爱情之“道”。但是毛姆笔下的这位“中国式”大家闺秀却并非一个单纯的扁平人物,换言之,我们依旧可以在毛姆别具一格的写作风格中感受到其略带畸形的女性观。她吸鸦片、妆容浓重,这一形象在任何的社会背景下都无疑是被视为堕落的。究其根本,源于毛姆没有摆脱对女性形象根深蒂固的歧视—他认为女性原本就是易于依附于人的物种,小时候依附于父母,长大后依附于丈夫,满族格格虽勇于和沃丁顿远走高飞,但本质上也是因为她明白沃丁顿值得她依赖。
二、存在主义视角下的女性觉醒
《面纱》中对凯蒂的出身、婚姻、爱情、异乡经历的描述,以及在经历了东方之旅后对自身价值的启发,都反映了其女性意识的觉醒,想要冲破精神枷锁的渴望和对自由的追求。这里将运用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观来探索《面纱》中的女性精神觉醒和女性对自由的追求。
《面纱》中,女性从生下来就是依附于男性生存的。女孩出生的时候,首先依附于自己的父亲,步入婚姻之后转而依附于自己的丈夫。凯蒂的家庭地位构成虽然是以母亲为主导,但不可否认的是她们全家人还是需要依靠父亲来维持一家的开销,而凯蒂的母亲贾斯汀夫人在培养女儿的过程中也无时不在灌输“嫁给一个杰出的丈夫”的教育思想,她把全家的未来都寄托在了女儿的丈夫身上,也是这个原因,凯蒂才成为了所谓的“二流货色”,虚荣、轻浮、愚蠢,将自己的价值和人生的幸福寄托于婚姻和爱情。凯蒂从小就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选择瓦尔特作为自己的丈夫也是出于现实的无奈而被迫将就;选择前往疫区,是因为生活所迫,除了依附于自己的丈夫别无选择。她一直是被动的、消极的,希望依靠别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她从未真正清楚,作为女性,自己的人生价值是什么,而这一次前往疫区的赴死之旅则激发了她对自己作为女性价值和意义的思考。
波伏娃认为,女人的自由是接受自己的性别而不是否定自己人生的意义,能够获得与男性等同的存在和价值,得到宽松的处境和平等的机会,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身体,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她能够平等地与男人建立爱情关系,自主地进入婚姻,成为妻子和母亲;她也能全身心地投入事业,自由地在社会中施展才能。女性只有摆脱依附性的枷锁,走出内在性的囚笼,才能从精神上得到深刻的变化;只有为自己而活,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实现自己的价值,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在疫区,凯蒂照顾孤儿、做缝纫,这与她之前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前半生的她只需要做一个可供观赏的花瓶,将人生寄托于他人,却从未考虑过自己的价值和追求。在工作中,她慢慢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意义—“凯蒂觉得自己的心里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生长。一刻不停地忙碌分散了她的心思,窥见他人的生活,他人的视界唤醒了她的想象,她开始恢复元气,变得更舒心、更强壮了”。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凯蒂在主动创造社会价值,也在逐渐走出内在性封闭的空间,意识到自己不能依附于他人,其女性精神终于得到了启发。在重回伦敦后,她与父亲亦达成和解。她开始慢慢理解父亲,发现一直受母亲支配的父亲其实也一直渴望做回自己。这部分对父亲的描写也是在暗示她将作为独立的个体去掌握自己的命运和人生。“我希望是个女孩,我想把她养大,使她不会犯我曾经犯过的错误。……我要把女儿养大,让她成为一个自由的、自立的人。我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爱她,养育她,不是为了让她将来和哪个男人睡觉,从此把这辈子依附于他。”从这段对未来女儿的期望中可以看出,凯蒂已经明白造就自己荒唐前半生的原因,她不会再重蹈覆辙,将实现超越性的可能寄托于自己的女儿身上,而是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于世。
从凯蒂自身来看,并不能说她自己彻底实现了所谓的“自由与解放”,但从她经历了这一切的精神变化和思想转变上看,她明白了作为女性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这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与解放。
让我们回到毛姆的女性观:通过剖析毛姆在《面纱》中刻画的女性形象,我们可以深入了解毛姆女性观的偏见性和波动性。蜕变前的凯蒂贪慕虚荣,为了跻身上流社会而不择手段;凯蒂的母亲贾斯汀太太从小给女儿灌输丈夫即赚钱工具等带有偏见的理念,处处打击丈夫……由此可见,毛姆对女性形象的刻画充满了偏见性。毋庸置疑,他鄙视和厌恶女性—但我们也经常能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一些“看似理想”的女性形象。他不吝贊美之词描写沃丁顿的满族妻子,笔下饱含牺牲精神与乐观心态的修女们也印证了他对女性的态度并非传统认知中“直线”式的不变,而是“波浪”式的反复,其女性观的波动性由此可知。
最后,从凯蒂的一系列经历中可以看出,毛姆认为女性需要经过磨难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独立的“人”,仅靠女性本身无法完成自我进化。毛姆一直以上帝视角审视其笔下的每一个女性角色,女性所谓实现精神上的觉醒与解放也是出自他手。文中满族格格这个形象的引入暗示着他心目中的女性应该具备的模样,这本质上还是没有跳出当时固有的社会观念,是一种资本主义父权社会下的男性凝视。
本文从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相关理论出发,深入分析毛姆的《面纱》。在解读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三个女性形象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毛姆作品中的女性侧写,多带有他个人的偏见—女性生来缺乏灵性与主体性,且其自我意识的觉醒并不是自发的。《面纱》中的凯蒂在经历了一系列变故后,才终于看透了所谓生活华丽面纱下的真相,完成了从一个被世俗束缚的客体向解放自我、拥有独立人格的主体的蜕变。即便是他笔下看似“完美”的女性形象,也并未真正跳脱出父权制社会下男性的固有视角。综上所述,毛姆笔下的女性角色虽具波动性,但注入了他本人固有的落后成见,缺乏客观平等的两性视角。
项目名称:探究毛姆作品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创作风格的影响(项目编号:202010673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