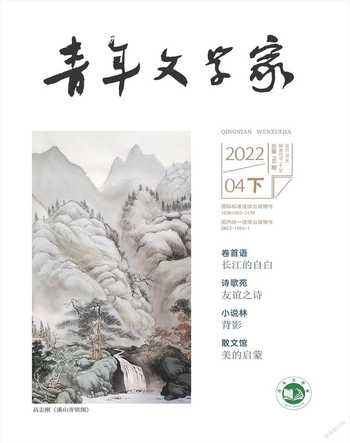浅谈中国诗画关系
宋雪薇



诗画观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一直有被视为一体的概念,宋代苏轼提出了“诗画一律”的重要命题。近代以来,诗画关系问题开始被美学家和批评家广泛讨论,是受到莱辛《拉奥孔》的刺激。莱辛在著作《拉奥孔》里讲了绘画与诗歌在功能上的不同之处,朱光潜在《诗论》中指出用莱辛的学说分析中国诗画关系的困难。宗白华指出这一区分对艺术科学具有重要影响,他将诗画的“微妙分界”作为现代美学的首要任务。与他们不同的是,钱钟书从文艺批评的角度直接讨论中国传统诗画观的问题。他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间写了一系列论文,其中《中国诗与中国画》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批评中探讨诗画关系问题的代表性论文。这篇论文历经时代和历史的沉淀,经过后代学者的不断探讨和质疑,发现了钱钟书在这篇论文中存在的偏见。正是由于后代学者的不断探讨,才使中国诗画观的认识不断深入,更加成熟。本文试图剖析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对诗画观的偏见,再将近年来学者的质疑与探讨进行梳理综述,期望能对中国诗画观的认识提供一点粗浅的建议。
一、对莱辛的误读
钱钟书的《七缀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5年12月出版,这本书一共收了七篇论文,其中就有《中国诗与中国画》和《读〈拉奥孔〉》这两篇论文,讨论的都是诗与画之间的关系问题。《读〈拉奥孔〉》是钱钟书对莱辛名著《拉奥孔》的一点看法和意见。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也是受到了《拉奥孔》的启发而创作的论文。从这两篇论文中不难看出,钱钟书完全认同莱辛的观点。因此,他对莱辛诗画观的认识,没有表现出质疑与批判。
在《拉奥孔》的第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出莱辛扬画抑诗的偏见。由此可见,莱辛的《拉奥孔》很大程度上是这种扬画抑诗偏见的产物。莱辛写《拉奥孔》意在说明诗歌不配与绘画相提并论。而钱钟书对莱辛的认同,则是基于另一种偏见,即画不如诗。也就是说,钱钟书是从与莱辛相反的角度出发,达到与莱辛诗画观相同的认识—即诗画不一律。
在《拉奥孔》这篇论文中,莱辛将诗歌不及绘画之处作了详尽的叙述,钱钟书也并没有发觉他与莱辛之间看待此问题的出发点不同,而误以为莱辛也持扬诗抑画的观点。因此,我们也可以说,钱钟书的两篇论文,即《中国诗与中国画》和《读〈拉奥孔〉》,都是基于对莱辛的误读而产生的。
二、《中国诗与中国画》与《读〈拉奥孔〉》的基本观点
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和《读〈拉奥孔〉》,主要是讨论诗歌与绘画之间的关系。《中国诗与中国画》意在说明在中国古代,“诗画本一律”的观念较为盛行,但实际上,评价诗与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标准,这是因为诗与画在本质上是不相同的。“画中有诗”是绘画的最高境界,而“诗中有画”却不是诗歌需要达到的成就。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提出,古代人们评价诗和评价画时,所持标准实际上并不一致。
事实上,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也是在强调中国诗与画的评判标准是不一致的。但诗歌和绘画的标准究竟是怎样的不一致,钱钟书并没有谈到。而在《读〈拉奥孔〉》一文中,钱钟书套用莱辛所持的理论,详细地分析论证了诗歌与绘画的评判标准如何不一致。然而,钱钟书应该从分析论证诗歌有绘画所不能及之处和分析论证绘画有诗歌所不能取代的功能这两方面来论证此问题,但对第二个问题,钱钟书却并未提及,只是从其他角度分析论证了诗歌相比绘画所不能及之处。
三、近代学者对中国诗画观的研究概述
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不仅在学术界上引起了文学学者的关注,也引起了美术界学者的热烈讨论。本节分为两部分,按学科划分,梳理不同学科学者对中国诗画观的不同认识。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首先最有权威的言论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的王彬彬,他在《钱钟书两篇论文中的三个小问題》一文中,对钱钟书《七缀集》中《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两篇文章中有关诗画观所列举的部分例证提出三点质疑。第一,达·芬奇也许放错了地方。在西方美学史中,关于诗画之间的关系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诗与画的同源性和一致性,第二种则主张诗与画的异源性和差异性。而持第二种主张的学者,又往往是扬画抑诗的。西方学者本就有着扬画抑诗的传统,达·芬奇正是其中的代表,甚至是这种观点的起源人物。正因如此,钱钟书在列举西方美学史中主张诗画同源和一致的观点时,把达·芬奇放进去,似乎是举错了例子。其次,沈括是否被曲解了。钱钟书在论文《读〈拉奥孔〉》中,试图证明绘画的成就不如诗歌。因此,他对沈括的那句“凡画奏乐,止能画一声”十分感兴趣。但这也导致了他在两个方面都发生了错误。第一是他把“止能画一声”看作王维无法从《按乐图》中辨认出是《霓裳曲》第三叠第一拍的理由,并把这种认识强加于沈括;二是他把证明关于王维的那则传说是“妄”看作证明诗优于画的一种方式。第三,董其昌想说什么。为了论证画不如诗,钱钟书在《读〈拉奥孔〉》中,找了很多中国古代的例子。大多数人可能以为董其昌这句话说完了,然而王彬彬追根溯源,发现了伍蠡甫的《名画家论》中,收有《董其昌论》《再论董其昌》两篇研究董其昌的论文。在伍蠡甫的论述里,引用了董其昌诗画观的完整的看法:“‘水作罗浮磬,山鸣于阗钟’,此太白诗也,何必右丞诗中画也。画中欲收钟磬不可得,但众山之响,在定境时有耳圆通。正自觅解人不易。”很显然,董其昌这句话中的“但”后面的部分,才是他想要表达的观点—“画中虽欲收钟磬不可得,但又何必收钟磬!”画面上虽无法直接画出钟磬之声,但只要画家画出了虚静之境,而观画者又有着虚静之心,自能从画面上听到“众山之响”,自能从画面上听到“希声”的“大音”。由此可见,钱钟书只引用“但”字之前的几句话,让读者看见的是和董其昌想要表达的意思相反的观点。王彬彬的这篇论文对《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中存在的部分论据大胆质疑,小心求证,最终为钱钟书这两篇论文做出正误。他指出,即使是大学者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上,也难免断章取义,这对于我们如何准确地使用中外文献材料,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乐山师范学院文艺学硕士李良中,专门研究钱钟书。他于2007年写了《中国旧诗画没有正宗、正统的绝对地位—读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在这篇论文中,李良中首先厘清了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的论证逻辑,然后一一进行分析,指出在这一步之中钱钟书论证逻辑的错误。例如,钱钟书论证了王维不能代表中国旧诗的正统,而应该是杜甫。而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只取狭义上的“神韵”,即王维的诗风,而不是李白和杜甫的诗风。因此,钱钟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样看来,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对诗和画有不同的标准:论画时重视王世贞所谓“虚”以及相联系的风格,而论诗时却重视所谓“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因此,旧诗的正宗、正统以杜甫为代表。”此观点看似严谨,然而经过学者的细细推敲,钱钟书提出的中国旧画分南、北宗这一观点是比较牵强的,王维的旧画正宗地位也是他主观臆断所得出的。
文学界的学者对钱钟书诗画观大胆质疑,小心求证,不虚假,不隐恶。这体现出近代学者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上的一次进步。但是,诗画观中,不仅有诗,也有画。我们不仅要从诗歌的角度论证诗画观,还应该站在绘画的立场去看待诗画观。
由于笔者不熟悉美术绘画领域,故只能选取美术界具有代表性的一篇论文进行分析,即唐卫萍的《走出“诗”本位的诗画关系论:重读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美学研究,2019年06期)。古往今来,“诗”本位的诗画批评,一方面让诗歌的表现力获得了充分关照,另一方面却遮蔽了大量的绘画经验,以及诗画互动的历史环节。因此,重新调整诗画关系讨论的视点,梳理二者互动的历史就显得尤为重要。前文提到,钱钟书借助莱辛的视角,将中国诗画异质的问题设定为反驳“诗画一律论”,而論证的关节点在于对王维在诗坛以及画坛地位的认定问题。钱钟书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是成立的,但省略了相当多的历史环节,他只需证明王维不是“诗圣”就可以完成这个论证。那么问题的重心从诗画关系的比较估价转移到了诗学估价。唐卫萍指出:这一论证模式将诗画两极关系的互动、窄化为诗歌内部的风格和地位之辩,在以诗为主体的讨论框架之下,绘画的历史首先就是缺失的,被遮蔽的,绘画历史的缺失当然就会带来解释的障碍,这个问题本身是指向历史的,却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
我们需要回到诗歌与绘画互动的历史,用互动的环节来检验诗画标准到底是如何纠缠在一起的。视点的落点,不仅要聚焦文学,也要聚焦绘画。唐卫萍认为,只有诗与画的相互检验才能构成批评的准星,单从“诗本位”的角度去论述诗画观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诗与中国画》的论证在今天看来仍值得学者不断研究,这篇论文中所表现出的“诗画一律论”的中国传统诗画观早已被接受。而钱钟书在《谈艺录》《管锥编》等书中的观点,往往与这两篇论文中的观点相矛盾。诗本位的批评结构在处理诗画关系时需要重新调整焦点,即从诗画二者互动中探讨这一问题,而就目前已有的研究现状来看,从绘画的角度展开诗画关系探讨的学者似乎较少。因此,呼吁更多的学者从绘画的角度分析诗与画的关系,为中国诗画观的研究贡献成果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