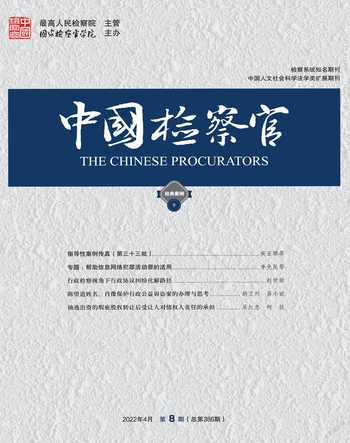制作虚拟钱包“钓鱼APP”的行为定性
蓝红霞 杜倩楠
一、基本案情
福建盈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某公司”)是一家提供应用程序设计、研发等服务的信息技术公司。2020年12月,该公司承接了一款仿冒“imToken数字钱包”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以下简称“imToken APP”)的业务。委托方要求仿冒APP的外观与正版APP相似,仿冒APP后台能自动抓取用户在该APP中输入的助记词(相当于账号和密码)。公司技术主管郑某负责该APP的后端程序开发及提供售后服务。后端程序制作完成后,公司又陆续完成APP前端程序开发、域名绑定等工作,并通过杭州基某科技有限公司实现签名分发。
2021年1月,盈某公司将仿冒的imToken APP交付给委托方使用,盈某公司获利人民币3万元。同年2月,被害人杜某经人诱骗,为领取所谓的福利虚拟币,通过扫描二维码下载了一款所谓的新版imToken APP,并依据系统提示输入用户名和助记词。在杜某输入助记词后,APP显示数据异常。杜某随即发现其存放于原正版imToken APP内的63个以太币被他人转走,造成经济损失约人民币61万元。
二、分歧意见
技术人员制作虚拟钱包“钓鱼APP”的行为定性涉及三个争议焦点,即与其紧密关联的仿冒APP实际使用人的行为定性、技术人员作为犯罪工具提供者的行为定性以及虚拟货币的价值认定问题。
(一)仿冒APP实际使用人的行为定性
对仿冒APP实际使用人(即实行犯)利用该APP诱骗被害人输入助记词,而后转走钱包内虚拟货币的行为如何定性,是构成计算机类犯罪,还是构成侵财罪。如认定为侵财罪,如何在欺盗交织案件中区分诈骗罪和盗窃罪。
第一种意见认为,实行犯的行为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虚拟货币不具有财产属性,仅属于计算机数据。实行犯通过仿冒APP非法获取被害人的助记词,再通过助记词转移虚拟货币,其行为符合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构成要件。
第二种意见认为,实行犯的行为构成诈骗罪。虚拟货币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信息数据,还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因此虚拟货币能够成为侵财罪的行为对象。实行犯以领取福利虚拟币需要更新imToken APP为由,诱骗被害人下载仿冒APP后基于错误认识自愿向该APP泄露具有财产价值的助记词,其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第三种意见认为,实行犯的行为构成盗窃罪。虚拟货币可以作为侵财罪的行为对象,本案中的被害人虽是经实行犯诱骗在仿冒APP上输入了助记词,但主观上不存在处分虚拟货币的意识。实行犯通过技术手段非法获取助记词后将被害人的虚拟货币转走,其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二)技术人员作为犯罪工具提供者的行为定性
技术人员郑某为他人制作和维护虚拟钱包钓鱼APP的行为应如何评价,是构成实行犯的帮助犯,还是本身就是实行犯,抑或仅是单纯的帮助信息网絡犯罪活动的行为。
第一种意见认为,郑某构成实行犯。郑某不仅提供了犯罪工具,还应实行犯的要求修改完善犯罪工具,并维系犯罪工具的运行。实行犯的犯罪行为是与郑某共同协力完成的,郑某的行为属于实行行为的组成部分。
第二种意见认为,郑某构成实行犯的帮助犯。郑某明知他人委托其制作的是“钓鱼APP”,仍积极提供技术支持,本质上属于为他人提供犯罪工具,应认定为实行犯的帮助犯。
第三种意见认为,郑某与实行犯不成立共同犯罪,其仅实施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行为。郑某只是依据实行犯的要求制作仿冒APP,欠缺与实行犯之间的犯意联络。
(三)涉案虚拟货币价值的认定
虚拟货币种类繁多,既有公认的主流币,比如比特币、以太币;又有所谓的“空气币”“垃圾币”,且价格波动异常激烈,如何认定价值已成为司法难题。
三、评析意见
笔者认为,郑某应构成盗窃罪的帮助犯。当前社会,一些技术开发人员为犯罪分子“量身定制”具有各种犯罪功能的虚假APP。他们从对接需求、编写程序代码,到购买域名、租用服务器,再到APP封装和分发,形成了分工明确的专业化犯罪链条。司法实践中,对于利用“钓鱼APP”转移虚拟货币的行为定性、技术人员的地位作用、虚拟货币的价值认定等问题仍然存在较大争议。本文以郑某盗窃案为例,围绕前述争议焦点展开分析。
(一)实行犯的行为定性
1.虚拟货币可以被评价为刑法上的财物。单纯从物理形态上看,虚拟货币是“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属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犯罪对象,不能被评价为刑法上的财物。但近年来,以虚拟货币为犯罪目标的刑事案件呈爆发式增长,已严重危及公民财产安全。虚拟货币是虚拟财产的一种表现形式。民法典第127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可见民法典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持肯定态度。以比特币为例,2013年《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规定:“从性质上看,比特币应当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判断虚拟财产是否属于刑法上的财物,只要在个案中判断行为人所侵害的虚拟财产是否具有管理可能性、转移可能性与价值性即可。[1]依据该标准,比特币、以太币等标准虚拟货币因其自身特点符合刑法上的财物特征。第一,主流币凝结了人类抽象的劳动力,具有客观价值;第二,主流币能够被存放于虚拟钱包,具有可支配性和可管理性;第三,主流币可以通过区块链加密技术实现转让并产生经济收益。故笔者认为,目前以比特币、以太币为代表的主流虚拟货币可以被评价为刑法上的财物。
2.实行犯的行为属于秘密窃取他人财物。从表面上看,实行犯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特征,表现为实行犯实施了欺骗行为,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在仿冒APP中输入助记词,最终使得实行犯取得被害人钱包内的虚拟货币。但该观点未注意到诈骗罪要求被害人在处分财物时必须具有处分意识。被害人在输入助记词过程中并不具有将助记词泄露给他人的主观意图,故实行犯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实行犯的行为属于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秘密窃取”在本案中表现为双重形式:一是实行犯在被害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趁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之机,利用技术手段通过APP后台秘密获取被害人输入的助记词;二是在被害人未发现助记词已被窃取的情况下,实行犯利用助记词登录被害人的账户并对虚拟货币进行秘密转移。基于此,实行犯的行为符合以秘密手段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给自己或第三人占有的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3.实行犯的手段行为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与盗窃罪之间系牵连关系。实行犯通过技术手段获取被害人的助记词,再通过非法侵入方式,转移被害人钱包内的虚拟货币,造成他人经济损失,依据刑法第285条第2款之规定,其行为符合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构成要件。
实行犯的手段行为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目的行为是窃取他人财物,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对牵连犯一般从一重处罚或从一重罪并从重处罚。本案以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作为量刑依据,鉴于盗窃罪的法定刑明显重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故应以盗窃罪处罚。此外,在分析牵连犯的处断原则时,也应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本案中实行犯的主观意图是非法占有具有财产价值的虚拟货币,而不是扰乱网络空间的公共秩序,依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对其行为更宜以侵财类犯罪加以规制。
(二)技术人员的地位作用
1.郑某主观上具备帮助犯的“双重故意”。郑某曾辩解自己只是依据委托方的需求制作了仿冒APP,并不知道该APP可能被用于窃取他人的虚拟货币。但纵观全案,可从多方面来推翻郑某的辩解。一是委托方不愿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且要求郑某使用具有“阅后即焚”功能的蝙蝠聊天工具与其沟通制作细节,推定郑某应当知道所托事项涉嫌违法。二是委托方要求郑某租用境外服务器,且拒绝实名认证和域名备案。作为资深的技术人员,郑某应当知道前述操作异常,对方的目的是为了隐匿犯罪痕迹和逃避法律制裁。三是郑某的手机在案发前已下载过多款虚拟钱包及虚拟币交易软件,证实郑某平时关注过虚拟货币,理应知道助记词是管理和处分钱包资产的“钥匙”。郑某明知实行犯意图利用仿冒APP窃取他人的助记词,仍为实行行为的完成提供犯罪工具,促成实行行为,其主观上具有帮助犯的“双重故意”。
2.郑某的客观行为为实行犯提供了加攻作用。根据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共同正犯与帮助犯的区别,在于参与人是否支配了犯罪事实。纵观本案,郑某未发挥支配犯罪事实的作用。一是郑某对APP的实际使用情况并不知情,对交付后的APP也不具有管理权限。虽然郑某曾在APP交付后,按照实行犯的要求修改完善犯罪工具,维系犯罪工具的运行,但其所实施的帮助行为无法直接支配犯罪的发展进程。二是实行犯能够独立完成盗窃行为,毋需得到郑某帮助。若实行犯在获取助记词和转移虚拟货币过程中,需要得到郑某实时配合,那么可将郑某的协助行为视为盗窃实行行为的组成部分,但本案中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郑某的帮助行为与实行犯的行为之间具有因果性,即帮助行为使实行行为变得可能、容易。从技术上说,郑某制作的仿冒APP属于专业计算机软件,只能由技术人员制作完成,具有犯罪工具专门化的特征;从犯罪对象上说,仿冒APP可以被任何一名网友下载使用,具有法益侵害广泛化的特征;从犯罪效果上说,郑某制作的仿冒APP足以以假乱真,順利获取他人助记词,具有犯罪结果有效性的特征。所以,可认为郑某提供仿冒APP的行为促进、强化了实行行为。
(三)虚拟货币的价值认定
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认定各类虚拟货币的价值,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可供参考的认定方法有四种,分别是估价部门出具的价格认定意见、案发时虚拟货币交易平台显示的交易价格、虚拟货币的销赃价格及原始购买价格。笔者建议以被害人购买虚拟货币的原始价格来认定。理由在于原始购买价格较容易被查证,侦查机关可以通过调取被害人的银行流水、支付宝交易记录等予以明确;且该价格能够客观反映被害人遭受的实际经济损失,以此为依据追责能够实现罚当其罪。
(四)盗窃罪与其他罪名的竞合问题
APP是大众参与移动网络生活的基础,仿冒APP的行为直接影响大众的网络生活质量,扰乱网络空间公共秩序。郑某明知他人利用仿冒APP实施网络犯罪,仍依照他人需求提供专门用于犯罪的APP,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根据刑法第287条第3款之规定,实施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因此本案仍应以盗窃罪追究郑某的刑事责任。
同时,仿冒APP的行为还侵犯了知识产权。根据刑法第213条之规定,如果imToken图标已被注册为商标,那么郑某在同类虚拟钱包APP上使用与imToken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可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郑某的行为侵犯了知识产权、财产权双重法益,由于郑某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情节较为轻微,根据“想像竞合从一重”的处断原则,仍应以处罚较重的盗窃罪来科刑。
[1]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9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