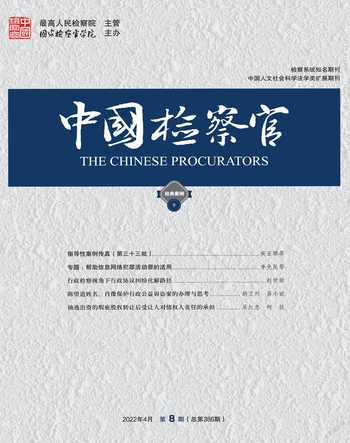“两卡”犯罪中银行卡提供者的行为定性
金燕 刘勋 李楠楠
摘 要:由于网络犯罪行为具有隐蔽性、意识联络趋弱性等特点,对于“两卡”犯罪中银行卡提供者的行为定性,难以适用传统共同犯罪理论予以规制,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将相似的帮助行为区别定性亦存在一定困难。对此,应全面考量银行卡提供者客观行为所侵犯的不同法益,并着重审查能够证实行为人主观明知方面的证据,依托客观证据合理运用经验法则予以刑事推定,从而准确认定行为人主观明知的内容和程度,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确保打击“两卡”犯罪不枉不纵。
关键词:银行卡提供者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一、“两卡”犯罪中银行卡提供者行为定性分歧
[案例一]2021年1月,张某、申某等人为牟取非法利益,明知所办理的银行卡提供给他人系用于网络犯罪,仍由申某办理工商银行卡等“四件套”经由张某邮寄给“上家”使用,后该银行卡接收被害人汤某某被电信诈骗钱款28万余元。[1]
[案例二]2020年8月,王某等人经共谋,在明知相关转账钱款系来路不正的情况下,仍纠集范某等多人通过网络提供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等收款二维码为“上家”收取、转移相关通过电信网络“裸聊”敲诈勒索钱款共计27万余元,并按照转账数额获取约3.5%提成。[2]
[案例三]2021年2月至3月,钟某利用网络联系刘某等人,在明知刘某等人实施“杀鱼”电信诈骗犯罪的情况下,仍纠集多人提供银行卡收款二维码帮助刘某等人接收、转移诈骗钱款,并按照转账数额获取约20%提成,截至案发共收取电信诈骗钱款24万余元。[3]
上述三个案例是在“断卡”行动中查办的行为人提供银行卡等账户帮助“上家”接收、转移电信诈骗钱款的相似案件,但对行为人的定性却存在分歧意见,主要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下简称“掩隐罪”)、上游犯罪的共犯等。对银行卡提供者是以上游犯罪共犯论处还是进行独立化定罪,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现象仍较为常见。
二、对银行卡提供者行为定性的困境及解决进路
(一)电信诈骗等上游犯罪分子未到案给共同犯罪认定带来困难
由于电信诈骗等犯罪的特殊性,司法机关往往基于本辖区被害人报案等线索启动刑事程序,并根据资金流向等证据抓获下游银行卡提供者,大多难以直接抓获上游犯罪分子,加之目前电信诈骗等犯罪已经出现从境内向境外发展的态势,例如本文三个案例中上游诈骗犯罪分子均因在柬埔寨、缅甸、阿根廷等国未到案,造成此类案件中大多欠缺上游犯罪分子供述证据,使得下游银行卡提供者在主观明知、共谋等方面存在较大辩解空间。
另外,由于网络犯罪隔时空、隐匿性、产业化等特点,上下游犯罪分子仅通过网络终端进行层级化的犯意传递,在行为人意思联络趋弱甚至为零的情形下,司法机关往往难以证明帮助者和受助者之间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而审判实践对关联犯罪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共犯理论层面,固守只有共同的犯罪行为、共同的犯罪故意等才能认定为共同犯罪的立场,限缩了共同犯罪的成立范围,这也是司法实践中认为行为人构成帮信罪而非上游犯罪共犯最多的裁判理由。[4]加之法律对部分此类帮助行为独立化定罪,行为人主观明知内容、程度、阶段的不同往往会导致司法机关得出不同的结论,而帮信罪、掩隐罪、上游犯罪共犯等罪名之间刑期差异巨大,行为人在趋利避害心理下更容易在供述时避重就轻,造成司法指控证明难度加大。
(二)相似的帮助行为给罪名准确适用带来困难
“断卡”行动中涉银行卡案件定性分歧产生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于此类犯罪行为的规定较为相似,罪名之间存在一定竞合,另一方面司法实践中如何将相似的司法解释落实到具体的刑事证据上亦存在一定困难。例如,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明知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他人提供非本人身份证明开设的信用卡、资金支付结算账户后,又帮助他人转账、套现、取现的,以掩隐罪追究刑事责任,并且另外规定了“实施上述行为,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根据刑法第287条之二关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其实,不论是刑法条文还是司法解释,都在本质上认同为电信诈骗犯罪提供银行卡是一种帮助行为,而将帮助行为正犯化独立定罪,正是因为帮助行为的危害性日益严重而有独立评价的必要。正如参与立法者所言,设置该罪名的立法初衷至少有三方面的考量:第一,部分犯罪借助网络形成了利益分享的产业链,产业链中各行为人具有相对独立性;第二,帮助行为经由网络技术被成倍放大,不仅降低了网络犯罪的门槛和成本,而且部分案件中帮助行为的作用与实行行为基本相当,甚至对案件具有支配性影响;第三,网络帮助行为改變了传统“一对一”的认定模式,其犯罪链条、犯意联络以及上下游关系复杂,认定共犯存在较大障碍。[5]
但由此带来的问题则是,如何合理运用法律论证方式将类似行为通过刑事证据予以准确区分。笔者认为,在法律适用逻辑上,首先应牢牢把握帮信罪作为“两卡”犯罪兜底性罪名设置这一定位,只有在行为无法作为上游犯罪共犯或者掩隐罪等其他罪名适用的情况下方可考虑该罪名,对于银行卡提供者,如果确有行为人与上游犯罪分子事前共谋的线索,则应积极引导侦查机关收集相应证据,而不能将本应按重罪认定的行为以帮信罪降格处理。例如,上述案例三中,虽然钟某实施的是电信诈骗中的帮助行为,钟某及其辩护人亦提出钟某应以掩隐罪定性的意见,但法院综合侦查机关收集的上下游同案犯供述、双方微信聊天记录等在案证据,尤其是考虑钟某系在观看“上游”诈骗分子向其发送的“杀鱼”诈骗作案视频,明确知晓“上游”犯罪手段后仍积极纠集多人提供收款账户,其系在诈骗既遂前进行犯罪共谋,并按照转账数额约20%获取高额分成,该分成比例亦远超司法实践中掩隐罪中行为人按转账数额获取的1%-3%分成,最终认定钟某构成诈骗罪共犯而非掩隐罪。
(三)以行为所侵犯的法益不同为区分
在涉银行卡类“两卡”犯罪中,更大的难点在于如何区分犯罪形态较为类似的帮信罪与掩隐罪,因为提供银行卡及收取、转移钱款等行为往往既可被归入帮信罪中“提供支付结算等帮助”,亦可被归入掩隐罪中“窝藏、转移”等犯罪构成之中。针对两罪的区分标准,有观点提出以提供银行卡等帮助行为是在上游诈骗犯罪既遂之前还是之后产生并发挥作用力,或者以银行卡是直接或者间接接收被害人钱款来区分。[6]笔者认为二者均存在一定不足,司法实践中下游行为人提供银行卡绝大多数发生在上游犯罪既遂前,因此单纯考虑时间节点难以真正起到区分罪名的作用。另外,银行卡提供者在提供银行卡后,并不知晓或介意银行卡具体是被用于接收还是转移钱款,以行为人并不知晓或无法控制的银行卡后期使用階段来区分前期行为罪名亦有“客观归罪”之嫌。
笔者认为,“无行为则无犯罪”,刑法所打击的是行为人具体实施的犯罪行为而非单纯的犯意,刑法所保护的也是与之相对应的法益,对于行为人在类似或连续犯意引导下实施的客观行为,可以参照行为所侵犯的法益来区分帮信罪与掩隐罪。这两个罪名虽均被纳入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章节,但细分二者,帮信罪系扰乱公共秩序罪范畴,掩隐罪则属于妨害司法罪。我国《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28条规定,“银行卡及其账户只限经发卡银行批准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因此,如果行为人明知他人使用银行卡用于犯罪活动,但仅实施提供银行卡等行为,则因行为人负有不得将实名制银行卡出租、转借等银行合同或者社会公共管理秩序等方面的抽象义务而构成帮信罪。如果行为人不仅提供银行卡,还帮助犯罪分子转移赃款以逃避、妨害司法机关对电信诈骗等犯罪的打击,则因其另行转账、取现等行为侵害了新的法益,社会危害性相较于帮信罪更大,则以掩隐罪定性为宜。
因此,在上述案例一中,张某、申某仅实施了售卖银行卡“四件套”这一个行为,其既未实施后续转账等行为,亦未从中获益,其客观行为止步于此,因此只能以其提供银行卡行为给社会公共管理秩序造成的抽象法益侵害定罪。而在案例二中,王某等人不仅提供收款二维码,还按照“上家”指示另行实施收款、转移等行为,并按照转账数额获取约3.5%提成,王某等人的行为具有内容的多样性,其不仅侵犯了抽象的社会公共管理秩序等法益,亦现实妨害了司法机关后续对此类犯罪的及时查处追诉,具有法益侵害的双重性。最终法院认定张某、申某等人仅构成帮信罪,而认定王某等人构成掩隐罪。
三、对银行卡提供者主观明知证据的审查要点
(一)严格区分不同罪名中银行卡提供者主观明知认定标准
“断卡”行动中查办的案件客观行为较为类似,因此行为人主观明知方面的证据对于准确区分罪名显得尤为必要。根据刑法规定,帮信罪需要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掩隐罪需要行为人“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
笔者认为,罪刑轻重应与公诉机关的指控、证明义务呈正比例关系,帮信罪作为法定刑最高为3年有期徒刑的轻罪案件,其对行为人主观明知方面要求不应高于法定刑最高为7年有期徒刑的掩隐罪,对帮信罪等轻罪案件设定过高的主观证明标准,不仅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也容易放纵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司法实践中,掩隐罪对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要求已经降低为只需行为人笼统供述明知“钱款来路不正”即可。因此,帮信罪中对银行卡提供者主观方面的要求应为行为人明确供述知道银行卡会被用于网络违法犯罪行为,或者通过其他证据能够推定行为人确知,或者事中知晓但怠于采取补救措施以至犯罪继续发生的均可构成该罪。正如有些学者所言,其构成要件可分为两种类型,既包括明知正犯犯罪计划或意图且有促进犯罪行为更容易实现的意思(“明知且促进型”),也包括虽然明知正犯犯罪计划或意图但是没有促进该犯罪行为易于实现的意思(“明知非促进型”),帮信罪的设定实际上正是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明知非促进型”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7]
(二)运用经验法则合理推定银行卡提供者主观明知
司法实践中较难认定的就是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明知”“故意”等主观因素,除非行为人主动如实供述,否则很难确定证明,尤其是在此类犯罪大多欠缺上游犯罪同案犯供述的情况下,如果行为人拒不供认,则进一步加大了司法机关将事实涵摄入相关罪名的难度。而此时,事实推定作为证据缺乏状态下运用客观事实证明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的唯一手段,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8] 《意见》中规定了可以推定行为人主观明知的各种情形。因此,对帮信罪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可以结合一般人认知水平和能力,考察行为是否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行为人是否逃避监管调查等多种情形综合评判。
易言之,主观付诸客观,司法机关调取的能够印证银行卡提供者行为异常的客观证据越充分,行为人主观知道或应当知道“上家”使用银行卡进行电信诈骗犯罪的结论则越容易得出。经验法则作为连通基础事实与待证事实的桥梁,根据基础事实与待证事实之间的逻辑联系,可以解决待证事实证明的困境,也降低了司法者对主观故意的证明难度。[9]例如,上述案例二中,虽然部分行为人提出不知晓钱款系犯罪所得的辩解,但法院综合钱款转账大多集中发生于凌晨时段,钱款到账后行为人按照“上家”要求立即删除转账记录,部分转账记录附言出现“报警、抓到你”等字眼,行为人与“上家”联系会专门使用具有自动销毁等功能的密聊软件,行为人从转账数额获取3.5%的高额提成等多方客观证据,最终并未采信相关辩解意见,而认定行为人构成掩隐罪。
(三)综合银行卡提供者主观明知内容、程度准确定性
帮信罪和掩隐罪中的银行卡提供者对上游犯罪多为概括性明知,其仅要求行为人认识到上游会实施或在实施犯罪即可,并不要求认识到实施特定犯罪,其对被帮助者所实施具体犯罪手段、危害后果等内容虽然具有认知,但难以具有清晰、确定的认识,其一般对上游犯罪的发生结果持放任态度,尤其是当帮助行为人仅明知自己在帮助他人实施犯罪,但并不知道犯罪的具体种类或具体情形时,或者行为人同时帮助多人实施犯罪,但并不知道每个人实施的具体犯罪种类之时,行为人仍以帮信罪定性为宜。例如上述案例一中,张某、申某供述称提供银行卡给对方用来“跑分”,银行卡会被用于收取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钱款,虽然最终查实银行卡内钱款来源于电信诈骗犯罪而非赌博活动,与二人认知的具体内容有一定差异,但在被帮助对象行为会涉及违法犯罪层面是一致的,该认知仍可被帮信罪的概括性主观明知构成要件所涵盖,张某、申某二人明知且放任后续诈骗犯罪的实现,应以帮信罪论处。但如果确有证据证实行为人事前即明确知晓上游犯罪的具体作案手段、后果等内容而仍积极提供帮助,行为人此时对犯罪结果的发生则持希望或积极促进的态度,其主观罪过更大,客观参与程度也更深,司法机关可在综合考量行为人分赃获利、帮助行为持续时间、行为社会危害性等因素后,对此类行为人以上游犯罪共犯论处。
总之,在打击涉银行卡提供者的“两卡”犯罪中,司法机关既要防止因有帮信罪等兜底性罪名而放纵对本应以上游犯罪共犯行为的打击,又要防止不顾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原则而笼统将银行卡提供者均以上游犯罪共犯论处的倾向,确保打击“两卡”犯罪不枉不纵。
[1] 参见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1)苏0104刑初574号。
[2] 参见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1)苏0104刑初188号。
[3] 参见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1)苏0104刑初644号。
[4] 参见欧阳本祺、刘梦:《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适用方法:从本罪优先到共犯优先》,《中国应用法学》2022年第1期。
[5] 参见臧铁伟、李寿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233 页。
[6] 参见李勇:《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适用误区》,《检察日报》2022年1月18日。
[7] 参见张明楷、刘艳红、周加海等:《关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理解与适用的讨论》,《民主与法制》2022年第7期。
[8] 参见杨宗辉:《刑事案件的事实推定:诱惑、困惑与解惑》,《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年第4期。
[9] 参见韩旭:《刑事司法如何运用好经验法则》,《检察日报》2021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