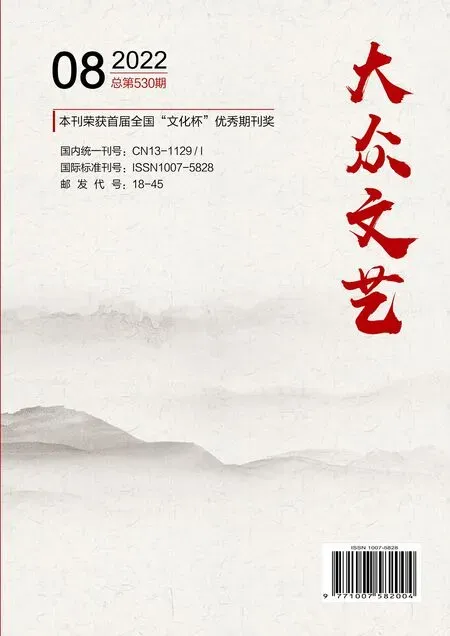“我”到哪里去了?
——时代语境下看鲁迅《祝福》的电影化改编
付艳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00)
一、“我”的消失带来的电影改编
(一)人物“我”的形象缺失
小说中以“我”的视角展开叙述,同时“我”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形象。小说中有大量的“我”的内心独白,这是小说中塑造“我”的人物形象的主要方式。从小说开头“我”和四爷的交往中,就透露了“我”的身份信息,“新党”,结合小说创作背景,即拥护辛亥革命的革命者,“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点明了“我”和鲁镇的疏离,因而“我”既是故事的参与者,同时又能够相对冷静地以外来人的视角审视鲁镇和祥林嫂。“我”对四爷的书房的“百无聊赖”的态度又表现了其对于封建传统文化的轻视态度。然而,接着与祥林嫂有关“有无魂灵”的对话却又揭露了“我”作为一个接受新知识的“新党”,在面对祥林嫂这样的旧式农村妇女的发问时,却无法承担起一个启蒙者的职责,而对此抱着“于我无关”的态度,即使为祥林嫂感到担忧和不安,也即刻为“福清楼的清炖鱼翅”给扫开了。从“我”和四爷的交往中,可以看出,在某一程度上,“我”和祥林嫂是共鸣的,也是个“谬种”,“我”与鲁镇、与鲁镇的人们是剥离的关系。而其中,又与祥林嫂不同的是,祥林嫂本身与鲁镇的人们是一体的,他们同在鲁镇的“祝福”之下,却又其实被这“祝福”所害,被这封建礼教所害;“我”是主动脱离鲁镇“祝福”的新式知识分子,不被鲁镇的人们所欢迎接受,我明白封建礼教对人的臧害,却在四爷对“我”的抗拒,在社会对“我”的不包容中彷徨苦闷,因此即使“我”是毫不介意魂灵的有无的,却也无法对祥林嫂进行启蒙,对祥林嫂的态度只能是在同情与不安中又保持着一定的疏离。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彷徨苦闷的新式知识分子的代表,一方面接受了新式知识教育因,思想上与封建旧文化浸染下的鲁镇的人们隔膜,另一方面又不为鲁镇人们的理解与欢迎,其受到排斥正表现了封建旧文化势力的顽固所在。
而在电影中,“我”这一人物形象完全消失了。电影用镜头代替了“我”的眼睛,“我”失去了叙述的功能后,影片中并未给出相应一个人物表现“我”这样一个新式知识分子的存在。
(二)叙述视角的转变
小说中,“我”作为一个鲁迅小说中常见的知识分子启蒙者,既是故事的主要参与者,又承担了叙述的主要视角。而在电影的改编中,叙述视角变成了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用镜头以全知的方式统摄整个故事。
小说中“我”的初次出现在“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在这之前是关于“我”眼中的鲁镇旧历的年底的描写。虽说是“新年的气象”,但其实“新”的喜庆不足,反而带点沉重,以至于“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这既是对环境的描写,也是“我”的心情的反映,同时也预示着“祝福”之下祥林嫂所受的压迫。接着,仍然是以“我”的视角,带着读者看见了鲁镇“祝福”的年俗,四叔的书房。到了这里,以“无论如何,我决计明天要走了”一转笔锋,叙述时间往回,转而写“我”的回忆,倒叙昨天“我”遇见祥林嫂的情节,有关“人有无魂灵”的对话。叙述时间回到当下,借四爷之口,写出“祥林嫂死了”这一事实。“我”又陷入了回忆,写“我”“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再由爆竹声将我从回忆中拉回现实,回到“祝福”。小说采用“我”的叙述视角,使得故事情节更具真实度,拉进与读者的距离,即使是到后半段,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我”的视角范围,但却巧妙地以“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将叙述视角“我”延续下去,即使是“道听途说”,也因叙述视角“我”也是故事的参与者而变得更具真实性和感染性。另外,由于“我”的新式知识分子的特殊身份,“我”的视角下展开的故事情节也带有强烈的主观意味与特定时代性质。
电影采用了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作为叙述视角。在影片开头就以画外音的方式,“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大约四十多年前,辛亥革命前后,在浙东的一个偏僻的山村里”。这样一段画外音,简单交代了接下来影片中的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等背景信息。明确点出的时间地点将观众与影片故事抽离开。接着,电影以远景镜头呈现了一个小山村的景象,随后镜头聚焦到祥林嫂身上,就此引出影片主人公。故事情节跟随着祥林嫂展开,讲述了祥林嫂的故事。整部电影中,镜头主要以一个上帝视角统摄着整个故事,它围绕着祥林嫂的故事,可以知道故事的任何一面,将小说中的“我”所听闻的故事都用镜头拍下,剪辑出流畅通俗的电影情节呈现给观众,使得影片更容易为人民大众所理解与接受。
(三)叙述声音的改变
小说中“我”作为参与故事的人物,身为“知识分子启蒙者”,却又承担不起启蒙的责任,也不知前方在何处,自身处于彷徨之中,因而其态度暧昧。祥林嫂因而得到自己站出来发声的机会,祥林嫂的人物个性不是“我”决定的,也不是小说的叙述者决定的,而是祥林嫂自己呈现的,小说呈现“复调”的结构,使得小说主题更加丰富。读者可以在小说的“众声喧哗”中更多地加入自己的反思。
与小说中“我”不同的是,电影中的叙述声音直接地给出自己的明朗态度,祥林嫂只是一个故事人物,不能自己站出来发出声音,祥林嫂的声音是通过叙述者传递出来的。在影片开头就以画外音的方式,“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大约四十多年前,辛亥革命前后,在浙东的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叙述声音的客观疏离性增加了观众与祥林嫂的距离,也弥补了图像叙事的不确定性,体现了改编者的态度意图。除影片开头的画外音以外,影片中还有中间和结尾分别有一处画外音,中间处为“日子很快地过去了,一年又是一年,人家说,祥林嫂交了好运,可是,这好运并不长久。……”结尾处为“祥林嫂,一个勤谨、善良的女人,经受了数不清的苦难和凌辱之后,倒下了,死了。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对,这是过去了的时代的事情。应该庆幸的是,是这样的时代,终于过去了,终于一去不复返了。”此二处的叙述声音的出现脱离故事本身,再次跳出来提醒观众其与影片中主人公的距离,语气客观冷峻,是一个与之无关的旁观者的声音。而叙述者的声音反而与观众更加接近,他站在观众的时间上,讲述一个过去的时代的故事,并且不断强调“这是过去的时代”,末尾就差点要高呼着“你们已经迎来了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我们已经迎来了新的时代、新的生活!”了。祥林嫂是叙述声音下的故事主人公,是叙述者借以传递思想号召的人物,叙述者以引导者的态度立场,告诉观众们,在过去的旧的时代,像祥林嫂这样善良、勤谨的女人意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劳动去追求幸福却命运悲惨,可是今天不一样,只要努力劳动,憧憬明天,就都能得到幸福,能够真正地被祝福。影片中有意拉开观众与故事的距离,消解真实性,从而观众获得的教化意义甚于对祥林嫂感到同情和悲伤的情感意义。
(四)叙述顺序的改变
小说中的叙述由我的回忆展开,因此小说中有插叙、倒叙的部分,而不是一叙到底的顺序模式。这样的叙述顺序与小说这一传统媒介的艺术表现需要有关,在回忆过祥林嫂的悲惨一生后,再回到鲁镇的新年“祝福”上,颇具讽刺意味,引发读者的深思。
而在影片中,叙述不再局限于“我”的眼睛和听闻,直接用镜头聚焦在祥林嫂的故事,将祥林嫂的故事按照顺叙的方式呈现给观众。先是祥林嫂在鲁镇做工;再是被逼改嫁;接着是接受贺老六,两人共同努力生活;再由于资产阶级的压迫将二人逼到走投无路,贺老六被逼死、阿毛被狼咬死,将故事推向一个高潮,祥林嫂的悲剧真正开始;祥林嫂回到鲁镇却不被接受,最后走向死亡。故事的叙述因顺叙的方式而变得更加流畅易懂,观众在观影完之后就立刻能明白祥林嫂的一生,看到了其一生的悲剧所在,又在画外音的结束中走向了对过去的思考及对未来的憧憬。
二、“我”的消失后主要的人物形象变化
(一)祥林嫂
祥林嫂在小说中被封建旧文化所迫害,她因守贞节的传统观念而不肯改嫁,被逼着改嫁却被人们指点诟骂;因“不祥”的偏见而受疏远;最后在“魂灵有无”“下了地狱被撕成两半”的预言走向绝望。但是祥林嫂一面是封建旧文化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却也是封建旧文化的忠实信奉者,祥林嫂的悲剧在某一程度上也是由其自身造成的,她也同样固守“守贞节”的传统观念,也同样相信自己是个不祥之物。只是这些想法都在其生活的文化环境中得到了深化和固化。
小说在新式知识分子的“我”的视角下,凸显了祥林嫂的愚昧与落后,而在影片中则弱化了这一面,如影片中祥林嫂不愿改嫁的片段加上了祥林嫂念叨、惦记着死去不久的祥林而非只是由于固守贞节观念,这一细节便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祥林嫂的愚昧落后,影片主要侧重强调其勤劳善良的一面。影片还特别突出了祥林嫂在改嫁后于贺老六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过程,反映了人民大众在劳动中靠双手创造幸福的快乐。
(二)贺老六
在小说中,贺老六的形象并不突出,只是众多封建势力之一,强抢祥林嫂。在小说中,贺老六甚至从未正面出现过,第一次出现是在卫老婆子提到祥林嫂被婆婆许给贺老六,第二次则是通过祥林嫂之口,称其力气大以表明自己与贺老六成亲是被强迫的。贺老六在小说中人物形象并不鲜活,只是一个符号,不需要有具体的形象,甚至可以不需要有姓名,只是在当时的社会里强大黑暗的封建势力之一。
而在电影中,贺老六的形象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他成了一个善良淳朴的农民。在面对祥林嫂的不情愿时,他没有强迫,反而主动提出要送祥林嫂回去。他的善良感动了祥林嫂,两个同样勤劳肯干的劳苦人民生活在了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另外,在影片中,他从一个强势的施暴者变成了一个处于弱势的被压迫者。贺老六受伤后去拉纤,压迫者却坐在船上撑着伞摇着扇子不断地吆喝着催促“快点”;两人的生活越过越好,对未来无限憧憬的时候,却被催债并要求其拿房子抵债,贺老六被逼死;体现了追求幸福的无产阶级劳动者与不劳而获的压迫者之间的对立和矛盾。
三、时代语境下的改编意义
任何文学艺术总是产生于一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反映一个时代的特点,也同时被打上了一个时代的烙印。小说《祝福》创作于1924年,而由夏衍担任编剧的电影《祝福》则拍摄于1956年。前后相差32年,但时代变幻,社会矛盾发生变化,时代语境也已然不同。
1924年,鲁迅在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工作,曾热切地投身于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热心于扶持新青年,一心为打破封建传统落后文化的束缚启迪民智而努力奋斗。而此时处于革命落潮时期,鲁迅正处于彷徨迷茫之中,更有千千万万的新式知识分子彷徨苦闷,而小说中“我”的形象就是这样一个代表。小说中的我,既暴露了自己在新旧文化交锋时的思想彷徨,也揭露了祥林嫂和鲁镇人们的愚昧和落后。祥林嫂既受封建旧文化的迫害却又坚守封建旧文化,既令人怜其不幸,又让人叹其愚昧。我作为“新式知识分子”,在鲁镇中没有自己的定位,也无法对祥林嫂进行启蒙。小说既在控诉封建旧文化对人的压迫,也在反映新式知识分子的迷失和启蒙者的失位。小说的主要矛盾其实聚焦于新文化思想与封建旧文化思想,而电影的改编其实已经随其时代语境悄悄转换了矛盾的聚焦点。
1956年,新中国成立了七年,正处于巩固新生政权建立新政权话语的重要时期,文学艺术也很大程度地被赋予了政治意义。此时新中国的文学艺术都以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思想,强调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强调大众化。电影中全知的叙述视角和顺序的叙述顺序都使得影片更加通俗化,便于人民大众工农兵接受和理解,符合大众化的要求,符合文学艺术为无产阶级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时代要求。另外,在电影中,矛盾的聚焦不再是新思想与旧思想的交锋,而转移到了勤劳善良追求幸福的农民阶级与不劳而获的压迫阶级的对立,电影中增添了四老爷和太太克扣祥林嫂一个月的工钱;贺老六受伤后去拉纤,压迫者却坐在船上撑着伞摇着扇子不断地吆喝着催促“快点”;贺老六和祥林嫂被催债用房子抵债逼得走投无路等情节都反映了这一对立。在旧时代,他们勤劳善良却不得善终,因而,叙述者跳出来说“这是过去了的时代”。电影中的叙述声音像是一个新时代的传声筒,像是一个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与传递,向着电影屏幕前的新时代的人民大众发出声音和召唤。因此,即使影片中上演的是悲剧的故事,也只是过去的故事,观众们却将沉浸在于新时代新政权下靠劳动获取幸福的美好憧憬和愿景中。电影的改编是一种再创造,反映了新时代的需求和呼吁,承担了政治教化的作用,向人民群众传递了在新政权下创造幸福生活的信心。
改编的成功与否不应单以“忠诚度”为标准,文学艺术具有强大的思想力量,通常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祝福》的电影改编以小说为脚本,但是并未局限于小说,而在小说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造,紧密结合时代背景,塑造了一个勤劳善良的祥林嫂的形象,传递了新时代劳动奋斗创造幸福生活的信念,使得祥林嫂在人民大众中深入人心,又做到了激发人们创造新生活的信心,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需要。
四、关于影片结尾的一点思考补充
小说中“我”和祥林嫂的对话这一情节由于“我”的消失而消失,改编影片中结尾以祥林嫂自言自语“人到底有没有魂灵”的形式来补充这一情节。在我看来,这一幕有画蛇添足之疑。小说中祥林嫂对我“人有没有魂灵”的发问直指人心,既戳中了代表新式知识分子的“我”,也强调了封建旧思想对人的迫害。而电影中“我”被主流意识形态的叙述声音所替代,祥林嫂最后的发问没有对话的对象,因而成了审视内心的意象,既不再具有冲击人心的力量,也脱离了电影叙事的主线,电影中关于劳动百姓与封建势力压迫者的对立的叙述已经在祥林嫂沦为乞丐中走向了深思和积淀,此时有关封建旧文化的反思的出现反而打破了电影叙事的完整性与在新时代语境的思考性。因而我认为,结尾无须再打着“忠于鲁迅”的旗号将“有无灵魂”的发问这一情节强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