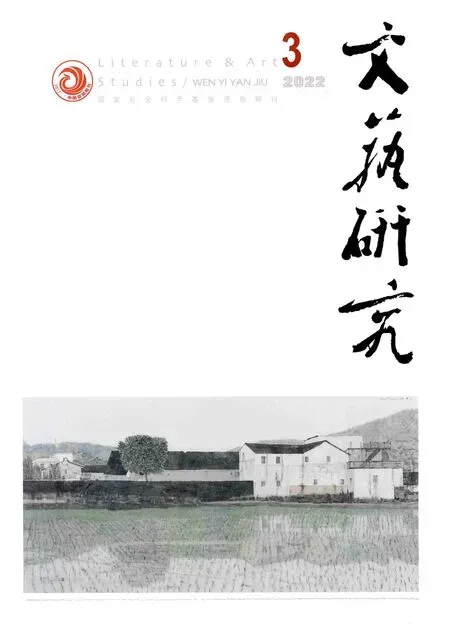现实何以消失:论维利里奥的后人类主义视觉理论
李三达
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是一位难以定义的思想家,他的专业领域是建筑和城市规划,可他同时又是一位媒介理论家。他的著作中遍布着“地堡”“炸弹”“后勤”“瞄准线”等军事术语,但令其名声大噪的却是对美学和电影的讨论。然而,如果说维利里奥是一位美学家,他又较少系统地讨论艺术和哲学的关系,而是专注于感知问题,尤其关注最新技术对感知造成的影响。作为媒介理论家,他对海湾战争在电视上如何呈现的思考经常被拿来与让·鲍德里亚进行比较,“消失”这一非常能显示其个人思想特征的关键词也不例外。鲍德里亚在《为什么一切还未消失?》这本小书中提到,资源是耗尽,种族是灭绝,这些都是“自然法则”,但是人类发明了一种新的模式,也就是所谓“消失的艺术”(art of disappearance)。鲍德里亚的意思是,在技术的发展下,我们用以再现世界的方式实际上抛弃了真实世界。实在世界终将消失,这可以被视作鲍德里亚拟像理论的衍生结论。受其影响,维利里奥也针对“消失”现象做出一系列思考,他虽然和鲍德里亚有着一致的结论,但更关注变化的过程。这使得维利里奥旗帜鲜明地指出,电影是“消失”的始作俑者,并以此为基点,将其理论应用至对更广泛的新型视觉技术的讨论中,由此总结出身体、技术、速度与现实感知间的关系。
一、感知的身体与摄影机器
维利里奥整个理论体系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是“消失的美学”(l’esthétique de la disparition),这也是他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一部著作的标题。和通常所理解的不同,这一概念并非意味着一种与艺术有关的哲学,“美学”在他的语境中更倾向回到其本义“aisthesis”,即一种感知或感觉。值得注意的是,在维利里奥的语境中,这种感觉并非日常的感觉,而是一种全新的、基于现实消失而产生的感觉。
现实之所以在感知中消失,是因为一系列电影技术的发明。斯坦福大学的建立者、曾任加州州长的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曾与人打赌,关于马的四个蹄子在奔跑时是否有全部悬空的瞬间。这个问题的解决者就是电影拍摄技术的鼻祖埃德沃德·麦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1878年,他受斯坦福委托与一位铁路工程师联手发明了一套运动摄影装置,这套装置包含12台摄影机器,让马在跑过摄影机的时候触发摄影机并拍下那一瞬间的照片。
最先提出马四蹄腾空问题并影响了麦布里奇的是法国生理学家埃蒂安-儒勒·马雷(Etienne-Jules Marey)。他所发明的便携式摄影枪(形状像一把老式的带有圆筒的加特林枪)是一种可以在一秒钟之内拍摄12次并且都记录在同一张照片上的装置,这种拍摄方法被称为连续摄影法(chronophotographie)。与麦布里奇不同的是,马雷不是一名摄影师,而是一位科学家,他不但研究过空气动力学,还制造了自己的航空器,所以他更倾向于用自己的设备研究昆虫、鸟等各类动物的运动甚至液体的运动。马雷出版了两部著作,一部是《鸟的飞行》(),另一部是《运动》()(图1)。他研究的对象有一共同的特征:这些对象由于运动速度过快,人依靠肉眼难以直接观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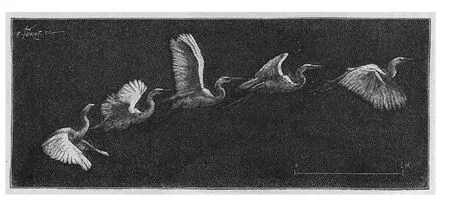
图1 埃蒂安-儒勒·马雷《运动》插图 1894
马雷在维利里奥的理论语境中极为重要,被反复提及,这不仅因为他所发明的摄影枪是一种前电影时代的连续摄影装置,还因为他身处航空技术迅速发展的时期。他所参与的这两个事件意味着摄影技术从静止拍摄装备向运动拍摄装备的转变。马雷的连续摄影法拍摄出来的影像,从效果上讲类似多重曝光,而移动的摄影机所拍摄出来的内容在放映时则是一个运动的世界。前者企图将不同的时间呈现在同一空间中,而后者则在眼睛和机器之间达成了一种一致性,从而呈现出一种运动影像。所以,正如维利里奥所言,多重曝光被移动摄影(traveling shot) 所取代,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依靠可以运动的运载工具。其实,维利里奥所描述的场景与我们乘坐交通工具时的体验类似:我们看着车窗中不断倒退的世界,就仿佛在观看一帧一帧放映的电影。与看电影稍有不同的是,在这种情况中不停变化的是观看者的位置,而被观看的世界处于静止的状态。卢米埃尔兄弟的《火车进站》(L’Arrivée d’un train en gare de La Ciotat,1896)是用固定机位方法拍摄的结果,镜头固定不动,火车缓缓驶过,各种人物在镜头前移动,维利里奥对此评论道:“这种电影是从外部观察运动,根本上,是以静坐不动的方式,投在运动物体之上的一种注视。”与之相反的是,摄影师比利·比泽尔(Billy Bitzer)在1898年把一台摄影机固定在快速行进的火车头的减震器上,模拟了在火车上观看后退景象的观众视角。这两种拍摄都是为了让观众建立起时间与空间的连续统一性,从而产生身临其境的效果。维利里奥指出,在这些例子中,“摄影机复制了习惯性视野的状态,它是对行动的一种同质性见证”。
人在观看世界的时候,可以在确定的时间和确定的空间中、在不同的视觉对象之间建立联系,联系的方式就是肢体的运动,所以“具身性”在日常生活的观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电影技术却不一样,由于摄影和放映的分离,以及蒙太奇等技术的运用,日常生活中原有的观看方式在观看电影时失效了。比电影更早被发明的摄影也是如此。每一张照片的诞生都意味着有一种现实就此流逝或消失,正如罗兰·巴特在《明室》中所说,“这个存在过”的意思是,“我看到的这个东西曾经在那里、在无限与那个人(摄影师或看照相的人)之间的地方存在过”。换个角度来看,当我们看见摄影中的世界时,在被拍摄时存在过的那个真实世界也就消失了。对这一现象加以利用,就产生了一种特别的视觉效果,这就是“停机替换手法”(stop trick)。法国导演乔治·梅里爱曾经描述自己在巴黎歌剧院广场上拍摄时,机器突发故障,要继续拍摄就必须得停止一分钟再重启,而这段时间内行人、车辆都发生了位置变化。等到重新开机拍摄时,原来的公交车变成了灵车,男人变成了女人。这一有着替换效果的技巧就是“停机替换手法”,其特点在于保持电影的镜框、布景、人物等位置不变,通过无缝对接的剪辑,从而造成某些细节或局部在视觉感官上的替换。
虽然梅里爱在1907年的著作《电影的视觉》(Les Vues Cinématographiques)里认为是他发明了这项技术,但实际上早在1895年,爱迪生制造公司的电影《玛丽一世的处决》(The Execution of Mary Stuart)中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拍摄手法,影片所展现的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的断头场景正是这种技术的产物。无论这一技术的真正发明者是谁,梅里爱的拍摄手法让维利里奥看到一种有关“现实何以消失”的美学理论,维利里奥认为:“科学所想要阐释清楚的关于‘失去时间的不可见’变成了梅里爱生产出显现(appearance)的基础,他用他的发明想要展现的现实是对已经消失的现实的不在场的持续反应。”也就是说,在这种拍摄中,有了现实的间断的不在场,才有了影像中呈现的在场,有了现实世界的消失,才有了影像中的显现。这其实给了我们一种暗示,即“电影”(cinéma)的本质就在于“运动”(cinématique),无论是拍摄对象的运动还是摄影机的运动。而在放映时,运动的效果(显现)之所以产生,又是因为一帧一帧的图像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时间缝隙(消失)。由于人类视觉无法把握日常生活中复杂运动的全部信息,所以我们在日常观看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时间的缝隙,也就是说,人类由于视觉无法处理海量的信息,只能筛选信息,忽略一部分,保留一部分。电影正是模拟了人类视觉的这一特性,由被拍摄的部分和未被拍摄的部分组成,而这就是“消失的美学”的主旨。
基于消失的感知之所以可能,其本质是因为人类的视觉感知与摄影机同构。这种人类视觉感知特性,在维利里奥的理论体系中被描述为“失神症”,法语为“picnolepsie”。就像维利里奥使用的大多数术语一样,这个词也是他根据古希腊词根创造出来的。在构词上,“picnolepsie”一部分来自古希腊词“picnos”,本意为“经常发生的”,另一部分来自“épilepsie”(癫痫),古希腊语中指“突如其来”的状态,也就是一种未能预见到的失神状态。所以从字面来看,这个词指的是经常发生的失神状态,换句话说,就是那些时间流动的意识被打断的状态。比如,在吃早餐时失神导致杯子掉落,这样的走神持续时间非常短,可能就几秒钟,与癫痫症的发作非常类似,过一阵子回过神来又能够继续手上的事情。再比如假寐的状态,明明有意识但又不是清醒的,眼球会快速地运动,半梦半醒之中那短暂的时间仿佛被偷窃了一般。对此,维利里奥指出:“失神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真的发生什么,那被错过的时间并未存在过。”
“消失的美学”即是将电影的本体论建立在失神论基础上:电影的本体就是消失。这让电影获得与其他艺术不同的特质和地位,成为全新的、后现代感知方式的代表。电影的特征是人和机器的联结:“电影是一个终点,在这里主流的哲学和艺术产生了困惑也迷失了自我,它也是人类心灵与马达心灵(motor-soul)的语言之间的一种原始混合。”“马达”是维利里奥对机器的惯常称呼。如果说,电影的发明让感知的身体与机器产生了一种融合,并带来一种感知的革命,那么“运输工具”(vehicles,另一种马达)的发展则带来了运动的身体与机器的另一种融合,并产生了另一种感知的革命。
二、运动的身体与机械运输器
在《消失的美学》中,维利里奥认为是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失神症,而带来失神症的运输工具在历史上有三种样态,他称之为“后勤角色”(logistical role)或“后勤配偶”(logistical spouse)。之所以这样描述,是因为在维利里奥看来,人与运输工具之间的关系可以被视为一种爱欲关系,即一种类似于男女结合的亲密关系。
首先,第一个带来失神症的运输工具是夏娃。亚当和夏娃不得不离开伊甸园,从神圣空间伊甸园坠入尘世。夏娃受到撒旦的诱惑,让人进入了另一个时空,并且开启了一种新的观看世界(尤其是自己赤裸的身体)的方式。在整个过程中,她就像一个运载器一样完成了时空的位移。此外,男人和女人结合为一体,女人即在神话意义上成为男人的技术载体,负责运送男人。维利里奥因此认为,夏娃扮演了“第一个后勤角色”。这一次“坠入”的最大意义在于,“时间”概念被引入人类的世界之中,“这次重要的离开对于人类而言是一次对身体和感觉进行探索的开始,从不可移动的永恒事物走向了那个被称作时间的范畴”。这次离开使得人类从此进入了不稳定的漂泊状态,运动和变化也由此而生,自此以后速度才具有意义。此外,之所以将这种神话般的描述选作第一个典型,是为了说明一种原型范畴。维利里奥在《速度与政治》一书中指出:“在没有技术运输工具(technological vehicles)的社会里,女性扮演着后勤配偶的角色,既是战争之母,也是卡车之母(mother of truck)。”他想要表达的是,男人与女人的爱欲角色是人与机器间关系的最初模型。
其次,人类在运输身体和货物方面先后经历了两次技术飞跃,也就出现了两种产生失神症的典型技术。按照约翰·阿米蒂奇(John Armitage)的说法,这两次技术飞跃都是“以人类移动(movement)为中心的技术超越”,一个是前现代的“嗜兽癖”(zoophilism),从字面来说就是对动物的爱;另一个是现代的“飞入未知领域”(flying into the unknown)。虽然阿米蒂奇的总结中所选择的意象之晦涩值得商榷,但他想表达的仍可被理解:第一次技术飞跃带来的结果是,人与动物之间产生了紧密关联,女性作为运输工具的时代结束,动物与人形成新的爱欲关系,它们构成了新的“生物运输工具”(metabolic vehicles)。关于嗜兽癖,维利里奥是这样描述的:“在技术对象更新之前,交通工具在耦合上的吸引力产生了嗜兽癖,就像是另一种形式的异性恋。”他以拦截俄狄浦斯的斯芬克斯为例,来说明这种人和动物的奇异结合。实际上,维利里奥想要表达的是,现代交通工具诞生之前,我们主要依靠动物的力量完成战争后勤的工作,所以以骑马为代表的依靠动物的交通方式被他看作动物对女性角色的取代。斯芬克斯的图像演变说明了这一点,它在后期显示出女性的样貌并且带有翅膀。也就是说,女性开启了人类移动的可能,而动物则为人类带来了第一次飞跃。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按照维利里奥早期的划分,无论是女人还是动物都是基于新陈代谢功能的生物体运输工具,与技术运输工具相区别。
第二次技术飞跃的结果是包括汽车、火车、飞机在内的机械运输器(mechanical vehicles)的发明,人类与机器进行了新的结合。“飞入未知领域”的说法来自维利里奥对飞行员让-马力·萨基(Jean-Marie Saget)的采访,它描述运输工具速度的不断提升。这也可以理解为维利里奥最主要的技术超越类型,因为他最终要考察的正是现代性之后的技术飞跃,人与机器的结合在现代世界中取代了人与动物的结合,技术力量开始控制人类社会的基本走向。这也在真正意义上脱离了以新陈代谢为基础的运输方式,而转向了以机械为核心的运输方式。
维利里奥之所以要讨论运输工具的变化,是为了给“感知的后勤”(logistics of perception)这一概念做铺垫。阿米蒂奇在解释这一概念时提到,此概念原指军方情报部门提供影像资料的行为,后来衍生为“通过战争运输与摄影机的合并形成新的电影武器系统”。更确切地说,维利里奥想要表达的是,对变化世界的感知如何借助运输工具完成快速传播。批评家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认为,维利里奥深受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的影响,但是他并不喜欢使用“现象学”这个词,而是使用“后勤学”(logistics)这个军事学术语来代替。克拉里的阐述显然过于简单,这一术语的更替有着深层次的考量,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维利里奥从来都偏爱对军事的讨论,他经常将自己称作“战争的孩子”。在他看来,军事技术的进步导致移动速度的增加,这具体表现在战场上各类可移动车辆或其他运输装置的发明。第二,这显然也暗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看方式。按照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方法,身体在我们的观看中占据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具有两个维度的特性,“我将我的身体看作是世界之中的一个客体,但它同时又是我观看世界的视角”。如果说在笛卡尔的世界中,“我思”是第一位的,人的眼睛仿佛一个镜头般冷静地观看着世界和自己,那么梅洛-庞蒂则更倾向于认为意识并不是基于“我思”,而是基于“我能”。也就是说,身体不仅是被感知的对象,也是能感知的主体的一部分。但是,这种依靠身体感知到的现实世界是在低速情境中呈现的样子。而维利里奥提出的“感知的后勤”则指向一种高速运动状态下世界在镜头前所呈现的样子,也就是说,必须摆脱肉身对感知的限制,让感知与运动的工具进行联结。
这种联结的代表就是航空连续摄影技术,它标志着一种新的观看方式。19世纪末,电影几乎与航空器同时诞生,两者发生了自然而然的结合,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航空摄影。一些电影从业者也曾是航空侦察小分队的一员,比如法国著名导演让·雷诺阿。这种航空连续摄影技术可以呈现一座村庄或农场从有到无的全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为决策提供各种情报。所以在后来的发展中,飞机上不但装载了摄影设备,还装载了电子通信系统。从此,飞机便与决策部门联系在一起,前者以“瞬息速度”(instantanément)向后者提供情报,坐镇指挥中心的军事首领们像观看电影一样分析前线的情报,电影与战争之间产生了深层次的关联:“军事交火唯有通过投射才能被感知,只有战争电影一格格的摄影画面才能够彰显出战事的内在动力机制,彰显出主导线索,给地面侦察只留下一个为战术控制服务的角色。”换句话说,瞬息万变的现代战场,由于高速移动设备的运用,每个人都失去了通观全局的能力,所以航空连续摄影带来的感知方式的转变正好适应了新的战场形势,感知重新跟上了人员和车辆移动的速度。在这个意义上,航空连续摄影已成为超越一般武器的新型武器。维利里奥认为,战场已经不再是各种物体之间的战争,而是“图像和声音的战争”,胜利的关键在于“不要丢失敌人的影像”,谁占据了全知全能的上帝之眼,谁就赢得了胜利。
航空连续摄影所带来的新的观看方式至少融合了三种技术:望远镜、摄影工具和高速移动的运输工具。前两种完成的是“感知”的任务,第三种完成的是“后勤”工作,也就是运输感知到的信息。这种军事化的观看场景是后来被实时通讯占领的日常生活的原型。而这些感知或运输的技术被维利里奥称为“技术假肢”(technical prosthesis)或“视觉假肢”(visual prosthesis)。早在《速度与政治》中维利里奥就开始使用“假肢”一词,这与他所感兴趣的战争话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17世纪开始,正是战争促使“整形外科”的诞生,后者为在战争中受伤的士兵安装机械装置来弥补受损伤的身体。维利里奥拓展了这个概念,将健康人所使用的各类扩展感知的装置以及加速运动的工具都称为“技术假肢”。因此,技术假肢最早可以追溯到诸如望远镜、显微镜等用来观察的装置,而望远镜也恰恰是所有这些用于观看的技术假肢的原型。维利里奥认为,望远镜为我们“投射了我们触不可及的世界,同时也投射出另一种在世界中移动的方式。这就是感知的后勤,这种方式开启了一种未知的影像运输,并且产生出远近叠加的效果,也就是一种消除我们的距离和维度体验的加速现象”。
技术假肢的发展和运用从两个方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问题。第一个方面是,技术假肢让人失去了梅洛-庞蒂所描述的具有积极意义的身体,人的感知从依靠技术假肢的辅助,变成完全被技术假肢左右。正如技术假肢这个隐喻所暗示的那样:身体与机械完成了融合,并由后者主宰了感知,从而形成了“自动感知”。第二个方面是,我们需要借助技术假肢抵抗失神症。现在最常见的技术假肢无疑是移动电子设备,这些技术假肢逐渐取代了各种器官的功能,并且带来了新感知方式的出现,这就是阿米蒂奇所说的:“通过各种技术假肢投射的光形成的失神症成为产生后现代感知或美学表征的关键。”阿米蒂奇之所以认为失神症是当代美学感知的关键,是因为在我们运用某些技术假肢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失神症状态。这就像柏拉图《斐德若》中对文字的描述一样,根据德里达的解释,文字是“pharmakon”,既是帮助人记忆的良药,也是让人失去记忆的毒药。同样,技术假肢帮助我们感知和记忆高速变化的世界,也像毒药一样让我们更加频繁地产生失神症,让世界在感知中消失。
三、懒惰的身体与视听运输器
通过电影和运输机器的发明,人的身体完成了两次与机器的融合,机器成为人的技术假肢。第三次融合最初本是战场上的景象,即指挥官凭借飞机航空连续摄影以及电子通信设备发回的资料坐镇指挥,但这景象最终成为每一个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场景。维利里奥说,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们完成了“移动运输器”(automobile vehicle)的发明和应用,那么20世纪末,我们则完成了“视听运输器”(audiovisual vehicle)的发明和应用。在这最后一次的大变革中,动态变为静态。他的意思是,我们的感知被技术假肢控制,远程在场取代了在场本身。这标志着一种偏爱静态的懒惰身体的形成,自此,获取信息不需要移动身体,机器的运动代替了人的运动。
新兴信息技术的运用,消除了知觉上距离远近的差异。在维利里奥看来,距离的缩减直接联系着“对空间的否定”(negation of space),从而在政治和经济上造成了巨大影响。除此之外,在视觉艺术领域,它导致传统图像再现方式的式微。这种古老的再现方式广泛地存在于古典视觉艺术作品中,如果说原有的观看依靠的是我们的血肉之躯和纯真之眼,那么在新的时代里,观看就离不开视觉机器的帮助,“这些综合感知机器(synthetic-perception machines)会在一些领域替换我们,也会在一些我们的视觉能力难以胜任的超高速操作中取代我们”。这是一种新的技术革命,要捕捉高速运动的物体,就必须将世界虚拟化为抽象符号,从而形成新的感知图示。维利里奥认为:“人们会忘掉物体与躯体,而关注物体与躯体的各种生理痕迹,出现了整套的新型手段,如各种作用于现实的传感器,不是对影像,而是对于振动、噪声、气味更为敏感;增强亮度的电视,红外线闪光灯,则意味着根据温度与生命机能来辨别躯体的热感成像。”一言以蔽之,人和世界的影像被替换为抽象的符号,对外形的再现也被对其他特性的再现所代替,这一切都是为了捕捉高速移动的物体的运行轨迹,从而看到人的肉眼看不到的世界。
如果说雷达、热成像仪等还是这种视觉机器的军事形态,那么维利里奥的语境中,民用形态视觉机器的标志就是电脑制图技术和互联网的结合。这种新现象的特征之一是极大的加速,它甚至胜过飞机加速带来的冲击,给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带来了超越摄影和电影的新变化。新的视觉机器开始涌现,比如如今随处存在的视频监控装置、各类不停滚动的大屏幕,更不用说21世纪以来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各种移动终端,它们几乎主宰了所有人的生活。
这些视觉机器以“远程拓扑(teletopology)的日常化”为方式摧毁再现。在一幢受远程监控的楼房内,“远程拓扑”是这样表现的:“在那里,从每个套房都可以观察所有其他的套房,更准确地说,每个不同的套房的房间都像一个视频控制室那样在运转,对全部其他房间进行监控。”简言之,维利里奥想要表达的是一种复杂的网状拓扑结构,也就是一种相互观察、相互监督、相互交流的远程实时在场结构。相比福柯的“全景敞视监狱”,它在关系上更为复杂。原本闭塞的日常生活领域开始被远程再现技术所拓展,通过身体感受到的周遭环境被同时出现的其他时间和空间中的影像取代。维利里奥对这一现象的评价是负面的:“人们会明白,这种远程客观性在何种程度上让我们丧失了对现实的把握。”正如梅洛-庞蒂所说,那个我们所熟知的“我能”的世界,也就是我能够得着、能看得见的世界已经不在我的掌控范围。更确切地说,因为知觉后勤的加速,或者说影像传输速度按照光速在运行,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伴随着视觉机器的发展而迅速变化。处于不同地点的人,可以在同一时间通过电话或互联网等方式进行无障碍的交流,仿佛所有人都在赛博世界里共处于同一个扁平的空间中,距离不再成为一个问题。真实世界的地形原本会阻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然而大江大河、山川丘壑在行动和信息传递上造成的障碍在赛博空间中被均质化。新的地形出现,数字化的平等空间诞生,一种赛博空间的地形学随之横空出世,这也就是“远程拓扑日常化”所想表达的内容。赛博空间重新塑造了人类观看世界的方式,克拉里对此有着精辟的总结:“人类眼睛在历史上的一些重要机能,绝大多数正被一些新的实践所取代,在这些实践中的视觉影像,不再需要一个观察者置身于‘真实’可感知的世界以供参照。”

远程拓扑视觉机器的出现让观察者进入自动观看状态,各种图像充斥着我们的生活,远程实时图像在电视上、商场的大屏幕上以及各种移动终端上滚动播出。我们不再需要主动去寻找图像,而是图像走向我们,不是我们观看图像,而是图像包围我们。维利里奥并不欢迎这样的时代,他十分审慎地指出其中的问题,将这种远程拓扑称为“实时的暴政”(tyranny of real time)。一般认为,互联网时代的实时在线给予了普通人便利和平等,但是,维利里奥认为,这种暴政是民主的对立面,因为反思将在其中受到限制,而我们会走向“自动主义”(automatism)。维利里奥发现,在摄影和能够实时在线的新媒体技术间存在着断裂,远程在场的现实取代了传统通过绘画、摄影等被再现的现实,这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视觉经验方式的变革。用来自美国且同样具有建筑学背景的媒介理论家威廉·米歇尔(William J.Mitchell)的话来说,“绝对的同步通信”作为特例正在取代更常见的异步通信,而这种同步在场的视觉感知最早源自13世纪城市公共场所中安放的时钟。但是,时钟带来的同步在场感知还是地域化的共同在场感,实时在线的新媒体带来的却是整个世界的共同在场感。这让维利里奥深恶痛绝,他对此最初的震惊来自看到巴黎地铁站台上的镜子被替换为电视屏幕,随后又在生活中发现越来越多的监控摄像头和视频设备,并因此认为实时在线一步一步地蚕食了我们的日常。
与维利里奥不同,米歇尔并不认为这样的实时有什么问题,他举出了一个艺术案例,这就是基特·加洛韦(Kit Galloway)和雪莉·拉比诺维茨(Sherrie Rabinowitz)在1980年10月的艺术项目“空间中的洞”(Hole in Space)(图2)。两位艺术家在那个时代就相当前卫地在美国东西海岸的两个城市间建立了双向视频连接,一个装置被安放在洛杉矶世纪城的商业中心外,另一个装置则被安放在纽约市的林肯表演艺术中心。视频中的人物与真实人物等大,过往的行人可以与美国另一个海岸的人们发生奇妙的相遇,感知被编码为信息并且按照光速传播,两个平行空间被电子媒介带到了一处。米歇尔并未批判这一装置,而是认为这就是未来。现实确是如此,这一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十分前卫的艺术项目,如今不过是21世纪日常生活的一小部分。

图2 基特·加洛韦和雪莉·拉比诺维茨 空间中的洞 1980
然而,维利里奥之所以对此感到厌恶,是因为我们的感知和观点都被实时更新的大众媒体所垄断,进入一个完全同时的世界。这些感知和观点并不具有个体性和特异性,而只是工业化量产的结果。由于我们被技术假肢劫持而失去反思的能力,所以一切对世界的反应都变得自动化。自动化观看是视觉机器的后果,也是人的身体被技术假肢控制的后果。人的身体与世界原本是主动感知的关系,如今却变成被动感知,我们仿佛时时刻刻都在观看远方的世界,与远方的人交流,又时时刻刻被打断,构成失神症更复杂的版本。维利里奥把视听运输器称为“最后的运输器”(the last vehicle),这是因为如今我们的感知信息从发送到接收都是以光速在进行,依照相对论,这已经是宇宙速度的极限,也就不可能存在更大的变革。在这一速度的参照下,我们肉体的移动速度显得微不足道,这也是导致技术假肢所传递的信息取代身体感知的原因之一。
四、一种后人类主义视觉理论
维利里奥的理论带有浓厚的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色彩,尽管没有证据证明他本人受过这一思潮的影响。但可以确定的是,有些后人类主义者将维利里奥的理论作为论证的一部分,这可以被理解为两者之间亲缘性的佐证。“后人类主义”是个含义混杂的词语,在诸多使用者那里,其用法并未达成一致,也不存在一种统一界定。但是,我们可以借助意大利哲学家罗西·布拉依多蒂(Rosi Braidotti)的划分呈现维利里奥与后人类思想之间的相似性。
在布拉依多蒂看来,后人类思想可划分为三个类型。第一个类型是对后人类思想的否定或者说消极形式,其代表人物是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这类思想来自道德哲学,其观点的核心在于,虽然承认科学技术带来社会经济的进步与挑战,但否认欧洲人文主义危机的观点,认为需要回归传统的人文主义和普遍主义价值来回应当代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类型并不是后人类思想,而是后人类思想的对立面。第二个类型则是分析型后人类思想,代表人物是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和凯瑟琳·海勒(N.Katherine Hayles)等。这一类型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掀起后人类思潮的先驱者,他们以对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为其整个思想的基础,普遍认为科学和技术改变了人类、生物和整个自然的生存方式,将科学和技术化的人类作为人类的参照。第三个类型则是以布拉依多蒂自己为代表的批判性后人文主义,其目的是要重建一种新的、非同一性的主体来取代以“维特鲁威人”为代表的陈旧主体,同时也是对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人文主义的批判。
根据布拉依多蒂的划分,维利里奥的理论更类似以哈拉维和海勒为代表的分析型后人类思想,但其中也隐含了对布拉依多蒂的批判性后人文主义思想的呼应。

其次,维利里奥提到的感知后勤,亦即视觉经验从作为发出端的机器到作为接收端的人的传输,从本质上说,就是海勒的信息论中对信息的描述。海勒认为:“后人类的主体是一种混合物,一种各种异质、异源成分的集合,一个物质-信息的独立实体,持续不断地建构并且重建自己的边界。”这种软件-硬件的二元对立被“湿件”(Wetware)替代的现状,无疑可以理解为对维利里奥技术假肢和视觉机器理论的抽象概括。但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维利里奥对这种变化的态度是消极的,他坚持认为,电脑屏幕上的内容是信息而非感觉,是一种“情感的缺失”(apatheia),人接受越多信息,越是身处世界的荒漠之中,反复出现的海量信息扰乱观察,让感知变得自动化,最重要的是,“信息不再是存储而只是展示”。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通过辨析找到维利里奥与后人类思想间的诸多一致之处,虽然维利里奥对这种人与机器高度联结的后人类状况的态度始终是否定性的。但是客观地看,无论维利里奥如何厌恶这些技术假肢,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后人类世界之中,而他基于批判态度总结出的视觉理论,则为我们标定了这种后人类主体观看世界方式的起源,这所有的一切都起源于电影发明时那个在拍摄过程中消失的现实世界。